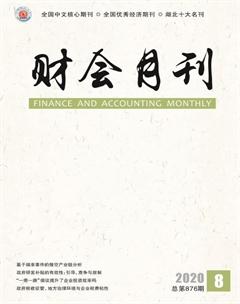政府研发补贴的有效性:引导、竞争与规制
宋建波 张海清


【摘要】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科技发展对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本应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却常常因研发的外部性问题而对此望而却步。为顺应科技发展的浪潮,国家普遍利用财政资金给予企业一定的无偿性补助以消弭市场失灵的罅隙。近年来,我国显著提高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扶持和补贴力度,但却因研发补贴低效问题而饱受争议。从思考“创新需要什么样的补贴调控”出发追本溯源,根据市场和政府的二元关系分析补贴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发现研发补贴低效的关键在于其制度缺陷和执行偏差;同时,尝试探求完善补贴政策的可行方法,提出在补贴方向上强化突出引导性、在分配方式中引入竞争机制和健全补贴资金的规制等提升补贴有效性的多维路径。
【关键词】研发补贴效率;市场机制;政府调控;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8-0009-7
一、引言
我国作为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的40年,已经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构成和带动力量。当前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早已起航,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我国与时俱进、前瞻性地调整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势在必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和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单一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的低廉成本优势,全国经济总量迅速提高的同时却也承继了难以忽视的积弊。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将有力缓解早期粗犷发展带来的资源浩劫、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实践中,创新的强大驱动内核难以释放,究其原因,创新活动一般都具有投入资金量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以及风险偏高的特征,并且研发成果的溢出效应明显,私人部门在权衡其中的利弊和风险后往往望而却步。
显而易见,在长期缺乏支撑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的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因较强的市场惯性约束而举步维艰,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之一。创新资源单一依靠市场机制配置,企业创新投入的能力受限、积极性受挫是现实市场运行中暴露出的既定事实,因此,为有效调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我国积极扶持企业研发活动。其中,发放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引导企业创新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之一。事实上,很多国家都通过财政政策对创新进行干预,以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已有不少学者发现,研发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补贴资金缓解了企业研发资源禀赋受限的困境,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明显增加了研发投入[1] 。诚然,研发补贴的应用实务中也出现了低效甚至失效的情形。一方面,补贴的分配中潜藏的资源错配因素抑制了研发补贴对于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寻租行为[2] 、政治关联[3] 、过度补助[4] 等因素造成补贴分配不均时,补贴低效问题更为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研发补贴的成效难以衡量和评价,补贴资金的运用缺乏规制和监督,易出现企业研发投入大部分依赖于政府补贴,挤出了企业原有自主创新投入份额的现象[5] 。甚至,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使研发补贴沦为部分公司操纵盈余、扰乱投资者视线的手段。
研发补贴失效的情况不容小觑,但是现阶段研发补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言而喻。要恰当地理解和完善研发补贴机制,首先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二元关系。为此,本文分析了政府在创新领域伸出“有形之手”的客观必要性,纠正了将补贴低效与补贴无效混为一谈、武断推崇以取消补贴方式解决低效问题此种饮鸩止渴的观点。盲目将企业自主创新与政府扶持对立起来,既忽视了创新领域的私有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事实[6] ,又不利于扶持企业走出创新困境以纾解国家创新动能不足、经济发展疲软的压力。与此同时,本文根据补贴政策的实施状况分析研发补贴的应用滞碍,指出研发补贴的功用未能有效发挥的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与执行的偏差,并非政府补助不葆有引导经济资源错配转向的功用。基于此,笔者尝试从补贴目的和方向、补贴对象的选取、竞争规制的引入以及后续监管等维度提出完善现行补贴机制的路径,以提升研发补贴的有效性。
二、研发补贴的内涵与现状
政府补助是政府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将财政资源无偿调配给企业或个人的一种财政支出行为。从补助的目的上看,政府补助大体可以划分为政策性补助、扶持性补助和捐赠性补助。研究开发类的政府补助(简称“研发补贴”)是扶持性补助的重要构成,主要是指政府无偿将经济资源转移给企业(或科研机构)以扶持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财政行为。研发补贴一如其他类型的补助,都具有政府补助的基本特征。政府补助的首要特征就是无偿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会获得一定的资源收益,但是无须向政府给付相应的商品或服务;当企业取得研发补贴后自行运用资金进行研发,无须将新创产品、技术反哺给资金提供者,这正是政府补助有效性存在监管难度的缘由之一。另外,政府补助活动中的直接主体为政府和受补助对象两方,研发补贴活动中的主要参与者即为政府和获研发补贴的企业,但是受研发补贴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远不止上述两方[7] ,这也正是研发补贴效率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研发补贴独特的个性特征也难以忽视。其一,研发补贴作为扶持性政策,异于政策主导的政策性补助和捐赠性补助。研发补贴机制突出以企业为主体,政府重点发挥扶持作用,企业在补贴获取和使用中保有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更强。其二,研发补贴资金指向明确统一。研发补贴一般与企业研究开发支出直接挂钩,而其他类型补贴因错综复杂的政治任务、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致同一类型补助的资金走向并不统一、资金覆盖面较为广泛。其三,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较难衡量和评价。一方面,从企业微观层面上看,不同类型企业研发的产品具有云泥之别,同企业不同产品线的研发产出也不同[8] ,企业研发活动的产出效率无从给予合理的评价;另一方面,研发补贴的效果往往短期內难以显现,及时评估和监控具有较高难度。研发创新是尝试打破原有生产边界或模式的高风险活动,研发投入成功转换为产出的过程道阻且长,短期内企业研发产出的多寡并不能充分反映补贴效果的优劣,也无法衡量补贴政策对于国家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
表1列示了各国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创新是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内核推动力,我国一直重视、支持和鼓励各领域的研究创新活动。根据我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我国研发支出的金额逐年上升,近十年来增长了近十倍,且在国有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2014年起研发总额逾13001.6亿人民币,超GDP的2%,早就超过全球研发支出的平均水平。环顾比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谙创新的力量,研发经费支出均持高不下,并且各国政府资金在研发经费总额中重足而立[9] 。Piekkola[10] 指出,美、法两国政府资金在研发支出总额中的占比过半,德日等国也均超20%。2016年,我国知识产权数量在全球的排名上升了17位,其中政府的扶持和推动尤为重要,我国研发经费中超两成资金源自财政。
从表2中我国研发经费的资金来源情况看,企业内部资金占主体,政府资金紧随其后,企业在研发中的主体地位和政府的扶持力量均不容小觑。我国现阶段大额的研发补贴支出,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创新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迫切驱使我们审视补贴的有效性、探索补贴政策的完善路径。
三、现行研发补贴政策的迷思
目前,我国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主要是在企业原有的研发支出税收减免优惠基础上,根据企业研发支出金额给予企业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审视研发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研发补贴低效的困扰主要表现在关于研发补贴的分配和后续使用中公平性与普惠性的争议[11,12] ,以下从研发补贴对象、补贴金额、补贴方式和补贴监管四个方面来阐述和分析。
困惑之一:研发补贴发给了谁?现行研发补贴发放对象显见专断性和随意性。补贴发放对象是补贴资金的运用主体,恰当的资金使用者是补贴资金合理利用的前提,是研发补贴切实为企业创新和国家发展助力的先决条件,即补贴对象选择的恰当性与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但是,研发补贴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补充手段,受补贴企业的筛选机制并非市场机制,而是由拨款机构决定获补企业并向其无偿提供资金。拨款机构及其执行者对于补贴发放对象并没有统一、固定的选择判定依据,贯彻落实政策时难免潜藏主观性,尤其是在补贴的决策机制不规范、不透明的情况下,专断随意地发放补贴的现象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当前补贴政策对于发放对象的行业保有人为设定,补贴政策倾向高新技术企业的恰当性有待商榷。随着补贴资金向高新技术产业聚集,虽有力促进了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但是传统行业企业同样开展研究开发活动,却因政策的人为设定并未得到支持。部分高新技术企业长期占用国家的大量研发资金,非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虽然也在从事着技术和产品的创新,甚至通过创新的方式进行着传统行业转型道路的探索,但是却因为专断条款的制约难以获得有效的政策扶持,很可能产生新的资源错配和分配不公。
困惑之二:该拨付多少研发补贴?当前研发补贴额度缺乏可解释力和激励性。补贴金额以上一年或当年的企业研发支出为基数计算,旨在通过补偿企业研发成本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实际上却产生了两种有悖初衷的执行效果。①各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差距悬殊,大型企业研发体量明显高于中小企业,研发补贴顺势大量流向大型企业,因而规模越大的企业往往越容易获得更高的补贴额度。如此锦上添花式的补贴偏离了公平和普惠原则,既未缓解中小企业研发的融资困境,又很可能加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固有的研发沟壑。②补贴发放金额单纯倚重研发支出情况,表面上直接拉动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但也容易导致企业轻视研发投入产出比,盲目调增研发份额而摒弃降低研发成本的路径,难免形成研发补贴资源的浪费。换句话说,如今的补贴分配着重于研发投入而非研发效果和效率,缺乏对于低成本高效率项目的激励导向。
困惑之三:发放方式是否合理?现行研发补贴的发放方式隐含悖论。现行补贴主要采用两种发放方式: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事前补贴是指,参照企业以往研发情况,政府事先拨付资金用于支持企业下一年度的研发项目;事后补贴是指,政府以当年研發支出金额为基数,在年末按照适当比率无偿拨付给该企业。这两种发放方式在实行中的弊端都在一步步地浮出水面,公众对于研发补贴的质疑之声甚嚣尘上。显而易见,事前补贴虽然便于企业掌握充裕的资金开展研发活动,但是由于获补企业提前取得了补贴资金,后续阶段政府无法有效管控企业研发资金的使用情况,常常出现企业并未将补贴资金运用到既定项目的情况。相较之下,采用事后补贴的方式,企业研发活动先行、补贴资金后继拨配,政府对补贴资金应用的掌控力更强。然而,研发补贴本为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扶持手段,补贴资金原为“高风险、高投入”研发活动的资金补给来源,事后补贴资金则更侧重于呈现奖励效应,却疏漏了缓解研发前期融资约束的效力,容易导致企业因缺乏资金支撑而错失研发契机。
困惑之四:研发补贴有何监管?补贴资金前期拨付制度不健全,后续使用中产出不明,补贴政策沦为寻租行为和财务舞弊的温床。追本溯源,政府将部分财政收入无偿拨付给企业用于研发,补贴资金的提供者为社会公众,政府并不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而是公权的执行者。政府旨在通过补贴手段调控市场失灵对于研发活动的干扰,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就是提升社会福利和效率的充分保证。尤其是研发补贴的拨款机制缺乏健全的制度规制,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巨大人为空间,寻租等低效的非正式制度无孔不入,缺乏制约和监管的补贴频频失效,由此加重了市场的资源浪费问题。除此之外,补贴资金运用过程中所有者缺位导致公众资金投入研发但产出收益却未能由资金提供者享有。换句话来说,公众所有的资金经政府拨款转移给企业,企业用其开展研发活动,但产出的直接收益归企业私有,公众更多享有的是研发产出的溢出收益。但是这部分溢出收益较难衡量,更为重要的是,无法监督和规制此类产出不明的资金的使用情况,因而补贴资金难以物尽其用,甚至成为部分企业营私舞弊、操纵盈余的手段。
四、研发补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研发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公众和理论界对于研发补贴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质疑之声不断。部分学者承认市场失灵在一段时间和研发创新领域的存在,但却认为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表现未必优于市场机制,由此将政府干预视为市场低效、资源错配中的新桎梏。因研发补贴政策应用状况不佳而“一刀切”地否定研发补贴存在的合理性,却并不深究补贴失效的真正缘由,这无异于因噎废食。其实,结合我国现行制度和国情可以判断,上述研发补贴的问题根源在于研发补贴的功用未能有效发挥,主要是制度的缺陷与执行的偏差,并非政府补助不保有引导经济资源错配转向的功用。风声鹤唳地否定政府补助存在的合理性,既不利于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也无法正确处理政府补助实际运行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有效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市场配置资源更为高效,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当前市场发育程度有限,不完备的外部环境下单一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使用很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特别是在研发领域中,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市场失灵问题尤为严重。一方面,当企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摸索形成新产品和新技术后,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技术外溢效应,企业承担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出现了外部性问题[13] ,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难免囿于原有熟悉的经营领域、开展激烈的红海竞争,如此势必会压缩创新产品和技术的生产空间。另一方面,若经济运行仅仅依靠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各参与主体将根据供求关系自发调节以牟取更高的收益。当前现实情况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并不能充分掌握交易信息以准确把控和预期供求情况[14] ,因而时常因供求短期波动而盲目采取投机行为,或因市场机制中的滞后周期而做出短视决策,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耗费。研发活动不能在短期内获取可观的收益,如果缺乏引导价格和供求机制决定下的市场,往往容易诱发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抵触情绪,短视地缩减部分可行的研发投入。
研发创新领域的市场失效正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有为之地。政府扶植和引导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以提升整体创新实力,对于重整市场失灵引致的创新资源错配来说十分必要。首先,研发补贴通过无偿向研发企业先行拨付资金的方式,直接补偿企业新产品共享、公共产品生产和技术外溢等外部性成本,可极大程度地消除企业由自我防御产生的研发顾虑,减弱市场机制下外部性问题对于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与此同时,取得研发补贴后将带给企业经济利益流入,在利益驱动下研发补贴将有力地引导企业重视研发创新,而不是盲目追求短期收益。其次,研发补贴具有较强的指向性,企业为了取得补贴资金会按照获补条件积极规划和调整研发行为。因此,良好的补贴政策可以指引企业按照国家产业规划方向开展研发活动,减少原有的各自为营、独立研发的资源浪费,脱离根据供求关系变化进行事后补救的迟滞困境。
此外,政府通过研发补贴将资金注入企业,而非直接参与或行政干预企业的研发活动,是保证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释放科技创新的自主空间的合理途径。科学技术早已成为提振国家经济的重要抓手,但是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面对巨额的资金投入、较长的回报周期和未知的盈利模式,创新主体在孤立无援情况下的自主研发举步维艰。尤其对于企业来说,研发活动需要资金保障,而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投资者和债权人往往因研发活动的风险性而心生芥蒂,无充裕资金的企业对于研发创新只能望而却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强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性,企业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是强化国家软实力的必行之路。政府在此伸出“扶持之手”,利用自身的政治职能和财政储备,通过研发补贴的方式为研发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对于自身禀赋不足的企业来说无疑是绝渡逢舟。
五、完善研发补贴路径的探索:引导、竞争与规制
通过补贴政策应用现状,能够找到修正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路径。挖掘研发补贴低效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研发补贴政策失效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制度漏洞)和非政策因素的滋扰(执行偏差)。前者是政策本身制定的不健全、不清晰所致,现行补贴政策的发放对象、金额和方式缺乏清晰的导向和合理的逻辑,加之监督政策趋近空白;后者则主要产生于政策执行流程中的人为空间,政策执行者并非完全公正中立、外生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公共权力的无主化和执行者的自利性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受到执行主体行为的影响,这也根植于政策制度漏洞的附带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研发补贴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有针对性地健全补贴机制来化解政策失效的困境。首先需要明确补贴的目的和方向,突出政策的引导性地位,并根据补贴方向制订合理的研发补贴分配方案。同时,政府的调控活动也不应排斥竞争机制[15] ,引入良性竞争可以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提升补贴的效率。此外,健全研发补贴整个流程的监督制度势在必行。
1. 研发补贴目的和方向应突出引导性。研发补贴应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发挥引导效应,缓解市场外部性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制约,此为补贴政策的初衷。无疑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更为高效,但因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外部性,也会存在失灵脱轨的现象,特别是处于研发领域的企业,其创新动力缺乏、采取短视行为等问题更为突出。虽然从整个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市场具有自愈能力,然而在这个逐步回归正轨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承继着巨大市场失灵的代价,并且修复时间极其漫长,因此需要政府以发放研发补贴为手段调控研发领域市场资源配置的罅隙。契合良治的补贴政策须首要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继而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创新,推动市场及时消纳资源错配的隐疾。在此过程中,坚持企业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是保持市场在政府宏觀调控下有序配置资源的重要环节。“有形之手”借用补贴资金的利益驱动发挥对企业和市场的导向作用,而不是事必躬亲地直接参与研发,否则又会陷入“政府办企业”的低效陷阱,偏离补贴政策的目标。在研发补贴运行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共同参照补贴政策协商合作机制,政府将补贴资金转移支付给企业,通过补贴机制调配企业研发活动满足社会对于创新的共同需要,从而实现公共价值;企业则得到研发补贴资金,转变为研发溢出的公共物品生产者和供给者,并在此研发过程中收获符合自身预期的盈利。表面上看,政府无偿将公众资金拨付给企业,企业因补贴的存在而敢于将资金投入具有正外部性的自主创新活动中;从实质上来看,政府作为公权的受托执行者,通过补贴资金的再次分配来兼顾研发产出的社会属性与市场参与者的产权利益,从而系统协调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与企业私有利益。
2. 补贴对象务必合乎补贴政策的目的和方向,补贴结构和比例亟待向公平性、普惠性和功能性优化。补贴资金的分配对象与补贴政策效果、效率息息相关,补贴结构和比例直接反映了补贴的目的和方向。只有具有明确合理的补贴对象、结构和比例,研发补贴政策才能有的放矢。现行研发补贴政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过多地偏重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内的部分企业,难免会导致财政支出在公平、普惠、功能性方面不能盡如人意。有效的研发补贴应协调分配补贴资源:①公平对待各行业的研发活动。人为选择性的补贴反而容易形成一种新表征的行业壁垒,研发补贴应强化其功能性和普惠性而非人为选择单一行业。这样做不但可以鼓励各行业重视研发活动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辐射带动资源密集型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活动平稳过渡到新兴领域,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淘汰过剩产能。②在各行业内不能过度偏好于补贴国有企业或是政治关联企业[3,16] 。国有企业因自身政治关联、战略地位等先天优势,更易于取得补贴资金,但是行业中资源过度集中于国有企业,既不利于行业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也容易让本就缺乏竞争的国有企业更加产生惰性,导致行业整体效率低下[17,18] 。因而在保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支柱地位的前提下,应渐进式改进、降低对国有企业补贴的比例和力度,维护企业间的良性竞争,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③可持续收效的补贴结构和比例并非一成不变。研发补贴的分配方案应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避免僵化滞后的补贴方案偏离补贴的目的和方向。
3. 引入竞争规则强化补贴的效率性。研发补贴是一种政府调和公共产品和市场外部性的重要“庇古手段”,诚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但根据补贴的宏观调控目标,自然亦非拒竞争机制于门外。缺乏竞争的研发补贴大体绩效不佳。譬如,参考海洋渔业过度捕捞问题的治理经验,早期政府无论采用征税、强制管制还是惩戒干预均收效甚微后,许多地区开始尝试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政府出台、监管渔业各个捕捞参与者的配额,每个参与者捕捞总额受限,此时捕捞者会自发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合理安排各期捕捞量以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用“准市场化”配额制的策略极大地减少了过度捕捞的现象,进而保护了共有的海洋资源。由此可以看出,将研发补贴放置于竞争环境中未尝不是提升补贴效率和研发产出的可行之路。竞争机制的引入主要针对研发补贴对象筛选领域,现行的补贴政策主要是企业按照规定申请符合补贴政策基本条款,资金发放单位审核后决定是否给予补贴,是一种没有总额、个体数约束的核准筛选,企业之间即使从事重复的相同研发活动也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逻辑,企业只要满足了政策规定的补贴条款就可以取得补贴收益,那么企业还会关注补贴资金运用的成果吗?换句话说,补贴政策确实起到了引导作用,但更可能使企业墨守补贴的有形规定而非提高研发成效[19] ,产生企业因补贴而压缩自主研发、挤出原有自身研发投入份额的效应。倘若根据补贴的初衷在研发补贴政策中采用竞争机制[20] ,构建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综合评价体系,筛选一批研发前景良好、具有较强研发比较优势的企业作为扶持对象,补贴资金将更多地流向真正能有效利用研发补贴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借此也可以正确引导企业重视研发能力和产出效率,取代趋之若鹜的寻租行为。
4. 健全研发补贴获取、使用和产出的规制机制。我国研发补贴领域的监督制度一直较为薄弱,既没有严格关于研发补贴拨款的监督,又缺乏对于补贴资金使用效果的约束。这主要是研发活动本身具有投入和产出的双重不确定性导致研发补贴的监管难度较大,丧失有力监督的补贴实务中会暴露种种弊端。面对投入与产出关系不明的研发活动,我国可以尝试重新构建研发补贴的规制方式,明晰各项研发补贴要达成的目标,以研发项目为补贴资金的微观载体,政府通过企业申报的研发项目来决策、评价和监督研发补贴的发放、使用和效果。具体来说,企业在申请获取补助时应确定补贴产出对象,政府以各项目的预期产出作为发放研发补贴的一项重要标准,既有助于政府合理分配补贴资金,又可以压缩本因拨款没有明确评价标准而泛滥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防范研发补贴发放中的徇私舞弊问题;在企业使用研发补贴资金过程中应专款专用,保证补贴资金确实应用于既定项目,政府和公众可及时监督补贴资金的流向;研发产出通过项目方式也更易于核算和衡量,结合各项目的投入情况,根据项目原始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价和监管补贴政策效果。诚然,以项目为载体的规制机制有助于引导企业将研发资金用于实质创新而非低效扩张,并且监管补贴绩效的成本和难度将大大降低,但更多监管制度还有待完善和探索,以进一步规范研发补贴资金的运用。
六、结论
企业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为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政府开展宏观调控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研发活动客观上投入成本大、开发周期长且产出不确定,并且,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将迅速被模仿、学习和再革新,进而带动相关领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这正是研发产出社会属性的主要源泉,但也由此挤压了私人研发的收益空间[21] 。因而在单一市场机制配置下,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相容性不佳,企业创新主观动力疲软。此时,政府调控的出现恰如其分,政府作为沟通社会共同利益和企业私有利益的重要桥梁,鉴于企业面对研发活动的畏难情绪和短视行为,通过一定的补助政策,利用公共资源鼓励企业勇于、敢于创新,以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外部性,缓解企业个体难以解决的创新资金瓶颈。值得肯定的是,研发补贴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企业因创新的风险成本和溢出效应伴随的利益损失,缓解了企业出于短视、自利角度而抗拒研发的问题。当然,运行中的补贴政策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研发资金发放显失公允、信息不透明、资金利用低效等,要解决上述问题亟须适当优化补贴的机制,逐步消弭其中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偏差。
探求我国研发补贴效率的提升之路远比无谓争论研发领域中政府应该出手干预还是放任单一市场配置更为有意义,两者之间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市场良好运行需要政府干预的保护力量,而有为的政府须以市场为基础实施宏观调控。这促使我们在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下,寻求合理的研发补贴制度建设和执行规范,以提升补助的效率。本文认为,政府应更重视补贴的引导效应,在保持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用制度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研发方向。同时,基于研发补贴的目的和方向制定恰当的补贴分配制度尤为重要。因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互补性[22] ,补贴资源分配机制可以利用竞争机制因势利导企业高效使用研发补贴、重视补贴资金产出。除此之外,提升补贴机制的透明度是降低执行偏差的必要保证。长期以来,我国针对研发补贴的监督较为薄弱,较为宽松的补贴政策执行中的寻租、腐败和浪费现象屡见不鲜。倘若公众能更多地知悉政府和企业运用研发补贴资金的情况,并通过健全补贴的规制方法,使各外部相关者能够监督补贴流程的执行,将有力驱散执行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阴云。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Bronzini R., Piselli P.. The impact of R&D subsidies on firm innovation[ J].Research Policy,2016(2):442 ~ 457.
[ 2 ] Du J., Mickiewicz T.. Subsidies, rent seeking and performance:Being young, small or private in China[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6(1):22 ~ 38.
[ 3 ]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 J].经济研究,2010(3):65 ~ 77.
[ 4 ] Marino M., Lhuillery S., Parrotta P., et al.. Additionality or crowding-out?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public R&D subsidy on private R&D
expenditure[ J].Research Policy,2016(9):1715 ~ 1730.
[ 5 ] 周亚虹,蒲余路,陈诗一,方芳.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 J].经济研究,2015(6):147 ~ 161.
[ 6 ]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 J].经济研究,2017(5):6 ~ 10.
[ 7 ] Duchin R., Sosyura 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1):24 ~ 48.
[ 8 ] Edgerton J..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symmetries[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0(11-12):936 ~ 952.
[ 9 ] Hsu P. H., Tian X., Xu 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Cross-country evide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4(1):
116 ~ 135.
[10] Piekkola H.. Public funding of R&D and growth:Firm-level evidence from Finland[ 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07(3):195 ~ 210.
[1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 364.
[12] 余东华,吕逸楠.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 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53 ~ 68.
[13] Colombo M. G., Croce A., Guerini M.. The effect of public subsidies on firms'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Transient or persistent?[ J].
Research Policy,2013(9):1605 ~ 1623.
[14] Guan J. C., Yam R. C. M.. Effect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incentives on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Evidences from Beijing
in the 1990s[ J].Research Policy,2015(1):273 ~ 282.
[15] 科斯著.劉守英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1 ~ 440.
[16] 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 J].管理世界,2015(1):75 ~ 86.
[17] 邵敏,包群.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J].中国工业经济,2012(7):70 ~ 82.
[18] 陆国庆,王舟,张春宇.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的绩效研究[ J].经济研究,2014(7):44 ~ 55.
[19] 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J].经济研究,2012(3):53 ~ 64.
[20] 孔东民,刘莎莎,王亚男.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 J].经济研究,2013(2):55 ~ 67.
[21] 温军,冯根福.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增值”与“攫取”的权衡视角[ J].经济研究,2018(2):185 ~ 199.
[22] 张杰,陈志远,杨连星,新夫.中国创新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理论与证据[ J].经济研究,2015(10):4 ~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