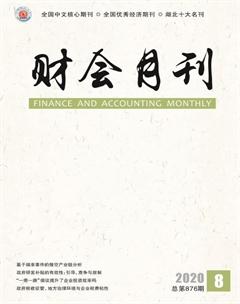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及其效果检验



【摘要】以2010 ~ 2017年滬深两市污染性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机理论和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污染防治动机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的影响机理,通过实证诠释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的影响、同异质性和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该作用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强的区域更为明显,但是在不同代理效率的企业之间却无显著差异,即无论何种代理效率的企业都倾向于合法性遵从环境规制。进一步考察作用路径后发现,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激发并形成了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由此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污染防治效果。
【关键词】污染防治动机;代理行为;中介效应;环境规制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8-0106-9
一、引言
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中国也是如此,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是企业过去疏于污染防治所致,需要制度约束和规范企业的行为[1] 。为此,我国加强了环境规制,相继出台、修订了多项环境法律法规。2014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法规。这些法规的出台与实施,促进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高。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污染防治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2] ,时有不和谐事件出现。如2019年江苏响水“3·21”重大爆炸事故的发生[3] ,2018年3月多家单位因用雾炮车喷淋干扰环境监测受到主管部门通报[4] ,2017年143家环评机构受到行政处理,其中环评文件质量问题占到90%[5] 等。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均表明我国企业执行法律的效率比较低[6] ,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的执行力度不够,类似现象早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发现,企业在报告环境规制执行情况时,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存在委托人和代理人“合谋”造假行为[7] ,与环保部门之间存在排污博弈[8] 。这些博弈并不是个案,此类现象确实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中。
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如何影响污染防治效果?动机影响其效果的路径是什么?这些是当前学者鲜有关注但又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一是进一步揭示企业污染防治行为的内在运行机理;二是创新性地从企业内在运行机理角度,探究企业污染防治动机的效果;三是为完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分类监管污染性企业,提供了参考依据;四是为更好地发展经理人市场提供了经验证据,以促进经理人市场全面健康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动机理论及作用机理分析
20世纪70年代,韦纳(Weiner)[9] 提出归因效果论并构建了动机模型。该动机理论认为人们出现某种行为,总可以寻找它的原因和动机,为行为结果找到根源。据此,原因形成动机,动机影响行为,行为产生结果,即动机效果。受归因效果论的影响,班杜拉(Bandura)[10] 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个体拥有控制自身多方面能力的信念或知觉等意识,这种意识形成个体的行为动机,并影响个体行为。这些理论广泛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中[11] 。企业污染防治也是如此。根据动机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我国企业污染防治行为动机的作用机理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政府环境规制是企业进行污染防治的直接原因,促使每个企业形成环保意识,但由于个体差异,不同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动机强度不同,从而引致不同的污染防治行为。具体表现为:自我效能强的企业,形成较强的污染防治行为动机,积极开展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优良的环境绩效,谋求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企业价值,不再是对环境规制的简单遵从;自我效能弱的企业,形成较弱的污染防治动机,采取应付环境规制的策略,刚好达标排放,即意向合法性遵从规制。由此看来,企业不同强度的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差异。
(二)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及其效果
政府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监督、检查等环境规制措施,是企业污染防治行为的直接动力,形成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动机。其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路径是:环境规制是企业制定环境友好型战略的唯一最重要的外部动力[12] ,促进了企业污染防治动机的形成,最终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就表现为企业的污染防治活动[13] ,进而影响环境绩效,产生动机效果。具体来说,企业污染防治动机表现为,通过环保设备购置、环保技术研发创新等活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即分别从“生产末端减排”技术和“生产过程减排”技术着手安排创新活动[14] 。一般来说,在政府层面环境治理的主导下,企业环境行为包含两个层面[15] :其一是企业层面的环境行为,其二是员工层面的环境行为。各自的行为表现及关注点有所不同,这些均是污染防治动机的外在表现。
1. 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企业层面环保行为产生的动机和根源是环境规制,具体来说,企业从执法部门和新闻媒体报道获取环境处罚的威慑信息,如其他企业处罚案例等,感受到威慑从而形成自觉遵法守规的意识,进而产生污染防治动机。企业层面这种污染防治动机是为了避免受罚而采取的行动和手段,具体表现为减排设施的投资[16] 和减排技术的投资[17] ,这些均促进了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1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于企业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外在表现越明显,污染防治力度越大,越能提升企业污染防治效果,企业环境绩效越好。
2. 地方政府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地方政府实施环境治理政策,结果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是通过环保政策宣传和强制性环境规制实施,督促企业降低污染排放量,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二是实施环境治理政策后,因征收污染性企业的环境税或排污费,引致企业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进而影响当地的财政税收。由于企业污染防治支出上升、产出规模下降,将有一批微利企业因无法负担环保成本而遭到市场淘汰[19] ,从而导致地区实体企业数量减少,进而影响当地民生和就业,引发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治理政策时,需要兼顾污染治理和民生就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平衡状况、财政负担状况、人口数量、环境污染情况等有所差别,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时候也会考虑地区实际情况出现选择性执法行为。
威慑理论认为,对违规者的督查概率和处罚力度均能产生相匹配的威慑效应,督查概率和处罚力度若有一方发生下降,都会直接削弱政策的威慑效应[20] 。具体到环境规制政策,从督查概率角度来讲,稳增长促就业的要求、执法资源的稀缺性、抽查替代全面检查之择机落实,这些因素均降低环境规制政策的威慑效应,进而影响到企业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响应效果。从惩罚力度来看,地方政府处罚违规排放企业,有的企业被要求停业整顿甚至被取缔,或是将企业迁入环境规制程度较弱的地区,这给当地民生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政府造成压力。因此,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自身裁量权对污染企业实施违规处罚时,会兼顾地方稳增长促就业的现实情况,从而影响环境规制的威慑效应。由于不同地区发达程度不同,政府治理水平也不一样,地方财政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也不同,这些差异均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范围,进而影响企业的污染防治动机及其效果。地方政府对于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越大,代表政府越重视环保问题,违反环境规制的惩罚成本越高,由此传导给企业的压力越大,企业污染防治动机越强烈,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污染防治效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越强,越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污染防治动机,从而提升企业的污染防治效果。
3. 代理人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当前,污染性企业受到了国家严格的环境政策规制,企业管理层以股东利益为导向做出环保决策,避免企业因环境污染问题受到处罚或取缔,从而助推企业污染防治行为的落实。根据代理理论,企业污染防治仅涉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21] ,即代理效率的问题。来自我国实体经济的经验证据表明,高效率的代理行为促进了公司绩效的提升[22] 。在2012年以前,我国各项环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往往更加重视企业的经营绩效,整体而言对于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高,企业经理人在履行受托责任时,也往往更加重视财务绩效,疏于污染防治问题,导致企业过去的污染防治决策与代理行为的不匹配。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自此开始,我国的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经理人不得不正视国家的环保要求,主动优化代理行为,积极采取各种环保措施,助推企业层面污染防治行为的落实和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以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受到环境规制的阻碍,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代理效率越高的企业,经理人能力越强,与企业所有者利益越趋于一致,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下,经理人有较强的动机,充分利用自身的管理手段调配企业各项资源,主动提升污染防治效率。同时,代理效率越高的企业,盈利能力越强,经营压力越小,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能力也越强。经理人通过优化公司治理和经营行为,促进企业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降低企业的违规风险,通过积极的环保行动,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外界形象,赢得投资者的青睐,争取更多的政府环保补贴,提升企业经营效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效率的代理行为增强了企业污染防治动机,促进了企业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后,我国环境规制明显增强,本文选取2011 ~ 2017年沪深两市污染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如下筛选处理:①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企业样本;②剔除了?ST和ST类型的企业样本;③剔除了数据缺失或不全的企业样本;④对所有的连续型变量在1%和99%的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后共得到5689个观察样本。
本文样本企业的数据来源于以下途径:①企业污染防治行为、环境绩效等方面的变量数据取自巨潮网站公布的企业环境报告、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通过手工搜集的方式從这些报告中获取相关数据并加以计算整理;②其他变量数据取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是其动机的外在表现,本文将动机类变量提前一期处理,剩余的变量数据均为当年度的数据。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污染防治效果,具体表现形式为企业环境绩效。本文在考虑构建企业污染防治动机效果的度量方法时,参考了以往文献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度量方法。通过检索发现,现有度量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方法比较多样,在该问题上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较多文献采用环境奖励、单位能耗、总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与排污费的自然对数之比等指标,度量环境绩效。之所以在企业环境绩效度量方面出现了多样化的指标,与当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多样化,不同企业之间的环境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的状况相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借鉴吴德军等[23] 的方法,用企业环境奖励评级考察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及其效果,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企业污染防治效果越好。企业环境绩效优良且获得奖励的赋值为3,获得多个不同级别的奖励时分数可以累加,以体现其异质性;企业环境绩效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但未获奖的赋值为2;环境绩效合格达标的赋值为1。此外,借鉴刘德银[24] 的方法,构建连续数据变量作为企业环境绩效的替换度量指标,以污染物(SO2)的许可排放量/实际排放量的比值度量企业环境绩效,用于后文的稳健性检验。
2. 解释变量。“动机”属于意识形态类,无法直接计量。因此,本文以意识形态类的“动机”的外在表现——污染防治的客观活动作为替代变量。
(1)企业层面实施污染防治动机。企业展开污染防治的活动是其动机的外在表现,对于污染性企业而言,主要表现为购建环保设施的资本支出。因此,以年度环保设施的购建支出作为企业污染防治的衡量指标。手工搜集在建工程中已完工并转入固定资产的环保设施数据,并对环保设施的资本支出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的度量指标。
(2)员工层面实施污染防治动机。员工层面的污染防治行为是其动机的外在表现,是企业层面污染防治的一种延伸和展现,具体表现为员工对企业购进的污染防治设备的精心操作和对企业现有污染防治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具有层次性。本文参考吴德军等[23] 的方法,手工收集员工的环境治理行为的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层次分类、整理,根据其表现和贡献按等级赋值,最后将各项得分加总作为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的代理变量。具体做法是,员工学习了环保设备操作技术知识赋值为1,因为技术知识是提升污染防治能力的基础[25] 。污染防治技术创新是提升防治能力的关键,根据March[26] 的创新分类方法,将污染防治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挖掘性、草根性的微创新,如员工提出了未取得专利权的节能金点子、方法改进措施等,赋值为2;另一类是探索性的创新,员工研发出取得了专利权的环保产品、节能降耗减排技术,赋值为3。
(3)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由前述理论分析可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是地方政府基于该地区社会、经济、人口、生态发展状况,在环境治理方面所表现出的一种主观意愿,不能够用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法规的数量来表征,考察的重点在于当地稳增长促就业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以及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现状给予地方政府的压力。如蔡贵龙等[27] 就是用财政收支之差等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放权意愿的代理变量。鉴于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域内的人均GDP作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法是,以地级市域内的上年度GDP除以人口数,再将比值取对数。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环境治理意愿也就越强烈。
(4)代理行为。对于代理行为的计量,学者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即销售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28] 。本文经过比较分析,仅采用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效率的表征变量。不选择销售管理费用表征代理效率的理由在于,管理费用存在较多“噪音”。管理费用除包含排污费外,还包含了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管理人员工资福利费、管理用的固定资产折旧等。相较而言,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行为的替代变量,更加具有可靠性,能更直接地衡量代理效率,更好地体现代理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一般而言,资产周转率越高的企业,代理人的能力越强,代理行为效率越高,高效率的代理行为会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企业的环境绩效表现也会更好。
3. 控制变量。除前述变量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后,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及其度量方法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前述假设,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29-31] 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1. 构建模型(1),检验假设1。模型中的变量含义见表1,controls代表所有控制变量。
mccepsi=α0+α1mactci-1+α∑controls+ε (1)
2. 构建模型(2),检验假设2。在构建模型时,为了避免参与交互的变量和交互项产生共线性问题,对参与交互的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mactc)变量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wgeg)变量进行了对中处理[31] ,即先求出变量与其平均值的差,分别形成新变量mactm和wgegm,然后再使用新的交互项mactm×wgegm代入模型。
mccepsi=β0+β1mactmi-1+β2wgegmi-1+
β3mactmi-1×wgegmi-1+β∑controls+ε (2)
3. 構建模型(3),以检验假设3。对参与交互的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mactc)变量和代理行为(ageneffi)变量进行了对中处理,分别形成新变量mactcm和ageneffim,然后再将交互项mactcm×ageneffim代入模型。
mccepsi=λ0+λ1mactmi-1+λ2ageneffimi+
λ3mactcmi-1×ageneffimi+λ∑controls+ε (3)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效果中位数为1,低于其平均值4.228,差异较大,表明多数企业污染防治效果不佳,污染物排放仅处于达标水平。初步验证了大多数企业是意向合法性遵从环境规制,并未超越遵从环境规制。企业层面污染防治行为动机的中位数为7.541,与其平均值7.592差异较小,表明不同企业的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具有趋同性。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的中位数为1,低于其平均数 3.385,差异较大,表明半数以上企业未充分激发员工的污染防治动机,也初步表明了大多数企业并未超越遵从环境规制。代理行为替代变量资产周转率的中位数为0.671,平均值为0.813,说明大多数企业资产周转率不高,结合标准差来看,企业间资产周转率相差较大。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在表2中做了披露,与其他学者研究较为一致,这些统计特征表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为接下来的实证检验提供了良好基础。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变量的相关系数。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与污染防治效果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与污染防治效果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代理行为的替代变量资产周转率与动机效果的相关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些初步表明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提升了企业污染防治效果,但只是意向合法性遵从环境管制,因为反映代理行为的资产周转率与污染防治动机效果没有显著相关。此外,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显著,且系数值普遍小于0.5,各自所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 2,这说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表明,本文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较为合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回归结果分析。本文采用了stata15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因变量为mcceps的模型(1),企业污染防治动机的回归系数为0.22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的污染防治动机促进了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验证了假设1。也就是说,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污染性企业在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时,在企业层面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污染防治动机,程度的区别体现为不同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的投资额度差异,由此导致了不同企业在污染防治方面的行为差异。自我效能强的样本企业,通过环保投资增强了自身的污染防治能力,继而提升了环境绩效,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污染防治效果,从实证角度诠释了“自我效能理论”。
表4中因变量为mcceps的模型(2),R2大于模型(1)所对应的R2,表明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变量和企业污染防治动机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交互项后,模型拟合优度有所提升。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此外,企业污染防治动机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258,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的污染防治动机对其污染防治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效应,且随着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上升而显著增强,交互项的传导机制效应也得到了检验。假设2得证。具体来说,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异质性,匹配于当地企业污染防治动机的差异性,说明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违规企业的督查概率和处罚力度均能产生与其执行力度相匹配的威慑效应,这一结论验证了威慑理论。
表4中解释变量为mcceps的模型(3)检验结果显示,其R2与模型(1)的R2相比,两者数值较为接近。这表明,引入代理行为变量资产周转率及企业污染防治动机与代理行为的交互项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企业污染防治动机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代理行为、企业污染防治动机与代理行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虽然也为正,但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不同企业的经理人在意向合法性遵从环境规制方面,没有出现显著的动机和行为差异。也就是说,管理层的代理行为没有显著地增强企业污染防治动机,也没有对污染防治效果发挥提升作用。假设3没有得到证实。管理层的代理行为具有自身的偏好,对于环保责任的履行,仅偏爱于不违法不违规的及格水平,实证结果从侧面证实了我国污染性上市公司管理层仅以企业经营绩效作为其唯一的目标导向,唯经营业绩论英雄的经理人激励机制没有因为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而发生变化,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没有成为经理人职业能力考核的一项关键指标。经理人履行受托责任时,疏于环境污染防治问题,从而引致了企业过去的污染防治行为与代理行为的不匹配,最终结果只能是企业合法意向性遵从环境管制,没有达到国家预期的行业领先企业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更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
2. 稳健性检验。本文选择另一污染防治效果动机变量mccepr[污染物(SO2)许可排放量/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替代原来的污染防治效果变量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等级赋值(mcceps),重新对模型(1) ~ (3)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替换变量指标后,被解释变量为mccepr的模型的回归结果与本文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内生性检验。本文在构建模型选取变量时,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将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变量、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等变量数据取值提前一期,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其他变量数据取值于当期。除此之外,本文参考Heckman等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避免“自我选择偏误”问题和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中位数为界进行分组,即分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高组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低组,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不同强度的代理行为对污染防治动机效果(mcceps)的影响差异。分组后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高组作为实验组,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低组中选择对照组,采用模型(1)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假设2。
從表5匹配结果中可以看到,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较好,企业污染防治动机效果依然呈现显著差异,说明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能够助推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再次证明了假设2。
(四)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是企业进行污染防治活动的根本原因,对环境规制的遵从,在企业层面形成了污染防治动机,并产生延伸的效果。员工是企业环保政策的具体执行者[32] 。具体来说,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由企业家和经理人将环境规制要求融入员工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激发并形成员工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具体表现为对员工在污染防治技术方面取得的改革成就、节能金点子等给予奖励。该举措有利于企业改进环保技术,节约能源资源,进一步释放和增强企业的污染防治能力,最终提升企业污染防治动机效果。从理论上分析,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是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与污染防治效果之间的中介变量,本文将对此中介机制进行检验。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法[33] ,以考察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发挥的作用及其作用路径。具体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mactei=θ0+θ1mactci-1+
θ∑controls+ε (4)
mci=γ0+γ1mactci-1+
γ2mactei+γ∑controls+ε (5)
具体考察步骤如下:首先,考察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α1,若α1显著,进行下一个步骤。其次,依次考察模型(4)的回归系数θ1和模型(5)的回归系数γ2,若均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最后,考察模型(5)的回归系数γ1,若其显著,则表明直接效应存在,同时中介效应也存在;若其不显著,则表明只存在中介效应。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前文表4,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模型(4)和(5)回归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模型(4)中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mactc)的回归系数为0.123,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激发了员工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验证了上述中介机制的存在。模型(5)以mcceps和mccepr分别作为污染防治效果的被解释变量,依次对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和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的回归系数显著,与表4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相比,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同时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提升企业环保绩效和污染防治效果。根据逐步回归结果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污染防治动机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同时存在。具体来说,一是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激发并形成员工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二是通过员工层面污染防治能力的释放,增强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所形成的污染防治能力,共同提升企业污染防治效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 ~ 2017年污染性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污染性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及其作用机制与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的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①基于国家严格的环境规制形成的企业污染防治动机,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污染防治效果。②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作用,受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具有异质性。③企业污染防治动机是一种对环境规制的意向合法性遵从;经理人高效率的代理行为只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提升作用,但是对于企业的环境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④员工层面的污染防治动机是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影响污染防治效果的中介路径。
(二)研究启示
1. 制定分类管制政策,有针对性地引导污染性企业有序排污,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大多数企业的污染防治动机仅是为了达到环保最低标准和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是一种意向合法性遵从环境规制。针对重污染行业企业可以根据其实际经营状况和污染排放情况择机提高污染物排放量标准,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动机,助推污染防治效果的提升,让企业发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主力军的作用;对于少数积极开展污染防治的企业,如果其能超额完成污染物减排任务,则应考虑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和物质奖励,使其成为行业标杆,激发其他企业提升环保积极性,提升污染性企业的整体环境绩效。
2. 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既要强化地方政府生态保护意识,也要兼顾该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2019年猪疫后生猪生产供应不足,影响民生,是各地执行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政策留下的后遗症,需要吸取教训。环境规制政策在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地域差异,针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既能稳增长促民生,又有利于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环境规制政策。鼓励政府官员和学者多深入地方调研,创新思路,把当地特色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充分联系起来,做到民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不误,地区环境保护政策合理了,才能使环境规制政策真正落地。
3. 完善经理人市场。健全经理人市场考核机制,改变唯经营业绩论成败的单一考核机制,将企业环境绩效作为经理人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对经理人施加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让经理人充分重视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增强其主动节能减排的责任意识和污染防治动机,才有可能充分激发企业全体员工的潜力,共同创新防污治污手段、改进生产方法和技术,从企业内部提升污染防治效率。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Peter M. Clarkson, Yue Li, Matthew Pinnuck,Gordon D. Richardson. The valuation relevanc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under the European Union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15(3):551 ~ 580.
[ 2 ] 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19/c_1122857595.htm,2018-05-19.
[ 3 ]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继续指导做好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应对工作[EB/OL].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1903/t20190325_697175.html,2019-03-25.
[ 4 ] 生态环境部.2018年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EB/OL].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1803/t20180330_433330.htm.,2018-03-29.
[ 5 ]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文件.关于2017年度全国环评机构和环评工程师查处情况的通报[EB/OL].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
bgtwj/201804/t20180410_434168.htm,2018-04-10.
[ 6 ] Lu Yi, Zhigang Tao. Contract enforcement and family control of business: Evidence from China[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9(37):597 ~ 609.
[ 7 ] 孟庆峰,李真,盛昭瀚,杜建国.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0(9):100 ~ 106.
[ 8 ] Wang H.,N. Mamingi,B. Laplante,S. Dasgupta. Incomplete enforcement of pollution regulation: Bargaining power of Chinese factories[ J].Environmental Resource Economics,2003(3):245 ~ 262.
[ 9 ] Weiner B.. An attributaional analysi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nogy,1970(15):1 ~ 20.
[10] Bandura A.. Self-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J].Psychological Review,1997(84):191 ~ 215.
[11] 張同斌,张琦,范庆泉.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36 ~ 43.
[12] Henriques I.,Sadorsky P.. The determinants of a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firm:An empirical approach[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381 ~ 395.
[13] Maria D. Lopez-Gamero, Jose F. Molina-Azorin,Enrique Claver Cortes. The potentia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change managerial perception,environmental management,competitivenes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0(18):963 ~ 974.
[14] Hartl F. R., Kort M. P.. Optimal input substitution of a firm facing a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97(2):336 ~ 352.
[15] 王凤,王爱琴.业环境行为研究新进展[ J].经济学动态,2012(1):124 ~ 128.
[16] Kagan A. R., Gunningham N.,Thornton D.. Explain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ow does regulation matter[ J].Law & Society Review,2003(1):51 ~ 89.
[17] Jorgenson D. W., Wilcoxen P. J..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 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314 ~ 340.
[18] 汪克亮,孟祥瑞,杨宝臣等.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101 ~ 110.
[19] 李江龙,徐斌.“诅咒”还是“福音”:资源丰裕程度如何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J].经济研究,2018(9):151 ~ 165.
[20] Richardaposne R..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legal procedure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73(2):399 ~ 458.
[21]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4):305 ~ 360.
[22] 徐寿福,徐龙炳.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J].管理科学,2015(1):96 ~ 108.
[23] 吴德军,黄丹丹.高管特征与公司环境绩效[ 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5):109 ~ 114.
[24] 刘德银.企业环境绩效综合评价探讨[ J].理论与改革,2007(1):106 ~ 108.
[25] 郭会斌等.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机制——一个基于八家 “百年老店” 的多层次构型解释[ J].南开管理评论,2018(2):95 ~ 106.
[26]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1):71 ~ 87.
[27] 蔡贵龙,郑国坚,马新啸,卢锐.国有企业的政府放权意愿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J].经济研究,2018(9):99 ~ 114.
[28] 李寿喜.产权 、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 J].经济研究,2007(1):102 ~ 112.
[29] 胡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 J].管理世界,2017(3):76 ~ 93.
[30] Ronald L. Tinnermeie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M].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1 ~ 550.
[31] 唐国平,万仁新.“工匠精神”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5):81 ~ 93.
[32] Robertson L.,Barling J.. Green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leaders' influence on employee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3(2):176 ~ 194.
[33] 方杰,溫忠麟.三类多层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比较[ J].心理科学,2018(4):962 ~ 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