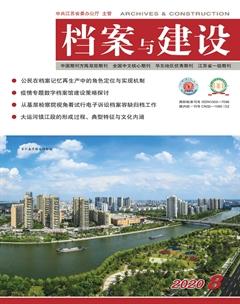档案治理的涵义、内容与内在逻辑
李孟秋
摘要:档案治理体系的建立以治理理论为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治理观,以中国治理观为根基,吸纳国外治理观可借鉴的理念,剖析了治理理论的思想实质。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档案治理的认知体系,包括档案治理的涵义,由档案基础业务、档案行政管理、档案法治化建设等基本领域与优化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创新档案公共服务、促进档案数字转型等基本目标组成的档案治理内容和以价值创造为目标、以能力建设为前提、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以规则制约为保障、以效率优化为支撑的档案治理内在逻辑。
关键词:档案治理;治理观;国家治理;公共服务;多元主体
分类号:G270
Connotation, Content and Internal Logic of Archives Governance
——Based on Chinese and Foreign Governance Views
Li Mengqiu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archives governance system is based on governance theory. By comb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governance views, taking Chinas governance view as the foundation and absorbing the reference ideas of foreign governance views, this paper summarize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governance theory. On this basis,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archives governance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of archives governance; the content of archives governance which is consisted of three basic fields including archives basic business,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nd legal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and three basic goals including optimizing archives resource system construction, innovating archives public service and promoting archiv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archives governance which focus on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building,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rule restriction and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Keywords:Archives Governance; Governance Views; State Governance; Public Service; MultiSubjects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是治理理念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政策的开端。此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内涵与发展要义逐渐丰富,并逐渐成为各项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治理一词分别出现24次和81次。可见,坚持治理理念已逐渐成为中国应对国际及国内复杂形势的重要基础。
档案是国家重要战略性、历史性的信息资源,“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2]。档案工作是国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以治理思维审视档案与档案工作,构筑完整的档案治理体系,成为档案与档案工作面临的全新课题。2016年,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3],首次出现了有关档案治理的表述。其时,档案治理的主要内容在于强化档案法治化建设,构建完善的档案法律体系。且随着档案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次研究的深入,其内涵逐渐丰富,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结构。
在国内,晏秦[4]、常大伟[5]、徐拥军[6]等人以治理理论为基础,对档案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陈忠海[7]、金波[8]等人分别从国家、档案事业、公民的角度论述了档案治理的价值取向。唐一芝[9]、常大伟[10]、吴建华[11]等人则分别论述了档案治理的参与主体及其关系。国外并未专门展开面向档案治理的相关研究,而是将档案融入国家治理与信息治理的宏观视野。在档案与国家治理中,档案被视为“生产知识的宝库,国家权威的见证,也是汇集秘密、法律和权力之间联系的宝库”[12],“有效的档案管理与善治构成了国家有效运转的保障,其中,档案成为善治的基础”[13]。在档案与信息治理中,有研究者认为,一方面,信息治理是档案管理的机遇,“档案将在信息治理的框架中得到重塑,并满足利用者的信息需求”[14],另一方面,“有效的档案管理应该成为政府信息透明建设过程中的贡献者,使信息公开满足合规要求”[15]。可见,对于档案治理的探讨需要结合语境,根据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赋予其价值。目前关于档案治理的研究呈现出“研究对象概念化、目标指向社会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在于目前对于档案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框架、对于档案治理的内容尚未达成共识等。档案治理体系的建立需要明确治理理论的基本意涵,因此文章首先通过分析档案治理的发展动因以明确其动力,接着系统梳理国内外治理理论,并以中国治理理论为根基,吸纳国外治理理论中可借鉴的成分,在此基础上明确档案治理的内涵、内容与内在逻辑。
1中外语境下的治理观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治理理论在中国与外国学术界实际是一种表述、两套话语体系。由于国家发展沿革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与主要挑战不同,中外治理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亦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就中外治理观作比较性阐释,以明确其主要内容。
1.1中国语境下的治理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治理概念囊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个层次,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被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成为重要改革内容”[16]。因此,把握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需要首先明确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意涵。
国家治理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思想的基础上坚持国家建构、法治化建设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其思想核心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基础,领导人民、依靠人民实现国家的科学、民主发展;政府治理则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由国家行政体制和权力体系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利益诉求;社会治理则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及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既发挥国家公共权力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又积极吸纳社会公民权利参与,使各项活动能反映出公众利益需求。
基于对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意涵的简要探析,可以发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观包含以下要点:
以强有效的国家建构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对国家与社会事务起着重要的领导与协调作用,这是由中国当下的国情政情社情所决定的。
有效的治理以法律规范为基础,通过依法治国战略推进国家、政府、社会的法治化建设。
立足人民视角,以人民利益作为治理活动的根本目标,既全面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设计符合其利益诉求的发展路径,又在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的基础上开放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与人民协同共进。
1.2外国语境下的治理观:去政府与善治
在外国学术界,治理(Governa- nce)作为一种否定传统管理(Management)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演进,“治理”一词已广泛指代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美国学者福山认为,治理具有两种典型含义,一为“去政府化的治理”,一为“以国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善治)”[17]。
“去政府化的治理”根植于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也由此形成两种适用环境。基于国际环境的去政府化治理,传统国家之外的国际组织通过不同渠道的合作[18]形成了国际治理的主要形式。基于国内环境的去政府化治理,实际源于企业经济学的社会网络理论,将治理视为自由组织的组织间网络[19]。去政府化治理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资本优化为前提,认可政府在新环境下的职能弱化,提倡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向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善治”既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学者们对于失败的去政府活动的反思,也是重新思考政府权力向非政府组织转移的原因。目前,政府依然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职能,需要以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政府职能与现有的能力,支持私人部门對于公共活动的参与,进一步强调自由民主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对外国语境下治理意涵的阐释,可以产生以下共识:
政府职能弱化是现代治理理论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将在一定阶段内承担政府部分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在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合作过程中,主体多元、去中心化成为行为逻辑主导,个体能力成为权力分摊的主要依据。
在治理活动中以经济学理论为依托,重视治理活动的效率,将资本要素纳入治理活动,提升治理效率。
重视治理活动的“公共性”,以有效公共服务供给为治理前提,通过多中心合作,“重新塑造公共服务,以便使政府能够集中处理服务管理和协调的事务,而由那些私有的、营利的或非营利的组织去从事具体的服务活动”[20]。
2档案治理的涵义、内容
2.1档案治理涵义
档案治理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理论与现实背景。第一,近年来,全球形势呈现出新特征,这些特征影响发展态势,重塑国际关系,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催生了国家发展的新课题。档案与档案工作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立足国家治理视野发展档案治理体系,增强档案治理能力。第二,在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档案不但是建立社会信任的重要资本,也是推动建设依法治国体系的有力支撑。因此,推进档案治理建设、强化档案赋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第三,档案治理的发展是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能力演进的必然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档案的重要价值,通过主动获取、利用档案满足自身需求,各主体建档、管档、用档的能力也随之增强,愈发关注档案法治化建设等相关业务动态,积极建言献策。第四,随着档案与社会互动的深化,档案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变化,档案参与主体、对象与方法也呈现出新态势,档案社会化趋势愈发明显。
中国语境下的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其内涵的界定需以治理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档案与档案工作的特殊性进行组配,从而揭示档案治理的本质内涵。可以发现,中外语境下的治理观,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共性。外国语境下的治理观过于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缺乏对于主体关系与顺序的界定,且其理论基础在于萎缩的国家建构与政府能力,并不符合中国实践。因此,应以中国语境下的治理观为基础,以国家建构为根基,发挥国家及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协调社会与个人的参与,通过法规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示,从而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然而,国外将经济学理论引入治理研究的思维值得借鉴,在以人民为首要标准的前提下,激活资本,使治理活动反映国家生产力的需求,将增强国家能力的建构,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同时,强化公共服务思维,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将会使治理活动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基本诉求,优化社会资本、增强社会信任。
通过上述对于国内外治理理论的回顾与总结,并系统集成现有文献中对于档案治理的论述,档案治理这一概念实际上囊括了国家层面、机构层面、个人层面等多个维度,且尚未形成可被普遍理解的认知,因此不宜采取过于精细的定义方式,而应直接揭示其本质特征。由此,文章认为,档案治理是指在党政机构领导下,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导,各级各类档案机构、社会组织与个人协同,在法治化建设框架下以民主方式共同参与对档案及其相关事务的管理,从而促进档案事业发展,强化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满足国家、社会、公民需求,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的过程。
2.2档案治理内容
在早期档案治理相关文献中,存在“档案治理就是档案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21]的观点,这类研究将档案治理与档案行政管理视为同位类概念,与早期国家档案局文件对于档案治理的表述契合。然而随着治理理论的完善,档案治理的范围与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档案治理是一个囊括各层级需求的综合性概念,难以从现有术语中找到同位类概念。因此,从文章研究目的出发,结合档案治理的内涵,将档案治理的内容划分为三个基本领域与三个基本目标。档案治理的基本领域是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档案治理的基本目标则决定了基本领域的发展脉络,两者相互作用,强调基本目标的重要性,有利于使档案治理按照既定方向发展。其中三个基本领域包括:
第一,聚焦档案管理领域,将档案作为治理对象。以“档案的接收与征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目与检索、编辑与研究、统计和利用服务”[22]为治理内容,提高档案业务在机构中战略地位,加强业务协同,树立全员责任意识,促进管理层、业务部门、信息部门、技术部门对于档案业务的参与。通过提升话语权、主体协作、基础设施协同、技术创新等措施提升档案馆(室)的档案管理能力,实现档案管理创新发展。
第二,立足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档案行政管理机制,提升档案行政管理效率,从而增强档案管理主体能力,促成多主体共同参与。以近年来开启的新一轮档案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重新梳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业务机构、各类社会组织的权责关系与职能定位。明确各行为主体的主要责任,发挥其主要优势,聚焦特定管理需求开展活动,更好地发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档案事业统筹规划、宏观管理的职能,并将各类具体职能向档案业务机构与社会组织转移,做到“各有所长、优势聚焦、业有所精”。
第三,完善档案工作法治化建设,为档案治理提供准绳与标杆。“依照法律规范,遵守法治原则和要求建立档案治理体系,提高档案治理能力,真正从制度上保障档案治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23]。既要求从立法层面上进一步完善档案法律体系,也需要在执法层面上保障档案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更需在守法层面上提升各行为主体的法律意识。
而三个基本目标则包括:
第一,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拓宽进馆渠道、改变进馆标准、支持民间建档行为等途径建立结构更加完整、内容更为全面的档案资源体系,使其置于公民—国家框架中,更为详尽、系统地反映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从而实现维护政党治理可持续性,践行“档案民有、民治、民享”[24]理念的双向目标。
第二,强化公共服务思维,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创新档案公共服务路径。以档案资源体系为基础,建立档案公共服务体系,“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提供均等的档案服务和档案公共产品”[25]。
第三,引入经济思维,通过档案治理活动促进生产力发展。主动参与国家大数据战略,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积极响应数字转型,引领数字中国建设。注重技术支撑,通过单轨制与数据化发展完善档案数据治理,促进档案数据的资产化开发、安全保护、开放利用,支撑并打造数据要素市场[26]。
3档案治理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是事物的应然性起点,是基于其内在特质的结构性剖析,也是使其得以发展的原生动力。基于档案治理的涵义与内容,档案治理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
第一,以价值创造为目标。以往档案业务的开展具有确保档案安全、完成组织任务的思维惯性,并不注重档案与档案工作价值的进一步发挥。档案治理引入了经济学思维,强化档案与档案工作的价值意识,通过加强融入、主动挖掘、工具创新等途径实现多维价值的创造与发挥。立足以往档案工作基础,档案治理更加注重深层价值的挖掘,通过一系列策略创新优化档案管理体制,发挥各机构、部门潜力,提升管理效能;通過细化颗粒度实现数据化管理,进一步发现关联、发掘价值;通过树立公共导向,完善档案公共服务,探索出公民档案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以能力建设为前提。中国语境下的治理观强调国家建构,其实质是对于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诉求,而社会与公民力量参与的治理体系,则更加强调多元主体能力的共同提升。档案治理的复杂性,决定其所需能力的多样性,缺乏覆盖多主体的档案治理能力,就难以真正实现档案治理的基本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档案治理能力呈现出多维度、全方位的特征,常大伟将档案治理能力体系总结为制度、档案公共服务、档案业务、统筹与组织、社会参与、监管、回应[27]等七个方面,实际上概括了国家、政府、档案机构、社会、公民等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能力需求。
第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中外治理观的共性在于,基于共识性的治理目标,倡导国家、社会与个人对于治理活动的共同参与,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最大程度释放治理效能。基于此,档案治理秉持多元共治的基本理念,发挥不同主体优势,形成覆盖面广的治理体系。面对结构复杂的档案治理体系,档案部门不能也不应大包大揽,而是要鼓励并规范企业、档案中介机构、档案学会、个人等社会主体参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更有利于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好地实现为民服务的价值目标。
第四,以规则制约为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建制是中国语境下治理观的核心内容,通过推进法治化建设、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增强制度供给与保障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保障。由于档案治理内容广泛、参与主体多元,治理难度远胜于昔,因此亟待划定边界、明确范围。在复杂系统中,通过设立规则减少不必要消耗是减缓熵值增加的最优解。因此,需要在各层级建章立制:在国家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机构层面设立配套制度规定,在个人层面强化规则意识,确保档案治理活动在完整的规则体系下开展。
第五,以效率优化为支撑。治理活动的有效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注重效率,意味着治理主体进一步明确治理目标,并建立了针对治理目标的动态追踪与改进机制。在传统各项档案活动的开展中,由于负责部门能力不足、主体参与度缺乏、效率意识欠缺、技术手段有限等原因,片面追求完成任务而忽视了工作效率。档案治理追求治理活动的高效化与效益化,通过弥补能力缺陷、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技术能力,可实现效率优化。以较低成本投入换取较高成果产出,实现治理活动可持续发展。
4结语
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档案工作发展的新篇章。在复杂的理论与实践环境下,践行档案治理理念、推动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发展,更大程度发挥档案价值。档案治理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档案部门、社会组织与个人都应积极投身其中,通过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践行档案治理的价值追求,并不断推动档案治理现代化进程。
*本文系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00301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20- 07- 09].http: //www.gov.cn/jrzg/2013- 11/15/ content_2528179.htm.
[2]国家档案局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EB/OL].[2020-07-10].http://www.saac.gov.cn/daj/xxgk/201405/1d90cb6f5efd42c0b 81f1f76d7253085.shtml.
[3]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2020- 07-10].http://www.saac.gov.cn/ daj/xxgk/201604/4596bddd364641129d7c878a80d0f800.shtml.
[4]晏秦.论档案治理的内涵、特征和功能[J].档案管理, 2017(4):4-7.
[5]常大伟.档案治理的内涵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8(5):14-18.
[6][23]徐拥军,熊文景.档案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价值追求和实践路径[J].档案学研究, 2019(6):12-18.
[7]陈忠海,宋晶晶.论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档案治理[J].档案管理,2017(6):21-24.
[8]金波,晏秦.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J].档案学研究, 2019(1):46-55.
[9]唐一芝.社会治理视域下多元档案管理权力主体的功能定位新探[J].档案管理,2016(4):10-13.
[10]常大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档案制度改革[J].档案学通讯,2019(6):11-17.
[11]张帆,吴建华.基于档案治理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转型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9(6):18-26.
[12]Stoler A L.Colonial archives and the arts of governance[J].Archival Science, 2002(1-2):87-109.
[13]Kargbo J 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ood Governance and Record Keeping: The Sierra Leone Experience[J].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Archivists,2009(2):249-260.
[14]Brooks J.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rd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governance[J].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2019(1-2):5-17.
[15]Shepherd E,Stevenson A,Flinn A.Information governance, records management,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A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England[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0(4):337-345.
[16]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3):11-17.
[17]Fukuyama,Francis.Governance: What Do We Know, and How Do We Know It?[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ence, 2016(1):89-105.
[18]Rosenau JN,Czempiel EO.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9]R.A.W.Rhodes.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J].Political Studies,1996(4):652-667.
[20]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產: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构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21]刘东斌.档案治理概念辨析[J].档案管理,2019(1):47-49.
[22]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4]Ketelaar E.Archives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J].S.A.Argiefblad/S.A.Archives Journal, 1992(34):5-16.
[25]何振,易臣何,杨文.档案公共服务的理念创新与功能拓展[J].档案学研究,2015(3):44-50.
[26]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EB/OL].[2020-07-14].http://www. 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27]常大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我国档案治理能力建设研究[J].档案学通讯,2020(1): 1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