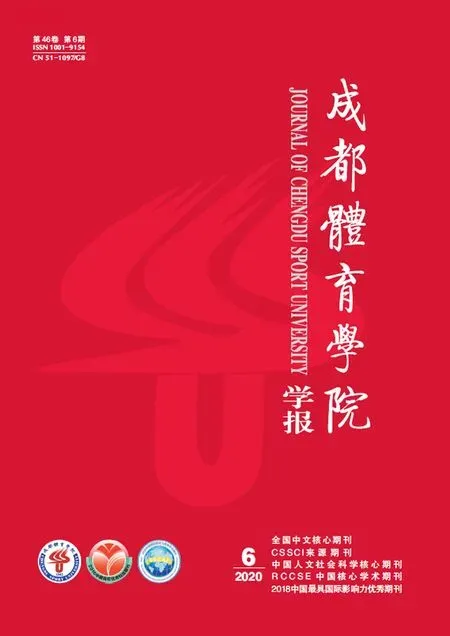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回顾与反思
孙淑慧 ,李 楠
1 “女性体育”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1.1 “女性体育”的内涵
“女性体育”看似是一个指向较为明了的范畴,指与“男性”相对应的“女性”的体育活动与体育现象;需注意的是在我国相关研究中同时使用的术语还有“妇女体育”“女子体育”,一般来说,“女性”“妇女”和“女子”三者间在内涵上有一些细微差别:“妇女”多指有婚史的或成年的女人;“女子”一词更突出与“男性”的对比等,此外,此3 个词背后还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只是:女儿、妻(媳)、母等具体角色,并无抽象的“女性”概念;近代在救国图强大背景下,“女子”概念兴起,并发展出丰富的内涵,从解放女子身体的反缠足运动、解放女子精神的兴办女子教育到争取女子权利的女子参政运动,蓬勃开展;新文化运动中,“女性”一词兴起,其背后体现了其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理解和接受;之后,“妇女”一词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带入了中国社会话语当中。“妇女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群体特征,“妇女”一词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其往往更强调“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因而有淡化性别特征的内涵[1]。笔者注意到,体育领域学者们使用“女性体育”“女子体育”“妇女体育”术语时,实质内容基本无区别。但在20 世纪90年代以前,习惯使用“妇女体育”“女子体育”,在20世纪90 年代以后“女子体育”和“女性体育”的使用频率提高,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背景下,随着整个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人们逐渐重新广泛使用“女性”“女人”取代政治色彩较浓的“妇女”一词,体育学领域稍稍滞后。本研究亦使用“女性体育”一词,同时“妇女体育”“女子体育”的相关研究也是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此外,除上述的差别,还应注意到女性体育之“女性”的年龄问题。美国著名的体育史专家阿伦·古特曼在其著作《妇女体育史》(Women's Sports:A History)中,称其关注的重心是“年长的少女和妇女体育”[2],他认为:“因年长的少女和成年妇女的体育通常比儿童的游戏揭示出更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确,尽管体育是性别分化特征鲜明的活动,但儿童期男女两性的体育活动差异并不大,只有从青春期开始,女性体育开始在时间和空间与男子体育才呈现出重要差异,从实际来看,至少从笔者所关注的时间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来看,现有的各类女性体育研究多是指青春期以后的女性。
1.2 研究“女性体育”的意义
传统认为,体育是“男性领域”,如在现代奥运会复兴之初,女性是被排斥的。但是,“女性”还是最终闯入了这一领域,且参与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有人甚至声称,体育运动进入到“她”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一过程并非风平浪静、水到渠成的,而是充满了“抗争”和“妥协”。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背后都是“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讯息,故探究“女性体育”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的远比“体育”本身多得多。而在体育领域,直到当下,体育仍被视为“残留的超男子气概”在现代社会化中的最后一层堡垒,男性很大程度上继续“拥有”体育[3],女性仍属体育领域的“他者”,研究探析作为“他者”的女性的体育经验、体育态度能丰富和加深我们对现代体育的认知。
鉴于以上,笔者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女性体育”研究当是一个极具吸引性的研究课题,这就使得总结与反思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的现况与存在的问题,必要而富有意义。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相关研究且主要以中国知网收录刊载的相关论文为分析样本,之所以以“改革开放”作为研究的起点,不仅仅因为其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具有特别和深刻的内涵,更重要是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兴起的。
2 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状况
为较为全面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子体育研究的状况,笔者以前述“女子体育”“女性体育”“妇女体育”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从1978 至2018年12 月所收录的中文文献进行了检索,并对所得信息进行了筛选,删去其中重复出现的记录(同作者、同题目的研究,凡是博硕库与期刊库中重复的,以博硕论文为主;期刊库与会议论文库重复的,以期刊库收录论文为主)。此外,为更直观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的状况,本文采用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作为辅助,以Citespace V 为分析工具,针对“女性体育”研究关键词共现、战略坐标等数据进行了分析。
2.1 逐步增长但仍显“小众”话题
经筛选汇总发现,1978-2018 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女性体育”的相关文献有1 370 余条。其中最早的当属《体育科学》1982 年2 期所刊载的《试论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兴衰与及其主要原因》一文,之后,陆续有关于女性体育的学术论文发表,整体来看,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女性体育发文量呈整体上升趋势(见图1),发文量最高为2014 年,达150篇。结合所发论文的主题来看,20 世纪80 年代为数不多的“女性体育”的学术论文多为引介境外和中国古代女性体育发展概貌,20 世纪90 年代后,女性体育的研究内容才有所拓宽,下文笔者会详细讨论有关女性体育研究主题。可以说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真正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此外,为进一步了解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女性体育研究的概貌,笔者对相关研究所属学科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女子体育”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体育学占86.2%;“女性体育”为主题词时,体育学占83.7%;“妇女体育”为主题词时体育学占92.2%,这一分析虽未排除重复记录,但可反映出改革开放40 年来“女子体育”主要是体育学科所关注的内容;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在1978 年到2018 年间体育学科中“体育”为主题的文献总量有41.98 万篇,女性体育仅有1 370余篇。

图1 “女性体育”年发文量趋势Figure 1 Trend of annual volume of pub libations on “Women‘s Sports”
综上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20 世纪80 年代后,中国女性体育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迅速崛起,女子体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中国女排在20 世纪80 年代初的短短的几年里创造了“五连冠”的辉煌。女子体育的快速发展的客观现实是女子体育研究受到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另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极大促进了中国性别平等工作,也唤起了许多学者关注与从事女性研究,包括女性体育研究①董进霞教授曾撰文称其从事女性体育研究源于世界妇女大会的启发。董进霞.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与我的女性体育研究[J]//刘伯红,谢丽华,吴华.女性的反响续集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二十周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09.37.,自此,开始出现以女性体育研究为志业并致力推动中国女性体育研究的学者,如北京大学董进霞教授等。但40 年来女性体育的发文趋势显示出,相较其他体育类研究,女性体育仍属一个关注者甚少的话题。笔者认为这和女性体育研究的价值不相匹配,有待突破,笔者藉此文,一则希望自身能在此领域持续深耕,更希望能唤起更多的同道者。此外还应注意一点,上述数据揭示,近40 年来,我国“女性体育”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学领域。但事实上,女性与体育运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女性体育决非单纯的“体育”问题,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角色及状态是与多样化的社会机制互动的结果[4],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视角及理论,才能揭示出制约与影响女性体育发展的复杂因素,这既需要体育学领域的学者们能不断拓宽学术视野,也需要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能“观照”到此问题。
2.2 出现了个别高产作者,但未形成相对核心作者群
研究者是推动研究领域和学科发展最具创造性的力量,诸多学科领域均十分注重研究者和研究质量改善间的研究[5]。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欲走向成熟,最主要的是有一批稳定的研究者和突出的学科带头人,即核心作者,坚守深耕,不断突破。故此本研究运用了普莱斯定律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是否形成了核心作者群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笔者检索到1 371 篇文献中,作者共1 286 名,根据普莱斯公式计算,截止2018 年我国女子体育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绝大多数为仅发表一篇相关成果的瞬时作者。笔者认为尽管女子体育领域尽管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但也有了一些高产作者,如前文所提及的北京大学董进霞,其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女性和体育”问题持续至今,共发表相关论文(含引介性质)17 篇,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外女性体育研究的引介、性别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状况等,当之无愧为国内女子体育研究的领军人物,董进霞教授还积极推动北京大学于2002年成立了“妇女体育研究中心”;在该中心成立10年后的2013 年又成立了“中国社会性别与体育研究会”,对促进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深化、细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此外,华南师范大学的熊欢及北京化工学院的阳煜华应算得上近些年女性体育研究的“新秀”,熊欢从2008 年开始到2018 年共发表11篇相关学术论文,阳煜华从2006 年开始关注女子体育问题,截至2018 年亦发表有10 篇相关论文,两位为高产作者名至实归。值得深思的是,女子体育研究领域众多的瞬时作者。笔者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现行评价体系下,一些研究人员为了完成科研任务和晋升职称,往往倾向于选择“容易发表”的问题展开研究,“边缘化”的女子体育话题相对新颖,因而,一些人尽管自身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基础,亦选择女子体育作为研究与“作”文的对象,这些瞬时作者严格来讲算不上女子体育的研究者,换言之,笔者以为,虽然历经40 年的积淀,但目前,国内真正从事女子体育的研究者还较少,更未形成一定的团队优势。笔者也不认为,成为所谓“显学”,学者蜂拥而上是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提升的良途佳径,但是真正有志于此的研究者长期的“坚守”却是不可或缺的。
2.3 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较丰富,但呈现出粗放和表浅的倾向
通过分析文献发现,总体上讲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女性体育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野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对我国古代妇女体育状况的梳理、国外妇女体育开展状况及研究状况的引介,到现在基本涵盖了女性体育的方方面面,现有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女子体育史研究。论从史出,回归历史研究,才能对理论产生的针对性、历史语境及局限性有深刻的理解。妇女体育研究欲更走向深入,历史视角的研究十分重要。综合来看,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女子体育史的研究在整个女性体育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笔者检索获得的文献中,从历史视角研究女性或者说研究女性体育历史的文献有340 篇,所占比例近1/4。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笔者以为这是女性体育研究领域中的“幸事”,这些研究中,有对中国古代妇女体育文化现象的梳理;有对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历程的总结;还有国外女子体育发展史的引介与评述以及杰出历史人物的妇女体育思想观的总结等,其中,唐代妇女体育及近代中国女性体育发展历程是其中之重点。著名历史学者严耕望先生认为唐代女性延续了北朝女性的开放风气,“或骑或射,或著男装,或男女博戏,皆无禁防,几与今日不异。”而在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现代性焦虑下,“女性身体”的规训及“强健”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近现代女性体育随之开始兴起。因此,女子体育研究中“唐代妇女体育及晚清以降中国女性体育变迁”颇受关注不足为怪,这正体现了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辅成关系。但,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反思:其一是有关中国女子体育史研究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寻根史学”特征,有一种证明与倡导“吾国体育发达之早,远过欧美……为今日提倡体育计,苟能就吾国固有之体育,发挥而光大之”[6]的倾向,且一些研究停留于史实罗列,缺乏必要的分析;其二,习惯于“宏大叙事”,即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倾向于关注大问题、大事件、长时段,“通史历程”式的研究,而忽视对个别的、具体的史实和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对史料的深度挖掘;其三,缺乏“世界性”视野。历史认识中应要有全球的眼光,一旦有“世界性”视野,对于同一历史现象的判断就会有很大差异:如对我国近代女性体育状况描述中,一些研究者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必定是落后的,但如果放在世界女性体育发展大背景来看,我国近代女性体育的发展未必落后很多。
——女性与体育锻炼及体育消费研究。健身是体育最本质的功能,何以且如何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促进健康,素来是体育学中的热点话题,女性体育研究中也不例外。笔者检索获得的1 371 篇文献中,有近41%(570 篇)论文是研究女性与参与体育锻炼及体育健身、体育消费的。从内容来看,笔者认为较为丰富,既有“全景式”调研我国女性参与体育锻炼状况的,也有地域性的;有从年龄分类,有从职业类别及所属研究女性与参与体育健身与体育消费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到了我国农村女性及少数民族女性参与体育健身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当中在女性与体育健身、体育消费问题这一主题上,值得反思的是这些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笔者注意到,相关的300余篇论文当中,有近80%的论文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众周所知,问卷调查法是一种从宏观的角度、采取定量的手段、依据客观的验证来认识和说明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方式,其适用于描述一个大总体的状况。对于较为深入了解和认识人们行为的动机、思想感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各种主观感受及心理状态等,问卷调查则十分有限;同时问卷调查本身的使用要求极高,从问卷的设计到效度、信度检验到统计分析等都有较高的要求。但,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把资料收集过程与问卷调查直接划等号,不管研究的问题的实质与属性,动辄使用问卷调查,且很少真实地对问卷的效度与信度进行检验,女性体育研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笔者曾在多份研究女性参与健身的研究的问卷中,看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知道《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是哪一年公布的? 笔者实在困惑于此问题与女性参与体育健身的深度关联性何在? 笔者以为,这些现象同样反映了我们学术领域学风不实,“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有待“矫枉”。
——女性与奥运会及竞技体育运动研究。如前所述,传统上,体育被视为“男性领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复兴之初本是“排斥”女性的,或许正是因为被拒绝,“体育”领域反而成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必争之地,“奥运赛场”则成为女子争取与男子平权的“切入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百余年来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女性”进入“赛场”并日益“辉煌”的历程。具体到我国,从重返奥运会之始,竞技赛场上的女性就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当中最亮丽的身影,她们一次一次让五星红旗升起在国际赛场上,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我国女子竞技的辉煌成就,甚至被一些人描述为“阴盛阳衰”。可能正是因为女子竞技体育发展飞速,其也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笔者检索获得的文献中,有近11%(150 篇)的论文是探讨女性与竞技体育的,从数量来讲,笔者以为较为可观;从内容来讲,笔者认为,现有的女子体育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比较于上述两个方面,视域较宽广,分析较深入,因而水准较高,一些研究引入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触及到了女子体育“形而上”的问题,如高鹏飞《差异下的平等:女性主义影响下的体育项目设置》[7]一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女性在参与体育运动项目中的嬗变趋势,揭示了体育运动中“平等”的复杂性。还有一些研究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探讨我国的女子竞技体育,并从与其他国家的相比较中剖析我国女子竞技体育超常快速发展的成因[8],从社会性别角度诠释了我国体育所谓“阴盛阳衰”的不真实性[9]等等,即中国女性相比男性更顺从、更听话,忍受力更强,故能更好地执行教练的意愿,等等,这些研究均有一定的见地。
但同时,笔者认为,有关女性参与竞技体育及奥运会的话题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如:对于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我们到底在期望什么? 早在2 500年前,古希腊著名戏剧家欧里庇德斯在其剧作中借一个角色问道“对于从斯巴达来的女孩——在那里,年轻女子半裸或全裸地与年轻男子赛跑,并且和他们分享跑道和角力用的建筑物,我们到底期望什么”[10],尽管已经穿越了两千多年,欧里庇德的问题仍值得我们去追问:女性“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到由男性定义的竞技运动中,对女性而言是公平的吗? 竞技体育活动经历对于女运动员而言,究竟会带来更多挑战还是机遇,等等,再有这些问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特殊性吗?
——女性体育传播与媒介研究。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加雷洛有言称,电视等媒介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体育”[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世界体育发展历程证明了媒介在现代体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故,体育与传媒关系是当代体育学领域颇受关注的话题。现代意义上的我国的女子体育,是西方的“舶来品”,其是由中国精英男性主导“启蒙”、倡导与推动的,这一过程中报纸、杂志等等媒介功不可没。我国女子体育研究当中,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女性体育与传媒间的关系,在笔者检索到1 371篇文献中,探讨女性体育与传媒关系的论文有76篇:其中,有一些研究是从历史视角探讨民国时期报纸、杂志如《女子世界》《申报》等在我国女子体育发展中的影响;多数研究剖析的现当代媒体所呈现的女性体育,揭示与应证了当前的媒介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着性别歧视或不平等:如媒介呈现的女性体育突出体育女性的性别角色,被特写的是“女”字。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存在着一种宏大叙事倾向:宏观的策略对策较多,微观层面的,深层描述成果较少。
——其他类研究。根据笔者检索所得文献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的女性体育研究,从内容上来看,除上述4 个方面外,较为集中的还有:国外女性体育理论引介、评价及中外比较视野下的女性体育研究37 篇;中国女性体育发展的价值与意义研究37 篇,女性体育研究的研究8 篇。在此,笔者主要想讨论“女性体育研究的研究”。作为科学意义上的近代学科的发展总是与该学科反思意识的自觉成正比的,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体育研究已成为我国体育领域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但从整体水来讲,与鲜活的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相比,女性体育研究有待深入,因而对女性体育研究的研究与反思是必要的,而从现有的数量极少的研究“女性体育研究”的文献来看,多是泛泛而谈的总结,且“褒多贬少”,远远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反思。
综上,笔者认为,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经历了从起步到不断发展、初有成效的过程,但仍存有较大提升空间。
3 “跳出”体育,转向“文化主义研究”——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未来走向的思考
笔者在前文提及女性体育研究对认识现代体育的意义,事实上女性体育研究的意义远不止此,正如南茜弗雷泽所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需要警醒,女性体育问题决不是一个单一的“体育”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问题,正如,董进霞教授所说,我们需要检视社会性别构造的社会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方式,才能对社会有更为清晰的洞察力,发现体育运动的整体发展、空间构造、在家庭和社会中对男女身体的定义,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等[12]。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西方女性体育研究兴起时就一直是属体育社会学、亚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议题,我国女性体育研究进一步提升,亦应更多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视野与方法,即应当跳出体育看女性体育。这就要求有志研究女性体育的体育学者们,充实相关学科理论素养。
笔者在前文提及,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多数研究止于泛泛而论,呈现出“粗放”和“表浅”的倾向。针对此,笔者认为借鉴伯明翰学派所确立的所谓大写的“文化研究”范式甚为紧迫。伯明翰文化研究范式或称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其强调文化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性,突出人的经验的本源性、真切性、生动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强调研究方法上更关注细节、本地经验以及日常生活所模仿与体验的象征性微观世界等等[13],其崛起于20 世纪60 年代,90 年代开始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14]。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针对文化主义研究不足之处进行反思,但笔者认为从改进我国女性体育研究中普遍的“宏大叙事”倾向而求得更鲜活、更深层的事实和认识而言,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女性问题研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取向于这一范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结缘,非嫁接伯明翰话语不成体统,这也几成共识”[15],以其为“依据”,笔者就提出有如下策略和方法。
3.1 培养学术“批判”的勇气与思维
从源头上说文化研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立场,而这种立场最明显的是一种“批判姿态”,正是以批判为基础,文化研究范式形成了“重当代文化,不重历史经典;重大众文化,不重精英文化;重边缘文化,不重主流文化;重文化实践,不重宏大叙事;重具体情境,不重一般模式;重跨学科性,不重学科立场”的研究路径与领域。批判思维是学术研究创新的动力,我国女性体育研究要实现突破,走向深入和“鲜活”,学术批判的意识不可或缺。但遗憾的是,当下,我们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多习惯于为既有“政策”寻求合理性,尤其是现代意义上我国女性体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的的确和中国“女权”的兴起和妇女解放相勾连,使更得妇女体育研究中更是歌颂式诠释偏多,因而,“批判”的思维更需要勇气。
3.2 坚持“同命者”“局内人”视角
质性研究中的“局内人”指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她)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看法[16]。因与研究对象共享同一文化,“局内人”在与被研究者的对话中比局外人更容易进入对方的世界,建立信任关系,进而更准确地理解对方,提升研究的效度。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女性体育研究中特别需要作为“局内人”的女性研究者的视角和体验。如前已述,现行体育运动大多是基于男性价值和经验而塑造的,大多数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是通过男性开始的或由男性定义的,医学研究也表明性激素的多寡才是左右运动能力高低的关键。女性若参与其中并取得优胜,须适应男性的规则和心理,甚至是生理。在当今的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一些女运动员或许是成功的,但她们同时又被认为有男性风格,不仅仅是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甚至是生物学意义上,如一些项目的女运动员易出现男性性征——喉结增大,胡须、腋毛、体毛明显、声音粗重,凡此种种,对参与其中的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寻求这些答案的过程中,笔者以为,“同命人”或局内人的视角或经验比男性的经验更准确地反映现实与“揭秘”现实。如,绝大多数研究中认为,晚清以来我国女性体育的发展变迁过程总是和女性解放和地位的提升相关且往往是从国家体育史的视角来进行的,多数研究总是先入为主地强调这一过程中女性是“被解放”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院游鉴明老师从女性经验出发,通过爬梳史料揭示出了近代女性体育中女性主体现象:女性在运动中不断地寻找自我,逐渐学会而且乐于掌握一些“主动性”的权力,对于这种权力的冲动欲望并不亚于男性,甚至她们要向男性看齐,与男性并驾齐驱的[17]。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我们借鉴。
3.3 积极而谨慎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
拒绝普世化的话语模式而注重扎实的田野调查,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甚至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体验亦是文化研究范式的一大特点。前文笔者已讨论过,从现有的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当中有一倾向是把问题调查等同于资料搜集。事实上,每一个女性都是具有特性的个体存在加之不同时代赋予女性的特殊存在性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事关女性的研究应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还原,即还原为女性具体的个体性的存在,具体分析其处境和状况,包括自然生理形成的、后天社会影响的因素,诸如性格的、心理的、教育的、公共角色和家庭角色等等因素。也只有这样具体分析还原的研究,才能使女性回到自己,解决与之相关的切实问题,并最终超越自身从而获得真正的发展。从此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深度访谈及个案研究法值得提倡。深度访谈即半结构式的访谈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非结构性,访谈的问题和访谈的模式都不是预先设定好的,研究者事先只是确定了简略的访问提纲和研究方向,所有的问题都在访谈的过程中生成的,是研究者和被访者共同创造的”,这也正是“文化研究范式”所倡导的方法,在笔者的检索的文献中,发现我国现有的女性体育研究中有类似的研究,如邱亚君等人对女性休闲体育限制性因素的研究[18],就是通过对65 名女性的开放式访谈展开的。通过这样具体的、细微的个体经验的梳理和把握,可更深入、更细致地呈现出与女性体育行为相关的社会事实,值得我们提倡。个案研究则是对一个个人、一件事物、一个社会团体或是一个社区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常常需要结合进行。这两者都要求我们能长期沉浸在研究现场和资料里,这对研究者而言是极大的考验,要求我们能忍受住“功利”的诱惑,“沉潜”下去。
3.4 关注女性体育中的“个体”价值的诉求
“民族危亡”集体焦虑的历史境遇,使得近代中国在许多社会现象及社会角色的“定义”及“内涵”大量渗入了家国情怀,如从晚清以来,对女性体育的“动员”与“倡导”总是突出解决国家命运问题的现实价值,这一“事实”有其历史合理性及“强大的主导性”,也使得我们在研究中也形成这样的“宏大叙事”目光:不仅仅是竞技体育中,甚至是健身活动,常常牵涉的是社会价值及意义。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人包括广大女性的“个体意识”不断觉醒,特别是正在成长起来的“80”后和“90”后她们不仅承认和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而且将个人利益、个人价值放到了与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中,“80”后和“90”后甚至正在成为主力,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能对“女性个体价值”的诉求予以关注。笔者相信,一旦我们立论的基点有所改变,就会有更广袤的、更鲜活的研究领域。
4 结语
综上,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女性在体育中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开始女性体育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讲,笔者认为,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尚处于“粗放式”状态,有待“于细微处见真理”。需声明的一点是:人文社科领域“小大之辩”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学者聚讼不已的问题,究竟是致力于勾勒总体性的宏大叙事,还是聚焦微观以深描人文世界的具体情态。研究视域的抉择,关涉学科领域建设进路的选择和学科知识风气的移易,更是研究者个人心境与愿景的折射。笔者所想表达的仅是个人努力的一种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