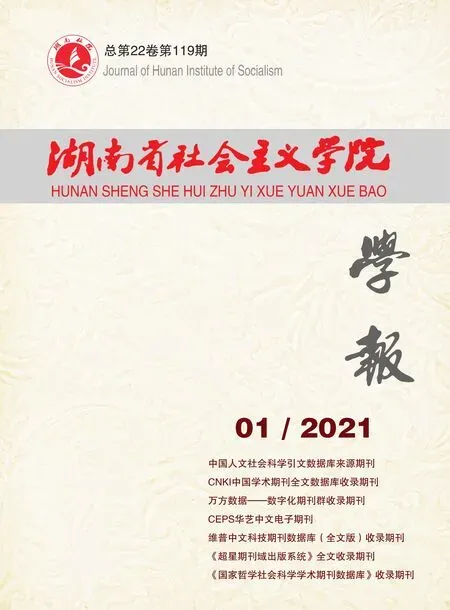瞿秋白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探析
姚满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108)
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瞿秋白就是主要代表之一,他在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中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破除宗法文化的“迷雾”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风云变幻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变革不断加剧,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既体现着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外部诉求,又体现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内在诉求,加之,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并持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撕开了旧文化的裂口,还传播了新思想新观念,从而开启了伟大的思想启蒙。思想的闸门被打开后,外来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并与传统文化形成了争鸣与激荡的局面,所有这些构成了民国初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独特风景线,不言而喻,它也折射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态势。怎样认识、分析乃至批判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正是立足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和时代大势,瞿秋白展开了对作为过时意识形态的旧文化的批判。
在瞿秋白看来,宗法文化是中国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封建势力在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体现,“东方文化派”,或者说“国粹派”,是这一思想文化的鼓吹者和捍卫者。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备受思想界关注,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一方面,西方文化和苏俄文化的传播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所谓“东方文化派”则死守旧文化防线,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西文化交锋论战的局面。在这场论战中,瞿秋白以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积极参与了论战,展开了对宗法文化这一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
瞿秋白认为,宗法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典型表现,在本质上它属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随着满清朝廷被推翻,尤其是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宗法文化已日渐落后时代大势,一些人力图以“国粹”或“国故”之名来固守宗法旧文化,难免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1]。更有甚者,宗法文化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思想堡垒,两者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牢固根基,要彻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要进行实践上的革命,还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摧毁其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上,瞿秋白指出,它们的不同“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2],西方文化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而东方文化却停滞在封建宗法时期,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宗法旧文化重伦理纲常,这些伦理纲常虽然在历史上曾一度起到维护和规范人们行为和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到晚清民国时期它们却成为束缚人的绳索,而“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3]。在对待宗法文化的态度上,瞿秋白主张破除封建宗法思想之迷雾,因为唯有进行彻底批判后,才能让社会思想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奇彩,为东方文化拓展新空间,这就是他所说的“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倒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4]
可见,宗法文化作为一种旧意识形态,其虚幻之处就在于以“正统”之面目掩盖其落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宗法文化的捍卫者不愿意、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对宗法文化的这些消极面,瞿秋白采取了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与批判。
二、揭示资产阶级思潮之“虚假”
在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既包括知识精英宣传的西方思想文化,又包括政治精英所推行的西方政治文化,瞿秋白对这些具有浓厚虚假色彩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针对胡适、张东荪等知识精英所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瞿秋白既肯定西方文化的领先地位、强大的征服力以及科学文明的民主性质,又明确指出了西方文化因重物质层面而导致的百病丛生。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就由原来崇尚的民主主义逐渐转变为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由原来高呼的科学主义日益演变成了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这种转变恰恰根源于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和武力侵略的本性,他坦言,“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5],因此,决不能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唱赞歌。
针对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瞿秋白明确指出,一方面,实验主义看重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方面,其“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为某种行动的‘动机’”[6],可以说,它是一种行动哲学;另一方面,实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偏向于将主体需要和实际利益作为真理的衡量标准,从而忽视理论本身的真实性和确定价值。综观之,“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7],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相距甚远,正因为如此,实验主义便“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决不是革命的哲学”[8]。就当时中国实际而言,更谈不上寄望于这样的思潮来改变中国现状。
针对国民党内部以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反动思想倾向,瞿秋白一针见血地进行了揭露。在瞿秋白看来,戴季陶主义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国民革命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这种思想倾向,瞿秋白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揭示:一是揭示了戴季陶等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歪曲。以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用唯心主义道统论作为哲学基础来阐释三民主义,其意图非常明显,在理论上,希望通过发扬封建道统来建立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在实践上,就是把国民革命变成“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9],从而明目张胆地反对农工民众革命。二是明确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实质,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10],它把民族文化作为最高原则,把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曲解为“人口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的“美化”,不消说,“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11]三是指出了戴季陶等人对俄国革命的误读、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滥用”,这些人将俄国革命的胜利视为民生主义的实现,既明确反对社会革命,又忽视民权主义,把民生主义看成是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的“万能妙药”。四是揭穿了戴季陶主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戴季陶等人借用“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假面具,妄图通过“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撇开广大农工民众的利益,来把国民革命演变为狭隘的国家主义,破坏革命统一战线,排斥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参与和指导,从而把国民党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见,“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12]。
显然,在民国时期,无论是知识精英所宣传、所吹捧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还是政治精英所强调、所奉行的西方政治文化,都是资产阶级利益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但它们却是以“普世的面孔”在社会上“流行”,以致难免有虚伪性,因此,从当时的中国革命现状来说,对这样的思潮进行批判与揭露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批判党内错误思想的“盛行”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右或“左”的错误思想倾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就是当时党内“盛行”的意识形态,这些错误思想倾向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有着直接而现实的消极影响,因而,也成了瞿秋白批判的重要靶子。客观地说,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阶段,加上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导,特别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缺乏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判断,以致在党内几次出现了错误思想主张的“盛行”,先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危害。
就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来看,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党的三大,党的三大虽然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改组它,从而建立国共合作,但大会认为国民党是革命的“中心势力”和“领袖地位”,于是,“多少种下了后来犯右倾错误的种子”[13]。从当时现实局势来看,随着五卅运动的发生以及大革命高潮的出现,国民党内部因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而出现了分裂,其右派分子已公开反共,面对这种复杂局势,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没有进行积极斗争,相反,他们在党内提出了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错误方针,并逐渐演化为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从时局出发,借以对彭述之批评的方式来揭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具言之:一是深刻揭示了彭述之主义的理论实质。瞿秋白认为,彭述之主义就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既是孟什维克(即当时所谓的“孟塞维克”)在中国的化身,又是中国式的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它不能对当时中国革命阵营中各阶级的阶级立场、革命态度以及革命诉求进行科学分析,只是一味大力鼓吹革命领袖权(即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中。二是深入驳斥了彭述之主义的革命措施。在瞿秋白看来,以彭述之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机械而教条地对待革命运动,在革命策略上,机械套用“‘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14],以至于坚持“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15];在革命方略上,秉持孟什维克的独立观,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意识和独立性,缺乏对国民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估计;在组织纪律上,采取命令方式,要求绝对服从,不允许询问、提议和讨论,以致盛行“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16];在宣传教育上,偏好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多宣教少启发,使得宣传工作呆板,难免脱离工人和革命实际。三是明确指出了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机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瞿秋白指出,“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之思想与政策”[17],在表现形式上既有改良主义,又有工团主义,既有无政府主义,又有孟什维克主义,而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最痛苦的结核,当以孟塞维克的染毒为最”[18]。四是敏锐分析了机会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机会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忽视,提倡“二次革命论”,就此,一方面,瞿秋白指出,这“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革命领导权于资产阶级”[19],只有战胜机会主义,才能团结群众,增强党的斗争力,从而避免其带给中国革命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他否定“二次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仍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民权主义革命,它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之模范”,“‘由民权主义革命而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模范”[20]。
就“左”倾错误思想而言,主要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情绪和思想。瞿秋白集中对盲动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阶级属性上,盲动主义乃代表着非阶级化分子的见解,实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形势判断上,盲动主义夸大了反革命阵营中“崩溃”的实际,低估了反动势力的力量,忽视了武装起义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中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21];在行动方法上,盲动主义“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22],从而往往强迫群众进行武装起来,这样就难免把革命变成为恐怖行动,显然,这是瞎乱盲干;在后果影响上,盲动主义由于不顾群众、脱离群众,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依靠少数个人去进攻强大的敌人,最后造成了系列武装起义的失败,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总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一名重要的理论家,瞿秋白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在展开对上个世纪20-30年代流行的各种思想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初步探索和积累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