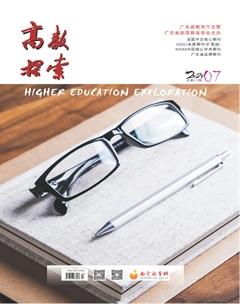志缘交往:民国教育家群体交往的重要样态
摘 要: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存在大量人际交往活动,以共同学术爱好和价值目标为纽带、以社团为依托的志缘交往活动尤为突出。通过数位教育家联合发起、团体联合发起形成创办社团的集体力量,在具有高度参与性、在场性的社团集会中,通过制定规范的会议程序、采用自由灵活的讨论方式以及采取多数决定、集体决策的决策方式,实现教育互动中民主协商与民主表决的统一,使教育家的知识权利得到表达、落实和满足。参与群体性集会,不仅使民国教育家拓展了教育交往网络、积累了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而且在触发教育家教育情感、坚定教育信念、增添生活趣味、迈向社群生活等方面亦有较大影响。他们在群体互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性、独立性,能相对自由表达观点、质疑互辩,进行现代教育知识生产,推动了教育共同体形成。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育家;教育交往;志缘交往
美国社会学家西奥多·M·米尔斯指出:“在人的一生中,个人靠与他人的关系而得以维持,思想因之而稳定,目标方向由此而确定。”[1]“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志为友”,自古以来志同道合在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中亦被视为重要原则。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下,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存在大量人际交往活动[2],以共同学术爱好和价值目标为纽带、以社团为依托的志缘交往活动尤为突出、活跃,他们因共同职志联手发起成立众多教育社团,以此为依托构建复杂的志缘交往网络,对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人生事業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志缘交往有不同于地缘、学缘交往的特殊性,故此专门探讨民国教育家群体的志缘交往问题具有独特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分析民国教育家如何在与同时代教育精英的交往中形成、调整身份认同和个人思想等,另一方面有助于认识民国教育家如何搭建互动平台形成教育共同体以及如何在共同体中与同道互动等。本文拟从日常的、微观的、具体的教育活动入手进行探讨,以展现民国教育家群体志缘交往的历史图景。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在近代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的时代感召下,诸多功能性和专业性的教育社团陆续创建。民国肇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进入近代教育社团创建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式各样的教育社团尤其是民间教育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活跃在民国的教育舞台上。据统计,从1912年至1949年,先后成立教育社团202个,其中官方性质(含半官方)61个,民间性质141个[3],同时亦形成以教育社团为组织依托的教育家志缘交往群体。总体来看,民国时期教育社团的创办主要有两大方式。
(一)数位教育家联合发起
民国时期有相当部分教育社团由数位志趣相投的教育家联合发起而成。这种成立方式也是教育家相互合作、彼此支持的重要表征,它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凭借教育家的社会资本提高社团影响力、关注度,是民国教育家创办教育社团的重要路径。社团创建前后专设有董事会,通常情况下董事会成员从发起人中推举而来,构成社团的核心领导集体,负责社团正常运行。这种由数位教育家联合发起成立社团的方式,在创建过程中优势明显,一方面可使教育社团的创设有充足的社会资源作为支撑,同时通过集体办理增进了教育家之间的交流和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其中,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颇具代表性。
20世纪20年代初为使星散在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有统一性组织,其时对平民教育颇为热心的陶行知、晏阳初、朱其慧与黄炎培、胡适、袁希涛、傅若愚等人商议,并先期与蒋维乔、王伯秋等人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表宣言,募集经费,创办平民教育试验学校,旋即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顺势成立平教会总会,设置总理其事的董事部,选举董事40人,推定执行董事9人,朱其慧、陶行知、陈宝泉、蒋梦麟等人为董事。又,推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平民教育运动有了全国性教育组织,使得平民教育活动得以统筹推进。
同样,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成立前,作为重要发起人的黄炎培就已动用社会资本广泛联络全国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1916年12月黄炎培专门致函蔡元培,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初稿寄之阅示,并请其担任职教社发起人。经过精心酝酿和筹备,1917年5月16日,职教社在教育界、实业界等48位知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宣告成立。其成立离不开教育界宿儒之参与,亦不可或缺实业界、出版界乃至政界著名人士之支持。他们彼此间存在地缘、学缘等复杂人际关系,虽所受教育背景不同,甚至学术思想也有分歧,但对职业教育的共同情结、期盼和希冀使他们聚集在一起。[4]在这批精英的支持下,该社自创立后,“以倡导职业教育为职志”[5],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大量职业教育实践和研究活动。除此之外,民国教育社团如实际教育调查社、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社会教育社、国难教育社、生活教育社等,皆是由教育家联合发起成立并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二)多个团体联合发起
这种方式类似于团体结盟,既有从事相同工作的组织团体为便于沟通经验、展开合作联手而形的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教育团体,又有功能不同的教育社团为了相同的教育目标改组统合而成的教育团体。如1933年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同乡村建设团体和力量为了加强联络与协作发起成立乡村建设协进会,其筹备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渊源最早追溯至1926年5月15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东南大学农科及教育科联合发起成立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6]此后,该董事会多次开会,最终选取沪宁线上交通便利的昆山县徐公桥为第一试验区,后因时局和经费问题,合作单位相继退出,中华职业教育社独自承担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的各项工作。[7]
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乡村教育的推进,各地陆续成立乡村改造团体,这些团体组建统一联络机关以交流乡村建设经验。基于此,1932年12月,王怡柯、梁漱溟、晏阳初、高阳、李景汉、梁耀祖等乡村工作领袖,在参加国民政府内政工作会议期间,专门在中央饭店召开小组会交流意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常规性的会议或组织以使各地从事乡村工作的同志互通声气、“亲切联络”。[8]他们深知创建有效力的组织团体之不易,若单方面发起极有可能招致流产。为慎重起见,晏阳初、梁漱溟、王怡柯等人立即赶赴北平,专程拜晤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章元善、燕京大学教授杨开道、许仕廉等人,盛情邀请他们作为发起人支持乡村建设协进会的创建,并共同协商筹备事宜。章、杨、许皆为对乡村建设素有研究的知名人物,如章元善为知名的慈善家、热心乡建,与晏阳初是旧相识,此前晏曾盛情邀请章赴邹平讲学 。[9]
联系到诸多同道后,最后商定由梁漱溟、梁耀祖、王怡柯、李景汉、晏阳初、高阳、章元善、许仕廉、张鸿鈞、杨开道、严慎修等11人联名发起成立“乡村建设协进会”(后改名为“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确定第一次集会日期。[10]1933年7月14日,乡村建设协进会第一次集会在山东邹平如期举行,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仕廉等6人为主席团成员,标志着以乡村建设为己任的全国性教育团体正式成立。后又于1934年、1935年分别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影响颇大,并在第二次会议中专门成立乡村建设学会,精心筹备和主持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些发起人之间此前彼此熟识,多有互动。[11]正是在这些以教育家为主持者的团体不懈努力下,抛开具体学术观点之歧见,聚合成有稳定联络机制的协同组织。
此外,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国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等教育团体皆是通过团体发起或重组的方式而成立。多个社团联合发起之最大优点,实乃一经成立便能召集分团体会员加入,较短时间内聚合庞大的人员队伍,组织实力大幅扩充,其缺点亦较为明显,分团体皆有各自工作重心,久之内部不同势力间利益恐难协调,往往易招致团体之分裂。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集会把处于不同地域之人召集一处共同探讨相关问题,是进行集体性思想交流和生成实践性措施的基本方式。与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网络便可远程视频通话召开会议的现代社会不同,民国时期受通讯技术之局限,教育家群体间的多方互动主要依靠有身体在场、有身体参与的社团年会方式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总结教育经验,阐发教育观点,咨询质疑,进而群策群力地推动教育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教育事务的推进。
(一)制定会议规程以使互动规范化
规程既是教育社团提升自身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亦是顺利举办会议的基本保障。反之,若无特定的规程,会议秩序则难以保障,更有甚者会导致集会的杂乱或骚动。由于教育社团举办年会时参会人数较多,故制定规范性的会议规程往往成为民国时期规模较大教育社团的必然选择。
中华教育改进社自1921年12月改组成立后,不仅制定《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又旋复推定胡适、陈宝泉、陶行知起草《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规程》。该规程内容详备:第一,把年会的事务划分为议事部和执行部,分别管理相应事务。议事部由主任干事推请五至七位委员组成,是年会各种重要事务的议决部门;把执行部分为总务组、注册组、议案组、编辑组、招待组、交通组、交际组、卫生组、询问组等九个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年会不同事务,而且明确规定了每组成员数量及推选方式。第二,根据会议性质不同,把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分组会议两类,全体会议有社务会议和学术会议;分组会议类别更多,多达三十个,有教育行政组、高等教育组、中等教育组、初等教育组、幼稚教育组、义务教育组、师范教育组、职业教育组等,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形态,可谓面面俱到。第三,对会议议案提交方式,讨论、审查、表决程序,记录办法等作出具体要求。提议案要求尤为严格,会议动议必须经过足够数量人员附议方能被讨论且须提交议案组存查。[12]可以说,制定规程成为教育社团规范化的必备程序。除中华教育改进社外,另一规模庞大的全国性民间教育社团——中华职业教育社制定类似会议规程,如议事员会议细则、办事部会议细则等。
统观中华教育改进社对年会的制度设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会议细则,对各环节皆有周详规定和部署,彰显出正式会议对参会人员彼此间规范互动较高的制度性要求。这些规程大都经讨论通过后对外正式公布,进而制度化、合法化,成为群体互动的重要遵循。
(二)因事制宜彰显互动灵活化
尽管规程对会议的筹备、讨论、表决、记录、发言时限等诸项都有明确规定,对于某些重要问题有些教育家有深入研究,针对小组讨论、大会演讲中因时间限制却未能尽意的情况,大会通常在开幕、闭幕式中专门留足时间请名家作长篇论述。
譬如,1935年在江苏无锡举行的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中,为满足教育家充分阐述观点之需求,特意增加主题演讲环节。开幕、闭幕式上晏阳初、梁漱溟分别作了《农民运动与民族自救》、《如何使中国人有团体组织》的长时讲演,对相关问题充分发表看法。晏阳初充满感慨地分析了外敌入侵中国犹入无人之境的原因以及乡村建设对于组织和训练民众以实现民族自救的伟大意义和实施途径,而梁漱溟通过分析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认为中国人最大弊端在于散漫,散漫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后天生活的社会环境所致,一气呵成地对如何培养中国人的团体意识开出药方。[13]二人的长篇演讲亦成为乡村建设经典文献。
乡村工作讨论会还灵活采取书面报告与口头讨论相结合的讨论形式。由于会议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投寄报告颇为活跃,第三次会议收到报告足有三十余份。若仍依前次会议逐一报告,无疑将拉长会期。故,会议决定采用书面报告与口头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把各团体书面试验报告先期分发,留下更多讨论时间。同时,预留特定时间,专设个别谈话,代表若想深入了解定县、邹平、无锡乡村建设情况,可单独面询晏阳初、梁漱溟、高阳解惑答疑。[14]
同样地,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中亦会针对不同情况灵活采用会议讨论方式。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通常采取“全体会议”形式,先由大会推定的主席致辞,继而由各部门负责人报告社务,然后开始讨论职业教育发展并决议提案,在前六次年会中基本上采取该方式,使社员直接知晓全部社务、参与所有提案,此为其优势。但亦有缺憾,即难以对有关问题进行针对性、专门性分析。故,从第七次年会起,便增设分组会议,对某些专题深入讨论。[15]这种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宜措施,彰显教育家在群体性互动中对交流方式的高度关注,通过不断完善会议机制,以使会议取得更大实效、增进深度交流。
(三)自由发言以保证讨论民主化
议案是民国时期教育社团年会的核心工作之一,對如何讨论议案也规定得颇为细致,参会者皆有就议案发表观点之权利。自由发言的互动方式,参会者被赋予较多平等参与的权利,不仅有助于保障教育家集体互动中的基本权利,大大提高议案讨论质量,而且它所采用的议案先行公开制度、价值无涉的会议主持人制度、时间有限的自由讨论制度,对推进规范民主的会议讨论制度形成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当然,尽管会议中激烈的争辩、观点的对立、双方的交锋时有发生,时间有限的讨论也并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皆能达成共识,有时候问题需要多次讨论才能有一致的看法,但至少教育家在某些教育问题上有发出声音的权利,阐述各自观点和理由,缩小分歧,或达成彼此理解,这本身就有利于内部和谐。
《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规程》规定:“欲发言者,须先起立报告号数,得主席承认后,始得发言。”为使发言人顺畅表达观点,其他人不得同时发言,并且发言每人每次不得超过五分钟,内容也要和议题相关,不得涉及议题以外的事。除质疑答问外,同一议题发言人不能超过两次发言。又把讨论分为“初读”、“二读”、“三读”三个层次。“初读”主要讨论大概,以决定该案是否可以成立,“二读”逐条讨论并表决,“三读”仅修正文字,议案已基本成立。除对与会人员讨论方式规定外,还对会议主席职权进行规定。主席若自行参加讨论时,需在议席区发言,主持工作由副主席代行以确保讨论公平。[16]制度层面如此设计,有利于参会人员以平等身份参与议案讨论,最大限度排除地位、身份、性格等外在因素之影响。
由于每位人员在讨论中都有自由表达议案看法之权利,故在会议期间经常出现热烈讨论之场面,甚至产生激烈论争。如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中,王伯秋在高等教育组所提临时议案《改良省立法政教育案》即引起激烈论争。[17]不管该案后续在教育界惊起的反响结局如何,但至少可以表明在小组讨论中双方皆有发表内心真实想法的权利,至于通过与否则取决于表决程序。这种自由发言、热烈讨论的场面,在民国时期教育社团年会中比比皆是。[18]
(四)公开表决促进决策民主化
民国时期诸多教育社团具有代议性质,通过的议案可直接呈送教育部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在此情形下,大会中提议案经与会人员充分讨论后,表决就成为重要事项。这也是民国时期教育家参与社团管理、行使社团权利的重要体现。如中华教育改进社颇为重视议案审议,视之为全体社员之公事,而非某个社团领导之私事,故除重视议案充分讨论与否外,对议案裁决方式也颇为注重。该社明确把表决程序写入年会规程,并对表决方式、决议方式等进行详细规定,如下:
第二十九条 表决前,主席须将应付表决之议案明白宣布,即行表决。表决后,会员不得再就本议案发言。
第三十条 表决方法分举手、起立两组,由主席临时定之。
第三十一条 表决议案取决于多数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主席。
第三十二条 分组会议之议决案提出大会报告后,即认为大会议决案。其已经该组多数通过之议决案,而该组少数会员要求将少数之主张一并提出大会者,则该案应经大会表决手续。[19]
中华教育改进社采取的公开表决方式,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多数人同意后议案方可通过。若会员另有主张则可再次就增加内容进行表决,既照顾到大多数,又充分考虑了少数人之意见。这种通过表决的方式和程序使教育家的主张得以实现的设计,体现出群体性教育决策中较高的民主性,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
从社会学上讲,作为统一的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驾驭着各种信念和利益的对抗,看似简单的表决在把个人的争端纳入一种最终统一的结果的手段中,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手段之一。[20]当然,这种表决基于协商和讨论,参与表决的当事人在此之前有平等表达、自由陈述个人主张之机会,相关少数主张也可以一并提出继而经大会表决。它所采用的公开表决方式相比于无记名投票看似有悖民主,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现代民主的一种基本要求,尤其是用于议事人员从所代表群体或组织出发表达意见。实因民国时期不少教育社团实行省区及院校代表制,每个表决者所代表的不仅是其个人态度,而且还代表了背后推选者之态度,也就是说他代表着一个群体,需向背后推选人负责。所代表的学校、群体利益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表决行为。如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废止法专门学校案中,专门学校的参会代表提出明确反对意见。当然,会议中产生论争也并非全部源于利益不同,有时则是因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不同。[21]
民国教育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实,致使教育家必须协调各方利害,方能为顺利开展活动铺平道路,彼此间也才能相互扶持、友爱关怀,协商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协商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也不是一方依附另一方,而是代表们充分表达各自意愿,意味着意见的权衡与协调,最终最大限度地达成理解与合作。与此同时,民主协商程序的有效运作,是以不断扩大和制度化与会者的参与为基本动力,交往双方在互动中有着高度的主体间性。总言之,教育家群体在以社团年会为依托的志缘交往中,通过制定规范的会议程序、采用自由灵活的讨论方式以及采取多数决定、集体决策的决策方式,实现了民主协商与民主表决二者的统一,使教育家的诉求得到集中、落实和满足。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通过召开大型集会,对近代教育社团而言,诸多重要决议由此议定,社团的教育推进工作也由此来部署和动员,而从实践的主体——人的角度来说,这些集会无疑对加强社团负责人之间、负责人与普通会员之间、普通社员与普通社员之间的联络、协作,以及对他们探讨教育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合作等有着重要促进作用。①从社会互动层面来讲,集会是以身体的在场进入交往场域,是包括教育家在内的参与者进行生命体验、书写各自教育历史的重要方式。
(一)触发教育家的教育情感,坚定教育家的教育信念
参加社团会议,除与教育同道进行常规性学术交流外,民国教育家还常利用开会之机,考察教育、拜会友人、游览参观了解当地教育状况、风土人情等,产生的感触委实不少。1933年7月,对黄炎培来说一如既往忙碌,他参加了两场大型社团年会,一为职教社开封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另为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山东邹平召开的第一次讨论会。会议期间,黄炎培活动繁多,包括人际交游、教育考察、会议讨论、外出参观等诸项,尤其是参加邹平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经历,不仅使他对邹平风物有了更加切身的认知,而且通过与乡建同道的直接接触,对乡建同道身上体现的执着信念大为佩服,一连写就四首诗作以寄别这些“知交”。离开邹平次日,当闻及与江问渔、李石曾、许仕廉、晏阳初、章元善、梁漱溟等6人同被推举为乡村建设协进会主席后,又集诸人姓字赋诗一首,抒发其志:
晏起初阳早上台,荒江漱石许徘徊;
渔樵生事廉能乐,李杜文章善起衰。
任重岂愁溟渤远,扶元曾仗栋梁才;
之秦之楚非求仕,欲问黄农话劫灰。[22]
黄炎培对家国前途、乡建前途的殷殷关切以及对教育同道帮助的感佩之情跃然纸上,不求做官、只为做事、一心为百姓疾苦奔走的教育信念和人生信念更加坚定。
(二)为教育家生活增添趣味,丰富个体人生体验
民国教育社团的大型集会除学术活动外,亦会增加诸多生活性活动以丰富集会内容,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教育世界延伸至生活世界,进而实现彼此间的深度了解和营造友爱氛围,主要有交际会和参观游览等。1922年7月3—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召开年会期间,组织了两场交际会,主要节目有歌曲表演、舞蹈、京调、游戏等,到者八百余人,晚上十一点方散会,足足进行四个小时,第二场观看人数同样众多[23];另外,为便于参会人员游览山东名胜,体验山东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专门编订游览指南,人手一册,且对济南的地图标注得颇为详尽,以方便参会者会议期间的日常生活[24]。8日下午会议结束后,由陈鹤琴和赵叔愚负责招待,相约游泰山。[25]与此类似,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社团,年会期间同样经常组织交谊会、游览活动。如职教社开封年会期间,组织社员游览龙庭、繁塔、禹王台等开封名胜古迹。[26]这些富有生活性和娱乐性的参观游览、交谊活动,为紧张的学术会议增添趣味,也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拓展了教育家的教育交往空间,使交往回到生活世界。[27]蔡元培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年会告别词中就曾动情地说:“我们这一回开会,赞助我们的不但社员,山东的教育界没有一位不是我们的同志,或者把会所、校舍借给我们开会与寄宿,或招待我们去参观,或到我们会中来旁听,真没有一位不是本社可以互相提携的同志,我们很感谢山东教育界诸位。”[28]
(三)开拓教育家人生新境界,促进教育理想追求之实现
群体性集会亦是教育家甚至是包括每一位普通社员在内参会者发挥聪明才智、贡献教育智慧的绝佳平台,思想在与他人互动中逐渐稳定,目标方向也由此而确立。有的教育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成长,无不得益于在与他人互动中不断生成各种教育经验和符号,不断进行自身的社会化、教育思想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群体性互动中,他们既善于团结和发挥集体力量,同时又务求做到彼此间的相互独立,在独立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达到共同发展。在陶行知的人生成长和教育生涯中,团体有着相当重要影响,学生时代“依靠团体献力于公益的尝试,不仅锻炼了陶行知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而且也培养了他运筹团体力量的技能和服务社会公益的精神”,归国从教后又积极参加诸多文化教育团体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生活教育社等,他于自己所参加的这些团体,“均能依据中国教育革新事业的时代要求或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坚持借团体之力以服务社会为原则,尽职于其中的各项事业”[29],也由此使自己的教育事业大放光芒,不断开拓人生新境界。可以说,凭借团体力量,加之自身出类拔萃,富有创造力、行动力,从平民性格深处所体现出来的乐于、善于、勤于与他人交往的真诚品质也是其与同时代教育家进行良性、持久、有效互动的基础。正是以“交换意见、消灭冲突、协同一致、奋发扬励、收得良效”的交往路径为基本遵循[30],在集体中与他人进行交往互动,同时也鼓励依此方法來与他人合作,以促进团体内部的整体和谐,进而达成共同目标之实现。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陈鹤琴、胡适等民国教育家无不善于聚同道于周围,无不善于与他人交往合作,凭借和发挥团体力量以服务社会为原则,尽职于其中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使各自人生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四)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共同体形成
基于社团的群体性交往,使得民国教育精英走出狭小的个人空间,由单一的个体联合成具有共同教育目标、一致教育信仰的共同体,迈向更加开阔的群体生活。这种由成员“本质意志的结合”、通过“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的联合体不同于一般教育者群体,其行为动力主要来自信仰的召唤而非制度的规约。[31]第一,无论是数位教育家联合发起还是团体联合发起,无一不是事先沟通、精心筹备然后努力促成之结果。前期彼此间的熟稔程度、交往关系的深入程度以及教育志趣的相似程度是创建教育学术组织团体的必要前提,无任何交集或任何人际联系的教育家难以真正结合成联盟。正因教育家间有着友好的人际关系,并通过沟通、协商、联合等手段促成了团体之创立。第二,社团创建前后,常推选专人共同草拟相关章程以使社团合法化。如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前,既已由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三方公推陶行知、陈宝泉、李建勋、马叙伦、朱经农共同起草社章,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对外发布。第三,社群生活反过来又促进教育家的人际互动。社团为教育家提供了交往互动的重要平台,他们此前或许并无直接联系,但通过“桥”而聚集,缔结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虽有强有弱,或长或短,但使得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实现教育理想携手共赴时艰。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2]民国教育家也只有在教育共同体中过社群生活才可能有个人的学术自由,在相互的合作与交流的关系中获得一定的权利以及相互之间的认可,形成真正的教师权威和知识权威。[33]此外,民国教育社团年会中所通过的议案虽然没有政府层面的法律效力,但对社团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是社团活动的行动指南,“可以看见的重要结晶体”,“现代中国教育界思潮信仰的缩影”,为后续活动注入持久的原动力。[34]
综上所述,基于共同志趣而形成的群体性交往,是民国教育家在近代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使自身融入群体、在联合体中与他人交往互动并把自身的影响扩散到其他人员以及教育团体之外的实践活动,不断拓展人际交往网络获得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这种以共同教育诉求为核心的教育家联合体的形成,既离不开教育家们的积极参与和亲密互动,更离不开在此过程中与同道教育情感上的共鸣和教育成绩上的彼此认同。他们在群体互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性、独立性,能相对自由表达观点、质疑互辩,在公共空间内表达知识权利进行现代教育知识生产,推动了教育共同体之形成,集会中常常伴随教育旅行、教育考察、友人拜会等活动,对触发教育家教育情感、坚定教育信念、增添生活趣味、开拓人生新境界等皆有裨益。在当前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学人互动愈趋深入的背景下,教育学人尤应继续加强彼此间基于共同教育志趣的交流对话和包容互鉴,兼收并蓄、共同进步,汇聚集体智慧携手应对教育大变革时代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提质发展。
注释:
①对于民国教育社团集会内容及其中国近代教育之影响,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代表性成果如于潇的《社会变革中的教育应对:民国时期全国教育会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孙广勇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但不难发现,作为活动主体的教育家在教育互动中受到的影响及情感体验还罕有人视为重要问题专门论述。
参考文献:
[1]西奥多·M·米尔斯.小群体社会学[M].温凤龙,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3.
[2]郭景川,申国昌.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史:类型、特征及走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8-75.
[3]金順明.近代中国教育团体的发展历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1):60-70.
[4]谢长法.教育家黄炎培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59-60.
[5]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J].再生,1945(104):25.
[6]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成立[N].申报,1926-05-17(7).
[7]朱考金,姚兆余.“富教合一”: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初探[J].中国农史,2007:125-131.
[8]晏阳初.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R]//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329-335.
[9]晏阳初.致章元善、陈致潜[Z]//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4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185.
[10]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4:1-6.
[11]曹天忠.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J].学术研究,2006(3):96-102.
[12][16][19][30][34]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75,376,377-378,380-384,265-266.
[13][14][18]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7:21-62,19,28-48.
[15]陈梦越,楼世洲.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研究(1917-1937)[J].职教论坛,2016(16):89-96.
[17][21]分组会议记录[J].新教育,1922(3):395-396,390-391.
[20]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35.
[22]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4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197.
[23]交际组报告[J].新教育,1922(3):700.
[24年会筹备情形[J].新教育,1922(3):683-684.
[25]赵永青,许文彦.殊光自显不须催:徐养秋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7-118.
[26]会务一览表[J].教育与职业,1933(147):520.
[27]申国昌,吴艳君.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教育交往史研究的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19(4):1-6.
[28]蔡元培.告别词[J].新教育,1922(3):731.
[29]余子侠.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33-137.
[3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
[3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33]卢盈.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式微与公共空间的建构[J].高教探索,2016(8):100-104.
(责任编辑 刘第红)
收稿日期:2020-10-21
作者简介:郭景川,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教育学博士。(新乡/45300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教育家群体的教育互动与日常交往研究(1901-1949)”(项目编号20YJC880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项目编号BOA20005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