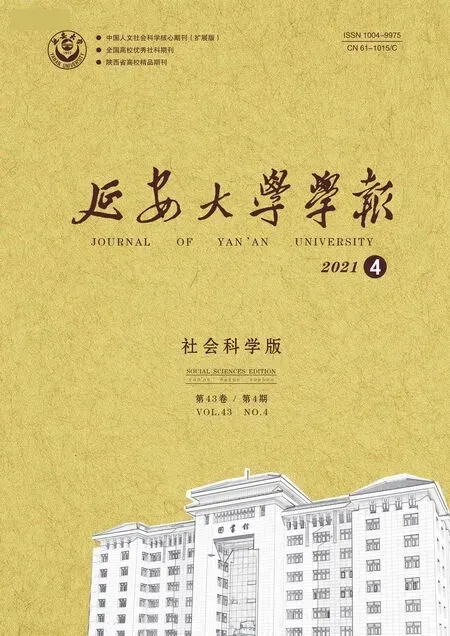基于文化视角的日语语感探究
王 钦
(1.延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日本东亚大学 综合学术研究科,山口 下关 751-8503)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日语的语言表达,非常尊重听者的感受,讲究使对方感觉舒畅的语言效果,其中语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任何语言都具有语感,但日本民族素以谨小慎微、感情细腻而著称,日语的语感问题也由于感性成分居多而呈现出较为复杂微妙的特点。因此,中日有关日语语感的先行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语感的理论与分类、日语拟声·拟态词的语感、日语学习中的语感培养等方面。尤其“在日本,词汇层级的语感研究始终是绝对的主流”,[1]而对影响日语语感的文化心理因素较少论及。
一、语感是日语的重要标识
(一)日语语感的概念
语感作为词汇的一种附加表达,在某个语言集体里是共有的。在日本,语感指对词汇的感觉。“日语的词汇除了有词义之外,还能给人某种感觉,以唤起某种感情的情绪意义,可把此类意义视为语感。”[2]74其在日语辞典里面的定义诸如:“词语给予人们的感觉。词语所具有的调子·声音。”[3]“由语言感受到的微妙的感觉。词语的细微的差别。”[4]“词语在其主要内容之外所表现出来的细微感情。”[5]“每个词语,除了有自身固定的中心含义外,还有着语言、颜色、声音、调子和感情等周边感情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把这些统称为语感。”[6]根据以上解释,日语中语感的所有定义,基本都是围绕“词”来进行,即用语言向对方传达某些信息时,对方在听取信息的同时从词语那里获得的某种印象、感觉或情绪色彩。
(二)日语语感的特征
1.日语语感的评价性
“语感本身是一种对语言和声音的感受,而人的言语语音并不一定都是价值中立的。像日语中的清音、浊音这些说法本身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日语的语感则存在于这种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7]我们在表达某件事情或描述某种事物时,怎样看待这个指示对象、如何进行词汇选择和价值判断,带给听者的主观印象也会千差万别。由于说话者自身的内在把握会导致不同的表达效果,对于原本作为外部客观存在的指示对象而言,说话者对于词汇的选择责任就体现在其对于指示对象的评价之上。中村明认为:“在现代日语当中,意义相近而语感不同的类义词群体广大。”[8]如评价某人用“真面目(认真)”,无疑是正面的语感,给人的印象很好。而形容此人如果用“くそ真面目(一根筋)”或“ばか真面目(死认真)”的话,对指示对象的评价则明显降低。再如,当形容词“長い(长的)”加后缀变为“長たらしい(冗长的、啰嗦的)”时,传达出的语感也会从中性变为负面评价。由于一个词语加上接头词或接尾词而导致的价值下降在日语中非常普遍,听者立刻能够判断出其属于负面、不好的语感。因此,如何看待和解释指示对象、如何根据日语语感的评价性去选择用词,在用日语进行交际时需要格外注意。
2.日语语感的情意性
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指出:“语感最朴素的阶段就是给予听者‘愉快’与‘不快’的感觉。我们在语言交际中会运用许多浸染上情绪色彩的词语来表达语感的色调,并对其进行自由地调色。”[9]语言给予听者的心理感受,到底是“愉快”还是“不快”,是“悦耳”还是“刺耳”,取决于它们各自所依附的文化价值观念。除了最能表达情绪色彩的形容词以外,日本人认为日语中不同的词种在语感上也具有差异性。“和语词(日本固有词)具有卑俗感,汉字词郑重、优雅,而外来语给人一种时髦、高级的语感。”[2]75例如:“田舎(农村)”这个和语词,他们认为有种“田舎者(乡巴佬)”或“田舎臭い(土气)”之类的粗俗感觉。如果用“地方”这类汉字词来代替,如:“東北地方”“地方自治”就会给人的印象比较文雅、中性。而如果用“ローカル”这样的外来词,如“ローカルカラー(乡土情调)”,会烘托出富有地方特色、个性时尚的氛围。此外,日本民族细腻的感受性和对“音”的敏感性还体现在日语中大量存在的拟声·拟态词上面,这些词在语音、语感上的微妙差异,构成了日语在情感表达方面的独特性。其中最明显的是清浊音这种“音形态”上的对比,日本人认为会带给听者不同的心理感受。如说到“さらさら”,就会联想到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或小河潺潺的流水声,而“ざらざら”的发音听起来就会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如“ざらざらの壁(不光滑的墙壁)”。他们普遍认为清音的语感好,给人以干净、好听、愉快的心理感受;而浊音的语感差,听起来肮脏、刺耳、不愉快。这样的例子在日语中不胜枚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日语语感的情意性特征。
3.日语语感的民族性
语感因语言而不同,因民族而相异,日语的语感折射出日本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格。日本的语言学家,根据国民心理,将日语词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他们认为“语感好”的词汇(以下简称A类),一类是“语感差”的词汇(以下简称B类)(1)参见新世界教育在《谈谈日语的语感》一文中对日语词汇的语感分类和举例。新浪网,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77eefa1d0100r3ve.html.2011年4月6日。。比如日本人喜欢恬静、闲寂、幽玄的意境,故将“侘び、寂び”作为A类词汇,这也是日本中世以后形成的一种代表性的审美观。而将“騒々しい(喧嚣)”作为B类词汇。此外,日本人喜欢沉默是金、以心传心的交流方式,把隐忍持重、寡言少语作为一种做人的美德。所以把“黙々(沉默的)”作为A类词汇,“おしゃべり(爱说话的)”作为B类词汇。日本的一家语言机构在通过长期调查后发现,一般日本人在听到A类词汇时,心理感受愉悦,听到B类词汇时,心理感受差一些。因此该机构建议,在报道或演讲时,应当优先考虑使用A类词汇,以使受众获得良好的印象和心理感受。例如在报道一场棒球比赛时,两队实力悬殊,甲队优势明显。尽管如此,乙队还是坚持比赛到最后。第二天新闻的标题是《黙々と最後まで投げた(默默地打完比赛)》。由于使用了“黙々”这个A类词汇,将乙方队员默默坚持投出最后一球的顽强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传达给读者正面的语感,乙队虽败犹荣,仍然得到大家的尊敬。由此可见,日语的语感依托于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和文化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二、日语语感的文化特质
(一)以心传心的文化心理
“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其语言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词汇是语言必不可少的要素,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日语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日本文化要素,体现了浓郁的民族色彩。作为词汇附加意义的语感,它传达出的信息,往往比其概念意义更加广泛而深远。”[10]如前所述,“沉默”是日本民族推崇的一种个性,所谓“言わぬが花(寡言为美)”。这种价值观体现在语言表达上,即所有与“沉默”相关的词语都被认为具有正面、好的语感,而“多言”类的词语则代表负面、不好的语感。例如:
A类词汇:沈黙、黙々と、黙然と、無口、粛々と、寡黙
B类词汇:おしゃべり、ぺらぺら、ぺちゃくちゃ、長広舌
究其原因,是因为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由始祖神统一的国家。皇恩浩荡,神明早已洞察一切,用不着庶民自己多嘴多舌,对任何事都应保持沉默。”[11]他们一直以来把“以心传心”看作人际交往的最高准则。“以心传心”本是佛教用语,是禅师离开语言文字而以慧心相传授的一种方法,注重的是心有灵犀。日本人很崇尚这种交际方式,因此日本文化也被称为“体察”文化。它讲究的是交际双方内心的默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往往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足以揣测对方或表达自己。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勘がいい、勘が働く、気が利く、察しがいい、飲み込みがいい”这类表示悟性高、有洞察力的惯用语被日本人划分为A类词汇,具有正面语感。与此相反,“気が利かない、察しが悪い、飲み込みが悪い、空気が読めない”等属于B类,意为不懂察言观色。日语的流行语“空気が読めない”,缩写为“KY”,在日本是对别人非常严重恶劣的评价。直译为读不懂空气,是没有眼色、情商不够的意思,负面语感很强。封闭的岛国属性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日本在民族成分、语言构成等各个方面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形成了独具其自身特色的“以心传心”的交流方式。
(二)以和为贵的处世观念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以和为贵”作为处世信念。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之后,中国儒学中“以和为贵”的处世风格也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国民性格。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日本人大体都贯彻了“和”的处世精神。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特质,主要表现在对“和”的追求上。早在日本飞鸟时期,圣德太子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提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睦,不要斗争。此后,“他们把儒学、佛教思想融入日本的本土神道信仰之中,并作为日本文化的主要基础,一直影响到近现代日本的教育、人文思想以及当代日本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2]
在语言交际行为中,日本人多采用模糊、省略等较为含蓄暧昧、模棱两可的委婉型表达方式。如只用一个终助词“が”就足以传达出婉拒的语感,“が”的后半句往往省略,给人一种言不说尽、给对方留有余地的听觉感受。还有“はい(是)”这种随声附和的行为也并不一定表示赞同对方的意思,它传达出的语感可能只是一种倾听。这些在外国人看来颇为高难度的语言交际行为和心理特征,其实是日本人为了追求和睦的人际关系、增添和谐气氛所特有的,是基于“和文化”而产生的一种自发性的合作意识。追溯至日本的弥生时代,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日本社会特别强调集体协作精神和团体意识。为了适应水稻耕作的需要,在自然灾害中保证收成,内部必须团结一致,从而形成了村落共同体以及“家”“村”制度。“村”内的集体行动要求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服从者会受到“村八分”(2)村八分指日本古代村俗,是对不守村内规矩者的制裁。意为除了婚礼与丧礼此“二分”外,村里的其他活动都不让其参与。在从前的封闭社会,绝交和放逐等于宣布一个人的死亡。的处罚,全村人都会与其断绝来往。
在此文化背景下,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为薄弱,而“角が立たない(磨去棱角)”“合わせの心理(从众心理)”“世間体の意識(体面意识)”则很强。与日本人交流时很少能听到“我”这样的第一人称代词,因为他们把凸显自我的惯用语都划分为负面语感,如:“我を張る(固执己见)、我を通す(一意孤行)、我が強い(很自我)”等。甚至连“我爱你”在日语中也是不出现“我”和“你”,只用一个动词的“愛している(爱)”来表达。这类省略主语的现象在日语中很常见,只有压抑“自我”,迎合“大众”,才能获得良好的口碑和社会评价,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受此价值观的影响,“察し(察言观色)、思いやり(体谅)、推し量る(推测)、勘ぐる(揣摩)、遠慮(客气)”这类表示体察、关怀他人的词汇自然受到日本国民的喜爱,具有了正面语感。
(三)敬畏语言的言霊信仰
禁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语言交际中,有一些词语的使用会招致他人的不快和反感,这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禁忌语。日语中的“禁忌语”一般叫“忌み言葉”,日本《大辞林》对其定义为:“因为信仰上的原因,或者特定的职业和场合中,因容易使人联想到不吉利的事情而被人们所忌讳、并需要尽量避免使用的语言及其代用词。”[13]“禁忌语本是古代人们的迷信说法,不同的国家、地域和文化所产生的禁忌语是不同的。因为宗教信仰、民俗生活以及教育领域等不同影响,禁忌语也随之不断地完善,至今,禁忌语已成为一种语言上的文化遗产”,[14]不仅是重要的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表象。
禁忌语存在于日本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面非常广。在日常会话中,尤其是社交场合,人们为了趋吉必凶、扬长避短而不能、不敢或不愿说出某些词语。这些词语或危险、或神秘乃至神圣、或不堪入耳,通常只能用别的词语或委婉性的表达来代替,尤其是跟死亡、疾病、痛苦相关的带有消极联想的词语。由于具有引起人们不好的、不愉快的联想色彩成分,所以从语感上来说,禁忌语明显属于负面语感。如“潮(しお)”的发音会使人联想到“死のう(死的意志形)”,所以说到浪潮就用“波の花”来代替。日本人的数字禁忌也反映了这一点。他们很忌讳“4”这个数字,就是因为其发音和“死(し)”完全一致。“9”也是如此,日本人虽然喜欢奇数,但因“9”的发音与“苦(く)”一样。“4”和“9”的结合则更为不妙,“四苦八苦(しくはっく)”意为千辛万苦,受尽苦头。在日本,任何场合下大家都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数字。日语中有大量关于“死”的代替语,如“あの世に行く(到另一个世界)、帰らぬ旅(不归的旅途)、成仏(成佛)、長眠(长眠)、往生(往生极乐)”等等。此外,一些特定场合如看望病人、参加宴会、结婚仪式等都有各自不同的禁忌语。究其根源,这些禁忌语的产生主要来源于日本自古以来的“言霊”信仰。
日本民族相信万物皆有灵,“言霊”是指寄宿在语言中的神灵。古代的日本人认为语言是有灵魂的,对语言有着极其原始的敬畏感。他们相信“大和语”是拥有一种被神灵加持过的、神秘力量的语言,并由此传承下来一种言霊思想,后来发展成了言霊信仰。[15]被称为日本诗经的《万叶集》当中有一位名叫柿本人麻吕的和歌诗人曾说过:“日本是由一种不可思议的语言力量所加持的幸福之国。”言霊信仰早已潜移默化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深处,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力行着言霊之力。日本人骨子里认为日语里存在着其他语言所没有的“神灵”,会左右人们的幸福。吉利的话语会带来幸福,禁忌的词语则会招致不幸。语言的这种魔力在日本的一些艺术作品里甚至被塑造成发动咒语的力量让人生畏,这也是日本人用词谨慎和重视语感的另一大原因。
三、日语语感文化对交际的影响
(一)读懂语言背后的情绪意图
综上所述,日语语感的文化特质不容忽视。因为我们在语言交际中,传达的不仅仅是语义,还包含着说话者的各种情绪意图。“每一个具有相对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民族,都在按照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来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并由此构成了其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主要形式。”[16]共同的语言意识和行为是维系一个民族的主要纽带,尤其是日语,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民族,日本民族的个性、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习惯,以及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图式等都是影响日语语言交际的潜在因素。因此,在日语交际中读懂语感的文化特质,即读懂了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各种情绪意图和言外之意。
基于“和”“以心传心”“言灵信仰”等文化意识的影响,日本人在社交生活中尽量避免与人发生言语冲突,强烈地希望维持一种和睦、愉悦的人际关系。所以往往通过省略、模糊、附和、推测、共话、多意等较为委婉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传达出说话者的感激、尊重、请求、婉拒、体谅、抱歉等语感。只有理解这些语感所蕴含的各种不同的情绪意图,领会语言背后的弦外之音,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用语习惯和交际规则,顺应其语言交际心理。
(二)注重交际中的文化语境
在日本式人际交往中,为了避免引起他人的不快与反感,使人际关系更为和谐,从而达到一种心意相通的交流目的,一定要注意恰当的词汇选择和语感表达。因为语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语言交际的效果,所以不仅要根据各类词汇所具有的不同语感来灵活运用,性别差异、身份地位、用语的场合等文化语境也是选择词汇时的重要依据。如敬语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现为尊敬、自谦等不同的语感。严格的等级序列影响下的日本民族,衍生出一整套复杂的敬语体系,这也是日本社会特有的“内外”意识在其语言交际模式上的延伸。[17]
即使是同一个词的语感,也会根据用语的场合、语境及文体发生较大的变化。如宫沢贤治的童话作品《奥侈倍尔与大象》中反复出现的语句:“奥侈倍尔果然了不起呀!”(3)参见《日本语教育事典》,大修馆书店1982年版,第292页。日本语言学家西尾寅弥有关“语感”的例句。这里用“了不起”一词表示的是一种反讽的语气,属于负面语感,与该词原本表示欣赏的语感大相径庭。再如,松尾芭蕉的俳句“朝露に汚れて涼しい瓜の泥”(4)参见《日本语教育事典》,大修馆书店1982年版,第292页。日本语言学家西尾寅弥有关“语感”的例句。(汉译:“香瓜沐朝露,我抚其上红泥土,凉从瓜中出。”)这里“泥”的语感与“泥で汚れた手”(被泥弄脏的手)等一般意义上的“泥”之语感相比,可以说清爽得多。不仅没有不好的感觉,反而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美的意境。此外,日语中意味相同的称呼语,因“内”“外”关系和交际场景的差别,在日常交际中需要根据对方是内部还是外部人士来决定用词。
(三)认识中日语言表达的差异性
如上所述,日语使用的是一种委婉型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日语语感的细微含义,往往通过其语言表达得以体现。特别是在情感表达方面,与汉语简洁明快、直抒胸臆的表达习惯相比,日语的措辞方式则表现得十分模糊婉转。如“远虑”这个词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在日本经常会听到或看到如:“电车中使用手机请远虑”的告示,尽管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同中文一样,都是“深思远虑”的意思,但在这里应理解为“请最好不要在电车内使用手机”。与此相对,我国在公共场所一般会开诚布公地使用诸如“严禁随地吐痰”“博物馆内禁止拍照”等命令式的语言表达。日本人喜欢用“远虑”这样婉转的劝告式语气,来表达在其他语言中本应该用“强烈和直接”语气表达的语感。“这种迂回、含蓄的表达方式源于日本社会的同质性,社会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细微的眼神、表情、语气的变化,甚至是肢体上的细微动作来传情达意,因而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18]由此可见,中日语言差异反映着本质上的文化差异。
日语学习者可以通过中日语言对比,认识中日语言表达的差异性,加深对日本人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的理解,揣摩其语言背后的真实含义和意图,从而形成合乎日本人表达方式的语感意识。并且对一些不符合日语习惯的表达方式有判断、指出和订正偏误的能力。在进行语言交际时,还要遵循得体的语用原则,有意识地克服母语的语用负迁移,减少语用失误,这样才能在语言交际,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减少摩擦和冲突。
总之,语言承载的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外部结构,更是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尽管中日两国同属于东亚儒教、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但二者无论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文化观念上,均表现出典型的异质文化差异。日语的语感问题正是如此,不仅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用语习惯、心理感受和价值判断,更体现了日本这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心态。因此,日语的习得、日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即一种文化意识的培养、一种价值观念的接纳、一种日式思维的养成。我们要在掌握这门语言本身的特质之上,不断通过语言实践,提高对日语语感的敏感性,同时还要重视语感文化在日语交际中的作用,培养语感意识,并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