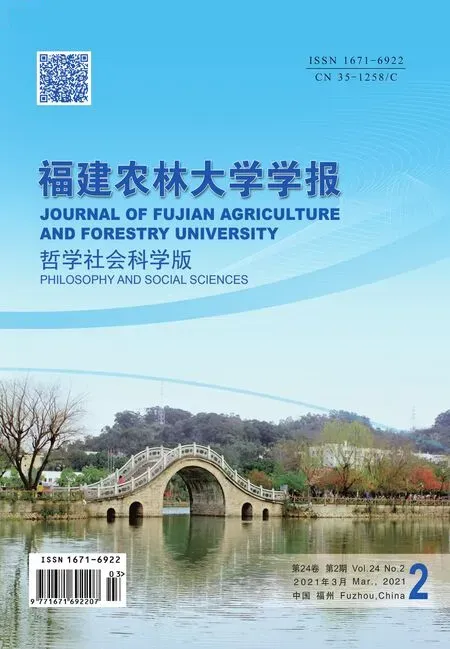三要素阶层式:罪行极其严重走出理论迷思的应然解释路径
刘 念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我国1979年首部刑法规定死刑的裁量标准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由于罪大恶极属于通俗化表达,有违立法的严谨性和科学性。1997年修订的刑法采用了更为科学性的表述: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是刑法条文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但罪行极其严重过于抽象,学界对其理解存在差异。司法工作人员在不同的理论学派指导下审判案件,即使达到了同案同判的结果,也无法完全满足同案同理同判实质正义的要求。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目前存在罪大恶极说、客观危害说、主客观统一说等多种学派,在同一学派之下也存在不同要素的规范理解。故此,有必要探讨罪行极其严重的应然解释路径,以期走出理论迷失。
一、根源:同案同理同判的必然要求
案例一:被告人金某甲去被害人胡某乙住处,意图向好友胡某乙借款3万元用于置办杂货铺,但胡某乙称无闲钱可借而拒绝。金某甲借钱未果便向其另一好友孙某借钱。孙某称自身确实无钱可借,但是前几天在银行取钱时看见胡某乙曾向银行存款5万元,且当时胡某乙对孙某称是将闲钱存入银行赚取少量利息。金某甲听后不悦,回想起当初曾多次向胡某乙借钱,便再次去胡某乙住处借钱,胡某乙称自己确实无闲钱可借并与金某甲发生争执,金某甲遂拿起胡某乙住处的水果刀捅刺胡某乙腹部十多下,胡某乙之妻任某见状便拿起手机意图报警,金某甲发现后又持水果刀猛刺任某数下,致使胡某乙和任某因脾脏失血过多死亡。后金某甲从胡某乙家中逃离,邻居报警,金某甲被警察抓获归案。法院认为被告人金某甲因生活琐事与被害人胡某乙和任某产生争执,后持刀捅刺两人致使两人失血过多死亡,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实属罪行极其严重,故判决被告人金某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
案例二:被告人买某与其兄买某丙因借款问题发生争吵,买某丙拒不借钱给买某。买某想毕竟是亲兄弟肯定会借钱。于是买某在吃完晚饭后便又去买某丙家中借钱,买某丙还是拒不借钱,双方发生争执,买某丙厉声呵斥买某没有工作只会花销,买某一时恼怒便跑去厨房拿起菜刀向买某丙颈部砍上数刀,买某丙发出求救。买某丙之妻张某闻讯从卧室出来,见状便拿起手机报警,买某手持菜刀向张某跑去,并用菜刀向张某腹部颈部砍去,致使买某丙和张某因大动脉破裂而失血死亡。买某藏匿于其好友家但最终被公安民警顺着线索抓获。法院认为被告人买某因借款问题与其兄买某丙发生争执,在买某丙拒绝时手持菜刀砍向买某丙和买某丙之妻张某,致使买某丙和张某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深,罪行极其严重,判决被告人买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
上述2个法院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可以说是司法同案同判的典范,但法院是基于不同裁判理由而作出的同案同判结果。裁判理由差异主要体现在关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上。案例一的裁判理由比案例二的裁判理由多了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同案同判体现了司法公正的要求,但这种正义不仅是形式公正下相同案件相同判决的体现,更是实质公正下相同案件相同理由相同判决的需要[3]。司法公正是在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也即司法公正应是结果公正和过程公正的一致表达,但在实践中,司法公正更多地体现为结果公正。司法裁判不仅是法官对案件事实情况予以确认的过程,而且是法官对法律适用进行推演证成的过程。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定罪量刑时有明确的法律文件可循,但由于审判法官的知识、经验以及专业技巧和内心确信程度不同,法官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也会出现裁判差异的情况。这种裁判差异不仅体现为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也体现为同案同判不同理的情况。在同案同判不同理的情况下,虽然裁判结果具有一致性,但裁判是对犯罪分子人身综合情况(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款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得出的结论。如果裁判理由存在差异,那就意味着对犯罪分子人身综合情况或法律适用等司法过程的认定存在分歧,也即同案同判不同理对司法过程的公正性存在疑问,而不是对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存疑。但无论是结果公正存疑,还是过程公正存疑,都无法达到司法公正的要求,无法实现实质公正,只能在形式上通过同案同判来达到形式公正的结果。换言之,同案同判结果要通过裁判理由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来实现实质公正,而不是形式上的相同案件相同判决即可。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其中之一便在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考量。我国刑法规定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时要综合考量犯罪人的所有情况,包括人身危险性的情况。法官在裁判理由中对人身危险性的认定不仅仅是对犯罪人罪行本身的认定,也是对法律适用进行证成的过程,也即人身危险性在裁判文书中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人身危险性承载的不仅仅是对死刑适用条件的表达,更是对司法过程是否公正的检视。如果裁判文书省略了人身危险性的表述,那便是死刑适用条件考量因素的差异,更使得上述同案同判结果的公正性存疑。此外,罪行极其严重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差异,在学理上也存在多种理解。理论界的争鸣和实务界的分歧使得罪行极其严重的司法适用差异较大,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为消除法律界对该问题的分歧,有必要解决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问题,走出理论迷思,实现司法的结果公正和过程公正。
二、隐忧: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论迷思
我国首部刑法规定死刑的裁量标准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由于罪大恶极属于通俗化表达,有违立法的严谨性。再加上罪大恶极是由“罪大”和“恶极”两个异质因素组成的规制体系,难免对法条的理解造成障碍,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条件裁量失当,同案不同判或同案同判不同理的情况时常出现。在死刑限制论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为了更好地发挥秩序维护和自由保障的功效,修订后的刑法采用了更为科学的表述: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条款只是笼统地概括了死刑适用条件,并未明确犯罪行为达致何种程度才可适用死刑予以惩戒。在判案过程中,司法审判人员对于死刑适用条件的理解无法达成一致,形成了当下死刑裁判泛化的局面,有悖于立法的初衷。为了发挥立法条文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和践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若干司法解释,对罪行极其严重作了略为明晰的解释。但由于司法解释的高度简约性,罪行极其严重的考量因素也只是略加明晰,在学理上仍然聚讼不断,形成了多种观点。司法审判人员在不同观念的影响下进行案件裁判工作,即使在客观上达到了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也无法满足同案同理同案实质正义的要求,有违司法公正。
从立法沿革上看,罪行极其严重是从罪大恶极演化而来。学界不仅从词义本身和法条意蕴出发,还从两者的相互关系上进行阐明。考量因素的多元性使得关于罪行极其严重的学理观点问题颇多,分歧很大。目前,学理上形成了诸多学派,即使在同一学派之下也存在不同概念的对垒。
(一)罪大恶极说
持罪大恶极说的学者认为刑法修改后的罪行极其严重只是原有死刑适用条件“罪大恶极”的规范化表达,罪行极其严重包含“罪大”和“恶极”,前者主要评价的是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后者重点衡量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4]。罪行极其严重本质上属于犯罪具有极其严重的客观危害性,犯罪人具有特别大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二)主客观统一说
持主客观统一说的学者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包含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但该学说存在规范要素的分歧:(1)认为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以及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程度是死刑的考量因素(客观危害、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论)[5];(2)认为死刑适用条件是主观恶性特别恶劣和客观危害特别严重的结合体(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论)[6];(3)认为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是重要考量因素,主观罪过是主观层面的因素且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至少是间接故意,而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客观层面的因素,要在考虑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作综合判断(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论)[7];(4)认为适用死刑达致的具体程度是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和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客观危害和犯罪情节论)[8];(5)认为死刑适用条件包括严重的客观危害性和主观罪过性的考量(客观危害和主观罪过论)[9];(6)认为罪行极其严重要结合犯罪类型和规范评价要素进行评估[10],也就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上述6种观点便是当前主客观统一说下的6种评价体系,其理论分歧主要在于两方面: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是主观恶性还是主观罪过,人身危险性是否应纳入主客观统一说之下。
(三)客观危害说
持客观危害说的学者虽然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仅是针对客观因素的考量,但对客观因素要如何具体考量尚未达成一致。如张文等认为动用死刑只需满足犯罪行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11]。聂立泽认为死刑裁量标准必须是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或者犯罪情节特别恶劣[12]。王作富认为应从犯罪的性质和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进行认定[13]。童德华认同罪行极其严重只包含犯罪的客观危害性这一观点,但对于客观危害性的具体评估范围未展开系统论述[14]。由此可见,学界对客观危害性的评估要素也尚无定论。
(四)其他学说
其他学说,如罪行为主、主观恶性为辅说,本质上也属于主客观统一说[15],但其较主客观统一说有了显著的进步,使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晰,也使得死刑适用更具阶层性和体系性,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再如,客观危害和人身危险性说。持该观点的学者在客观危害认定上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客观危害应以犯罪性质和人身危险性为考量标准[16],有的认为客观危害是犯罪性质、犯罪后果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体[17]。此外,还有少数派观点,如最高法定刑为死刑的罪行说,认为罪行极其严重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18];再如国际公约标准说,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与国际公约的极其严重的罪行同义[19]。细究之,这些学理分歧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罪行极其严重是仅包含客观因素还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体;(2)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分别作何理解;(3)人身危险性是否包含在罪行极其严重的考量范围内。如此看来,由于死刑适用条件的解释差异化,罪行极其严重在学术界引发了诸多争执。在死刑限制论刑事政策的大背景下,死刑限制有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两种路径,其中死刑的司法限制更具实操性和安全性,但司法适用的前提是立法规定,因而死刑的立法限制更为彻底和周延。在高度民主化和法治健全化的中国现代社会,充分运行刑法解释方法,对刑法条文作合乎立法目的的解读是保障法律安定性和适应性的根本之策。死刑的立法限制目的在于明确死刑的适用条件,减少死刑适用,应对罪行极其严重作合乎立法目的的解读,充分发挥刑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三、消弭:三要素阶层式——罪行极其严重的应然解释路径
如上所述,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适用条件在理论界纷争不断,原因不仅在于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适用条件的充要性,还在于罪行极其严重本身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外加多样性刑法解释方法的指导,在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变得愈加丰富的同时,学界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差异也越来越悬殊。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走出理论迷思。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刑法根据论的指导下,笔者认为主客观统一说是罪行极其严重解读的应然路径。具体而言,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死刑适用条件的考量因素,三者的评判顺序应当是客观危害性第一、主观恶性第二、人身危险性第三,即三要素阶层式的主客观相统一。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人的行为不仅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在社会规范领域内也具有一定的属性特征。“在社会规范属性下,人的行为都是在大脑支配下实施的旨在达致某种社会效果的主观内在活动。所有行为的实施都是在主观心态作用下产生的目的性活动”[20]。在法规范意义下,行为人在一定的内心活动支配下实施法益侵害行为,对行为人施加刑罚其目的不仅是基于行为破坏的客观社会关系,也是由于行为人内心主观犯罪意图所带有的主观社会危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由行为人对社会主观危害和行为对社会客观危害贯穿融合表征的结果。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权为内容,因此又被称为生命刑,在死刑适用过程中更需严格贯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动用死刑剥夺犯罪人生命权的前提是满足死刑适用条件,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需要达致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罪行极其严重实则发挥了死刑适用和死刑限制的双重导向作用。在定罪量刑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指导下,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适用条件需要满足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其考量因素既包含客观因素,也包含主观因素,以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的局面。客观危害说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仅是针对客观因素的考量,不包含对主观因素的表达,这从根本上背离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现有刑法理论相违背。而最高法定刑为死刑的罪行说和国际公约标准说虽未直接表述死刑裁量只评价行为客观要素,但其论证理由是围绕罪行一词的词义进行的,仍未跳出只有客观评价要素的桎梏,存在不合理之处。
(二)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是科罪处罚的根据
“社会主义的刑法,其法理根基并非行为人与行为本身的断绝与排斥,而是建立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机联结的事实状态之上的”[21]。换句话说,对实施越轨行为的人判定犯罪施加刑罚,其目的不仅在于惩戒其侵犯法益的客观行为,也在于改造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申言之,国家制定刑法对犯罪予以定罪量刑,皆是基于行为和行为人2个角度的考虑,定罪量刑是制裁犯罪行为和改造犯罪行为人的外在表现。其一,在于运用刑法惩治犯罪行为,恢复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其二,在于通过刑法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消除行为人破坏社会关系的主观意图。从定罪量刑产生根源来看,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是对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在量刑依据下,死刑适用条件必然有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体现,这种体现外化于犯罪和犯罪人的考量因素之中。如果对罪行极其严重采取客观危害说,那么无论是犯罪危害后果严重、还是犯罪性质恶劣,抑或是犯罪情节恶劣,对行为刑法的体现都直观明了,但对于行为人刑法的体现却难以自洽。因为无论是犯罪后果、犯罪情节,还是犯罪性质,都是犯罪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并没有直观映射行为人因素直接参与的作用。因此,从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角度来看,单纯的客观危害说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三)立法演进赋予了死刑适用条件不同的内涵
我国1979年刑法划定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是达到死刑适用标准的主体要求,后将其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不仅仅是立法语言规范化表达的结果,更是暗含了对生命刑规制措施的改进。虽然1979年刑法明确规定了生命刑的裁量标准,但罪大恶极是极其口语化的表达,且在相关立法条文中无法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表达,再加上受当时社会民意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罪大恶极的评判标准失衡。1997年刑法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与刑法分则“罪行”保持协调,从而使死刑适用条件更具操作性。
罪大恶极说主张罪行极其严重就是罪大恶极的改良版,生命刑的裁量因素仍旧是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在罪大恶极说中既有客观因素的包含,又有主观因素的体现,表面看来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刑罚根据论的精神,但细究之下发现,罪大恶极说也有局限。此种观点认为“罪大”和“恶极”在死刑适用中占据同等重要的作用,死刑适用条件是一个耦合性证成,无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孰重孰轻。虽然这种判断标准较为方便、快捷,但问题是在主客观因素竞合时如何判断是否达到死刑适用条件。1%客观因素和99%主观因素,以及99%客观因素和1%主观因素表面上看都达到了主客观相统一100%的结果,但是两种情况是否都是符合刑法正义的结果还有待商榷。
从规范意义上来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确是客观危害和主观危害综合体现的结果。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意图的内心冲动破坏社会关系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其对社会关系的破坏是通过犯罪的客观危害性大小来体现的,主观危害则是通过对客观危害的推演外化的心理情感。换句话说,犯罪的客观危害比主观危害对社会关系的破坏面更广、破坏力更大。因此,按照作用加功理论,将主观危害和客观危害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有失妥当,不仅人为限缩了犯罪行为客观危害性的作用,还扩张了犯罪人主观危害性的效果。在死刑适用条件的判断中,根据不同因素的加功作用证成其作用力大小,应当先判断客观要素,在符合客观危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再去判断主观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严重程度。因此,犯罪客观因素是犯罪主观因素的衡量基础,两者在死刑适用条件中的加功应当有先后顺序。罪大恶极说虽然符合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但是由于其没有明确界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力大小,在没有明确判断基准的情况下,实则更易造成死刑适用条件衡量体系的抽象和混乱。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在具体案件中支配其破坏社会关系的内心冲动,有故意和过失两类形态,但其充其量只是在犯罪人主观恶性支配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心态,并不是犯罪人主观因素的综合体现。以行为人在犯罪时的心态来系统描述全案犯罪人的主观因素这一综合情况有以偏概全之嫌。此外,犯罪人的主观因素也并不是只有在犯罪时才体现,犯罪前的积极谋划和犯罪后的认错态度也是犯罪人主观因素的体现。因此,将主观罪过升至主观因素的指代内容不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故而,主客观统一说下的客观危害、主观罪过和人身危险性论,以及客观危害和主观罪过论均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
(四)死刑适用条件考量因素的法律证成
实证主义犯罪学派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实施犯罪后会基于犯罪利益诱惑产生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犯罪人再次破坏社会关系的变幻莫测的人格危险,为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人身危险性势必要成为对犯罪人定罪量刑的考量依据”[2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责任承担应当以罪行后果、手段心态和人身危险性为综合情况,系统评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死刑作为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在死刑适用裁量时必然应将罪行的人身危险性纳入其中,这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要求的必然结果”[10]。
如前所述,罪行极其严重考量中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指主观恶性,客观因素主要是指客观危害性,但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犯罪学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赋予刑法学上的意义始,理论界就围绕初犯可能性是否是人身危险性的内在要素而纷争不断,即犯罪人的犯罪利益诱使其他人犯同类罪的可能性是否应由犯罪人承担。因此,明晰人身危险性在刑法学上的内涵意义是研究人身危险性在死刑适用条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基础。广义说认为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人表现的人格特性所带来的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融合”[23]。狭义说认为人身危险性是“犯罪人未来再次破坏社会关系的盖然性,即再犯可能性[24]。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破坏社会关系后,基于犯罪利益诱惑驱策他人犯罪的可能性是犯罪的客观附随事实,并不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内容,从行为样态来看,诱使他人犯罪的可能性与人身危险性截然不同,相反其更契合犯罪本身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内容。此外,根据罪责自负原则,行为人承担自己的再犯可能性责任无可厚非,但若因自己实施犯罪后便要承担防范他人犯未然之罪的责任则有违刑罚公正。因此,刑法学上的人身危险性仅指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产生的行为人再次破坏社会关系的危险。
探讨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相互关系本质上就是在探讨人身危险性是否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协调,以及人身危险性与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相互关系如何。就人身危险性是否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协调这一问题而言,笔者认为罪刑责相适应原则以及死刑裁判文书所载明的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量就是相互协调的明证。如上所述,人身危险性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危险,这一危险主要是通过犯罪人的犯前经历、犯中表现、犯后态度以及罪行性质等综合情况来探知的。也就是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综合了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犯罪情节、主观罪过等因素体现出来的个人人身特征[25]。犯罪性质和犯罪危害通过犯罪具体情况彰显客观要素,而犯罪情节和主观罪过则通过犯罪整体情况映射主观要素,因此,人身危险性和客观危害性以及主观恶性本身就是对应关系,人身危险性始终贯穿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中。
至于人身危险性与客观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的相互关系,通过上文对人身危险性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解读可知,人身危险性、客观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是相互独立、彼此协同的存在。客观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是对犯罪行为已然状态的判断,映射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人身危险性彰显的是行为人后续实施犯罪的再犯可能性,两者分属于截然相反的评定区域[22]。人身危险性涵盖的是对犯罪行为人的评价要素,客观危害性涵盖的是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要素,前者属未来或然性,后者属现实实然性,两者分属完全不同的罪行评价体系,不可混淆,否则就失去了人身危险性独立存在的意义[26]。这也决定了评价客观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要采用不同的衡量基准,将行为因素和行为人因素截然分开,避免造成同一事实重复评价的后果。就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相互关系而言,由于其均是行为人的评价因素,因此其评价体系并未泾渭分明,但二者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犯罪人在实施破坏社会关系的行为时表现出来的人身特征和人格品性是人身危险性,行为人在犯罪心理支配下破坏社会关系所呈现的心理邪恶状态是主观恶性”[27]。前者是或然预测规制作用兼具报应和预防功能,后者是实然惩戒效果兼具特殊预防作用。主观恶性作为行为人呈现的心理本相,涵盖人身危险性的表现样态,但并不是人身危险性本身[28]。因此,在死刑适用条件评价体系中,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相互对应、相互协同的评价要素。
综上所述,笔者在对当前学界的所有观点进行评述后,结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及刑罚根据论,认为只有主客观统一说下的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论才是罪行极其严重较为合理的解读路径。不过相较原有理论,笔者依据作用加功理论,对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学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认为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死刑适用条件的考量因素,三者的评判顺序应当是客观危害性第一、主观恶性第二、人身危险性第三。即笔者支持客观危害性第一、主观恶性第二、人身危险性第三的阶层式评价体系。这种阶层式评价体系不仅在理论上明确了罪行极其严重考量因素中的作用大小,在实践中也使得罪行极其严重的评判更具标准化和实操性。三要素阶层式体系构造兼具功能主义和目的主义的导向,但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对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加功犯罪的具体幅度仍需进一步探讨。不过,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院一般通过犯罪性质、犯罪后果和犯罪数量来判断社会危害性,通过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和犯罪情节来判断主观恶性,通过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性质和犯罪后果来判断人身危险性。在审判实践中,以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的方式来描述罪行的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普遍做法。
四、结语
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必须要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但规定笼统含混,可操作性较差,司法工作人员只能借助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判案。目前,学界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法院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定罪量刑,容易造成同案同判不同理的现象,破坏了司法判决的安定性和一致性。本文结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刑罚根据论,认为罪行极其严重走出理论迷失的应然解释路径是三要素阶层式,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死刑适用条件的考量因素,以此发挥功能主义和目的主义的刑法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