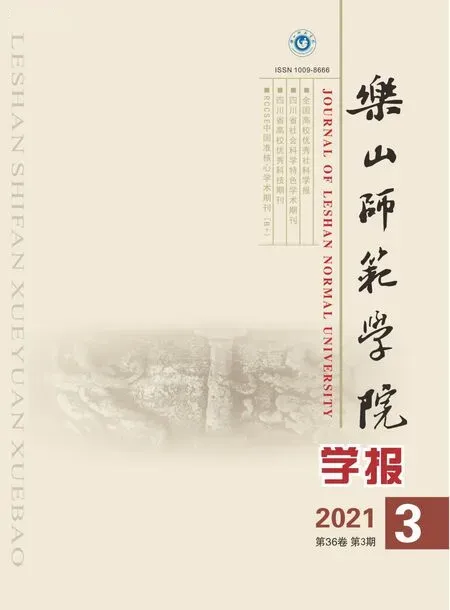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文化传播力探究
薛 梅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418)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让外界更好认识中国,“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近年来提升国家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已成为政府与知识界的共识。文学是文化传播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不同国家的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得以了解别国文化,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学作品随之成为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1]38。相比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在文化传播上有着先天优势。儿童文学受到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社会大背景的影响较小,注重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因而,产生的文化隔阂更少,最适合成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媒介。儿童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好形式之一,也是最容易“走出去”的文化产品。
2018年,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这是我国在海外举办的最大规模少儿出版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少儿出版和中国童书创作的国际化水平,为讲好中国故事开辟了新领域。虽然国内已经有不少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走向了海外,得到了认同,但是我国童书版权贸易引进大于输出的总体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儿童文学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的还不多,国际童书市场缺乏来自中国的原创声音。而美国本土的华裔文学作家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逐渐受到关注并跻身美国儿童文学“主流”,成为打破中外文化传播不平衡局面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作家的中国文化传播
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在美国正式确立以来,一直以其所包含的外国元素而著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学者开始发掘研究美国儿童文学中有关自身族群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多元化的倡导,全球化的推进和新移民的涌入,儿童文学中的多元文化格局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外国元素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中,与中国和中国人有关的描写,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它们大多出自中国移民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经过艺术加工而成,文学想象色彩浓厚。美国华裔作家一直在努力创作真实反映中国文化的儿童文学作品,颠覆美国人对华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在美国童书界,最有影响力的三代华裔儿童文学作家当属杨志成 (1931—)、叶祥添(1948—)和林佩思(1974—)。以下按照年代顺序分别介绍三位作家为传播中国文化所做出的成就。
(一)杨志成绘本作品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杨志成( Ed Young)曾三次获得美国童书界最高奖项“凯迪克奖”(The Caldecott Medal),先后两次作为美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杰出创作者被提名为国际安徒生奖候选人,并于 2016 年获得美国插画界终身成就奖,是当今华人儿童图画书界成就最高的作家。其图画书创作始于 1962 年,至今已有五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图画书创作生涯,形成了独特的杨氏风格。
1.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
杨志成童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完成基础学业后才随家人移居美国。他的绘本作品多以各国尤其是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比如WhiteWave(《田螺姑娘》)、TheLostHorse(《塞翁失马》)、TheStoryofRatandCat(《生肖鼠的故事》)、MonkeyKing(《美猴王孙悟空》)、RedThread(《月下老人》)、MouseMatch:AChineseFolktale(《老鼠嫁女》)和SonsoftheDragonKing(《龙生九子》)等等。对于古代典籍已有记载的民间故事,杨志成常在正文前的一页,用毛笔书法撰写典籍中的原故事,这是对民族文字和文化风景的直接展示。而MouseMatch:AChineseFolktale(《老鼠嫁女》)则采用了特殊的装订方式,可以将所有书页展开形成一个长卷,正面是图画和英文译文,反面是黑底白字如同碑拓一样竖排的汉字书法写就的汉语版故事。
中国美术将书、画、印三者融合一体,杨志成时常在作品中以中文字体的印章提醒读者注意故事的原始语言。TheStoryofRatandCat(《生肖鼠的故事》)的最后一页,他列出了十二生肖动物名称的篆体刻章,每个刻章名称下是对应的年份,并描述了每个属相的个性特征,这就像是中国生肖文化的“注解”,吸引读者去查看自己的出生年份所对应的属相,以及对照是否符合上面的个性特征。杨志成热爱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致力于用图像还原中国象形文字的哲学和精髓,他计划以10本图画书的容量,解读《康熙字典》里面的214个偏旁部首,到目前完成了VoicesoftheHeart和BeyondtheGreatMountains,这将是亲近汉字的绘本,让外国人在理解汉字的造字之法中学习汉字,不失为汉语语言文字的巧妙传播。
2.融合东西文化观念的图像语言
杨志成选择以图画书为媒介来传播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早期的他,更擅长绘制图画而不是故事文本的创作,他的许多书,大都是由别的英语母语作者创作文字。他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来表现绘本的主题,也会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创作题材来“量身定制”最合适的表现方式,从而完美、准确地展示绘画作品的主题。
杨志成第一本获凯迪克银奖的插画书TheKingandtheKite(《公主的风筝》),在当时的西方图画书界吹起了一股中国风。这本取材民间故事的绘本采用了中国传统剪纸的方式来表达古代宫廷、亭台楼阁、风筝等中国元素,在画面的构图上也有意设计了大量的留白,充满东方的智慧和禅意。《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的评语是:“令人惊叹的中国风绘本。”
获得凯迪克金奖的儿童绘本作品lopopo(《狼婆婆》),书名直接采用了汉语拼音而不是英文表述,明确表达这是一个中国故事,故事的原型来自中国福建民间故事《虎姑婆》。绘本运用了粉彩,但却画出了悠远的水墨意境,写意而非写实,充满东方故事的神秘与诡谲。作品还采用了剪影技艺,剪影的工艺由皮影工艺演变而来,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之一。在第一页,狼的正面剪影和老妇人的侧面剪影彼此交叠,暗示故事中的狼伪装成老婆婆。从故事的开头妈妈告别三个女儿出门去外婆家起,一直到狼现出原形为止,有14页的篇幅,画家始终没有呈现狼的真面目,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如妈妈出门时的画面,她其实就踩在了狼的鼻子上——她们房子下的那个山丘,山丘的形状是水墨晕染的影影绰绰的狼头的侧影,暗示危险的逼近。绘本采用不同宽度的“分镜头”来安排画面结构,是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由此产生了中西艺术风格的对比效果:分镜头的感觉是西式的,小女孩的面孔是中国风的,画面的色调和笔触的晕染都是中式的。相比之下,由田原插画的中国版《狼外婆》画面色彩鲜艳,人物形象写实,表现方式率真质朴,更具中国民间画的特质。
杨志成的插画大多基于民间故事,呈现民族或地域特色,但同时又融入西方现代甚或后现代风格的抽象元素,以多元化的艺术创作媒介和巧妙的设计吸引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TheCatfromHungerMountain(《饥饿山的猫》) 采用混合媒体拼贴画技法。拼贴艺术是西方19 世纪立体主义绘画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在画面中使用多种材质共同完成的艺术形式。在塑造住宅、服饰样式等中国传统元素时,作者运用纸、布、竹等多种不同纹理的材质作了富有想象力的奇特拼贴,形成多层次的立体感,强化了视觉效果。拼贴技艺还呈现出夸张的特写和写意的远景的结合,粗犷与细腻、平面和立体的并峙。这种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将一个关于奢侈和节俭的道德说教的旧故事表现得华丽和奇异。《纽约时报》称其为“令人惊叹的视觉交响乐”。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评价其为一场“眼睛、心智、灵魂的盛宴”和“一个视觉杰作”。
(二)叶祥添成长小说的华人精神力量传播
叶祥添(Laurence Yep)是在美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当代著名华裔作家,更以其对儿童文学的贡献而知名。他两次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被收录在美国中学教材中。叶祥添著作丰富,创作过写实小说、科幻小说、民间故事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与杨志成致力于以中西绘画艺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叶祥添作品的特色在于建立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构建正面积极的华人形象。
1.在文化碰撞中追寻华人身份认同
叶祥添最为儿童文学界所称道的是少年历史小说金山系列。金山系列小说之一Childoftheowl(《猫头鹰的孩子》),讲述了杨氏家族第五代移民凯西文化身份构建的经历。凯西自幼浸润在单一美国文化环境下,父亲发生意外令她不得不投奔住在唐人街的外婆。起初由于她不会讲中文又过于美国化,与唐人街的华人格格不入,开始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产生困惑和疑问。然而,在外婆与周围其他华人的关心和爱护下,她开始慢慢认识和理解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相关的一切事物,修复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最终,凯西走出困惑,由排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身份转而拥抱中国文化并接纳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贯穿文中的猫头鹰神话就是华人在中美两种文化中的处境的隐喻。猫头鹰的意象在西方民间传说中是智慧的象征,而在中国传统认知中却有不孝子孙的涵义,它象征着华人无法同时得到中美两种文化的认可,常常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流中都显得格格不入。叶祥添通过创造改写猫头鹰神话故事传递了中国文化伦理观,批判了华人背弃中国文化而追求完全美国化的行为,呈现了其独特的华裔文化身份观念。凯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实现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也正是叶祥添自身实现文化身份构建过程的投射。这部作品是叶祥添探索华裔美国人身份根源之作,也是促进华人积极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之作。
2.构建正面积极的华人形象
同样是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华裔作家, 同样是在作品中讲述中国人在美国寻找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父辈都属于经历过底层劳动的苦难和艰辛的早期来美移民,汤亭亭和谭恩美在审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时往往对其呈现出误读和疏离,往往为了刻意取悦白人读者,在作品中误读误用中国典故和传说,歪曲华裔美国人的本来面目。而叶祥添的作品塑造和传播的是正面的华人形象,与西方人眼中扭曲的华人形象有很大反差,更多表现的是华人在美国积极向上,勇敢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所描述的“中国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主旋律更多是友情、义气、同舟共济”[2]67。
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分别获得1976年、1994 年纽伯瑞银奖的金山系列作品DragonWings(《龙翼》)和Dragon’sGate(《龙门》)。《龙翼》改编自发生在一位中国飞行员身上的真实故事,激励读者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故事讲述小男孩李月影直到九岁才跟随远方亲戚从中国来到美国第一次见到父亲,在旧金山做着洗衣店工作的父亲有一个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在儿子的支持下,父亲经过内心的挣扎,终于抛开杂念,不顾旁人的嘲笑,为自己的梦想开始努力奋斗。在小说《龙翼》的后记里,叶祥添写道: “一直以来,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推翻以前媒体中美国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电视电影中的厨师、洗衣工及各种喜剧中的仆役, 那都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希望藉由这个刚到美国的中国小孩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父亲为了追求理想而奋斗的故事,刻画出当年吃苦耐劳、相互扶持的真正的中国人形象。”[3]363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融入了很多涉及文化信仰、艺术、节日等中国文化元素,如虚岁、风筝、烧香祭拜、灶神、门神和清明扫墓等。为能被更多美国读者接受,叶祥添在故事情节中融入了美国历史背景,以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历史事件引出小说主人公月影的父亲执着于自制飞行器的故事。小说塑造的父亲乘风,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少有的民主开朗的父亲形象。他说:“我不想强迫任何人做他不想做的事, 即使是自己儿子也一样。”这句话颠覆了中国儒家传统的父权思想。小说描述的第一次父子见面的情景也相当西化。乘风完全不是中国父权体制下的传统的严肃刻板、压抑内敛的父亲形象, 而是表现出兴奋和激动: “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 可是感觉却如此遥远。父亲笑着说:‘孩子 !’他弯下身, 张开双臂, 说: ‘我等这一刻等好久了。’我抛下箱子, 投入父亲的双臂, 我终于到了。”[3]这样如同好友久别相逢的场景的确鲜见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父子关系中。叶祥添塑造的华人勇于追求梦想的精神以及平等的亲子关系,都颠覆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龙门》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中国鸦片战争,美国淘金热以及跨大陆铁路建设的历史背景之下。故事讲述主人公水獭跟随父亲和叔叔在美国做劳工,工作危险,食物少,工资低,遭受歧视和压迫,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这些冲击带给水獭不一样的成长。故事强调美国东西横贯铁路的修筑是华人移民对美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在美国历史记载中几乎没有提及,作者希望通过小说打破沉默,为这些被历史遗忘的无名英雄争取应有的重视及尊严。主人公少年水獭,在看到自己的同胞遭遇不公正待遇时, 敢于和霸道的白人工头作斗争, 即使遭到无情的鞭打也不退缩,体现出中国人勇敢不屈的精神。
叶祥添的写作题材是多元化的,他的第一部科幻短篇小说TheSelcheyKids被收入1969年世界最佳科幻小说(World’s Best Science Fiction),随后完成了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SweetWater。这本身就打破了中国文化等同于古代民间传说的刻板印象,向美国社会展现了当代华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林佩思儿童文学的现代华人文化传播
林珮思(Grace Lin),是美国华裔儿童小说家和绘本作家。她的作品分为儿童小说系列、自传体小说佩思系列和学龄前绘本等几大类。她的作品多次荣获绘本最高奖项凯迪克大奖。她的童话小说WheretheMountainMeetstheMoon(《月夜仙踪》)荣获2010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其多部作品被收录到美国语言教材中。如果说汤亭亭、谭恩美和叶祥添那一代华裔美国人的文学作品重点表现了华人面对文化差异的纠结、痛苦和反思,那么新生代的林佩思的作品就是拥抱差异,同时接受并吸收中华文化要素,自信展现中华文化,以儿童教育的角度,富于幻想的童话故事感染西方读者。林佩思儿童文学的两个特点就是自信展现中华文化以及寓教于画。
1.自信展现现代华裔生活的风采
林佩思的成名作《月夜仙踪》以一个中国小女孩敏俐寻找月下老人,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的历险故事为主线,通过精彩的故事和精美的插图,向读者呈现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诸多神话传说,如阎王爷、牛郎织女、神笔马良、叶公好龙、吴刚砍树、月老、大阿福等。这部奇幻童话令国外读者联想到美国经典童话《绿野仙踪》,由此吸引了读者关注故事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正如她本人所说:“我只是将古老故事融入现代小说,藉着新文本,读到老故事!”
《月夜仙踪》一炮走红,为林佩思赢得更多读者,使她不再是专写亚裔美国女孩的“小众”作家,人们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她的自传体丛书佩思系列。佩思系列丛书包括三本自传体小说:TheYearoftheDog(《狗年》)、TheYearoftheRat(《鼠年》)和DumplingDays(《馄饨日》),真实记录了作者对华裔身份和文化从协商到认同到立志通过写作为华人发声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叶祥添在童年经历文化休克最终走向华人身份认同的觉醒,并立志通过文学作品追寻华人移民史的话,林佩思的作品则更多的关注当下美国华裔的现代生活。《狗年》描述了作者本人在纽约上州学区的成长和日常生活,塑造了亚裔美国人Pacy的形象。这本书在记录所有小学生关心的问题,比如交友、参加学校活动的同时,着重突出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如何使这些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如佩思在参与学校活动时受到种族认同问题的困扰。当Pacy尝试参加学校剧《绿野仙踪》时,她的朋友告诉她,剧中的角色多萝西不是中国人,她担心人们会嘲笑中国人扮演白人角色的想法。贯穿佩思整部小说的重要主题是Pacy站在一个亚裔美国孩子的视角,需要与学校、社区和家庭进行协商。小说的自我指涉强化了以亚裔美国人角度重写美国童年的行为。像林佩思本人一样,小说中虚构的人物Pacy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她想知道为什么美国的书籍中没有中国人的形象。她质疑了美国流行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忽视,“你从来没有在电影,戏剧或书本中看到过中国人”[4]。她去学校图书馆找关于中国主题的书,发现中国题材的经典童书《五个中国兄弟》(TheFiveChineseBrothers)并没有描述“真正的中国人”。由于时代的限制,五兄弟的形象仍然是西方人眼中的“苦力”形象: 眯眯眼斜吊着,留着长辫子,戴着瓜皮帽。Pacy不接受以歧视东方的视角来定义亚裔美国人,她呼吁美国当代小说应该真实刻画亚裔美国人。她参加了学校的写作大赛,写了一本书填补缺乏对亚裔美国人的真实描述的空白。这是一个曲折的自我参照,通过这样的写作,Grace Lin让年轻读者推断出Pacy获奖的处女作也是现实生活中她自己的真实作品:那个故事是“真实的”。读者也因此相信成年的Grace Lin实现了Pacy童年立志树立华裔美国人形象的雄心壮志。如果说华裔美国人在大众文化中的“不可见”意味着“中国人都不重要”,那么小说《狗年》及其续集则反驳了这一说法,证明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已经不同以往,他们是重要的和突出的。佩斯自传小说的另一个创作意图,据作者所说,是“着重反映华裔美国人的现代生活,向读者表明,华裔不仅仅有传统文化,他们也跟普通美国人一样生活在现代社会。”[5]109
以往描写神秘的东方习俗的小说,通过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可以获奖并将作者推入主流,而描写华裔美国人当下现实生活的书却做不到。这个事实反映了美国人以“观光多元文化”的方法看待种族和民族特征,强调了解传统文化而不是认同这种文化中的人的当代生活或实际的历史。教育家Derman Sparks将“观光多元文化课程”定义为通过对“其他”文化的“访问”的方式引入多元化,如通过介绍假日庆祝活动或者传统的异域形象,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切断、贬低和歪曲民族群体。而林佩思的自传体系列小说突破了以往华裔小说仅以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迎合美国“观光旅行”式的多元文化观。佩斯系列在对华裔美国人现代日常生活的叙述中自然穿插了中国文化习俗的描述,有对传统的坚持,也有现代化的改良。比如:在Theyearoftherat(《鼠年》)这本书中作者写道,“恰好这年除夕是周六,父亲于是提议一家人守夜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除了遵从一家人围坐一起团团圆圆,谈笑畅叙的传统外,还加入了西方人过新年表决心的习俗,孩子们都各自写下自己来年计划达成的目标,很有现代气息。在绘本ThankingtheMoon中,作者绘制了一家人中秋之夜在户外赏月、野餐、吃月饼的情景,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而户外野餐又是美国家庭的生活方式,二者和谐得融合在一起,毫无违和。
2.寓教于画的文化传播效应
林佩思的自传体佩斯系列和学龄前绘本系列以轻松活泼的表现形式,潜移默化的对英语读者进行了中国文化启蒙。学龄前绘本大多在扉页上画出故事中提及的所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的图片和相对应的英文单词,帮助幼儿学习掌握中国文化词汇。她还巧借中国特色的事物作为低幼儿童学习的教具,比如在ABigMooncakeforLittleStar(《给小星星的大月饼》)这本纽伯瑞银奖绘本中,通过小朋友一口一口地把月饼咬的越来越小,巧妙而形象得介绍了“月有阴晴圆缺”的月相变化。
杨志成的绘本文字大多数假手母语作者,而林佩思的作品文字和绘画均出自她一人之手。她亲自手绘小说插图,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手绘插画还让文字获得了更加饱满的在场感和故事性。比如:佩斯系列的DumplingDays详细描述了作者随父母回到故乡台湾过暑假的经历,小说从启程、在台湾的一个月生活一直到归途,全程都配有手绘插图。作者以画笔代替相机镜头,记录了繁华的台北街景、热闹的集市和布满各种小吃摊的夜市,呈现出一种质朴而不乏机巧的美,读者如身临其境,跟随作者一起流连于台湾各地的风情。佩思手绘插画看似随意却充满独特的亲切感和亲和力。插画还起到了补充解释小说细节的作用。有些插画用直观具象的方式解释了一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物件、习俗和饮食,如在描述自己和姐妹们一起去学篆刻和中国书法绘画时,配上了多副印章的图片,水墨画的图片,还画出详细分解图,讲解如何使用毛笔、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制作灌汤小笼包等。小说的最后一页特意画了各种不同名称和形态的dumpling, 图片下配以拼音解释汉语名称,如烧卖,混沌,煎饺等等,与小说的名称相呼应。文学想象里,最先出现的往往是画面,再落到文字;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文字反而累赘,有了示意图,读者立刻就懂了。林佩思的手绘插画拓展补充了语言的表现空间,在读者与作品之间建立了更牢固的联系。
二、华裔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化传播优势
(一)华裔身份之优势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过程,一直都伴随着作者文化身份的不断改变和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始终是美华文学身份定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6]。而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甚至作家个人的家庭背景又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策略和态度各不相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身份。出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杨志成,对自己在美国的身份定位是“异乡人”。他在中国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熏陶,又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艺术有了很深的理解。他博取众家之长,在创作中融合东西方艺术,形成了独特的杨氏风格。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作多元文化的图画书时,他曾说:“我参与儿童图画书工作的动机,一方面是想要引介中国的故事——我们有太多好故事了!另一方面,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来到美国,我也希望多理解西方的故事,好拓展我自己的眼光和表现形式。每次我投入一个异域文化故事,我都从中受益匪浅。”杨志成的作品是在西方表达东方,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杂糅淬炼出的精品,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图像语言。叶祥添是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第三代华裔移民,父辈属于早期移民的劳动阶层。他在童年时期也有对自身文化的困惑和疏离,但在成年后却转化为探索华裔美国人身份根源的写作动力,从而完成了一系列以华裔美国人历史为背景的成长小说。20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美国的林佩思也经历了自身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上困惑、协商与和解的历程。她的父母在台湾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在美国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林佩思与父母在对待中美文化差异方面并没有激烈的对立,对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骄傲。父辈们带来的生活习俗和中国的典籍,使她潜移默化地继承了中国文化,也给她的作品带来了一种未掺杂殖民主义的现代中国文化气息。
新生代华裔作家游弋于两种文化,秉持东西方双重文化价值观,既有与中国文化相传承的血脉关系,又具有新文化新语言的特质,极易打通作品与美国读者以及评论界的沟通渠道。欧美儿童文学的题材多为奇幻探险故事,强调文学的浪漫与诗性,叶祥添的成长小说《猫头鹰的孩子》在纪实性的叙事中穿插中国文化中有关猫头鹰的传说,产生亦真亦幻的奇幻故事的效果,容易激发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林佩思的童话小说《月夜仙踪》被书评界誉为亚洲版《绿野仙踪》,小说的中国主人公提供了一个除了金发碧眼的灰姑娘童话故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其写作模式也是沿用美国童话故事的奇幻探险母题,在西方文学评论界获得较高的辨识度。有人认为小说《龙翼》中父子相见的场景的西化描述,是源于作者本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经历。这种跨文化的经历, 使得叶祥添能够把他熟悉的中国元素, 以比较符合西方人思维习惯的形式呈现出来, 更符合美国青少年的阅读口味。林珮思的作品汉译后在国内发行,有国内的读者称其是典型的香蕉人:中国人的脸、美式的文化和思维;进而把《月夜仙踪》这样的书——东方文化的素材、西方的叙事方式和普世价值——称为“香蕉书”。实际上,此类“香蕉书”的出现,正是人类文明交流、借鉴、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进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二)儿童文学属性之优势
儿童文学具有世界性。与成人图书相比 ,儿童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无国界的童心童趣以及纯真情感, 少儿的阅读喜好和内容互通性更强。儿童文学的题材以故事为主, 内容贴近生活, 受到成年人世界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小,是最能够沟通人类共同的文化情感与社会道德价值的世界性文学,使得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跨界阅读成为最大可能。例如:杨志成的英语图画书虽然是对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述,却往往包含着具有人类共同纯真情感的母题,如亲情友情等,其道德和文化意蕴能够跨越民族界限和意识形态差异,其内容容易召唤不同民族的读者深层次的心理共识。绘本《狼婆婆》虽然根据中国民间故事改编,人物是中国人的面孔,但是讲述的主题却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他们同样会被三姐妹智斗野狼的故事吸引,同样佩服她们的勇敢、机智、冷静及团队合作等精神。叶祥添的小说《龙翼》虽然描述的是唐人街上的华人父子,但是他们那种不畏困难、坚持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以及父子之间的宽容、互助和家庭亲情却能深深打动美国读者,因为即使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的。
林佩思的《月夜仙踪》童话小说中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帮助作者构建出中国语境,同时作品融合了寓言的属性,充满宽容、爱、无私和感恩的伦理思想。国外有的读者从书中感悟到,善良比贪婪、谋略更能改变人的命运,还有善有善报的哲理。有的认为书中强调了亲情和友谊的重要性。这本童话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后,国内读者认为,小说表达了对自然的感激、对人的感激、对万物的感激。还有的读者从中看到了儒道文化中的弱德之美,在约束和收敛中坚持对理想的追求和品德的操守,常怀感恩之情,人生才可能幸福圆满。这些作品引起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共鸣,因而得以广泛传播。
儿童文学具有教育属性。儿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教育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7]40。儿童图画书往往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儿童读者对图画书的欣赏和理解,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态度[8]。以中国文化主题的童书影响一个国家的儿童阅读,就是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主流意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会让海外华人更加认同中国文化,也会令西方读者更加开放包容的看待中国文化。如杨志成的绘本《龙生九子》在介绍中国文化中龙的九种图腾形态的表征、涵义和起源时,是以龙王根据九个儿子的不同特点安排他们在人间各司其职为故事主线的,西方读者认定龙王是个开明的父亲,认为在教育子女中应该发现孩子的特长并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特质,在认同故事的家庭教育理念时,就会对龙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充满兴趣。林佩思的作品有意识的加入了儿童教育的视角,于无声处似有声的以童趣传播中国文化。她善于以中国元素创作基础认知为主题的绘本,如,Redisadragon和Roundisamooncake就是她非常热卖的学前绘本,这两本书以朗朗上口的英文歌谣的形式,藉由中国特色的事物分别教幼儿认识颜色和形状,如,在介绍红色时描述中国新年里的舞龙、鼓、鞭炮是红色的,介绍圆的形状时提到月饼是圆的,窗外悬挂的灯笼也是圆的。在书的末页,作者细心地列出书中涉及到的中国事物名称并提供详细解释,让孩子在学习颜色和形状的同时,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习俗和历史。
身为跨文化创作的美国华裔作家,杨志成、叶祥添和林佩思凭借自身的双重文化者的优势,以儿童文学作品为载体,自觉地担负起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职责。
三、对我国原创童书“走出去”的启示
华裔作家创作的中华文化题材的童书在美国大受欢迎,这为我国原创童书“走出去”提供了成功范例。通过研究华裔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国外读者的评论,可以看到异域读者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心态,为我们的原创童书对外出版提供借鉴。
文化传播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效满足接受者的需求。文化之所以能传播,其关键因素并不在于传播者做了什么,而是接受者需要什么。文化传播的一个策略是“利用他者来讲述自己”[9]。程爱民教授指出“海外华裔在整体上是更具有强烈文化感受力的群体,大多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文化(民族)属性及其‘他者’地位”[10]。海外华裔作家就是这样的“他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亲历者,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的接收者西方读者的需求,并能据此制定文化传播的策略,更能够精准打动接收者。让那些对中国文化身份引以为豪的新生代海外华裔成为海外中国文化传播的探路者,并加强国内作者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文化传播策略。
西方传播学的代表人物威尔伯·施拉姆(Wibur Schramm) 指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同’的东西,即我们努力想共享“信息、思想或态度。”[11]儿童文学在表达人类共同情感和思想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原创童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只要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同时,着眼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就更容易得到外国读者的共鸣,毕竟,好的故事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