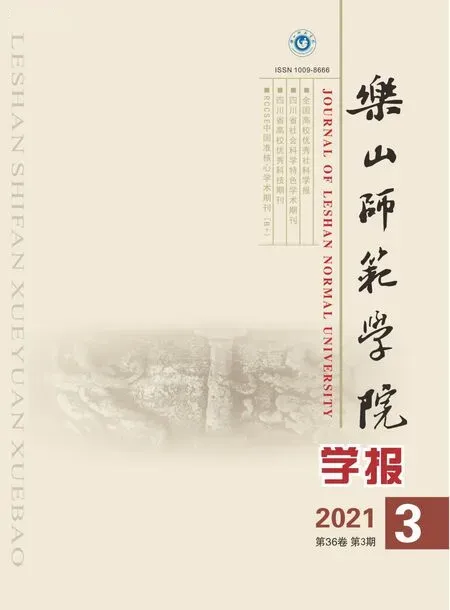民族考古学在史前宗教研究中的运用与不足
屈 谱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交叉学科是指在研究某一方面问题时,通过不同学科进行综合交叉辅助研究的一种学科。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可以把传统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大大扩展。通过不同方面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可以完善和补证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民族考古学,就是一种明显的交叉学科。
民族考古学运用于考古学的观点,最早是在美国新考古学学者路易斯·宾福德1962年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1]一文中提出。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许多学者对此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学界关于民族考古学理论及其本土化的研究已较为完善,最新研究评述有鲁大立、闫佳楠、孙旭旺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综述》;[2]陈虹利、韦丹芳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回顾与反思》[3]和张俭的《我国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述评》[4]等,都对民族考古学这一理论和中国学界对其研究的进程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归纳评述。
但学界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一直有所分歧未能厘清,汪宁生先生曾在《论民族考古学》一文中将其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派,其赞同广义的观点,认为民族考古学即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5]另外,据何鸳先生在《考古学大辞典》中编写的“民族考古”词条解释,“民族志考古”也称“民族考古”,即是通过利用当代现存的民族志资料,并用考古学眼光进行现代民族志的调查,探求人们特定的行为模式、生存方式和遗留的遗存之间的关系及模式,并供考古学家参考,试图通过考古遗存看到造就这些遗存的古人行为及生存方式。[6]
笔者较为赞同上述这两种观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由于外文翻译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已经讨论了数十年,难以厘清,而在这数十年之间,以民族考古为题或关键词的文章多如汗牛充栋,各取其义。笔者更愿意将民族考古学看作一种考古学或史前史的研究方法,即是提示了学界用民族志的材料作为考古资料的一种验证,以考古资料为主,民族志资料加以补充和印证。这样一种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于主要以前文字记载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史前史,特别是该时期的史前宗教信仰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史前史无文字资料的记载,而宗教信仰研究属于思想史的大范畴,在没有文献的基础上,很难准确理解原始先民在遗址、遗迹中蕴含的主要思想、信仰,这就需要民族志材料的印证,通过近现代记录的原始部落或少数民族残存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原始信仰,可以识读和验证一些我们在考古活动中发现的反映史前原始先民信仰的遗迹。总的而言,相较于其他时期的考古,史前史更需要民族考古的辅助;相较于其他考古活动方面,史前宗教信仰研究可以说与民族考古密切相关。另外,笔者认为这里的“民族志”一词可以有更为广泛的概念,立足中国来说,历代典籍记载了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礼制,依然可以看作一种广泛的“民族志”材料,与地下考古资料进行验证,早在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中便已涉及。
学界对于原始宗教的研究,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为原始宗教理论研究,如谢宝耿的《原始宗教》[7]、E.E埃文斯的《原始宗教理论》[8]、朱天顺的《原始宗教》[9]、吕大吉的《宗教学通论新编》[10]等;其二,对现存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资料的调查收集,如朱文旭的《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11]、张纯德的《彝族原始宗教研究》[12]、蔡家麒的《论原始宗教》[13]、张桥贵的《宗教人类学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14]、周锡银的《藏族原始宗教》、吕大吉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15]等;其三,通过考古发掘材料研究特定性质或特定地区的史前宗教遗存,如吕大吉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16]、王芬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宗教遗迹》[17]、李伊萍的《新石器时代“灰坑葬”中所见祭祀现象》[18]、陈国庆的《燕山南北地区史前原始宗教的形成与发展》[19]、萧兵的《略论西安半坡等地发现的“割体葬仪”》[20]和《北方史前氏族社会过渡中的原始信仰》[21]等。
学界已有前辈将民族考古学用于史前宗教的研究,如宋兆麟的《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22]、李仰松的《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的远古人类的葬俗的一些启发》[23]、汪宁生的《古俗新研(九)——有关特殊葬俗二则》[24]等。但总的来说,这种类型研究数量并不多,且多是对某一遗址某一时期的一种具体细化的考古遗存、遗迹进行补充说明,单篇中对民族考古学的运用并不多。对民族志的重视和运用,尚有可发展的空间。下面笔者列举一些例子,以期说明民族考古学对史前宗教研究的作用。
一、运用的例证
(一)民族志
老官台文化时期的大地湾遗址墓中发现有猪下颌骨陪葬,[25]68、861白家村遗址和北首岭遗址墓中有野兽獠牙,[26],[27]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基托伊文化人们喜欢以野猪牙作为装饰。[28]以上这些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结合民族志材料就可以发现其中思想层次的内涵。比如在近代纳西族中还有这样一些与猪骨有关的习俗,“曾经随葬猪下颌骨……还把吃剩的猪下颌骨挂在室内……也是家族安危的象征”[29],王仁湘先生籍此推测这些人们认为“用猪头、猪下颌骨随葬是对死者灵魂的一种护卫”。[30]79-85冯恩学先生也通过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中记载的斗东野猪的石老习俗资料认为基托伊文化人们以野猪牙为饰是将野猪当作是勇猛之神。[28]另外,中国古籍中有将猪作为恐怖象征的例子,例如《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封豨、修蛇,皆为民害”[31]句中记载的民害“封豨”即是指在远古时期为乱的大野猪。上述民族志资料和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原始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人们对于野兽的恐惧,从而引申出了对野兽的骨骸的崇拜,将其当作寄居动物灵魂的灵物,祈求猪下颌骨中的猪灵庇护平安。
另外,兴隆沟遗址兴隆洼文化时期的F22中发现有2件人头盖骨牌饰,[32]笔者认为其可能具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内涵。根据国外民族志记载,美洲的诺泽人在逝者死后,为了保持对死者的记忆,并利用这些死者遗骨的巫术力量,便会将死者某些部位的遗骨带在身边;澳洲的塔斯马尼亚人会在火葬死者后收集其遗骨,然后捆在兽皮之中,给其亲属作为护符随身佩带。[33]389-390此处兴隆沟遗址发现的人头盖骨牌饰也有钻孔,可能便是用于佩戴。按民族志的记载,我们便暂且可以做一个较为合理的解读,即这类人骨牌饰是灵魂观念影响下,原始先民在亲属死去后将其遗骨作为寄托逝者灵魂或巫术力量的灵物,随身佩戴以期获得庇佑。法国学者E·杜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一书中称:“死者的骨骸、他们的头发都很重要,算得上是巫师常常使用的媒介。”[34]42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除瓮棺葬现象外,出现了特殊的葬俗“割体葬”,例如M66墓主的下腿骨被砍断后和大腿骨埋葬在一起的,而其他更多的“割体葬”墓葬墓主是缺少手指,但有零星的指骨往往在随葬的钵或者墓葬填土中被发现。[35]据民族志资料记载,太平洋地区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萨摩亚人在为其部落酋长举行的丧礼上,曾号召群众共剁下百节手指;[36]陈星灿先生曾根据一本传教士所写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游记的记载,割体的手指可能为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后来随主人一起埋葬。[37]北首岭遗址的发掘者认为此类割体葬可能是为了驱除邪祟。[38]笔者认为割体葬体现的思想层面的内涵当与兴隆沟遗址人头盖骨牌饰相近,都是将部分遗骨作为了灵魂的寄居物。
半坡遗址还有典型的葫芦形器这种陶器类型,笔者认为这种葫芦形器当是女性生殖崇拜的体现,民族志资料中,我国西南地区的如彝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都有关于葫芦与人类起源、繁衍相关的传说,[39]闻一多先生也认为“女娲”的原意也是葫芦。
兴隆沟遗址F22还出土了两件人面饰,石制、蚌制各一件。[32]这当是目前西辽河地区发现最早的人像雕塑。马克思曾提到称“偶像最开始是作为死者的雕像被后人祭祀”。[40]民族志记载,我国的鄂伦春人现在依然在供奉一种被称作“阿娇鲁”祖先神偶像,寄居其中的祖先灵魂可以保佑生者狩猎平安、顺利和繁衍。[41]所以兴隆沟遗址这类人面饰品可能是对亡者的偶像崇拜。也有可能是巫术中使用的人偶。弗雷泽认为原始人相信“相似律”和“接触律”。①受这类观念影响,原始先民们便认为自己或巫师可以通过“交感巫术”、模拟活动去对目标事物施加或好或坏的影响。[42]民族志资料记载南非的祖鲁人就有这样的人偶。[33]330而在欧洲某些地区,为了惩罚情人,被抛弃的姑娘会用针刺情人的画像。[33]332现在中国的香港、广东地区,民间依然盛行一种称为打小人的巫术,即通过拜神婆用鞋子等物打击小纸人,以期脱离霉运或者是诅咒他人。
白家村遗址,考古资料显示该遗址晚期遗存中多数墓向都在220-280度之间。笔者认为发掘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白家村遗址墓向多统一向广义的西方,可能是西方被视为了死者灵魂应当回归的祖先之地。[26]据民族志记载,现代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的傈僳族人,在成年人逝去后都会举行一种送灵魂仪式,会请巫师主祭,唱出死者生前的事迹与希望,再唱出《傈僳族的迁徙》等,最终就是为了将逝者的灵魂送归到民族的发祥地,使其回到祖宗身边。[43]
瓮棺葬在老官台文化时期就有发现,主要为小孩葬具,②较为特别的是这种瓮棺或其器盖上常钻有小孔,云南省大墩子遗址发现的瓮棺葬中,多数瓮棺的肩、腹壁处、底部也有1至3个圆形的小孔。[44]这些器盖所用的陶器都是日用品,小孔当是将其作为葬具后专门所制的。民族志资料记载,世界许多地方都在其墓葬中或葬具上发现有这样类似的孔洞,例如“在法国、英国、苏联……巨石建筑的墓……的入口处,常凿一个方形或圆形的小孔……是供灵魂出入的”;[45]而太平洋新几内亚的超卜连兹人认为,他们是从一个大地的孔洞中来的,逝去后也要回到孔洞中去;[46]中国纳西族人前往墓地放置死者的骨灰袋时,会抽掉骨灰袋底部的线,以使死者尸骨可以触碰到土地,以便使死者灵魂可以“自由”地活动。[47]另外,宋兆麟先生也根据永宁纳西族人的民族志材料去理解仰韶时期特殊的小孩瓮棺葬习俗,其认为小孩的年龄小而没有举行成丁礼,不是氏族的正式成员,所以夭折之后不能葬于氏族公共墓地。[29]所以笔者认为这些小孔是在灵魂观念下,为了照顾亡故的小孩的灵魂,使其能够自由出入而专门制作的。半坡遗址中的割体葬可能也是为了灵魂出入而将肉体破坏。
河南省贾湖遗址发现有一件有契刻符号的柄形器。关于其性质,我们认同《舞阳贾湖》作者的观点,该柄形器的性质应当是类似于民族志记载中,澳大利亚阿兰达人的宗教法杖楚林噶,[48]或彝族毕摩祭司在宗教仪式中引导死者灵魂回归祖先之地的指路手杖。详细分析另有《中原地区前文字时代宗教信仰演进研究》一文。
(二)古籍的运用
另外,用历代典籍记载的古代风俗习惯和礼制去验证地下考古资料,上文笔者讨论猪骨性质时就已用到。学界亦早有学者进行运用,如容观敻的《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迹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信仰》、[49]田广林的《论东山嘴祭坛与中国古代的郊社之礼》[50]121-125和王震中的《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51]等。以下列几个例证,以期说明。
湖南省高庙遗址下层遗存中发现有祭坛,其中出土了大量带有凤鸟负日等图案的陶器,[52]这说明了后世楚国所在的地区早至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了太阳鸟崇拜。这在后世史籍记载中有所体现,如关于楚国祖先祝融的传说,《白虎通·五行篇》中将“南方之神”祝融其灵魂(本质)看作是鸟,[53]《古今注》中也记载楚国存在关于楚魂鸟的传说,[54]随州发掘的擂鼓墩一号楚墓中的漆盒上绘有一幅“楚人拜日图”,而后世所传的四灵兽之一的朱雀亦是正好在南方。
西辽河地区的赵宝沟遗址、[55]东山嘴遗址和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各遗址以及全国各地均有发现祭坛遗址。这些祭坛遗址性质的确认就多是依靠古籍的记载。如《后汉书·祭祀下》载“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56]2178《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等。[57]1217考古发现的祭祀遗址多是通过这类古籍记载而得以确定。
兴隆洼遗址中F166的居室墓(M134)中发现了一件骨笛,[58]榆树山、西梁遗址出土了1件刻有几何纹的骨笛F102①:4,[59]舞阳贾湖遗址也有大量素面骨笛出土。[60]根据典籍记载,音乐自古就和祭祀、巫术等精神层面活动密切相关,如商朝的音乐基本就可分为两大类,即“巫乐”和“淫乐”。[61]民族志中亦有记载,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仍在用歌的形式传颂神话和祭祀,例如我国苗族神职人员端公就善长于唱歌诵词。[62]结合这两者,同时分析原始社会生活水平落后,制作精细的骨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当是有精神上的重要作用,而当代民间依然有在晚上吹笛子会招来善鬼的说法。
二、问题与不足
民族考古学在史前信仰的研究中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运用不当,仅仅将民族志资料照搬比对,会使得最终的结果有失偏颇。
比如图腾崇拜的研究,“图腾”一词最早是在18世纪末的民族学专著中出现,[34]92图腾崇拜多在民族志资料中的澳大利亚人、印第安人中发现和证实。作为图腾崇拜象征的有纹饰、圣物和圣地等。[34]118-124许多学者仅仅将图腾崇拜的验证付诸于一种特定的图案,这是不妥的,如在兴隆洼遗址M118中发现,墓主两侧随葬有两具骨架完整、并列摆放、一雌一雄的猪骨。[63]9发掘者认为该墓葬中墓主与两具猪骨架并列埋葬在一起,体现有祭祀祖先灵魂与祭祀猎物灵魂相结合的图腾崇拜意义。[63]24笔者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宗教信仰方面只有人和猪死后都有灵魂的万物有灵观念,而同时期的兴隆沟等遗址的房址、墓葬中也都出现了大量猪骨,体现了当时该地区的居民可能经常以猪为食,由此而产生对猪灵的动物崇拜,祈求动物食物的丰产,猪骨一雌一雄也是这一考虑。而发掘者仅仅通过猪骨架摆放就认为其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还缺乏直接的证据。因为图腾崇拜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祖先与自然物的亲缘结合,原始先民将某一种自然物作为族群或个人的“图腾”,即是认为这些自然物和自身及祖先有着着亲缘关系。吕大吉先生称:“图腾不过就是氏族的祖先,图腾崇拜可以包括在广义的祖先崇拜之中。”[10]497在图腾崇拜的观念下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禁忌或族群仪式。
在史前宗教信仰的研究中,图腾崇拜是很难与自然崇拜相区分开的,因为史前时期的考古发掘中没有文字典籍的出土,原始先民的行为习俗也无法还原,思想层面更是无从了解,也就无法通过地下考古材料直接去证明原始居民对自然物与自身之间亲缘关系的看法,即史前的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很难判断原始先民是否将某种自然物看作其血亲,而这是判断图腾崇拜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在将民族考古学运用于史前宗教信仰研究时,要注意恢复当时的全方位社会经济环境,而不能照搬民族志材料和历史时期的记载,仍要以考古学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的。陈星灿、丁乙等学者也指出民族志材料与考古材料类比研究时要注意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相似等原则。如大地湾遗址随葬的猪下颌骨、白家村遗址随葬野兽獠牙的墓葬墓主多为男性,[26]可以通过性别的区分反映出这些猪下颌骨、野兽獠牙可能有勇武的象征或其载体。再如考古资料中,人形偶像很难以留下诸如“交感巫术”等宗教行为的痕迹,所以在史前宗教研究中,当将其主要视为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西安半坡遗址的葫芦形器,笔者之所以认为可能与女性生殖崇拜有关,一个出发点便是仰韶文化时期半坡遗址大量的鱼纹和蛙纹,而学界多将此两者当作女性生殖崇拜的体现之一。
史前宗教信仰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研究领域,因为在落后的原始社会中,许多事物都被赋予了迷信的思想内涵和作用,如文苑仲先生曾谈道:“在蒙昧时代,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原始艺术的雕塑……等在当时可能就是一种宗教或巫术活动”,[64]323王仁湘先生也在《人神之间:史前中国造神运动中的三次艺术浪潮》的系列讲座中谈论道:“对于最初出现的造型艺术……我认为它是一种灵魂艺术,可以明确地说是造神艺术,他们画出来的图像是他们要表现的神灵偶像”。[65]但就是因为资料的丰富和性质难确定性,使得这一主题的研究经常误入一个“利己主义”的歧途,即是将材料不经多重考证便加以自我定义。
注 释:
①“相似律”:原始人在特点的一些事件产生一种想法,即一个事件总是紧随着另一事件而出现,认为只要掌握了事物这个关联的奥秘,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接触律”:物体切断实际接触后仍可在远方互相作用。
②后来在姜寨等遗址中也发现有成人瓮棺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