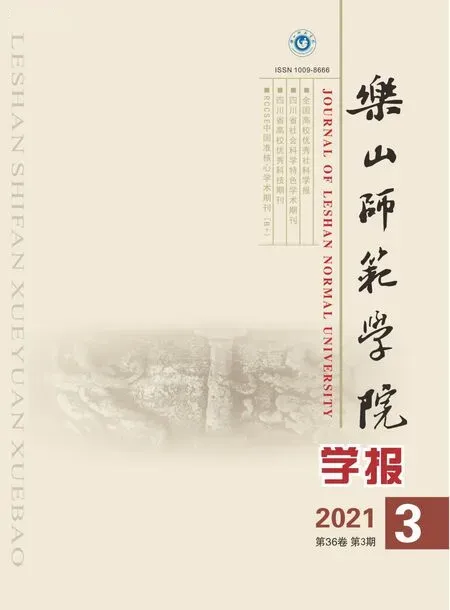宋刊《注东坡先生诗》的史学和文献价值
彭文良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沙坪坝 400044)
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三人合注的《注东坡先生诗》(42卷,简称“施注”)是今存最早的编年注本。关于三人的分工问题,最早见于陆游所作的序:“吴兴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属游作序。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工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赅洽。”[1]377根据该书实际情况看,句注当为施元之与顾禧共同完成,题注则是施宿独立完成。施宿于嘉定六年(1213)初刻此注,即后世所称的嘉定本,今存20卷,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景定三年(1262),郑羽补修重刻,即后世所称的景定本,今存32卷,由纽约辗转归藏上海图书馆。该注离苏轼所处时代最近,故最为可靠,在苏诗注释史上具有奠基性质。凡见过该注的学者皆盛赞不已,或誉为“海内孤本秘籍”[2]90,或叹为“人间奇宝”[3]。该注在文学上的意义早为学者公认,但在史学、文献,以及艺术方面的价值则尚未引起学人重视,今略作引论。
一、题注的史学价值
施注的文学价值主要见于句注,今特就其题注的内容及价值论之。施氏题注共430多条,6.6万余字,虽然还占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却是全书的精华。句注主要解释词句来源及含义,题注内容则异常丰富,下面我们据其性质分述。
(一)人物传记类的史学价值
此类注往往专论某一个人的家族谱系、籍贯、出身、仕宦经历、出处大节。根据具体人物的不同经历,而各有详略,最详者多达700余字,最略者往往亦数十字。这些材料往往成为《宋史》本传的直接来源。比如《李诚之待制六丈挽辞》题注为:
李诚之名师中,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时政。举进士。庞庄敏辟为县。杜、范、富公皆荐其有王佐之才。其志尚甚高,每见人主,多陈天人之际、君臣大节,自汉以下不道。请以进贤退不肖,为宰相考课法。在官不贵威罚,务以信服人,至明而恕。提点广西刑狱。知邕州萧注欲以峒蛮讨交址。经略使萧固、转运使宋咸,皆表里其说。诚之召注,折难之,遂罢议。会蛮徭入追亡,害巡检,注又张皇为骇奏,仁宗为之旰食。诚之劾注,并按固、咸,皆坐贬。熙宁初,拜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时薛向自贬所知凤翔,诚之言向在陕西,人畏忌之,闻其来皆破胆,愿置河北使立效,遂改潞州。西人入寇,以诚之知秦州。王韶上平戎策,神宗使得管勾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上奏乞筑渭源上下两城,遂开边衅,诱致青塘包顺。又言渭源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笼商贾利以治田。诚之极言其不便,谓所得不补所亡,渭源之田尽出诞妄。王安石当国,力主韶议。为罢诚之,遣开封府判官王克臣内侍押班,李若愚按实还奏,与李诚之叶。又遣沈起,乃以他田为解,诚之落职镌官,后还故职。因旱灾上书,其略曰:“今日之事,非有勤民之行,应天之实,臣恐不足以塞天变。一切利害,曾何足数!望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诣公交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轼、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臣泣血雨泪而拜封章,陛下闻臣此言,忍不感悟,臣未尝有一言及钱谷甲兵者,直欲以伊尹致君之事为师,不有人患,谁兴厉阶。臣欲杀身,无益于事。”书奏,责散官安置和州。诚之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诚之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后二十年,言乃信。王安石既恶之,又斥其所主,欲夺其待制,不果。后因上书,吕惠卿摘其语以激上怒,遂得罪,终其身。元丰元年,卒。此诗一篇形容诚之平生略尽,至于叹息其不遇,深致意焉。“愿斩横行将,请烹干没儿。言虽不见省,坐折奸雄窥”者,盖意有所指也。“邪正久乃明,人今属公思”,盖元祐间群贤毕用,而诚之死久矣,仅能追复旧职云。
全注凡673字,述尽李师中生平。这段注文被剪裁成为《宋史》本传:
李师中字诚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时政。举进士,鄜延庞籍辟知洛川县。庞籍为枢密副使,荐其才。召对,转太子中允、知敷政县,权主管经略司文字。提点广西刑狱。初,邕州萧注、宜州张师正谋启边衅,注欲以所管蛮峒酋豪往讨交址,云不用朝廷兵食。诏下经略使萧固、转运使宋咸,二人为注所饵,合词称便,而师中至,诏以注奏付之。师中邀注来,难之曰:“君以酋豪伐交址,能保必胜乎?”曰:“不能。”师中曰:“既不能保必胜,脱有败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罢议。会蛮徭 申绍泰入追亡者,害巡检宋士尧,注又张皇为骇奏,仁宗为之旰食。师中言无足忧,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敛失众心,卒致将率败覆,按法当斩。于是注责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贬。熙宁初,拜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4]10676—10678
为了节省篇幅,此处只节选了本传一部分,但我们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不仅内容一致,连用语亦高度重合,完全可以肯定本传内容实取自此注。
由于施注为本朝人所注,所距时间最近,可靠性最高,故《宋史》作者大量采信题注。类似情况非常多,比如:《送刘道原归觐南康》与刘恕本传、《送俞节推》与俞汝尚本传、《同王胜之游蒋山》与王益柔本传、《次韵朱光庭初夏》与朱光庭本传、《送程七表弟知泗州》与程之邵本传、《次韵王滁州见寄》与王诏本传、《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与晁补之本传、《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与王古本传,等等。
题注的传记价值不仅仅表现为《宋史》的材料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有的材料可补正史之缺。《宋史》为官方所修,自然只能择其要者,对那些史官看来并不重要的人事往往舍去。而施注为了取便读者,自然无此偏见,所注内容为正史所无,此部分价值尤高。比如与苏洵、苏轼交往甚密的刁约(字景纯),《宋史》无传,全赖题注保存,见《哭刁景纯》:
刁景纯名约,丹徒人。少卓越有大志,刻苦学问,能文章。始应举京师,与欧阳永叔、富彦国声誉相高下。及与永叔同试礼部,时宋宣献公名能知文,盛称二公,宜在异等,及奏名如其言。为集贤校理。苏子美因会客得罪,景纯在会中,通判海州,守太平、婺、越、扬、宣五州。同判太常寺,遂乞挂冠。景纯践歴馆阁踰四十年,典章故实,贯穿网罗,有问者焉,浩浩乎不可穷巳。英宗在宫邸,知之。及即位,谓宰相曰:“刁某可召使也。”会执政非所知,遂不果用。平居裕和,不与物争。当官正辞,毅然有不可夺之色。其在宠禄之际,泊如也。故屈于为郎,施不大耀。士友叹惜,而景纯未尝以为恨。好急人之难,海内之人识与不识多归之。不治产业,宾客故人常满其门,尊酒燕娱无虚时。重义轻施,有古人之风。年八十四属疾,王左丞和甫守润,往问焉,隐几笑语如平时。和甫登车,已逝矣。妻江,先景纯一年卒。东坡此诗形容其平生略尽云。
(二)关于同期人物的交游材料的史学价值
苏轼一生交游甚广,可以说北宋中后期政界、文坛、方外,凡有影响的人物基本都与苏轼有不同程度的往还。而时过境迁,这些重要的交游细节往往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庆幸的是,此注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材料。比如《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赠元素》题注:
元素,姓杨氏,名绘,汉州绵竹人。少奇警,读书五行俱下。登上第,入馆,为开封推官。知眉州,徙兴元府。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知谏院。论事语侵宰相曾公亮,神宗既行其言,虑公亮不自安,改兼侍读。且以手札命滕甫喻旨,奖予甚渥。然元素讫不就,曰:“谏官不得其言则去,经筵非姑息之地也。”未阅月,复知谏院,入翰林为学士,拜御史中丞。时安石始得政,纷更诸事,贤士多引去,元素极言其害。新法既行,抗论尤力,罢为侍读学士、守亳州,徙南京。移杭实与陈述古襄易地。东坡与元素交契最厚,又俱以论新法去国,在杭满三岁,时熙宁七年秋七月也。元素将至,赋二词以迎之。来未阅月,坡得密州以去。重阳前一日,席上赋《浣溪沙》词。又和元素《南乡子》。未行,而元素召还翰苑,自撰《劝金船》。坡既属和,又作《定风波》送元素。遂同访李公择于吴兴,作六客堂,张子野赋《六客词》。至润又和元素《菩萨蛮》词,自此分携。而元素以事贬荆南节度副使。未几,分司南京,起知兴国军。元祐初,复天章阁待制,再守杭州而卒。二公长短句倡酬凡七八,而诗止两章,其一在黄州次韵,恐不应寂寥若此,疑有亡逸尔。
此段材料除涉及杨绘在朝行迹外,非常简要地勾勒了与苏轼的交游梗概,相当于两人的交游提纲。我们查《宋史》杨绘本传[4]10448—10450,发现这些重要材料无一字见存。无论从了解杨绘,还是掌握与苏轼的交游论,此注皆有正史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时政类材料的史学价值
此类注包括当时朝野各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价值最高的是关于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度、人事变化、党争等,无论是对苏轼文学,还是对宋史研究,这都是极重要的史料。如《孙巨源》题注:
孙巨源名洙,广陵人。未冠,擢进士第。欧阳公、吴文肃举应制科,进策指陈政体,韩忠献读之,太息曰:“今之贾谊也。”同知谏院。后为翰林学士。神宗欲用为参知政事,忽得疾不起,年纔四十九。巨源博闻强识,明练典故,文辞典丽,有先汉之风。在谏院时,王介甫行新法,多逐谏官、御史。巨源心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但恳乞补外。知海州。旣会于此,东坡与刘贡父、刘莘老皆坐论新法以去;巨源旣同舍,雅相厚,又居谏省,而此诗云“终岁不及门”,则异趣可见。又用柳子厚“王孙、猿”事,终以“子通真巨源,绝交固未敢”之句,其责之深矣。子由亦和此诗云:“立谈信无补,闭口出国门。”然东坡与巨源交契甚厚,旣别于海州景疏楼,后登此楼,怀巨源,作永遇乐词以寄。元祐间,同子由微雪访王定国,子由言:“昔与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为之悲叹。”
此段材料也被《宋史》采用:
孙洙字巨源,广陵人。羁丱能文,未冠擢进士。包拯、欧阳修、吴奎举应制科,进策五十篇,指陈政体,明白剀切。韩琦读之,太息曰:“恸哭流涕,极论天下事,今之贾谊也。”再迁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治平中求言,以洙应诏疏时弊要务十七事后多施行,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乞增谏员以广言路。凡有章奏,辄焚其稿,虽亲子弟不得闻。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补外,得知海州。[4]10422
题注前半部分虽被引入《宋史》,实则后半部分更为重要,较详细展现了变法过程中苏轼与王安石、孙洙、刘攽、刘挚等人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同时还对该诗作的部分句子作了简要解释,没有这些疏解,就算读者借助句注能明白其典故来源,也未必能明白其隐晦曲折之用意。所以此注相较正史,反而成为我们研究当时时政更为重要的史料。
二、题注的文献价值
题注除了前文所论的史学价值外,其文献价值亦极高,仍根据其内容、性质分述之。
(一)苏诗墨迹、刻石类材料的传播学意义
此类材料主要记载苏诗墨迹在生前身后收藏、入石情况,是研究苏诗传播的重要资料,比如《鸦种麦行》题注:
先生以事至湖,赋诗以赠莘老。十二月来,遂为莘老作《墨妙亭记》。记文以党禁磨去,独碑目数存焉。记尾所谓“列其名物于左云”,盖亦先生所书也。有改定本墨迹藏奉化黄氏师是龙图家,又书此诗于后,题云子瞻。词并书皆当吴兴时作。楼参政大防尝跋云:《墨妙亭记》惜未登之石,《鸦种麦行》有章草体,别是一种风流。
和《次韵孙莘老斗野亭寄子由》题注:
此诗墨迹,钦宗东宫所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刻石余姚县治。诗尾题云:予自宜兴赴文登,过邵伯埭,埭上僧舍小亭名斗野亭,有孙莘老长韵。舍弟子由小诗,乃次莘老韵。留示子由。时子由以校书郎召,将过此也。
这类题注详细记载了墨迹内容及藏家、刻石地点,展现了苏轼作品在生前身后的命运。
(二)苏诗抄写传刻材料的校勘意义
部分题注保留了宋刊集本和墨迹的内容,不仅可以还原苏诗在当时的流播情形,在苏诗研究史上还具极高的校勘价值。比如《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题注:
集本云:“仙山灵雨湿行云”,“戏作小诗君一笑”。吴兴向氏有毕良史旧藏墨迹,“灵雨”作“灵草”,“一笑”作“勿笑”,今从墨迹。后又题“曾坑壑源”四大字。辅时为闽漕。
和《合浦愈上人以诗名岭外将访道南岳留诗壁上云闲伴孤云自在飞东坡居士过其精舍戏和其韵》题注:
此诗墨迹在玉山汪氏。集本云“不知老奘几时归”,墨迹作“几年”,后题“元符三年八月十日”。
此两处题注皆记载了苏轼墨迹的流播情况,以及集本与墨迹异同。由于施宿所见墨迹出自苏轼之手,可靠性高,故此类题注在更正后世文献错误方面具有无法逾越和取代的地位。比如《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题注云:
墨迹云:“蒙示二十一日别文之后佳句,戏用元韵记别时事为一笑。”后题云:“虽为戏笑,亦告不示人也。”四诗笔札皆精絶,楮墨如新。而每诗皆丁宁切至,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虑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吁,可叹哉!
此注完整保留于景定本。今存嘉定本相同位置处,从题目至“札皆精绝”前全缺。至清初宋荦时,嘉定本此处大部分当完整,邵长蘅删补《施注苏诗》时将此部分内容完全删掉。至查慎行始将此部分内容割裂为两部分,先于题下引施氏题注前一半:
石刻云:“请一呈文之便毁之,切告切告。蒙示廿一日别文之后佳句,戏用元韵记别时事为一笑。”末又云“虽为戏笑,亦告不示人也。”
后于篇末以按语形式引后部分:
慎按:施氏原注云:阴字韵四诗墨迹笔札皆精絶,楮墨如新。而每诗皆丁宁切至,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虑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吁,可叹哉!此段新刻本删去。今补録。[5]卷40,22
查氏瞒天过海,妄改施注。首先妄改“墨迹”为“石刻”,且妄补“请一呈文之便毁之,切告切告”一段;妄改“二十”为“廿”。其次,于后一部分再忘加“阴字韵”三字,殊无必要;然后将施氏原注开篇的“墨迹”二字与“笔札皆精绝”连在一起,既重复,又不通。估计是因为所见嘉定本残缺,又未见景定本,遂妄改且据为己注。至冯应榴又引为:
施注:石刻云:“请一呈文之便毁之,切告切告。蒙示廿一日别文之后佳句,戏用元韵记别时事为一笑。”末又云:“虽为戏笑,亦告不示人也。”□□□札皆精绝,楮墨如新。而每诗皆丁宁切至,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虑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吁,可叹哉!榴案:此段施注宋刊本前半皆残缺,惟“札皆精絶”以下乃今所存施注原文也。[6]2098
冯氏明言所见部分已经残缺,且描述情况与今存嘉定本完全一致,表现出应有的诚实;但所引前一部分,非施氏原注,实际完全引自查注,又不作任何无说明。唯一改进的地方是把查注所引的割裂部分重新聚合在一起,部分地恢复了施注原貌。至王文诰《编注集成》再引为:
施注:墨迹云:“请一呈文之便毁之,切告切告。蒙示廿一日别文之后佳句,戏用元韵记别时事为一笑。”末又云:“虽为戏笑,亦告不示人也。”札皆精絶,楮墨如新。而每诗皆丁宁切至,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虑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吁,可叹哉![7]3482
王氏虽将查、冯所改之“石刻”,恢复为“墨迹”,但“请一呈文之便毁之”一段,仍依查、冯之旧。“札”字前原缺三字,查氏乱改乱补,冯氏留其空缺,而王氏不作说明,又显得语意不通。故若无施氏此注,我们完全无法更正诸家的以讹传讹的错误。
此外,从艺术、印刷等角度看,此注价值亦极高。见过景定本的傅增湘曾云“字尽俊美,楮墨明净,生平所觏宋代佳刻,殆难其匹。”[2] 88事实上,嘉定本的艺术价值更高,清俊疏朗,明秀整洁,见之便觉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