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的逃逸:德勒兹论艺术中的节奏
高 畅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一、数与和谐:好的节奏
节奏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悬念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其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创作中的地位——节奏掌控着艺术的时间。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无不接受节奏的安排与调配,一首诗、一支曲或是一幅画、一段影像都必然遵循着某种节奏,正是节奏的这一责任使其天生不允许拥有悬念、天生地拒绝混乱,它正襟危坐于文本之中,呈现为清晰的结构与整体的态势,坚守着某一种风格的格式或章法,为观者提供进入艺术文本的重要线索。
从“节奏”这一词语本身,即可见出节奏概念的核心内涵。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语言表达中的“节奏”概念》一文中从词源学的角度较为细致地考察了“节奏”(rhythm)一词的源头及其意义的演变。本维尼斯特为什么会关注“节奏”这个概念?如他在这篇论文的篇首所说:
“节奏”概念是影响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观念之一。在我们意识到持续的时间和重复支配着人类行为的时候,以及在超出人类的范围之外,我们将节奏投射到事物和事件当中的时候,节奏甚至可以用来区分人类行为的不同类型,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这种人与自然在时间之下的巨大统一,以其间隔和重复,作为使用这个词语本身的条件。在现代西方思想的词汇中,节奏这个术语的普遍化是从希腊语经过拉丁语传到我们[1]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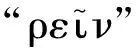
本维尼斯特通过考察指出,在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中,“ρυθμós”是一个关键术语,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中见出。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记录了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
那些以万物出于同一底层物质的变化的人认为“疏”与“密”为变化之本,他们同样认为在元素上的诸差异引致其它各种的质变。他们说这些差异有三:形状,秩序,位置。他们说一切“实是”只因韵律,接触,与趋向三者之异遂成千差万别;韵律即形状,接触即秩序,趋向即位置;例如A与N形状相异,AN与NA秩序相异,Z与N位置相异[2]。
据本维尼斯特的考证,原子之间三种差异的第一种“韵律”的希腊语原文即是“ρυθμós”,亚里士多德的引述确认了“ρυθμós”的意思为“形式”,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示例所显示的那样,A与N之间的差异即体现为形式和构造。
基于此,关于“ρυθμós”这个词语本身,本维尼斯特最后的结论是:(1)从最早的用法至阿提卡时期,“ρυθμós”都并不意指“节奏”;(2)“ρυθμós”从未应用于描述海浪的规律性运动;(3)“ρυθμós”的固定含义是“独特的形式,匀称的形象,排列,布置”,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会有改变。同样,“ρυθμós”的派生词和复合词,无论是名词性的还是动词性的,也从未指向除“形式”之外的其他含义[1]285。
通过本维尼斯特的考证可知,“ρυθμós”的本义为“形式”,其揭示出物质元素在构型与布置层面上的特质。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曾总结出西方美学史中“形式”概念的五种含义,他将“形式”的第一种含义称作“形式A”,“形式A”可以指向古希腊建筑、雕塑、音乐等艺术作品的可测量性、和谐性与秩序性,即是指艺术形式中各要素的排列,“古代希腊人用来表示美的词,在其词源上是指各部分的排列与比例”[3]。
显然,依据本维尼斯特的考察,“节奏”概念的本义应当归属至“形式A”的指涉范围,其与艺术文本(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的可测量性,和谐性和秩序性密切相关。可以看到,“节奏”概念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已然确立了其最核心的形式意味,这种可测量的形式在音乐中表现为拍节程式,在诗歌中体现为格律体制,在绘画中呈现为位置经营,在影像中内蕴于起承转合。节奏的形式意味将节奏确立为一种秩序,如柏拉图所言,“运动中的秩序称作节奏”[4],在古希腊思想中,这一秩序直接体现为数与和谐。而节奏概念自诞生伊始就一直为数与和谐所界定,因为“数与和谐”是“好的节奏”的保障。那么,何为“好的节奏”?
古人们很早就发现了节奏的强大力量,这集中体现于他们对音乐艺术的崇尚和理解当中。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开始探究音乐的奥秘。这个以道德和宗教为特征的学派将音乐视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聆听音乐同信仰宗教、沉思哲学一起被他们视为引导灵魂的重要方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音乐艺术具有净化灵魂的道德教育功能,“好的音乐”可以使灵魂得到完善,“坏的音乐”则会腐蚀灵魂,而“好的音乐”必然要求“好的节奏”,“好的节奏”则出自“好的灵魂”。毕达哥拉斯学派忠实的捍卫者达曼这样解释,“适当的节奏是一种有规则的精神生活的符号,并且向人们教授精神的和谐”[5]111;换言之,好的节奏即在于能够教育聆听节奏的人们坚守美德和品质。可以看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节奏的表现效果与社会功能层面定义节奏之“好”,他们认为好的节奏能以适宜的表现形式培养听者良好的道德品性、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一观点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中得到了更为集中且深入的阐发。
追随着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深化了音乐净化灵魂的观点,他们尤为强调音乐艺术的政治意义与教育功能。因为节奏和乐调能够强有力地进入至心灵深处,如果采用合适的教育手段,心灵将沉浸在节奏和乐调的美好之中而获得净化,反之,不适当的节奏和乐调则会导致心灵的丑化。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直言:“美与不美要看节奏的好坏。”[6]好的节奏源于心灵的善良,其可以表现勇敢和聪慧的生活。柏拉图指出,鉴于适度的观念和优雅的姿态在人类的行为中普遍缺失,我们应当通过乐调及节奏的和谐来帮助人们抵制无序与恶习。
事实上,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古希腊就形成了从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层面认知与规约其内在要素(和声、旋律、乐调、节奏等)的形式特征与表现效果的乐教传统。“好的节奏”即是这一乐教传统中至关重要的命题。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从节奏表现的外在影响力来看,节奏与人之气质性情的天然联系使得节奏必然肩负起灵魂净化与道德感化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阐发的是,从节奏形态的内在特性来看,正是节奏本身所具有的和谐属性才使得节奏能将这一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明确了何为“好的节奏”之后,还需进一步分析的是,节奏何以为“好”?
节奏因数与和谐而“好”。
毕达哥拉斯通过铁匠铺里铁锤落到铁砧上的声音,发现了谐音与音程之间的数值比例关系。从这一比例关系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之和谐的思想推举到了宇宙天体,提出了“宇宙谐音”的观点。他们认为,各种形态大小、运动速度、间隔距离互不相同的宇宙星体有秩序的运转方式合乎数的比例,因而产生了和谐的乐调。亚里士多德对此这样解释: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然认识到音律的比例及变化都可以通过“数”来计算,由此他们联想到自然间的万物似乎都可以用“数”去解释和规范;“数”遂成为宇宙自然间的第一要义,数的要素即是万物的要素,而全宇宙就是一个数,同时也是一个和谐的乐调。“宇宙谐音”的观点对于艺术研究影响深远,其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阐释艺术的可操作性的思考路径,这一路径专注于探寻艺术形式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结构构成。而从“数”的角度来观照节奏,可以说,节奏即是数,好的节奏即是和谐的数;节奏可被抽象为数量关系的结构化图式,这一图式揭示出乐曲旋律间音调高低、节拍快慢、段落长短等运动形式之数值的有序排列及变化。如中世纪的音乐美学论著《音乐守则》中所言:“旋律中所有甜美的东西都是数以复杂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而节奏中所有使人愉悦的东西,既在旋律之中也在节奏的运动之中,只源于数;声音转瞬即过,而数则犹存。”[7]167
但必须承认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毕达哥拉斯的耳朵。我们可以用数去分析节奏之和谐秩序的构成原因,但流淌于听觉感知中的旋律与节奏并非机械的算数程式,而是令人满心欢娱或忧伤的和谐声响。音乐创造的审美理想即在于追求和谐,和谐的内涵在于音乐文本中对立元素的统一协调与适度恰当的形式法则。“好的节奏”即植根于此:统一协调指向对立元素的相融共生,比如节奏中变化起伏的长短疾徐。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勒劳斯所解释的那样,“和谐是许多混杂要素的统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5]114。适度恰当则指向一种有节制的情感表达与共同遵守的形式体制,(1)希腊的音乐起源可追溯至古代,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的特潘德创立了音乐的标准,他所确立的音乐形式基于古老的礼拜仪式歌曲,被希腊人称为“nomos”,即法则或秩序的意思。这一法则是一种由七部分组成的单声部旋律的曲调,后来变成了强制性的形式。参见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这一形式体制以实现音乐的社会功能为目标,要求节奏的表现效果呈现出适宜得体的和谐,如罗马帝国时代的音乐研究家普鲁塔克所言,“音乐的精义在于对所有事物给予适当的度量”[8]。
由数与和谐所界定的“好的节奏”从节奏的构成和效能层面为节奏理论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诚如塔塔科维兹所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后来的那些继承了他们观点的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好音乐与坏音乐的区别上。他们要求对好音乐要给予法律的保护,而在这个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随意和冒险将是不允许的。”[5]109在今天看来,将“好与坏”作为评判节奏的标准过于单一且绝对,而节奏似乎也不再被赋予提升道德、净化灵魂的重要职能。只是,“好的节奏”也许已经过时,但“没有悬念的节奏”则俯拾即是。可以看到,在从古代到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当下,节奏一直都处在数与和谐的阐释框架之中。因为这一框架稳定且实用,其以客观而理性的视角为艺术中的节奏研究提供了可靠有效的分析思路及方法。而与此同时,塔塔科维兹所说的“随意和冒险”依然被这一框架阻隔在外,直到节奏决定从数与和谐中逃逸出来。
二、节奏开始逃逸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节奏开始逃逸的某个具体时间点,但节奏的逃逸很容易被发觉,因为其偏离了数与和谐的阐释框架。事实上,在奥古斯丁那里,节奏已经开启了一次逃逸,我们甚至有理由将其视为节奏的第一次逃逸。
如前文所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节奏的研究,学者们的目光都聚焦于节奏表现的情感力量与道德功效,聆听节奏的具体过程反而被忽视,奥古斯丁令人欣喜地打破了这一局面。奥古斯丁的音乐思想基本承袭了古希腊音乐观念中数的眼光与对和谐、适宜原则的追求。而对于节奏,他则有创新性的见解,在他唯一流传至今的美学著作《论音乐》中,他从审美知觉与经验的角度将节奏区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
假如我们正在朗诵诗歌,你认为诗中所含的那四种短长格存在于何处?是仅存在于可闻的朗诵声中,还是也存在于与听觉有关的感觉印象中,存在于朗诵者的动作中,或是由于诗章已为我们所熟知,在记忆里也有它的存在……我将乐意问,你认为这几种节奏里何种最完美,但是你看……第五种又出现了,它存在于对所获听觉印象的本能的欣赏中,建立在我们因音程的有序性而欢喜、因其中的缺陷而愤慨的基础上。我认为应把它与所有其它几种节奏区别开来,因为产生声音是一回事(我们将此归于人体),听见声音(在声音的影响下,灵魂通过肉体感知它)、加快或减缓声音、记忆声音又各自是另一回事,而依据某种自然法则的力量,对所有这一切作出判断,接受或拒绝它们则又是一回事。
在五种节奏中,让我们把第一种称为音响的节奏,第二种称为感知的节奏,第三种称为运动的节奏,第四种称为记忆的节奏,第五种称为判断的节奏[7]77。(2)奥古斯丁的这段论述出自他《论音乐》的最后一卷第六卷——“从感觉中的节奏追溯真理中不朽的节奏”,这部书成书于389—391年间。国内对《论音乐》的节译刊于朱立元主编的《西方审美教育经典论著选》第1卷的第428-463页(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译者潘道正是根据Pendragon Press1986年的版本译出。这一译本中将引文中的五种类型译为“五种类型的数”:“第一种为审判之数,第二种为提升之数,第三种为记忆之数,第四种为感觉之数,第五种为声音之数。”按照何乾三的说法,拉丁文numerus同时有数字、节奏之意,她本人亦采用了“节奏”的译法。参见钟子林:《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1999年版,第415页。结合塔塔科维兹的著作,可见两种译法均为可行。综合考察,《中世纪美学》中所载的奥古斯丁的原文更为紧凑连贯,故在此处引用更为适合。事实上,两种不同的译法正好揭示出西方古代美学将节奏的本质视为数的观点。当然,此处着重突出的是奥古斯丁研究节奏的知觉经验的角度,故而不在译法的相异问题上多作滞留。
奥古斯丁对节奏的分类揭示出知觉者感知节奏的具体过程。这“五种节奏”并非是平行层面上的区别,而是在一次由创作者开启的完整的声响知觉活动中节奏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内在于创作者的“运动的节奏”指向创作主体血脉的震动与循环往复的呼吸,“音响的节奏”指向存在于声响文本中客观的节奏形式,“感知的节奏”指向知觉主体在听到声音的那一个个连续的瞬间中所生发的直观体验,“记忆的节奏”指向知觉主体心灵内部先在的节奏记忆,“判断的节奏”指向对节奏表现的整体鉴赏。奥古斯丁对节奏的分类实则回答了他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当人在听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9]跳出数与和谐的阐释框架,奥古斯丁真正注意到了“听”的知觉。塔塔科维兹切要地总结了节奏的这一次逃逸:
在奥古斯丁看来,审美经验本身也具有美的本质特征,即节奏。由于美的事物中含有节奏,因而对它的体验必然具有节奏;离开节奏,审美经验便不可能存在。……古代学者曾从数学的角度(毕达哥拉斯学派),或教学法与伦理学的角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节奏进行分析和归类,奥古斯丁则通过对感知、记忆、动作、判断等各类节奏的区分,引进了心理分析理论。他有关节奏的心理分析理论的特征在于肯定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由自然赋予的永恒不变的心灵节奏。这在一切节奏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它,我们既不能感知,也无从创造节奏[7]65。
节奏之所以能在奥古斯丁这里发生逃逸,是因为奥古斯丁注意到节奏与人的心灵和感觉密切相关,他引入的知觉和记忆的概念使节奏得以从冷静的数中脱身,进入到节奏之创造和感知的内部场域。只是在节奏观念史中,这一次逃逸可能只是一个微小的凸起,其隐没在数与和谐的阴影之下,几乎要被抹平。
而在19世纪的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这里,节奏终于冲破了数与和谐的框架,曾经微小的凸起蜕变为不断扩大的逃逸出口。汉斯立克直言,“音乐的美跟数学是不相干的”,“审美的领域是在这些初级比例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开始。数学只管原始素材,使它能接受精神的处理,在最简单的关系中数学隐蔽地起它的作用,但乐思无需数学就能诞生出来”[10]64。也就是说,可从本文中离析出来的数与比例无法解释乐思中的情感与想象,或者说,音乐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其与观者的知觉体验直接发生关系。汉斯立克有这样一段论述:
一切音乐要素相互之间有着基于自然法则的秘密联系和亲和力。这些亲和力无形地主宰着节奏、旋律以及和声,并要求人类的音乐必须遵循它们的法则,并且使一切违反这些法则的结合显得丑恶逆理。它们虽然不是以科学意识的形式存在着,但却本能地为任何有教养的听觉所具有。因此,乐音组合中凡是有机的、合乎理性的东西,或是逆理的、反自然的东西,都可单纯通过直观被这种听觉所感受,不需要什么逻辑概念作为尺度或比较点[10]52。
这段论述颇有奥古斯丁的味道,当聆听音乐的耳朵跳脱出辨析音乐形式的数理意味之时,它忽然间就领悟到音乐元素与自然法则、生命体验之间的呼应;由这一思路穿过节奏,可以发现,作为形式的节奏就不仅仅是数理形式的表现,而是富有生命意味的运动。
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显然践行了这一思路,她的思考亦受到汉斯立克的影响。她认为音乐的本质“是虚幻时间的创造和通过可听的形式的运动对其完全地确定”[11]144。朗格所言的时间并非可为数值所标注的时间,而是音乐艺术所生成的虚幻的时间序列,“它与实际的、科学的时间不仅存在着量的不同,而且存在着整体结构的差异”[11]127。朗格借用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描述这一时间序列,指出乐音的运动形式是纯粹的绵延,是一种活的、经验的时间意象,而节奏在这一时间意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包容于流动的绵延当中,音乐中的节奏反映了生命机体的连续运动。由此可见,朗格是站在生命体验与时间形式的角度观照节奏,她将节奏性视为生命活动最独特的原则,尽管节奏的重复性与规律性显而易见,但她否认了重复是节奏的本质,因为节奏并不依赖周期性的运转与均匀划分的时间,从时间绵延的角度来看,“节奏的本质是紧随着前一事件完成的新事件的准备。……节奏是在旧紧张解除之际新紧张的建立。”[11]146朗格将节奏的运动比作一个接一个的冲浪,其连接了音乐形式在绵延中的起伏与动静,使得生命体验的运动性与延续性在音乐节奏中彰显出来。在朗格这里,节奏延续了汉斯立克为其设定的逃逸路线,与绵延的内在时间和生命缠卷在一起。
我们当然无法穷尽节奏所有的逃逸路线,在杜威、卢卡奇、列斐伏尔、梅肖尼克、阿甘本等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节奏面朝着不同方向,以各种方式在继续逃逸。而在前文所述的内容中,可以发现,节奏同时也遵循着一种向其自身折叠的内在逃逸路线,在知觉和记忆的助攻下,节奏一直在找寻属于自身的、自律性的真相。而这一真相在德勒兹那里得到了最具想象力的彰显。
三、德勒兹:节奏—界域
行文至此才进入德勒兹多少有些偏题的嫌疑,但前文的论述对于理解德勒兹的节奏言说至关重要。如果说上文以对“节奏”的词源学考察为起点大致勾勒出节奏在观念层面的逃逸史;那么在德勒兹这里,他一方面续写了这一逃逸史,另一方面,他发掘出节奏自身的逃逸方式与逃逸力量,他让节奏充满悬念,赋予我们观看艺术的另一种新奇的眼光。
对于本维尼斯特对节奏的语言学考察,德勒兹并不信服,他认为这一被视作权威性的文本有些含糊不清,因为本维尼斯特援引了德谟克利特和原子论,却并未考察水力学的问题,《千高原》中这样解释:
最近关于节奏、关于此种观念起源的研究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据说节奏与波浪的运动无关,而是指涉着普遍性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有规则的、有着整齐节拍的”运动。然而,节奏和节拍决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正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论述节奏的人之一,那么,不应该忘记,他正是在波动的情形之中论述的,而且,原子所形成的形式首先就是不可度量的聚合体、平滑的空间(比如空气、海洋甚或大地)。确实存在着某种可度量的、有规则的节奏,但它相关于堤岸之间的河流或一个层化空间的形式;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无尺度的节奏,它相关于流的涌动,也即一股流占据一个平滑空间的方式[12]522-523。
本维尼斯特对节奏的考察侧重于这一词语本身的含义,德勒兹的微辞并不能否定本维尼斯特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分歧也并非此处论述的重点,重点是从德勒兹对本维尼斯特的质疑中所反映出的他的节奏观念,德勒兹的绝妙之处即在于他从空间的视角观照节奏。
德勒兹明确指出节奏与节拍的绝对差异。在节奏观念的逃逸史中,节奏与节拍即是一组非常关键的概念,诚如日本学者野村良雄在《音乐美学》中指明,节奏理论中最严重的混乱即在于把节奏和拍子这两个概念混淆甚至等同起来。野村良雄的观点是:“拍子是被合理地设计出来的,被人为地、机械式地规定出来的东西。而节奏,从本质上说,是由于这类东西才具有自由的生命的。但是,节奏的本质决不是清一色的、全都是合理性的东西,我们还必须承认它有某些非合理性的、甚至是超合理性的东西。”[13]野村良雄还援引了德国音乐美学家梅尔斯曼的观点以补充自己的结论——旋律法与和声法是以乐音为基础的。乐音的连续与音响,水平性的与垂直性的音程,都是具有素材上的直接性的声响现象。但是,声响的节奏性根源则存在于声响素材的形式之外,存在于时间之中,因此,节奏力量的根源实际上是超音乐性的东西。可以说,野村良雄抓住了节奏使乐音受到生气灌注的根本原因,正是节奏的非合理性与超音乐性赋予乐音以生气。节奏的非合理性指向节奏不同于节拍程式之客观理性的主体感性,节奏的超音乐性指向节奏不受限于乐音材料之物质性的自由的生命力量。野村良雄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苏珊·朗格那里我们也看到了相似的见解。这是节奏对数的反驳,节奏的内在力量并非来自可测量、可计算的节拍划分,而是来自一种非合理性的冲动。
而在德勒兹这里,他同样强调了节拍与节奏的非同一性,但不同于其他学者专注于节奏的内在时间,德勒兹用空间的概念打开了节奏。如前文的引文所述,德勒兹将节奏视为一股流占据平滑空间的方式,节奏如何占据空间呢?其不同于处于非互通性环境之中的节拍一直按照预设的编码行动,节奏是无规则或无尺度的,其始终处于超编码的过程之中,“拍子是独断的,而节奏则是临界的,它将临界的瞬间联结起来,或在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的过渡之中将自身联结起来。它并不是在一个同质的时空之中运作,而是通过异质性的断块实施运作。它改变着方向”[12]446。可以看到,德勒兹发现了节奏的居间状态,受启发于巴什拉的节奏分析,德勒兹指出,节奏与有节奏者决不会处于同一个平面之上,也就是说,节奏一直在流动,一直在逃逸,一直在生成,“当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进行一种超编码的过渡,当不同的环境进行互通,当异质性的空间—时间相互协调,节奏就出现了”[12]446。而节奏本身就是环境对于混沌的回应,当节奏的回应具有表达性时,界域就产生了。由此,德勒兹勾勒出混沌—环境—节奏—界域相互生成的一个内在性平面。“这种平面只具有经度和纬度,速度和个别体,我们将它称为容贯的平面或复合的平面(与发展或组织的平面相对立)。”[12]376一旦我们将节奏置于容贯性的平面中去感知,如德勒兹借布列兹的说法所言,就实现了对时间的解放和瓦解,生成了一种飘逸的音乐所具有的非律动的时间。非律动的时间为节奏的逃逸创造了最佳环境:“一个被解域的节奏断块,它抛弃了点、坐标系和拍子,就像是一叶醉舟,与线融合在一起,或勾勒出一个容贯的平面。”[12]420-421对于如何理解节奏经由解域的界域化所形成的容贯平面,他指出:
在容贯的平面之上,一具肉体只能通过经度和纬度而被界定:也即,那些归属于它的物质元素的集合,这些元素处于某些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之中(经度);它所能产生的强度性的情状的集合,这些情状处于某种力量或某种力量的程度之中(纬度)。唯有情状,局部的运动,差异性的速度[12]367。
可以看到,容贯平面充满相互交错的强度和力度以及起伏不定的情状,在此平面之上活跃着节奏的逃逸,其沿着解域之线从一个环境逃遁到另一个环境,留下充满悬念的踪迹。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文本内时间的流动形式,朗格所阐发的虚幻的绵延也无法解释节奏在环境之间的往返穿行,野村良雄的超音乐性和非合理性则在这具体的节奏运动前略显空洞。这是德勒兹所发掘出的一个“节奏—界域”的配置,节奏—界域揭示出节奏的内在性逃逸机制,这一机制使得艺术文本充满极富想象力的褶皱和动荡,节奏在界域化的逃逸中不断开拓出文本的内在性容贯空间。
德勒兹对画家培根的论说可被视为“节奏—界域”的经典案例。德勒兹将培根作品中出现的绘画元素总结为:结构、形象与轮廓。结构由色彩的平涂构成,它建筑起画面的空间;形象就是作品中处于变形状态的诸种身体及其事实;轮廓,一般表现为圆形或是椭圆形,它也可能变形为黑色雨伞或是白色洗脸池。德勒兹指出,轮廓为形象与结构提供一个运动场地,它具有多重功能,它可以把形象从结构中孤立出来,也可以吸引形象使其逃离结构,所以德勒兹说“轮廓”可以同时作为“隔离物”和“搬迁者”出现,也可以是“引导者”或是“解辖域者”。而节奏,即产生于结构与形象在轮廓间的双向交流之中。
试看培根1978年的一幅作品《绘画》(图1)。面对这幅作品,德勒兹认为,“一切都分布为在每一个层面都出现的生理般的舒张和收缩。收缩是紧紧地挤着身体,并从结构朝向形象;舒张是将身体伸展,使它消遁,是从形象到结构”[14]44。但收缩与舒张不是线性的接替运动,而是同时性存在的。

图1 弗兰西斯·培根:《绘画》(1978)
可以看到,这幅作品非常精彩,在形象与结构的双向互动中,培根实现了他所想要打开的诸种感觉的层次——右侧的主体形象正奋力延展,试图穿过这一圈橘色的轮廓,培根甚至在它的脚趾间很无力地夹上一把钥匙,钥匙处于孔洞的边缘,但是观者无法分辨它是已经拔出还是即将插入。与此同时,这个身体形象又被一个反向的强力所占据,使它非常坚定地在原地皱缩,仿佛马上要发生一次静止不动的坠落。左侧的形象更富有戏剧色彩,培根对画面结构的处理使它一方面具有不在场的冷漠,另一方面又成为右侧主体形象的一个镜像,体现出强化的功能。再加上这两个非常表面化的红色箭头,又为整幅作品平添上一丝反讽性的幽默。培根很好地表现出感觉中的身体所发生的变形的节奏——攫取与开放,收缩与舒张,逃离与坚守,激情与沉默,这些运动所产生的节奏在身体变形的旋涡中积极地逃逸,不断地进行界域化。节奏是有情绪的,是具有方向性的,是空间性的,如德勒兹所说,节奏是感觉的矢量,节奏是使感觉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动力。
如果说在培根的单幅作品中,这种有节奏的形象还呈现为一种被折叠的表达,那么在培根的《三联画》中,节奏—界域的配置运行得更为肆意。
德勒兹认为,培根1972年的《三联画》(图2)是培根绘画中最具深刻的音乐性的作品。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的画面本身具有一种很强烈的剧场感,其中形象与结构在轮廓之间的双向运动呈现出绵延的流动性,左侧形象的胸膛正在被挖掘,右侧形象的下肢正在流淌,而中间的形象则在最确定的紫色轮廓中变形为最不确定的预备蜷缩或是预备舒张。诸种身体变形的节奏因为三联画的并置形态而达到了极大的强度和广度,这种强度和广度并不依赖于三幅作品在表层上的联结,而取决于三个形象之间内在的、自足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节奏不再从属于形象,节奏本身成为感觉,成为形象,感觉在朝向四周流动,因为身体的坠落与器官的消融而被分配为三个节奏形象:积极的节奏形象,发生逐步增强的变化;消极的节奏形象,发生逐步减弱的变化,见证的节奏形象,它见证了变形的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但是还是不选择介入。

图2 弗兰西斯·培根:《三联画》(1972)
德勒兹对“节奏形象”(Figures Rythmiques)的区分是受启发于20世纪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所提出的“节奏角色”的概念。梅西安在对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春之祭》的分析中提出了“节奏角色”。他以一种戏剧冲突的视角观照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的节奏表现,他发现了三个不同节奏型的交替重复,第一个节奏型起主导作用,就像戏剧表演中的施动者,第二个节奏型受制于前者,是处于被动的角色,第三个节奏型则肩负起冷静的见证者的角色。在梅西安看来,节奏并非是以标准时值为单位的对音乐文本的节拍划分,内在性的节奏可以扮演诸种角色,它不是静态的节奏模型,而是活的细胞,永远处于此消彼长中的争斗之中。故而,梅西安认为,“节奏角色”的概念完美契合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创作中的节奏表现。参照梅西安的观点与论述,我们也可以说,“节奏形象”的概念也完美诠释了培根《三联画》作品中的表现力量。
节奏形象即是节奏—界域的形象化表现,其并非一个物质化的、形态化的图像,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图像去捕捉节奏,但是我们不能明确界定,《三联画》中间的形象即是见证的节奏形象,两边的形象分别是积极的和消极的。甚至在培根单幅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多层面的节奏形象。或许可以说,“节奏形象”是穿梭于变形的身体之间,在混沌之中不断生成的一种“生命流”,其勾勒出节奏的逃逸路线和逃逸方向。在培根这里,节奏以坠落的方式实施逃逸、实现界域化。这也是德勒兹关于培根的灼见。经由培根,德勒兹发现了节奏的一种充满强度的逃逸方式——坠落。重力势能给予坠落得天独厚的力量优势,这是积极的、现实的、充满张力、充满痉挛的坠落。“坠落是在感觉中最活生生的东西,感觉在坠落中能够感到自己是活生生的。”[14]105而坠落也是节奏成为形象的必经之路,在画面中,“在这一静止不动的坠落中,发生了最为奇特的重新组织、重新分配的现象,因为这时候是节奏本身成为感觉,是它成为形象,根据它自己的各个方向:积极的、被动的、见证的……”[14]94。
德勒兹的“节奏—界域”是节奏观念的逃逸史中充满颗粒质感的一笔,他发现了节奏在内在性容贯平面上以坠落的方式实施逃逸。在德勒兹这里,节奏不仅从数与和谐的阐释框架中逃逸出来,节奏也从绵延的时间流动中逃逸出来;更重要的是,在知觉与记忆的基础上,德勒兹引入了感觉和身体的概念,看到了节奏在内部平面空间的折叠与缠卷、坠落和痉挛,节奏的逃逸因而具有了生成空间的强度力量,这一力量为我们进入艺术标识出另一条充满悬念和想象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