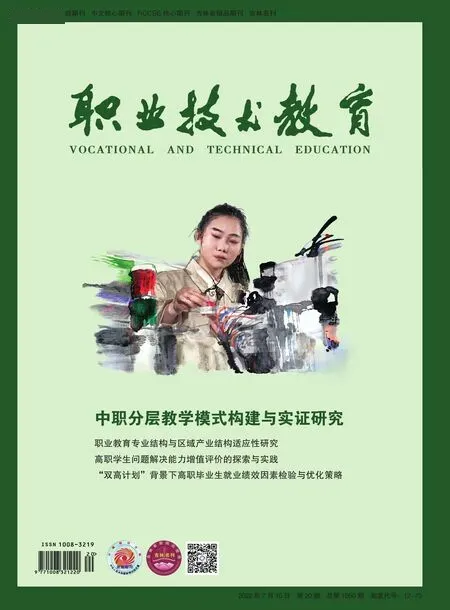医教协同驱动下的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验证
刘 琼
一、问题提出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强调“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基础工程,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在此政策推动之下,各高职院校深入实施了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工作,在推进校院合作、加强师资建设、深化教学模式改革、加快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当前高职院校开展医教协同培养医学人才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平衡,衍生出医学教育与医药卫生行业的分离;第二,专科(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结构的不对等,衍生出医学生学历晋升与职业教育规范化的矛盾。
在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模型构建方面,国内外研究的方向略有不同。国外以评价学生的能力为主[1],主要有德国“双元制”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英国“BETC工学结合”质量评价体系、北美以能力为基础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这几种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与企业关系密切,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使得评价体系具有多元性、全面性。国内对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不多,有代表性的如方向阳构建的“以需求为导向,以课程为核心”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体系[2]、周应中提出的高职专业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3]、牛志宏构建的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4],等等。进一步梳理发现,国内相关医学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研究更少,主要有方家选等人提出以能力为导向构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5]、佟玲等人对人才培养质量监测与评价进行了完善[6]、陆海建立了常态化教学评价与反馈改进机制[7]。
综上,国内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普遍存在评价主体和评价手段单一的问题,医学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未形成,从而导致医教协同培养医学人才缺乏有效反馈,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改进。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医教协同驱动下的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以期为高职医学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二、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高职医学人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秉持四个原则:科学性、系统性、适应性、职业性[8][9][10]。科学性原则主要是指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建立高素质、高修养、高品质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引导和促进培养以符合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性人才;系统性原则主要是指将每个评价环节系统相关联,形成有机整体,使整个评价体系均衡和完整;适应性原则主要是指确保评价体系具有社会适应能力,在保持高职院校特殊性的前提下,能根据社会与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职业性原则是指高职院校要培养与行业企业相适应的人才,评价体系的构建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岗位理解能力的评价。
在医教协同驱动高职医学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医学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更加注重知识技能、职业道德、能岗匹配等。因此,高职院校在建构人才培养供需平衡机制时,既要考虑职业道德、心理素质、品质修养等精神属性需求,也要考虑医学基础理论和实操技能等专业属性需求。在精神属性需求方面,高职院校需要注重医学人才的内在修养,培养能胜任医生这一神圣职业的高素质、高修养、高品质人才,其核心在于“医德”的塑造;在专业属性需求方面,高职院校既要传授学生丰富的医学基础理论,又要紧抓临床实操技能培养,培养“理实一体化”的专业性人才,其核心在于“医术”的养成。因此,本研究从“医德”和“医术”两个角度切入,结合人才培养供需平衡机制,以医学人才核心素养培育为落脚点,构建了包含知识素养、技能素养、创新素养、职业素养、道德素养5个维度、12个三级指标的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三、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验证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聚类分析法来验证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主成分分析是指在众多变量中筛选出关键变量,剔除无关或占比重较低的变量,进而反映数据的原始特征,按照主成分得分进行样本排序;聚类分析是指在筛选得出的关键变量中进行样本聚类,并对样本聚类进行排名,从而获得数据的本质特征。具体步骤包括六个方面。
1.数据标准化处理
通过调研获得原始数据,但由于原始数据往往差别明显,会造成数据显著,因此为了使获得的数据映射到统一维度,引用标准化处理公式,公式如下:

2.构建样本相关系数矩阵
由协方差结果得出相关系数矩阵,公式如下:

其中,R为相关系数矩阵,Sij为Xi和Xj的协方差,Si和Sj分别为Xi和Xj的方差。
3.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依据特征值计算公式,求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λ1,λ2,…,λq,并求出特征向量μi={μi1,μi2,…,μip}。
4.筛选主成分变量
计算主成分对原始指标的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αi,公式如下:

其中,λi为特征值,当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等于85%,且λi>1时,即可得出主成分的个数m,取前m个变量为主成分。
5.计算主成分得分
通过上述步骤计算得出特征向量μi={μi1,μi2,…,μip},与已有指标Xp={X1,X2,...,Xp}一起代入如下公式:

基于m个主成分变量构建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函数:

6.进行聚类分析
将前方筛选出的m个变量作为新的原始数据,并对新数据进行聚类分析。依据主成分得分,引入欧氏距离计算公式:

用dij表示Xi到Xj之间的距离,计算各样本之间的距离即得到距离举证D=(dij)m*n,用最短距离法进行聚类分析,用Dpq表示Gp类Gq类之间的距离,则:

以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例,依据各系部的m个主成分得分,将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相近的归为一类,计算各个类中的平均主成分得分,依据得分高低进行类间排序,进而对各系部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排序,以评价各系部在医教协同人才培养供需平衡机制下的优势和劣势,并提出改进措施。
四、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验证过程
首先,收集原始数据。基于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问卷,各指标按1~10分质量升序排列。以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随机选择的5个系部作为研究对象,面向各系部教师、教工人员及学生随机采集数据,原始数据见表2。

表2 各系部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原始数据
其次,进行实证分析。借助SPSS22.0软件,输入公式(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托公式(2)(3),计算各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构建相关系数矩阵和成分矩阵,见表3、表4。

表3 评估指标相关系数矩阵

表4 主成分筛选结果
由表3可知,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大,如X1指标与X2、X9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900,容易引起各指标之间的重复计算,导致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结果不精准。因此,需要通过筛选主成分来消除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以求获得客观的质量评估结果。
由表4可知,成分1的特征值为12.358,方差贡献率为50.18%;成分2的特征值为6.254,方差贡献率为25.40%;成分3的特征值为2.853,方差贡献率为11.59%。以上3个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了85%,可见以上4个成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解释率达到了87.16%,可以充分反映质量评估结果。因此,选择前3个成分作为评价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主成分。
将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代入公式(4)(5),求出F、F1、F2、F3的表达式;依据表达式计算5个系部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见表5。

表5 质量评估指标主成分得分与综合得分结果
将表5结果代入公式(6)(7),依托SPSS22.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校医教协同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结果可划分为以下3类:{2};{3,4};{1,5},即系部2在质量评估中排名第一,归为第一档;系部3和系部4在质量评估中分列第二、三名,归为第二档;系部1和系部5在质量评估中垫底,归为第三档。
五、高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验证结果分析
由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学校各系部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可划分为三类(档),下面对各类质量评估结果进行详细讨论。
第一类(档){2}:系部2综合得分为15.908,在质量评估结果中排名第一。高职医学教育兼顾“教育”与“医药卫生”行业属性,前者由教育相关部门主管,后者则由医药卫生相关部门主管[11]。一方面,由于教育供给侧不能有效对接行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上没有形成真正的“产教融合”,跨行业、跨机构、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育人机制和教学运行模式缺少政策制度和法律规范引导和约束,导致医学教育与医药卫生行业的分离、人才培养与机构用人的分离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医学职业教育供给与民生健康需求的不匹配,造成医学职业人才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不对等,在人才类型、人才结构、人才水平与社会对医学人才培养需求的错位,亟待建立“订单式”“学徒式”“规培式”等定向或非定向培养机制。因此,该系部应在学校人才培养供需平衡机制下积极配合高质量医学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政府+医疗机构+高职院校”三方协同育人的平台作用,针对性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建设、临床实训等教学改革工作,使得该系部学生各方面核心素养培育较好,实现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无缝衔接、医学理论与临床实操的有机结合,医学人才培养质量高。
第二类(档){3,4}:系部3和系部4的综合得分分别为10.984和8.753,在质量评估中分列第二、三名。高职医学职业教育内容通常划分为专业性教育和通识性教育,前者涉及医学人才必须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后者则重点涉及“医德”“职业理念”“价值观”等思想政治内容[12]。在专业教育方面,高职专业课程建设难以摆脱“学科体系”困境,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方面与行业需求、执业标准及岗位任务等方面出现较大的“脱轨”,由此影响到高职医学人才的竞争力和职业可持续发展。在通识教育方面,高职现有的三年制人才培养模式造成了培养周期的缩短,某些公共课、思政课、体育课被压缩,加上教师和学生的不重视,导致医学人文素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缺失灵魂。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两个系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临床实践,多次开展与附属医院的合作交流,指导学生前往医院进行见习实训,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场景中,同时与社区卫生机构、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完善的见习实训场所。但是,由于出现“重临床,轻理论”的情形,导致在课程开发和专业建设方面均低于学校平均水平,这一点从学生的知识素养评估中可以体现。此外,由于缺乏对医学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视,未能很好地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整体教育教学中,导致在道德素养评估方面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系部3和系部4应在推进临床实训机制的同时,加强课证融合、课程思政、“双师型”教师培育、综合质量评价等方面的机制建设。
第三类(档){1,5}:系部1和系部5的综合得分分别为5.270和3.870,在质量评估中垫底。高职(专)、本科、研究生等教育结构的不对等,反映出不同学历层次人才的供给问题,既包括低学历到高学历的提升难题,也包括不同学历层次人才的差序竞争困境[13]。原因之一在于,高职(专)、本科、研究生医学教育缺乏行之有效的贯通机制,高职医学生在学历提升时缺少渠道,超过半数的毕业生停留在原学历层次,一方面与医学生升学意愿有关,另一方面与医学教育学历提升机制有关。原因之二在于,医学人才结构呈现“金字塔”格局,高学历人才数量要显著低于低学历人才,加上部分医学岗位设置学历门槛,导致高职医学人才难以流动到意向岗位。此外,这两个系部没有很好地执行供需平衡机制,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较为模糊,没有充分利用好医教协同育人理事会和三方一体化育人平台所创设的机遇和条件,在学历提升、临床实训、专业建设、课证融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落后于其他系部,导致质量评估结果相对较低。因此,系部1和系部5应严格执行供需平衡机制,积极推动医教协同育人、能岗匹配对接、课证融合改革等方面的教学工作,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