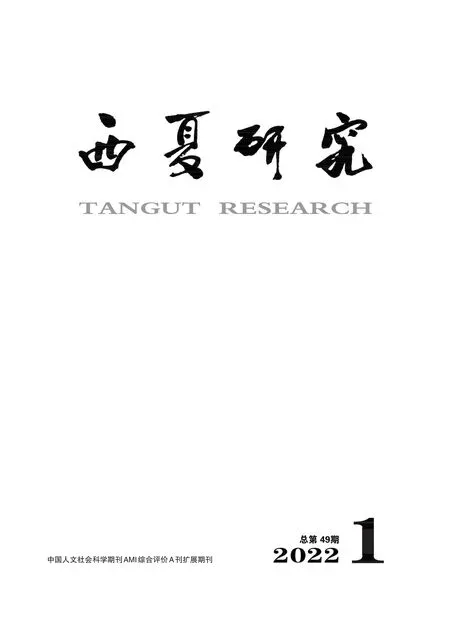明代党项人的党项姓和蒙古名
□聂鸿音
公元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随后陆续有党项人从河西进入中原,服务于蒙元王朝,有关其后裔的信息一直保留到了16世纪初。党项后裔中有一部分人住在京城,他们希望贴近蒙古文化,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给孩子起名时放弃了本民族的传统,转而仿照蒙古语命名,至多还沿用了旧日的姓氏。在存世文献中保存着一份用西夏字记录的蒙古语资料,这是此前学术界没有认识到的。本文尝试解读这些党项人的姓名,希望由此管窥元明时期党项人的文化认同取向。
一
本文研究的基础资料是明宣德五年(1430)北京能仁寺刊西夏文译本《高王观世音经》。这是由一个喇嘛发起,24个党项人参与的发愿本,当时印制了一千册,今仅存孤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件于2005年刊布。[1]402-408从卷末的发愿文可知,刊印发起者名叫缘旦监剉(yon tan rgya mtsho,功德海)。据《明实录》“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庚午”条记载,他在当年被封为“灌顶慈慧妙智大国师”[2]。尽管密教僧人历来习惯称藏语或梵语法号而不用俗名,这使得法号不能用作判断僧人族属的依据,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用西夏文发愿的缘旦监剉国师是党项后裔。再考虑到发愿文里说到印成的经本要“施诸族人”(礠砫唐涸,rjur mjɨr do mji),则可以进一步猜想他是当时京城党项人的宗教首领——助缘者的姓氏表明他们都是党项人,那些姓名用西夏文记载在下面的段落里:
菞墅坤己膡砄弛斧宁氦翆祼聚禋氦坚,镁癏腞激弛冠弛蝳萅且菋镣缾,订谍葾礮涸粵藶丑腞:羢冈竁碽恼粧宁晦晦,羢冈蓀科萿弛,羢冈蓮科羦宁,羢冈病篘碽辟粇胅,藹脟脖笌,藹脟紬毋冠宁,藹脟蓨豪罚稙萇碽,藹脟稾东蝜科,敏勉篤紻荵东,抖傅石,抖綣總蝳,抖脜没鹅紬毋,禔撂东恼宁,禔紬金宁,籋弛冯僧筗,籋弛羖藹弛稙萇碽,羖宁撂笋笆蒜兽,睼竁臡,睼抖没鹅萿弛,敏东紬毋稙萇碽,冈笌榜綒毋宁,冈笌榜荵笌,冈笌榜綒石弛,冈笌榜搔紬恼弛緜饯。纚纚矖揉科聁搓癦癦,竀纚玛蟁煎蝷窮,脝秊癪雷蘈疾,菋竃碒玛皺,籄疤葾繕科絻毯。緂东禛弛紧科蒜弛羦东藶。[1]408
史金波把这段文字翻译如下:
大明朝壬子[须能斗盈]五年正月十五日,发愿者余能答能耶。没苍并共众,施舍自己净物。令刻者:移讹依口栗迦他盈都督,移讹卯五葛能、移讹饿五罗盈,移讹氏尼口栗干什令、耶和昔义、耶和谋罨答盈,耶和?名鸠天么口栗,耶和顶?半五,平尚罕罗衄□多缚罗,多索那耶,多党小狗谋罨,李麻?迦盈,李谋葛盈,遏能箜多知,遏能南耶能天么口栗,南盈麻得赤勒葛,王依竭,王多小狗葛能,平□谋罨天么口栗,讹义罗大罨知,讹义罗衄义,讹义啰大罗能,讹义罗婆谋迦等围绕相住,法界中一切有情,现在时去掉灾祸,官事坏毁谗言,虽于身丧时,能生最安净土中。知□人能中五耶能罗□刻。[3]327-328
史先生的西夏录文基本正确,但是未能看出那些音译名词的语源,只是据《番汉合时掌中珠》里的对音汉字硬译,由此导致除了汉语借词“都督”和“李“”王”两个汉姓之外的解读全部失当。例如最后一句实际记录的是刻工,应该译成“能仁寺内林郎雕”——“緂东禛弛紧”(nwə-ŋjĩ-n tśjow)是刊刻地点“能仁寺”而不是“知□人能中”,“科”(·u)的意思是“内”而不是音译的“五”“;蒜弛羦东”(ljɨ-n lja-ŋ)是刻工名“林郎”的音译而不是“耶能罗□”。能仁寺是当年北京城里一所著名的寺院①,故址在今北京西四南大街砖塔胡同和兵马司胡同之间。寺院系元延祐六年(1319)必兰纳识里三藏(?—1333)主持建造,其后多次重修,直至20世纪下半叶荒废,最终于2001年连同所在的能仁胡同被一并拆除。必兰纳识里是回鹘高僧,同属“色目”的党项人后裔在能仁寺刻经当属自然。由这个词的解读可以想到,如果参考相关的史书,助缘者的姓名应该大都可以得到解释。
二
24个助缘人的姓名都以“党项姓/汉姓+蒙古名”的形式构成,西夏文音译采用大字与小字相配合的格式。这种格式发端于西夏中期以后的佛经咒语翻译,最初旨在准确表现梵语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4]138。蒙古语和汉语都没有复辅音声母,而党项语除了没有复辅音声母之外还没有辅音韵尾和元音韵尾-i、-u,所以发愿文里的西夏小字只借用其声母来表示前一音节的收尾音。由此判断,凡包含小写西夏字的译音词一定不是来自党项语,例如“砄弛斧宁”(sju njɨtew·jij)译写的是明宣宗年号“宣德”(sju-n te-i)[5]。发愿文里起这样作用的小字共有六个,即“宁”(·jij=-i)、“科”(·u=-u)、“萇”(mo=-m)、“弛”(njɨ=-n)、“东”(ŋə=-ŋ)、“胅”(rjijr=-r),只不过其用法看上去稍有随意,那应该是受了实际言语流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用西夏文译写外民族语时,译者在有些情况下依据的是“语音”而非“字音”。
助缘人的姓氏表明他们来自十个家族。其中的“李”和“王”是常见的汉姓,估计是西夏人进入中原之后采用的②。同样的情况还有“籋弛”(ŋa-n),这个姓的音译是“安”③,参看居庸关六体石刻汉文题记中提到的大都留守“安赛罕”,对应的西夏文题记作“籋东涅底篤弛”(ŋa-ŋsã-i khian)④[6]292。发愿文里另外有“敏东”(phjij-ŋ),从大字加小字的书写格式看,这肯定是个汉姓,只不过在汉文本《杂字》里恰巧没有读音相当的汉姓用字。考虑到《百家姓》有“顾孟平黄”一句,这里建议译作读音相当的“平”。
其余六个姓氏都来自党项语,可以解读如下:
“藹脟”(·ja xwa),见《三才杂字?番姓氏》的第30行[7]49,以及《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旧译“耶和”[10]。实际对应的汉译见同时出土的汉文本《杂字?番姓名》,作“野货”[11]。下文又有“藹脟蓨豪”(·ja xwa mbja),这是个由姓氏加部族构成的“复姓”,应该译“野货-麻乜”。“麻乜”见汉文本《杂字》⑤,又见“宋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作“麻乜族皇城使”[11]。
“敏勉”(phjijśjo),见《三才杂字?番姓氏》的第20行[7]49、保定西夏文“胜相”经幢,以及西安市文管处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题记,对应的汉译见汉文本《杂字?番姓名》,作“並尚”[11]。
“抖”(tow),见《新集碎金置掌文》[7]110,据读音对应“党”,不知是否与“党项”有关。《集韵》卷六荡韵底朗切:“党项,虏名。”
“羖宁撂”(na-i mja),当译“乃蛮”⑥,借用蒙古时期部族名naiman为姓。这个词在《元朝秘史》多见,旁注汉语“种名”。
“冈笌榜”(·o gji rar),这似乎是一个复姓,但不见于《三才杂字》。前两个字据字面拟译“讹计”,《德行集序》的作者称“节亲讹计”[12]41-42。第三个字拟译“啰”,党项的许多姓氏里都含有这个字,或许是其中某个姓氏的省称。
三
这一跟在姓氏后面的人名名单是迄今仅见的一份以西夏字对应蒙古语的完整资料。以下按照通行的习惯,西夏字标音采用“国际音标+拉丁转写”⑦,蒙古语采用通行的拉丁转写⑧,其中的b、d、g实际读p、t、k,其中的p、t、k实际读ph、th、kh⑨。西夏时代党项语的浊辅音在明代有变成清音的趋势,即与蒙古语和汉语一样,声母都只有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两套,而不再表现为严格的清浊对立。由此看来,译名中出现西夏时代的党项语跟蒙古语或汉语对音中出现清浊混乱,甚至出现送气与不送气的混乱都不足为奇。特殊的是蒙古语的小舌声母q,它只出现在a、o和u前面,同时代的汉语和党项语都没有这个音,所以汉译者不得不借用晓母字和匣母字替代,而党项译者则在k、ɣ两个舌根音之间犹豫不决。由此带来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即那些用西夏字记录的名字究竟是直接译自蒙古语,还是通过汉语的媒介转译的,甚至是兼而有之。当然无论答案如何,在已知的音系框架下,我们仍然能够对发愿者的名字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读。
根据经验,人们如果打算起名用外民族语,则总会倾向于直接选用外民族现成的词,例如现代中国人可以叫“马约翰”之类。由此想来,多数发愿者的蒙古名应该能够在元明史料里找到对应的汉译。当然,对应的汉译只是用来证明早年蒙古语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词,同样的名字并不意味着指的是同一个人。
这些人名中此前获得正确认识的只有“没鹅”(kəta)。这个词的意译是“小狗”,在黑水城民间契约里多见,也出现在元刊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发愿文里。孙伯君注意到《元史》卷二二有一条相应的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秋七月,“遣肥儿牙儿迷的里及铁肐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于是她据此将这个人名音译作“肐胆”[13]。同样的人名在《元史》卷三又写作“刚疙疸”:“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务持两端。”除此之外,大多数助缘人的名字也都可以在《元朝秘史》和《元史》里见到完整的汉译。
“竁碽恼粧宁”(ji rjɨr kja tha-i),来自蒙古语irgetei,《元朝秘史》卷十(§230)作“亦儿格台”。
“蓀科萿弛”(mior-u ka-n),来自蒙古语ma’uqan,《元朝秘史》卷七(§193)作“卯兀中罕”,对应汉语“歹”。汉译“卯罕”更为切合西夏字音,《元史》卷一〇七有“卯罕大王”。
“蓮科羦宁”(ŋjow-u lja-i),蒙古语读音构拟作a’ulai,汉语对音“奥赉”。《元朝秘史》卷七(§196)有“阿屼剌宜”(a’ula-yi),对应汉语“山-行”。
“脖笌”(sjɨgji),当译“星吉”,来自蒙古语的藏语借词singgi(<藏语sengge,狮子)。星吉在《元史》卷一四四有传。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有“目萅臡脖笌”(nja-m kha sjɨgji),汉文作“南加惺机”,回鹘文作namkašingki[6]292,278,“惺机”即“星吉”自不待言。
“稙萇碽”(tjij-m rjɨr),来自蒙古语temür。《元朝秘史》卷八(§199)作“帖木儿”,对应汉语“铁”。“帖木儿”用作人名在《元史》中多见,或作“铁木尔”。
“稾东蝜科”(tjij-ŋpã-u),当是汉语借词“天宝”,蒙古语构拟tembau⑩。《元史》卷二〇七有人名“天宝奴”。
“傅石”(ba kjwĩ),来自蒙古语baqu,对应《元朝秘史》卷四(§141)人名“八中忽”。《元史》卷一二有人名“八忽带”。
“總蝳”(no·jar)来自蒙古语noyan,《元朝秘史》多见,音译“那颜”,对应汉语“官人”。
“紬金宁”(bu da-i),来自蒙古语budai,对应人名“不歹”,《元史》卷九四有人名“朵鲁不”。《玉篇》:“,多改切,音歹。”
“僧筗”(to tśji),来自蒙古语中的藏语借词dorjˇi(<藏语rdo rje,金刚)。蒙古语汉译“朵儿只”在《元史》多见,西夏读作“朵只”(dorji)⑪,为藏文口语音。
“笆蒜兽”(tśhjo ljɨgia),前两个字来自蒙古语地名čöl,《元朝秘史》卷二(§279)作“啜勒”,全词仿《元朝秘史》对音规则作“啜里哥”(čölge)。
“竁臡”(ji kha),来自蒙古语yeke,对应人名“也客”,《元朝秘史》多见,对应汉语“大”。《元史》卷九五有人名“也可”。
“紬毋”(buɣa),来自蒙古语buqa,《元朝秘史》卷七(§195)作“不中合”,对应汉语“强牛”。汉译又作“不花”,带有“不花”的人名在《元史》多见。
“紬毋冠宁”(buɣatja-i),来自蒙古语buqadai⑫,《元史》卷三三作“不花台”,这里仿《元朝秘史》译“不合歹”。
“綒毋宁”(thowɣa-i),来自蒙古语toqai,汉译“脱孩”。《元史》卷二一〇有人名“脱罗脱孩”。
“綒石弛”(thow kjwĩ-n)来自蒙古语toqon,《元朝秘史》卷八(§202)作“脱欢”,带有“脱欢”的人名在《元史》多见。又作“妥欢”,元顺帝名妥欢铁木尔。
“紬恼”(bu kja),来自蒙古语böge,忽必烈之弟名阿里不哥,《元史》多见。
另有些助缘者的名字是在蒙古语词后面增音而成。
“辟粇胅”(ɣiăśji-r),在蒙古语qaši的后面加-r构成,《元朝秘史》卷四(§137)、《元史》卷一〇七有人名“合失”,则西夏名当译“合失儿”(qašir)。
“撂东恼宁”(mja-ŋkja-i),在蒙古语mangga的后面加-i构成,人名“忙哥”在《元史》多见,则西夏名当译“忙该”(monggai)。
助缘者名单里有几个单独使用的词来历不明⑬,参照元代蒙—汉翻译习惯构拟如下。
“罚”(kjiw)拟译“古”(gü),“抖”(tow)拟译“党”(do),“綣”(so)拟译“琐”(so),“脜”(to)拟译“多”(to),“冯”(khow)拟译“豁”(qo),“笋”(tjɨ)拟译“得”(ti),“搔”(bia)拟译“巴”(ba)。
四
在以上考察的基础上可以把《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的助缘者名录翻译如下:
发愿者缘旦监剉(Yon-tanrgya-mtsho)并友众,施舍己之净贿使雕者:口移讹亦儿格台(Zj-·o irgetei)都督,口移讹卯罕(Zj-·o ma’uqan),口移讹奥赉(Zj-·o a’ulai),口移讹(Zj-·o)氏只里合失儿(jiri qašir),野货星吉(·Ja-xwasinggi),野货不合歹(·Jaxwa buqadai),野货麻乜古帖木儿(·Ja-xwa M-bja kütemür),野货天保(·Ja-xwa tembau),並尚哈喇章(Phjij-śjo qarajang),党巴忽(Tow baqu),党琐那颜(Tow so noyan),党多肐胆不合(Tow to geda buqa),李忙该(Ljmonggai),李不歹(Ljbudai),安豁朵只(An qo doji),安那颜帖木儿(An noyan temür),乃蛮得啜里哥(Naima tičölge),王也客(Wow yeke),王朵肐胆罕(Wow do geda qan),平不合帖木儿(Phjij buqa temür),讹计啰脱孩(·Ogji Rar toqai),讹计啰掌吉(·O-gji Rar jagi),讹计啰脱欢(·O-gji Rartoqon),讹计啰巴不哥(·O-gji Rar ba böge)等具在周围。所在法界之一切有情,现时祛除灾祸,断事禁毁谗舌,身丧时往生极乐净土。能仁寺内林郎雕。
在蒙元王朝为官的党项人及其后裔大都不再使用传统的党项语名字,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直接采用蒙古语,有些人的名字则采用蒙古语里的藏语借词。前者如元中期的大都路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bayan temür)⑭、荣禄大夫昂齐(anggir),后者如世祖时的中兴路新民总管朵儿赤(dorči<藏语rdo rje)、顺帝朝的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亦怜真班(irinjin bal<藏语rinchen dpal)。蒙古人没有“姓”,所以在传统史书里也几乎见不到蒙元时期党项人的姓氏。即使名字前面有“姓”出现,例如“杨朵儿只”,我们也无从判断那个“杨”究竟是有意改用的汉姓还是某个党项姓的音转。当然,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同时代的西夏文姓名资料极为稀少,但从《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看来,元代一部分党项人用蒙古语起名的偏好一直保留到了明代。
这种用蒙古语起名的传统延续了二百多年,尽管反映了党项官员一致的文化认同取向,但元明两朝党项人的初衷并不相同。可想而知,元代的党项官员身处蒙古人治下,他们取蒙古名字是为了造成蒙古族上司对他们的亲近感,有利于自己在官场立足。与此相对的是,明朝的党项官员身处汉人治下,已经没必要用蒙古语来讨好上司,这时的蒙古语名字只是作为前朝的传统,用来对下级和百姓宣示自己与汉人不同族类,甚至是希望汉人把他们看作蒙古人。按蒙元旧例,蒙古人的地位高于西域色目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这造成了世代党项人在汉人面前的优越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进入民国的八旗子弟经常以莫名其妙的自大形象出现,逢人就说“我们祖上如何如何”,应该是出自同样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史书里的记载只反映了党项贵族的情况,平民的心态则与此不同。元代初年从河西地区征调了大量的“军户”到内地驻防,其中一部分人到了明代仍然在河北保定市的韩庄一带聚居,他们的名字记载在今莲池公园所存的西夏文“胜相”经幢上。从姓名的语源看,除了一些僧人使用藏语或梵语名字外,其他人使用的都是党项传统的姓名[8],而没有像贵族那样使用蒙古名字。这表明在当时的党项平民看来,受哪个民族的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周边人口众多的汉族。当然,随着明王朝发布政令禁止蒙古色目人内部通婚⑮,民族间的这种区别意识就很快淡化,乃至最终消失了。
注释:
①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录明正统九年(1444)胡濙《大能仁寺记略》:“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1424),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加赐大能仁寺之额。”按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即必兰纳识里。
②目前见到的西夏文献中的“李”姓都属于蒙元时期的党项人,例如至元年间的高僧李惠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裱经者李耳卜(膳監禔,jɨrbu lj),以及发愿时提到的李耳塞(膳葾禔,jɨr sej lj)、李七什(禔关粇,ljtshjɨjśji)。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人在西夏覆亡之后改用了汉姓。
③在党项人说的汉语方言里,影母开口一等字的a前面有时要加上辅音声母ŋ-[14]。下文“奥”字仿此。
④“安”的辅音韵尾在居庸关译作-ŋ,不及《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译-n符合汉字音。译音者是希望表现的是“安”的舌根韵尾-ŋ受了后面“赛”的舌面声母s-的影响,被同化成了舌面韵尾-n。
⑤史金波首次研究《杂字》时把其中三个“乜”字误录为“女”[15],此后所有的研究都沿袭了这个误会。孙伯君始为校正。
⑥在党项人说的汉语方言里,山摄二等字没有韵尾-n[14]。
⑦西夏字标音采用李范文转引的龚煌城构拟[16],但那只代表西夏时代的读音,明代有些声类与那时不大相同,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已经没有全浊声母了。
⑧蒙古语标音形式及词语转写据栗林均[17]。
⑨感谢内蒙古大学的正月教授帮我校订了文中的蒙古语形式。为清晰起见,本文用斜体字表示蒙古语的拉丁转写,用正体字表示西夏字的读音构拟。
⑩“天”的韵尾西夏译作ŋ而不译作n,是因为这两个辅音在实际口语中都会被后面“宝”的声母p同化成-m。
⑪这个名字西夏多译“矟惮”,见保定西夏文“胜相”经幢和元刻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13]。
⑫这个词依西夏对音本当作buqadai(不合歹),但是文献里没有见到这个人名。
⑬这些单用的字总是放在“姓”和“名”之间。他们不会都是党项语,因为党项语里不会有q-(豁qo)。纯粹作为猜想,我觉得有些字有可能是表示党项语或蒙古语的某种排行,例如“琐”(so)或许相关党项语的“戊”(so,三),“豁”(qo)或许是蒙古语“豁牙儿”(qoyar,二)的省略,但目前的资料远不足以证明这个猜想。
⑭党项人的族属判断据白滨[18]47-50。
⑮正德四年(1509)重校刊行的《明会典》卷一四一“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