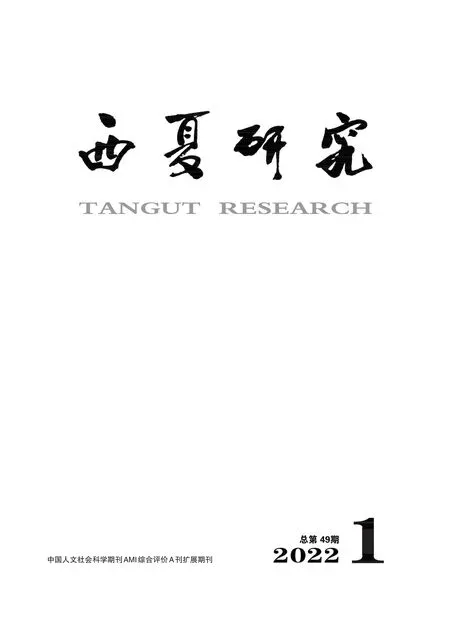居夏宋人眼中的西夏乡村
——以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为中心
□郝振宇 王晓梅
目前,农村(乡村)社会史研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从空间上看,华北和东南地区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从时间上看,多集中在明清时段,对其他时段的关注略显单薄[1]95。因传统文献疏于记载,深刻剖析并清晰认识西夏乡村社会实有困难。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一种最集中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诗歌可以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2]221。通过对诗歌内容进行辨析和研究,并佐以同时代的历史文献、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等,可为认识西夏乡村提供视角。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发现于今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据考证,《诗集》中主要诗作的作者是西夏仁宗后期(约1180—1193)从宋陕西迁居西夏贺兰山地区的汉人[3]91,他在西夏至少生活了15年,对西夏乡村有深入的认识。该《诗集》有诗70余首,保存有诗名的近60首。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该《诗集》进行了细致整理与完整刊布[4]256-268。《中国藏西夏文献》以《佚名“诗集”》为题将其编号为N21·014[F051]重新刊布[5]132-161。牛达生[6]、聂鸿音[7]、孙颖新[8]、孙昌盛[9]、汤君[3][10]、宋华[11]、徐希平[12]185-189诸学者从作者身份、词句用韵、诗文内容与艺术特色等方面对《诗集》进行了有益探讨。本文试以《诗集》为考察中心,并与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对诗作关涉的乡村景象进行分析,以此窥视具象的西夏基层社会。
一、乡村聚落景观
关于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作者的居住环境,据聂鸿音先生推断,此人居住在今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附近的某个村落里[7]225。徐希平先生也认为,从《诗集》中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他可能是居住于贺兰山附近乡村的一个汉族文人[12]186。该作者居住在贺兰山地区乡村是确定事实,诗作描述的生活场域中的诸多乡村景观也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我们可以就此讨论贺兰山地区乡村聚落的相关内容,了解西夏村居概况。
(一)民居
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的诸多诗句都涉及对乡村建筑的描述,其中蕴含着诗人文人般的闲情逸致的主观感受,若仔细辨识,亦可从中了解乡村普通民居写实的一面。《诗集》有一首无题诗,其文如下:“环堵萧然不蔽风,衡门反闭长蒿蓬。被身□□□□碎,在□□□四壁空。岁稔儿童有馁色,日和妻女尚□□。□□贫意存心志,□耻孙晨卧草中。”有学者指出,此诗化用晋人陶渊明、唐人杜甫、南朝梁萧子显、东汉孙晨等人的典故,类比出诗人穷困潦倒的生活景象[3]93。据考证,此诗是诗人在这个乡村为私塾先生时所作。诗中关于居所的描述化用典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实际的简陋居住情况。
这种乡村普通民居的简陋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一致的。关于西夏普通民居概貌,《隆平集》记载:“(西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以覆之以瓦。”[13]603《西夏纪事本末》的记载较为详细:“廨舍庙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14]68以传世文献推测,西夏普通民居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屋顶无覆瓦,居舍与棚相类,应是泥舍茅屋之属。另西夏文献《圣立义海》有“九月诸物生长期过,盖房室伐木干”的记录[15]53,表明树木是重要的房屋建筑材料。综合文献分析,西夏民居应主要是土木结构。另外,苏冠文先生指出,西夏民居以土坯或砖砌墙,用草拌泥或石灰砂浆涂抹墙壁,用草拌泥、石灰砂浆或瓦覆盖屋顶,建造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房屋[16]79。这与文献记载“民居用土,止若棚焉”的房屋建造情况有一定差距。实际上,砖木结构房屋应该是西夏民居的一种,但砖、瓦等建筑材料烧制成本较高,对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可与宋朝类似情况作对比。
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治家》中指出:“余尝劝人起造屋宇须十数年经营,以渐为之,则屋成而家富自若。盖先议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为高,或筑墙穿池,逐年渐为之,期以十数年而后成。次议规模之高广,材木之若干,细至椽、桷、篱、壁、竹、木之属,必籍其数,逐年买取,随即斫削,期以十数年而毕备。决议瓦石之多少,皆预以余力积渐而储之。虽僦雇之费,亦不取办于仓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17]170袁采出身官宦家庭,其父曾任泉州知府,家庭经济条件良好且生活优越[18]9,他所谓的“起造屋宇”不是简单地建造茅舍,而是涉及基址选定、房屋规模、材木与瓦石准备以及工匠费用等系列问题,所以,袁采认为“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难事”,需要经过十数年的准备。很显然,这种房屋建造情况是经济条件一般或贫困的家庭难以承受的。而在宋人《千里江山图》和《清明上河图》中,更多地出现郊野农舍使用茅草顶的情况,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农村经济不发达与普通民众家庭条件一般的社会现实[19]342-343。与之情况相类,对西夏普通民众而言,用砖瓦建筑材料建造房屋亦属不易。所以,“民居用土,止若棚焉”式的土木结构房屋应该是经济实力一般的普通家庭的主要选择。这种“若棚”之类的建筑仅为满足基本的居住要求,与宫殿建筑、军政建筑和寺庙建筑等是无法比拟的。《诗集》中诗人所谓“环堵萧然不蔽风”的简陋屋舍应是贺兰山乡村居民的基本居舍类型。
虽然我们可以大体确定西夏乡村屋舍的建筑情况,但因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所囿,关于民居的具体规模不甚清楚,只在黑水城地区发现的西夏卖地契约文书中的附带物一项记有“院落三间草房”“宅舍院全四舍房”“二间房”“房舍、墙”“四间老房”等相关信息[20]585-602。若所卖宅舍确为卖者的日常居住场所,那么,西夏普通民居的居住规模应是两至四间房屋、外加一个院落。若此符合实际情况,两至四间房屋的规模与家庭人口数量是相适应的。据西夏户籍文书分析,两代乃至一代核心家庭是西夏社会主要的家庭模式,家庭人口一般在4—5 人[21]64-68。按照生活逻辑,4—5 人的家庭居住在有两至四间房屋的宅舍中是合适的。受制于文献资料,黑水城西夏卖地契约中虽附带院落屋舍等相关情况,但内容远不如敦煌出土的房基账、宅地买卖类文书记载的民居结构与面积等详细。据学者研究,唐宋时期敦煌部分城居百姓的宅院为一院式或两院式的完整宅院,采用四合院式布局,建筑有内堂、东西两房、厨舍以及门道。因宅院买卖与兄弟分家等综合因素,更有每家一二间房而三四家合院的普遍现象,城外则是园舍地一体的空间布局。[22]20,39从黑水城西夏卖地契约文书分析,民众卖地附带房屋院落,其应是舍地一体的空间布局。通过实地调查与作物年代测定确知,在居延地区绿城遗址东南古耕地遗迹中,树枝状分布的引水渠之间有多处西夏的房址,并有石磨盘等生活用具[23]46-50。通过房址在耕地中错落有致的分布,可以确知舍地一体的空间布局应是乡村常见的聚落形态。与乡村宅院布局相异,西夏城居百姓的宅院不见明显的院落分隔,一般两三间房舍为一居住单位,成线状排列[24]8。但因资料奇缺,我们很难确定乡村地区“院落三间草房”“宅舍院全四舍房”等宅院的具体布局。只能推测或为唐宋时期敦煌城居百姓的四合院式布局,或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城外百姓的前厅后舍式布局,抵或还有西夏特色的宅院布局。
虽能推知西夏普通民居屋舍基本情况,但屋舍的具体布局以及具体用途难以进一步讨论。按照生活逻辑推测,房舍的最主要用途是居住与生活。若以实际生产生活用途考量,“二间房”的房舍更体现居住用途,“院落三间草房”“宅舍院全四舍房”的房舍或有相应的厨房和放置农具、粮食等物的房间。
综上,西夏乡村地区普通民居的概貌应是,规模大小不一,房屋两至四间、呈院落型,宅院周围应有院墙与院门。贺兰山地区树木较多,建筑材料多使用木材;黑水城地区缺少树木,多以茅草替之,总体宅舍较为简陋。宅舍功能单一,多为安居生活之所。
(二)农田
在诗人笔下,农田是出现次数较多的乡村景观。诗人对农田不是简单地白描式书写,而是将其置于与农人生产生活切实相关的人文情境中。《和雨诗上金刀》云:“至仁祈祷动春霄,雨降霏霏旱热逃。洒济郊原枯草嫩,救□垄亩揠禾高。村中农叟歌声远,窗下书生咏意豪。咸颂□□忧众德,田畴焦土一时膏。”汤君指出,“金刀”应是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在久旱时起草祈雨类文字代皇帝求雨成功,得到“村中农叟”的赞颂[3]95。诗人作诗缘由可能在拉近与“金刀”之间的关系,以谋求一定的职位。如果将关注焦点从“金刀”与诗人关系转向诗作基于的客观环境,就会发现诗中包含“郊原”“垄亩”“禾”“村”“农叟”“田畴”等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西北春旱多发也属当时实情,庄绰《鸡肋编》记载:“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25]80所以,《和雨诗上金刀》一诗虽有恭维之意,但其中关涉的乡村景观应是客观真实的。另外,诗人《久旱喜雪》中亦有乡野描写:“旱及穷冬从众怀,忽飘六出映楼台。为资黎庶成丰兆,故撒琼瑶显瑞来。密布南郊盈尺润,厚停北陆满□培。农歌村野为佳庆,乐奏公庭绮宴开。”与《和雨诗上金刀》相比,该诗几无恭维之意,更多地体现了诗人的安恬之心,极有可能是诗人的身份、地位已发生变化。我们从该诗中得到的基本信息是冬季盈尺大雪将使旱情得以缓解,乡间出现“农歌村野为佳庆”的场景。该场景极可能出现在以“南郊”“北陆”为代表的城外乡村。
考察诗人入夏后的轨迹,发现他应是从贺兰山地区的乡村教书先生,到夏州(或银州)的巡馆驿使,然后再到朝中任职的翰林侍行学士[3]96。虽然他的身份、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但活动的贺兰山拜寺沟、夏州(或银州)以及都城兴庆府都属宁夏平原。宁夏平原是西夏的重要农耕区,该地农业类型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灌溉农业。灌溉农业是以引水浇灌来满足生产的农田依赖水渠分布。实际上,自秦汉以来,宁夏平原就开凿有多条水渠以供灌溉发展农业。[26]124-125西夏对这些水渠多数接续利用。《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渠之利,岁无旱涝之虞。”[27]14028另外,西夏又新开凿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即“昊王渠”或“李王渠”。古渠的疏浚和新渠的修筑为宁夏平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工生态环境[28]458。而根据高清晰度航拍影像资料及地面实地考古调查综合发现,同属灌溉农业类型的西夏黑水城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南岸)亦有发达的灌溉渠网系统。这些灌溉渠网与古城址和农田紧密联系,渠道从引水口通向重要城池,并在四周形成渠系,农田则依渠系分布[29]244。另外,齐乌云等人的实地调查亦证明西夏时期黑水城遗址附近有大量的树枝状分布的引水渠以及带有灌溉引水渠的古农田遗迹[23]50。
在西夏乡村,农田与灌渠是不可分隔的整体,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也成为乡村地区居民维系稳定密切关系的重要纽带。农田灌溉虽是家庭独立行为,灌渠的建设与维护却属公共行为,需要群体共同参与,如西夏法律中有“沿渠干察水应派渠头者,节亲、议判大小臣僚、税户家主、诸寺庙所属及官农主等灌水户,当依次每年轮番派遣”“春开渠发役伕中,当集唐徕、汉源等上二种役夫,分其劳务,好好令开,当修治为宽深”等相关规定[30]499,508。而且,西夏还将在灌渠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纠纷情况从法律层面予以禁断,从制度设计上确保农田得到及时有效的灌溉,以保障农业生产、家庭运行和社会秩序。
(三)私塾
据考证,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的主要作者从陕西地区移居贺兰山某村庄后,曾以教书供养家人[7]224。他曾在《上招抚使□韵古调》中自述:“自惭生理拙诸营,更为青衿苦绊□。□□晨昏莫闲暇,束脩一掬固难盈。家余十口无他给,唯此春秋是度生。”从“自惭生理拙诸营,更为青衿苦绊□”可以看出诗人拙于经营,只以教书为生业。侧面反映出他所居乡村有对知识的需求,也有私塾性质的场所。诗人以教书者身份在乡村谋求生活应与西夏当时转向文治的社会环境有关。据史记载,西夏仁宗为推广儒学,曾“令州县各立学校”[31]412,并“尊孔子为文宣帝”[27]14025。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西夏儒学发展与文教兴盛,而诗人能在乡村私塾教书为生,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西夏教育普及,尤其诗人所在地区应是如此。得益于崇文的社会风气,诗人得以教书收取束脩供养家人。但“□□晨昏莫闲暇,束脩一掬固难盈。家余十口无他给,唯此春秋是度生”,在无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只以束脩勉强维持家中十余人生活。而束脩仅是学生入学敬师的薄礼,《论语注疏》记载:“束脩,礼之薄者。”[32]588宋人朱熹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脩是至不直钱底。”[33]871诗人除束脩而无薪俸等其他收入,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教书之地非官方设立之学校,只是乡间私塾,甚至是在自己的宅舍办学。
通过诗人笔下的诸般乡村景观组成了我们可以想象的村落概貌,这应该是诗人生活的乡村实景。正如学者分析宋人笔下的村落景观那般,诗文为我们展现的或许未必如现实中美好,但从基本的生活逻辑来看,这些都是村落常规的组成部分[34]72。因缺乏丰富细致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将民居、农田与私塾等置于合理的区位以再现西夏乡村整体布局还有相当难度,只能待以考古资料的新发现。
二、村居群体的生存状态
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的主要作者笔下描写较多的村居群体是农人、樵父与渔父。通过了解他们的生计状况,我们可以此对西夏村居群体的生存状态有一鲜活认知。
(一)农人
一般而言,农人是以农耕为主的村居群体,他们在乡村中所占比重最大。诗人对农人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主要将农人置于生产生活的情境中进行衬托。《和雨诗上金刀》云:“至仁祈祷动春霄,雨降霏霏旱热逃。洒济郊原枯草嫩,救□垄亩揠禾高。村中农叟歌声远,窗下书生咏意豪。咸颂□□忧众德,田畴焦土一时膏。”该诗将农人置于久旱逢雨的情境中,“村中农叟歌声远”反映了农人因春旱逢雨农田得以浇灌的喜悦心情。与之相类,《久旱喜雪》亦云:“旱及穷冬从众怀,忽飘六出映楼台。为资黎庶成丰兆,故撒琼瑶显瑞来。密布南郊盈尺润,厚停北陆满□培。农歌村野为佳庆,乐奏公庭绮宴开。”此中,“农歌村野为佳庆”的原因亦是久旱逢雪得以缓解旱情。这两首诗虽然从正面描述农人因旱情得解的欢乐形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农人因旱情而愁苦的状态,这背后隐含的是农人对未来作物生产与生存状态不可预知的焦虑。
关于农人的生产生活状态,西夏文《三才杂字》的作者曾在序言中指出:“村邑乡人,春时种田,夏时力锄,秋时收割,冬时行役,四季皆不闲。”[35]83他认为西夏乡村农人始终处于耕作与行役的无限循环中,终年无休。宋人司马光对农人生产生活的描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此群体,其言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36]8589-8590两相对比,宋夏农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基本无太大差别。司马光在肯定农人常年无休的辛苦劳作后,更直接指出他们为生活温饱和公税私债等所背负的重担。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常态,在西夏亦不罕见,尤其西夏还盛行高利贷[26]242-251。为解决生存危机,农人可通过卖地、卖畜与典贷暂时维持基本生活。如土地买卖主要集中在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是时正值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阶段,普通民众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选择售卖土地以维持生活[37]133。谷物典当和借贷也是贫困家庭在青黄不接时暂缓生活困难的重要有效措施。普通农人的生活水平常处于低水平甚至贫困状态,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灾害和长期战乱的影响。
自然灾害贯穿于整个西夏时期。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计有旱灾40 余次,平均每5 年发生一次[38]233-235。旱灾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而导致饥荒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大安十一年(1085),银、夏等地春夏连旱,禾麦尽皆枯死,粮食绝收引发大饥荒[31]311。光定十三年(1223),兴庆府和灵州等地春夏五个月不曾下雨,以致出现“三麦不登,饥民相食”的悲惨景象[31]489。另外,旱灾还可引发蝗灾。因为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大量蝗虫吞食禾田,严重损害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以致发生饥荒。如乾祐七年(1176)秋七月,河西地区出现旱灾,进而诱发蝗灾,河西诸州农作物被啃食殆尽[31]443。在遭遇春夏连旱和并发蝗灾的年景,农作物减产与绝收基本已成事实,若农人家庭没有充裕的粮食储存以抵御灾害,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变卖家产维持生计。
另外,西夏与辽、宋、金和蒙古等战争不断。以宋夏战争为例,重要的大规模战争有十数次之多,每次战争都会造成西夏青壮年人口的死亡和被俘,导致劳动力缺乏,繁忙的劳作缺少人力承担,妨碍正常的生产生活。如宋熙宁四年(1071)宋夏罗兀城之战后,宋人韩绛就指出此战对西夏民众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诸将攻讨,斩获招降不少,况荡平和市,焚毁村族甚多。今西贼一二百里之外方敢住止,使其弃失庐井,老小流寓,已废春耕,不为不困”[36]5390。由此可知,此战给西夏普通民众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二:一是焚毁村族,致使普通民众流离失所;二是因战争而害农时和废春耕,破坏了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西夏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对民众饱受战争之苦的境遇亦有论述:“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31]371
(二)樵父与渔父
《诗集》中虽有明确与樵父和渔父相关的诗作,但囿于相互印证的史料极少,故对樵父与渔父的生存状态的讨论远不及农人详细。《诗集》中名为《樵父》的诗作有两首,一首较为完整,诗曰:“劳苦樵人实可怜,蓬头垢面手胝跰。星存去即空携斧,月出归时重压肩。伐木岂辞踰涧岭,负薪□□□山川。算来□□□留意,却没闲非到耳边。”另一首残缺较多,只存四句:“凌晨霜斧插腰间,□□驱迟岂□□。□□□□登险路,劳身伐木上高山。”诗人以“劳苦”“可怜”“蓬头垢面”等词语勾勒出一幅樵人辛勤穷苦的画面。由“星存去即空携斧,月出归时重压肩”“凌晨霜斧插腰间”等句可知,樵人往往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的砍柴谋生。而为了能够更多地砍柴,他们经常“登险路”“上高山”“踰涧岭”,才能在归家时获柴压肩。又因入山太深,甚至会出现“漠漠樵夫迷涧壑”的危险境况。此诗呈现了樵人为获取生计而难辞辛苦的生存状态。
《渔父》有诗一首,诗曰:“处性嫌于逐百工,江边事钓任苍容。扁舟深入□芦簇,短棹轻摇绿苇丛。缓放丝轮漂水面,忽牵锦鲤出波中。若斯淡淡仙家□,谁弃荣辱与我同。”此诗以“渔父”为名,展现的是一幅处性恬淡的怡然画卷,内含诗人聊以自慰的心绪[3]93。实际上,乡村渔父的生活应是充满着劳苦艰辛,对普通民众来说,凡以谋生为手段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故另有诗《时寒》曰:“阴阳各闭作祁寒,处处江滨已涸干。凛冽朔风穿户牖,飘摇密雪积峰峦。樵夫统袖摸鬓懒,渔父披莎落钓难。暖合围炉犹毛幕,算来谁念客衣单。”此处为我们展现的却是“渔父披莎落钓难”的图景。
上述三类群体是诗人笔下主要的乡村群体。实际上,乡村群体的组成远不止这些,或有如诗人一般的教书人和以手艺谋生的匠人等。史籍对他们虽无详细记载,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可能亦不尽如人意,如诗人在乡村教书时就曾自述家庭生活为“□□晨昏莫闲暇,束脩一掬固难盈。家余十口无他给,唯此春秋是度生。日暖儿童亦寒叫,年丰妻女尚饥声”。诗人全家依赖束脩度日,其教书对象家庭应该不会太过富裕,否则所给束脩可能较为优厚。另外,宋人曾对西夏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给予整体性描述,“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冬食沙葱、野韭、拒霜、白葛,以为岁计”[13]603。如果采食野菜补充日常生活“以为岁计”确属事实,西夏乡村群体的家庭生活应处于较低水平。
三、结 语
除上述内容外,在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中还有许多诗作与节日有关,如元日、人日、上元、立春、重阳、冬至。孙昌盛先生对元日、上元、立春、重阳、冬至等节日已有专论,他认为这些诗中包蕴着当地风土人情、思想情感等诸多因素,西夏节日习俗与中原地区基本无异[9]72-74。实际如此,我们可以人日为例再窥究竟。人日即正月初七。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天生地植·人日》引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39]10《荆楚岁时记》亦明确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其俗为“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40]15。此知,人日风俗有七菜羹、戴人胜、赠花胜亦作“华胜”、登高赋诗等。《诗集》中有《人日》一诗:“人日良辰始过年,风柔正是养花天。镂金合帖悉□上,华胜当□□鬓边。薛道思归成感叹,杨休侍宴着佳篇。本来此节宜殷重,何事俗流少习传。”其中,“镂金合帖悉□上,华胜当□□鬓边”指戴人胜与赠花胜习俗,“薛道思归成感叹,杨休侍宴着佳篇”应是赋诗习俗。两相比较,西夏节日风俗确与中原地区相类。这些风俗活动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寄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了解时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也反映了10—13 世纪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总而言之,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的诗作为我们勾勒出西夏乡村鲜活的历史场景,展现了丰富的乡野风物和较真实的乡村生活。民居、田地和私塾等乡村景观组成了村落应有的实景,勾勒出诗人生活场域中的村落概貌。农人、樵父与渔父等村居群体的贫困样貌展示了西夏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简陋和劳作生涯的辛苦。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固然是文学作品,作者借此表现自己的心灵活动和情感情趣,但诗词之景贵在真实,作者很难脱离实际的生活场域为我们呈现毫无依据的场景。所以,仔细辨别可见西夏基层社会的乡村风物。因文献记载多集中于社会上层群体的历史活动,对基层乡村记载较少,所以要通过作者主观加工的诗歌以了解其所处的现实生活,需认真甄别。正如包伟民先生所言,如何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去发掘出可资利用的历史信息,进而将其拼凑成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绝非是一件轻松的工作[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