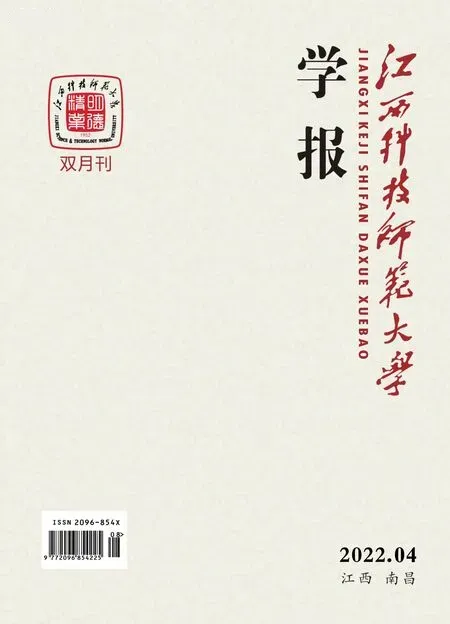评《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
阚绪良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白话”一词本为“空话”“说话”之义,到了二十世纪初,获得了新的意义:与文言文相对的口头语,此词见诸当时许多文人的笔下,如瞿秋白《文艺杂著·荒漠里》“‘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说是白话文应该明白如话……但其实现在许多的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刘半农《刘半农诗选自序》“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一九二0 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以上据《汉语大词典》有关各条)对于白话文本进行研究始于胡适《白话文学史》,胡著讨论文学体式演变,为白话文运动寻求谱系上的支持,没有涉及白话词汇,有之则自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始。
关于白话资料的研究与介绍已有学者为之,举其大者有刘坚《古代白话文献简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见《刘坚文存》)、梅祖麟《〈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全面整理介绍则是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
《论稿》初版共分十二章,这十二章是:绪论;古白话词汇的重要语料文献概貌;古白话词汇的来源和特点;古白话词汇研究史;构词法的研究;专类词语研究状况;古白话词语专题研究概况;语源考探与常用词演变;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古白话词典的编纂;古白话词语研究的方法和释例;古白话词语研究的反思和趋势。其后著者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陆续又撰成《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在此基础上又撰成《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1),增订本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增删,增订本除绪论外分六章:古白话词汇概貌;古白话词义的演变;古白话词义系统;词汇系统的文白转型;文白演变的动因及取向;古白话词汇与词典编纂。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初版介绍性内容较多,增订本把初版的十二章调整为六章,删除了大量介绍性内容,如初版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及其他章节的部分内容,新写了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三四两节、第五章,增补了古白话书面语系统、习语俗谚的发展及其词汇化、古白话词语类聚系统、通语的南北分合演变、明清圣谕宣讲和通语传播、文白演变的动因、古白话词汇演变的价值取向等,这些内容既是著者本人多年研究的心得,也包含了语言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说《论稿》初版的特点是“全面”,那么《论稿》增订本又有了“深入”,与初版相比,增订本“犹昔书,非昔书”。
《论稿》增订本“深入”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宏观,也体现在微观,兹举三例以明之。关于市语“者”,《水浒传》第四回“娼妓之家,讳‘者、扯、丐、漏、走’五个字。”胡竹安《水浒词典》“者”条下引用了元《百花亭》和明《客座赘语》,未及其他,论证显单薄。《论稿》增订本则在此基础上又举了《露书》《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词林摘艳》《南宫词纪》《西游记》等文献(第49 页),论证完备。又如“泰斗”一词,《汉语大词典》只举了《文明小史》为书证,给人的印象是此词是晚清出现,《论稿》增订本则为我们增补了宋李洪、明孙承宗和清傅维鳞等人的作品为例(第196 页),把“泰斗”一词出现的年代大为提前。又如“筷”这个词的出现,《汉语大词典》举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为例,予人以该词是明代江南地区出现的印象,《论稿》增订本则抉发出宋代李之仪(李为河北沧州人)的作品为证(第315 页),此说不仅提前了书证,也改变了我们对“筷”产生区域的认知。类此者尚多,本文不一一列举,有心人自可从中取其所需。
《论稿》增订本的第二个特点是视角的新颖独特,这方面的例子也较多,本文也不一一罗列。笔者认为增订本在明清圣谕宣讲所带来的词汇变化这个方面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第四章第三节),此前语言学界从未有人涉及这个话题,首先注意到明清宣谕的是历史、文学、文化学者,如周振鹤《月月读的圣谕广训》(周著《中人白话》)、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北京社会科学》2010.2)、赵克生《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史学月刊》2012.1)、王学泰 《说大诰——朱元璋独特的法律文件》(《王学泰自选集》),语言学界注意到明清圣谕的语言学价值及其对平民语言生活影响的增订本当是第一个。增订本此举不仅让我们从语言学层面加深对明清圣谕的价值及其作用的了解,也为以后的白话词汇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增订本把古白话分为四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文中夹白期)、隋唐宋元(半文半白期)、明清(相持分流期)、清末民初(文消白长期),这样的划分自然很精当,相比此前学界的笼统认知,这样的划分要明晰得多,但是笔者认为增订本应该在隋唐宋元时期多加笔墨,因为这一阶段是白话文发展的转折点,白话至此与文言分道扬镳。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唐宋时代说”来解释。内藤湖南疏理三千年来的中国史实,发现了唐和宋的显著差异,他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湖南名之为“唐宋时代说”,后人称之为“唐宋变革说”“唐宋变革论”,此说打破了中国史研究传统的王朝史体系,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此说有争议,但其影响仍然很大。(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II 卷)内藤湖南没有提及唐宋之际汉语的变化,实际上,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的汉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为“唐宋变革说”提供语言学上的支持。
吕叔湘在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所作序言(1983)中指出“我们发现,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的口语作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掺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序言中),吕氏的说法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暗合。
吕叔湘的看法也可以从“书语”一词的出现得到验证。“书语”就是书面语,它的出现说明当时口语和书面语已分为两途,才有“书语”的出现,如果书面语和口语一致,就不会出现“书语”以示区别。据笔者见闻所及,“书语”一词最早出现在《隋书·宇文化及传》“化及默然,俯视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南城毛道人》“富家慕道者往造之,杳无一言,与之善者怪而问焉,应曰‘吾藜苋之肠,何能陪膏粱之腹,与读书人掉书语哉!’”
下面的两个故事形象地告诉我们“书语”一词产生的背景。宋吕居仁《轩渠录》(《说郛》卷七,又见王利器《历代笑话集》)记载:“族婶陈氏顷寓严州,诸子宦游未归。偶族侄大琮过严州,陈婶令代作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耍劣,奶子又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茁儿、肐胝儿也。’大琮迟疑不能下笔,婶笑云:‘原来这厮儿也不识字。’闻者哂之。因说昔时京师有营妇,其夫出戍,尝以数十钱托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忔憎儿,每日根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汪囊,不要吃温吞蠖托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以钱还之,云:‘你且别处请人写去!’与此正相似也。”这两则小故事说明口语和书面语的隔绝程度,以至于不能有效沟通。
增订本在论述“文白演变的动因及其取向”时论及“平民意识的萌发”对白话演进的促进作用(第五章第五节),所论极是,只是对于白话的载体与底层百姓语言生活的互动关系着墨不多,似可增补。民间的白话经文人之手加工成小说,而小说(包括与之关系密切的戏曲)的传播无形中又推动了白话的流行与演进,在这个方面,钱大昕提出的“小说教”可为我们提供启发。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正俗篇》注意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教。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儒、释、道而更广也。”钱氏的分类虽然逻辑上有暇疵,但是揣摩其用意就是借此强调小说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则是目光如炬,以下材料可为钱氏之说的注脚。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袁枚(袁年长于钱)《随园诗话》卷五“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一般来说,文人使用语言比较保守,但是袁文中的“进士”尚且无法避免俗语,平民百姓受到的影响自可想见。必须指出的是,钱大昕所说的“小说教”明代以前即已经出现,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刘克庄《田舍即事十首》之一“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前者可能是与《琶琶记》有关的故事,后者可能是《前汉书评话》。
钱氏所指陈的“小说教”现象在其身后并未消失,阿Q 没有文化不识字,却也会唱绍兴乱弹《龙虎斗》“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 虽是虚构人物,但是是现实的反映。古琴名家成公亮回忆他童年时期“这些男女老少们现实生活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吃穿无保障,婚姻更不浪漫,但他们把理想都寄托在戏里,相信世界上还有那么美好的书生和小姐,自己也成为梁山伯、祝英台、莺莺和张生、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及那些美好的感情和事物。他们平时谈甚么事情也会用戏里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某某家新来的媳妇又聪明又厉害,真是个王熙凤。’要说中华文化在底层老百姓中的传承主要就是靠这些戏曲,也就是说,未必要通过读书或上学获取知识,受到熏陶,戏曲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起到了传授知识、艺术、道德的功效,在汉族人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的母亲没读过多少书,但她跟人谈话,能讲很多道教、儒家的、佛家的哲学,还能谈历史,汉代是怎样,唐代是怎么样的,甚至偶尔有《论语》里的原文,这些多半是从戏里学来的。”(成公亮《秋籁居忆旧》第36 页,中华书局2015)成公亮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具体论述而言,笔者也聊贡刍荛之言以备采择,《朱子语类》有“不如程子整齐严肃之说为好”语,《论稿》增订本说“‘不如……为好’也作‘不如……好’”(第107 页),这么说还要更多的证据,笔者认为还是视为两种不同的句式为妥。“不如……好”之“好”表达祈使语气,始见于中晚唐,如《祖堂集》卷七“亦须著精神好”“大须努力好”,卷八“莫无惭愧好”莫错好”(蒋绍愚《祖堂集词语试释》),此“好”出现得很突兀,与宋元时期的“后”“呵”有无联系有待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安徽东南地区(笔者家乡)方言仍然有此“好”。
《论稿》增订本谓“从总体上看,表示‘树木’的概念先秦以用‘木’为常,而到了两汉之交,表示‘树木’的概念几乎已经以‘树’一统天下,现代汉语木本植物统称“树”的格局远在汉代已经形成。”(第308 页)此说固有所本,但是值得进一步探究。我们认为,“树”完全取代“木”是唐宋之际的事,证据就是“种树”,“种树”本为近义词连用,“栽种”“栽培”之义,如《汉书·循吏传》“务耕桑,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种树畜养”为骈列结构)《后汉书·酷吏传》“数年迁扬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第85 页脚注引用此例,认为是“栽种树木”之义,本文不取此说。中古汉译佛典已有“栽种树木”义之“种树”,但中土文人笔下未见,至唐宋文人笔下始多见,诗文中径以“种树”为题者有唐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于鹄《种树》、孟郊《观种树》,宋许景衡《种树》、洪适《园中观种树》、韩淲《种树》等,诗词中出现“种树”者有唐孟郊《审交》、马戴《过野叟居》《集宿姚侍御宅怀永乐宰殷侍御》,宋贺铸《历阳十咏》、陆游《幽居》《秋怀》、杨万里《题周鲠臣浩斋》、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事戏作》等,宋以后则不胜枚举。文人使用语言比较保守,行文一般不轻易采用口语词汇,而“树”竟出现在他们笔下,说明“树”已很流行,以至于避开不得。不过,其中还有细节需要讨论。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树”出现4 次(业种树、视所种树、知种树而已、问养树),而“木”也出现了4 次(木寿且孳也、木之天、木之性、植木之性),可见在中唐时期“树”和“木”仍平分秋色,到了南宋,情形有了微妙的变化,姜夔《长亭怨慢》序中说“桓大司马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正文“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许”也是从“树犹如此”衍生而来。“树犹如此”值得玩味,此典出自《世说新语》言语55 条“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姜夔引作“树犹如此”,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引用桓温此典也作“树犹如此”,这种无心之误正透露出南宋时期“树”已彻底取代“木”,据此我们推测“树”完全取代“木”应是唐宋之际的事,具体何时尚待进一步研究。
笔者通读《论稿》增订本一过,感受是“如在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91 条)我相信读此书者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增订本不仅是研究白话词汇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古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收获,对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