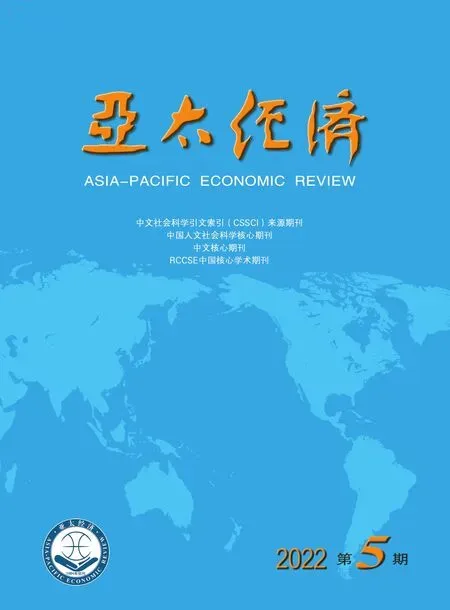新形势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
张蕴岭 潘雨晨
作者简介:1.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与经济。威海,264200。2.潘雨晨,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威海,264200。
亚太地区正面临新的形势,其重要的变化是以APEC 为主要框架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受阻,面对诸多挑战,需要就如何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继续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凝聚共识。在新的形势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创新思维和行动,以务实见效的功能性合作为引导,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环境改善,把落实2040年远景目标坐实。
一、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特征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提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由于在产品生产与价值增值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区域化而非全球化特征(Baldwin 和Lopez-Gonzalez,2015),因此亚太区域经济不仅在全球生产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一直带动区域内商品、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的快速流动,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东亚经济的崛起以及东亚与北美的经济链接,但二者在经济结构上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北美具有明显的“一家独大”特点,相比之下,东亚经济结构则总体呈现出地区贸易失衡、结构复杂(张红力和刘德伟,2010),各国发展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变化迅速(周小兵,2012),经济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特点,这令东亚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中。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在2010 年之前,日本GDP 占东亚各国GDP 之和的比重相对较大,占比均值为65.88%,而同期中国GDP 占比均值仅为21.82%;在2010年之后,中国GDP 占东亚各国GDP之和的比重相对较大,占比均值为57.38%,而日本则下降至27.76%。
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生产链条最多、生产分工程度最深、价值链贸易额与经济总量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和产业链体系(张志明等,2019),因此东亚和北美之间的经济关联主要表现为生产分工的关联,并在利益、成本和技术三个方面分别提供了充分的驱动力。具体来说,在利益驱动方面,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促进了东亚和北美两个市场的对接,双边市场的互补、市场内巨大的需求规模以及多元的需求结构为地区合作提供了动力。在成本驱动方面,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领域内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美国、日本等国家在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互补的基础上,通过投资和外包等方式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从而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深化东亚和北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在技术驱动方面,出于对技术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市场的方式承接来自地区内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促进了东亚和北美的技术对接。在经济链接的基础上,亚太区域经济蓬勃发展,但随着地区内各经济体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亚太区域经济在不同时期也展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一)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90年代
在这一时期,由于美国的东亚战略以及东亚和北美在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二者经济借助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形成紧密联系,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亚太区域经济也因此呈现出一体化潮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贸易和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产业结构快速演变的特征。在这期间,日本成为连接东亚和北美的关键国家。一方面,日本通过承接来自北美的产业转移,在战后快速实现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在“雁行模式”下,日本凭借自身产业优势不断向东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进行投资和分工,从而全面带动东亚经济发展。这一分工格局又进一步促进亚太区域形成了“三角贸易”模式,即区域内较发达经济体向区域内其他后发经济体出口中间产品,并在其国(区域)内进行中间品的加工组装环节,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刘洪钟,2020)。虽然其间日本与美欧之间的竞争带来一定区域经济摩擦,但也为之后亚太区域内的制度合作奠定了经济基础(刘均胜和沈铭辉,2012)。在此基础上,不仅日本成为亚太区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和经济体也实现了共同快速发展(如表1所示)①。

表1 亚太区域主要国家1960—1989年经济增幅 单位:%
(二)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
随着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的建立,亚太区域在经济制度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0+1”“10+3”“10+6”、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等合作机制的概念相继提出,加之全球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产业链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使得这一时期的亚太区域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区域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新发展动力不断涌现、区域内经济格局演化的特征。其中,区域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合作机制的多形式并存,既包括功能性合作机制与制度性合作机制间的并存,也包括开放性合作机制与封闭性合作机制间的并存。此外,区域内经济格局演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主要国家经济受到明显的冲击,且日本由于国内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其在以往东亚产业链中的“领头雁”作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嵌入北美和东亚之间的分工中,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对接北美的另一关键经济体和国际资本青睐的投资地。如图1 所示,1990—2008 年,在北美,美国吸引了大部分直接投资;在东亚,中国和东盟的吸引外资规模快速超过日本,尤其是中国在加入WTO 之后,FDI增速进一步加快。在此基础上,区域内的贸易结构也由“三角贸易”转变为“新三角贸易”②,在这一格局下,形成了后发国家或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弥补对日贸易逆差的三角关系(刘洪钟,2020)。这也使亚太区域获得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并且吸引着国际资本向这一区域转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发展中,亚太区域内的贸易不平衡却愈发严重。UNCOMTRADE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进入21 世纪以来,北美对东亚的贸易逆差逐渐扩大,2007 年的逆差约为4716 亿美元,而2008 年这一规模则迅速扩大至5346亿美元。

图1 1990—2008年亚太区域各经济体FDI净流入额(亿美元)
(三)2008年至今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太区域各个经济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且随着北美市场的萎缩,区域内的贸易失衡问题加剧,而这一影响进一步传导至东亚,并使得东亚生产网络出现剧烈波动。虽然之后通过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共同调整,贸易失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随着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全球逐步转向区域,亚太区域内外的市场与生产分工格局再次出现巨大变动,区域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较大冲击。因此,这一时期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大国经济博弈升级、区域摩擦频发、经贸合作“碎片化”趋势严重、区域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征。一方面,由于中国综合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亚太区域经济主体间的力量结构发生进一步改变,这引发了区域内的摩擦不断。如图2、图3 所示③。自2008 年以来,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对外增加值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不断提升,并成为亚太区域货物增加值出口最多的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一直是亚太区域内增加值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呈现出快速追赶的态势,尤其是在2009至2018年,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如图4所示,近10年来中国所受到的来自亚太区域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从2016年以来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2010年的水平。由此可见,随着亚太区域内国家和经济体发展趋势的不同,区域内国家间博弈及其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在不断升级。

图2 2008—2019年亚太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增加值出口额(万美元)

图3 2008—2019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增加值出口额(万美元)

图4 2008—2019年中国受到来自亚太区域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件)
另一方面,亚太区域各类自贸协定与合作机制的实施促进了各国间的经贸合作,扩大了贸易规模,但各机制之间的原则和条款各不相同且相互交织缠绕,在区域内形成了“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其中错综复杂的原产地规则不仅增加了企业出口成本,还影响了亚太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安排的运行效率(唐国强和王震宇,2014)。美国深入参与东亚经济以及自由化的竞争使得区域经济合作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其所造成的影响早期主要集中在东盟,尤其是TPP 的提出对东盟内部的凝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限制了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中心作用。近年来,美国主导下的碎片化合作则主要意在冲击中国。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实施大大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但“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以及其他合作机制的提出,不仅给一体化进程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纵观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区域,亚太区域一直推动着区域内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区域内各经济主体间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亚太区域经济也形成了诸多结构性问题,区域贸易失衡问题越发明显,区域内贸易摩擦事件频发,这给亚太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挑战。因此,为了促进亚太区域经济科学合理地发展,促进区域内各国间合作的不断深化,维护区域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在亚太区域构建一个合理的合作机制具有其必要性和时代性。
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
(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探索进程
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开放的政策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尽管亚太地区不像欧洲那样逐步建立了具有区域治理职能的区域组织,但通过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合力推动区域市场的开放,改善发展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使得区域性经济链接越来越紧密,营造了有利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亚太地区作为环太平洋的地缘区域,链接的主要机制是市场,而促进市场链接的则是政府开放的经济政策。二战后,随着亚太经济的联系增加,有关构建区域合作机制的呼声增高,并由企业和专家层面逐步上升到政府层面。1980年,由工商界、学界和政府参与成立了协商性的非政府间区域机制“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PECC);1989年由政府直接参与成立了政府间合作机制“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1993 年11 月20 日,在美国的推动下,首届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举行,使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④。APEC“名人小组”就APEC 的发展进行研究,发布愿景报告,明确提出亚太区域合作的目标是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根据“名人小组”的建议,APEC 成员就构建开放与合作的亚太区域大市场达成共识,制定了“茂物目标”。按照该目标的设定,亚太开放市场的构建分为两步走,即发达经济体成员到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成员到2020年实现市场开放。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靠“两轮驱动”:一是推动市场开放的轮子,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轮子,提升发展中经济体参与的能力,通过两轮驱动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目标。此后,APEC为落实“茂物目标”先后制定了多个行动议程,包括1995年《大阪行动计划》、1996年的《马尼拉行动计划》及《马尼拉行动框架》。
1997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原来设定的议程被搁置,APEC 成员的主要努力转向应对危机。2000 年后,APEC 曾做出新的努力,力图推进“茂物目标”的落实。2001 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上海共识》,把推进亚太市场开放、按时实现“茂物目标”作为共识行动;2005 年通过了《釜山宣言》;2006 年通过了《河内行动计划》等。然而,这些实施行动并未见大的成效,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成员,并没有按照“茂物目标”的要求在2010年率先实现市场开放。
2009年美国宣布领衔谈判TPP⑤,此举改变了此前协调一致共同推动以APEC为主轴的亚太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的共识。美国组合一些APEC 成员推动TPP 谈判,主要是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面对美国的改弦易辙,APEC 成员力图做出新的努力,继续推动以APEC 为主轴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2010 年在东京召开的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推动构建亚太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FTAAP)的倡议;2014 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出了构建FTAAP 的《北京路线图》,并且决定由中国和美国牵头就落实路线图开展联合研究,提出可行性报告;201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利马FTAAP宣言》(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2016)⑥。然而,此时美国决意要推动排斥中国的TPP 谈判,对于构建FTAAP 并不感兴趣。事实上,在TPP 协议签署后,关于FTAAP 的进程就被搁置起来了(Stephens,2014)⑦。
特朗普执政后,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宣布退出TPP,并提出了基于安全导向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可见,在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和政策定位中,APEC被边缘化了。拜登执政后,在战略和政策取向上,把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坐实,充实了“印太战略”中的经济竞争内容,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显然,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宣布放弃APEC,但是,已经不把推动以APEC 为框架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作为重要选项。
(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基础与阻碍因素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的发展看,主要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从一开始,区域内成员在“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区域机制”这一问题上就存在分歧。美国积极推动APEC 合作机制构建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美国与东亚区域的经济连接紧密,希望与东亚区域构建更为紧密的联系,并通过机制构建加强其对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导向力;二是欧盟构建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高度联合,美国希望通过构建亚太合作机制与欧洲统一大市场抗衡。为此,美国开始希望构建具有实质内容的“亚太经济共同体”。但是,东盟国家对构建美国领导的亚太经济共同体难以接受,其一直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强调参与上的自主性。在此情况下,“开放的区域主义”被认定为开展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由于亚太区域开放市场涉及复杂的利益交换和平衡,没有约束力的软性构建方式难以让成员经济体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按照推动“茂物目标”落实的方式,需要将成员经济体单边行动与APEC 集体行动协调一致起来。但在实施进程中,无论是成员经济体的单边行动还是集体行动,都难以达到目标。在APEC的协调一致行动议程难以见实效的情况下,基于不同利益考虑、不同组合和规则的自贸区得到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TPP、CPTPP、多方参与的“东盟+1”自贸协定以及RCEP,等等。
推动构建由APEC作为主轴的区域合作机制,在实际的发展中受到多种制约。比如,APEC本身是一个具有论坛性质的区域机制,没有让成员切实履行共识议程的能力;各成员经济体的利益差别大,各自维护自身利益优先的驱动力很强等。因此,在亚太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区域,是否和能否构建统合的区域合作机制,各方在认识和行动上并不一致。
此外,亚太区域一直存在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结构,为此,APEC 只谈经济问题,避谈安全问题。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一旦上升到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势必会影响经济,而这主要反映在中美问题上。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实力和竞争能力不断提升。这令美国开始重视由于中国竞争力和总体实力提升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政治与安全的影响(Clinton,2011;Kroenig和Oh,2017)⑧。奥巴马政府构建不包括中国的TPP,试图通过制定新规则制约中国的竞争力,提升自身经济优势,限制中国在亚太区域拓展空间。特朗普执政时则采取制裁中国、边缘化亚太经济合作的政策,把安全放在首位,推出安全导向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把安全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基于政治与安全定位的投资审查、供应链、融资、数字规则。美国安全导向的政策,使得亚太区域的二元分离更凸显,分歧增大,破坏了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共识基础。
三、新形势下亚太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
亚太这个地缘广袤、差别极大的区域,正在经历区域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国际关系的大转变,究竟会走向何方?传统的区域经济联系纽带以美国与东亚的市场需求-生产供给连接维系,这个连接会发生根本性断裂吗?布特拉加亚2040目标是否会像“茂物目标”那样落空?如今,如何使亚太区域的合作继续进行?
(一)维护亚太产业链供应链有效运行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亚太区域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北美与东亚的经济对接构成了互补型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网络。东亚逐步发展和扩展区域性生产网络,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加工业中心,美国产业外向转移,深度参与东亚区域的生产分工和供应链网络,成为东亚区域最重要的产品需求地,并且,这种区域性供需互动带动了金融等服务业的大循环。
亚太区域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建立在互利和互动的基础之上。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根据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构建了系统的分工链,从高到低、从复杂到简单、从大到小,各环节相互交融与配合。就亚太区域框架而言,高度发达经济体居于分工的高端环节,提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中度发达经济体居于分工的中端环节,提供制造技术和重要零部件,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主要进行再加工和产品的终端装配,居于分工的低端环节。就经济运行而言,亚太区域呈现一种动态的产业分工和竞争优势转移,推动分工与供应链运行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其一,公司依据成本效益比较,进行产业分工转移,让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分工序列;其二,上游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竞争能力,进入更高层次的分工序列,把低端让给更具比较竞争优势的经济体。重要的是,在这种区域体系中,参与各方对于参与获益有着坚定的信念,为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提供了便利和有保障的环境。
(二)增强新兴经济体在亚太区域中的作用
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不断加入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新兴经济体,其加入对于亚太区域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成为加工制造业中心、出口中心和生产网络的枢纽,使原来的东亚产业链条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中国成为东亚生产与美国需求之间的终端链接点,而贸易条件的不平衡(美国逆差,中国顺差)在一段时间内也集中地体现在中美之间。市场对于结构不平衡的调节是通过竞争力的转换来进行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竞争力结构发生转变,大量成本型产业由中国向越南、印尼、印度等国转移,一则推动东亚经济区的结构重组,创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二则扩大了太平洋经济区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属于南亚区域的印度,为了构建与东亚的联系,采取积极的“东向政策”。印度的加入,大大拓展了亚太经济区发展的基础,有助于把亚太经济的联系延伸到印度洋区域,逐步构建亚太-印度洋区域经济的链接。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基于经济开放与合作的机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提升亚太区域市场的开放性
亚太区域囊括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正是亚太框架把太平洋区域链接起来,构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区。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区域性技术与产业分工的循环、资本回转流动的循环与开放合作导向的有利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市场向好预期的认定。通过共同参与的合作,不断推动亚太区域市场的开放,使得经营环境改善、投资和贸易成本降低,促进了区域供应链的发展。在新形势下,亚太地区如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需要继续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维护区域经济链接与供应链运行,支持技术升级与产业分工升级。现实发展中,在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导向下,各经济体在构建对外经济关系中会有不同的选择,在参与上体现出多向、多层参与的特点。作为区域合作机制,应该把重点放在减少障碍、推动开放上,以降低因相互交叉安排而产生的“面条碗效应”,这也就是为何在APEC框架下要推动FTAAP构建的原因。
(四)促进亚太与印度洋区域经济对接
从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角度看,推动亚太与印度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崛起对区域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印度制定“东向政策”,旨在推动与东亚区域构建紧密的经济联系,参与区域经济分工和供应链⑨,并以此为基础,与亚太区域加强合作。可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网络对印度来说是有益的。尽管中印之间存在边界争端以及战略定位上的差别,但中印之间实现经济链接,并且融入区域经济网络,符合两国的发展利益,也有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两国通过金砖合作机制也构建了经济网络。因此,推动亚太与印度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把中国与印度置于更大的区域经济框架,对各方来说都是有利的。东盟对于印太区域构建有着清楚的认识和定位。在东盟印太展望文件中,其明确表示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和以东盟为中心、在印太发挥地缘链接中心的作用,印太合作向所有区域成员开放(ASEAN,2019)。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前景可期,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参与,印太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的紧密连接与合作是亚太与印太区域经济获得新发展的前提。美国力推不包括中国且以中国为对手的“印太战略”,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
(五)多角度协同搭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网络
继续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是使该区域获得可持续发展环境的重要保证。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上,亚太区域已经有多层市场开放安排,有为数众多的双边自贸协定,有次区域的协定,有规模较大的自贸区协议,各不相同的安排之间相互交织,而理想的选择是推动以APEC 为框架的亚太自贸区建设,把相互交叉的各种安排统合到一个区域框架内⑩。鉴于变化的亚太环境,短期内重聚这样的共识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可以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加强经济对话与协调上,以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亚太区域开放与合作的大局,把近期的努力方向转向推进务实见效的功能性合作上。
此前,APEC 先后在推进金融合作、绿色经济、新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合作上达成共识,并形成了文件,应该大力推进落实。针对目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需要采取务实而有效的合作措施。应该特别重视推进亚太区域物流网络、大数据网络、数字化网络的开放与合作,以便在新领域创建面向未来的亚太发展潜力与活力。企业是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动力,需要为企业创建开放与合作的经营环境⑪。
(六)改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环境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面临诸多新的变化。各国更加关注自身发展中的均衡、平衡、可持续,因此,亚太区域合作未来应该更多关注社会普遍受益、公平受益以及提高公民参与能力的问题。APEC 应该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区域经济综合治理、互联互通网络与运行体系、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新技术以及稳定和均衡的发展上,并在推进亚太区域的功能性合作中,把这些理念和方式融通到合作项目之中,纠正新自由主义导向下重市场自由化、轻综合经济发展环境提升的偏向⑫。
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因素缠绕,使得区域经济关系和环境发生重要转变。美国战略与政策实施的转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综合影响,以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等,使得亚太区域开放与合作的共识基础大大削弱,特别是对于推动以APEC 为主框架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能动性降低。面向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需要加强政治对话,通过对话增进理解和共识。因此,应该拓展领导人对话的内容,把构建政治理解和互信作为重点,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和信任,开展合作就非常困难。
世界处在大变局之中,亚太区域是大变局的中心地带,推动亚太合作,一是把变化的大国关系置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对话与协商的渠道,消减冲突,增进理解与合作,避免发生大国对抗的局面;二是把大国与其他国家置于开展对话图合作的框架,增加其他国家对大国的影响力和压力,通过对话,降低大国冲突的风险。从以往的经验看,APEC 在提供政治对话平台上还是起到了显著作用的,特别是在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各方可以利用APEC 机制开展对话,释放善意,让紧张局面转圜。在美国政府的战略驱动下,亚太区域存在诸多引发对抗、冲突的风险,因此维护亚太区域的协商对话、加强APEC 机制的政治协调功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与启示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基于共同参与和开放合作的理念,逐步推动区域市场的开放和合作机制构建,使得这个区域获得了经济上的繁荣,让所有成员从中受益,同时也促进了这个区域的稳定与和平。在全球多边体系面临挑战、全球化退步的形势下,亚太区域需要承担区域和全球的责任,因为亚太区域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亚太地区不能保持开放、合作与发展的大势,世界就会陷入危机。
亚太地区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需要面向未来,朝开放与合作的方向行进,而不是转向分裂与对抗。事实上,面对新的挑战,2020 年APEC 制定了面向未来的新愿景,即“布特拉加亚愿景”(Putrajaya Vision),并提出到2040 年把亚太建成“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与和平的亚太共同体”。2021 年APEC 领导人通过了落实远景目标的行动计划(Aotearoa Plan of Action),APEC 领导人集体承诺,落实新愿景目标,推进行动计划的落实(APEC,2020;APEC,2021a;APEC,2021b)⑬。这表明,在复杂形势下,各方就继续推进以APEC为主轴的区域合作取得了重要共识。
当然,APEC 不是一个具有执行力的区域组织,而是一个自愿参与、非约束、共识性的区域对话合作机制,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论坛。如何让开放与合作成为主导,还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美国,需要真正放弃排斥性、对抗性战略竞争思维和布局,在落实APEC领导人集体达成的共识上有切实行动⑭。
注释:
①此处仅展示了在所选期间内具有各年度全部数据的国家,其他数据缺失的国家并未进行展示。
②即由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生产并不断向中国出口中间品,中国从事产品最终生产环节的加工组装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
③由于缅甸的增加值贸易数据不可得,因此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④1992 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改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APEC 创始成员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中国于1991年以主权国的身份正式加入APEC,同时,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的身份加入其中。
⑤TPP原本是APEC四个成员(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于2005年发起的优惠贸易倡议,属于“领先者行动计划”,并邀请其他APEC成员参加,以加快实施APEC框架下的市场开放进程。美国将其改变为新的自贸区协议谈判。
⑥中国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在制定《北京路线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⑦FTAAP被认为具有反击TPP的意图,这无疑会使美国政府对其缺乏热情。
⑧2011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就提出美国把重点放在亚洲,要推行“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要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出针对中国的“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2017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规则和秩序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需要把捍卫价值和秩序作为主导性战略。
⑨印度退出RCEP 谈判是基于本身竞争力的考虑,在现实情况下,印度难以向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从未来发展看,印度参与东亚区域安排的利益驱动是显著的。同时,RCEP成员也明确宣布,对印度加入的大门是开着的。
⑩在2022年4月召开的APEC工商咨询委员会会议和5月召开的贸易部长会议上,都提到要讨论如何构建FTAAP的问题。参见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22/deepening-economic-integration-and-equipping-business-for-dynamic-inclu‐sive-and-sustainable-growth;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22/minister-apec-should-push-for-strong-policies-tofutureproof-the-region-from-crises。
⑪2022年4月APEC 企业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政策建议报告强调,APEC需要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采取有效的措施。参见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22/deepening-economic-integration-and-equipping-business-fordynamic-inclusive-and-sustainable-growth。
⑫2022年5月召开的APEC 贸易部长会议强调,2022年的APEC 会议把推动亚太地区的开放、链接与均衡作为主题,促进经济恢复,推进数字和供应链,推进人员交流。参见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22/minister-apec-should-push-forstrong-policies-to-futureproof-the-region-from-crises。
⑬愿景文件和行动计划强调,把APEC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合作机制,在投资和贸易领域,构建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与可预测的环境。
⑭美国专家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提出,中美需要放弃对抗,进行“有条件的竞争”(Conditional Competition),共同维护开放的经济环境。不过,美国的确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他对美国政府能否重新回到支持以APEC 为主轴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持怀疑态度。他出版了一本新书——《美国与中国寻求全球经济领导者》(The United States vs China-The Qu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在笔者与他的讨论中,问及美国政府能否重回对APEC 的支持,他表示怀疑。因此,如何让美国政治重回亚太区域合作轨道,落实APEC领导人关于建设开放、合作的亚太共同体所达成的共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