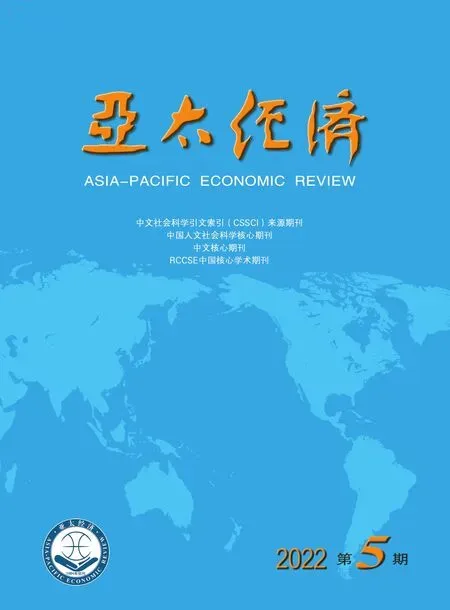价格杠杆能否持续主导能源转型?
——来自亚太地区农业深加工产业的证据
赵 甜 沈 曦
作者简介:1.赵 甜,山东科技大学财经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济南,250031。2.沈 曦(通讯作者),美国东北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福利分析。波士顿,02115。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和保障,能源结构转型一直是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纵观近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能源市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的煤炭时代、近代工业化的油气时代和尚在发展中的智能化电气时代。在可持续低碳发展的背景下,以新能源电力为主导的新型能源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青睐,碳中和成为“十四五”规划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维度内的大级别确定性主题。欧盟、美国等地区或国家均先后出台了减排路线图,中国也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与此同时,以风能、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以下简称“风光新能源”)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陆续实现了去补贴,逐渐成为能源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即便市场规模在过去十年呈现出指数型的增长态势,风光新能源在整体能源中的占比依然徘徊在10%~15%的水平,对比减排零排目标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化石能源依然更受终端用户的青睐,如在中国、印尼和印度等国,煤电等传统能源项目仍然占据60%以上的份额。
长期以来,价格杠杆一直被认为是主导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因素,早期新能源发展得益于政策性补贴,弥补了产业在幼稚阶段的成本劣势。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张和技术持续进步,新能源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渗透到全球能源市场。在新能源完全去补贴以后,价格杠杆能否进一步推动用能主体的消费结构转变呢?加速推进低碳能源转型以实现碳中和目标更应依赖哪些驱动因素呢?本文应用四大粮商(艾地盟、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亚太市场主要国家投资并经营的农业深加工工厂能源消费结构的数据,基于修正的AIDS 模型,研究不同样本时间内驱动企业用能结构转变和能源决策优化的原动力因素,重点分析成本价格在企业寻求能源替代过程中的边际贡献,重点讨论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企业能源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能源产品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二,在能源发展的不同阶段,用能主体对于能源产品的要求和关注点是否存在动态演变?第三,对比能源转型进程中油气对燃煤的替代,实现成本平价优势能否保证新能源对能源消费结构的持续渗透乃至成为能源供应的主导?
(一)能源转型驱动因素研究
能源转型被定义为政策导向下与经济长期增长并行的半市场行为(Podobnik,2006),随着低碳转型的加速,尤其是风光新能源陆续实现去补贴,针对转型驱动力的研究逐渐突破单纯的能源经济性层面,有关学者先后考察了能源禀赋驱动(Wang 等,2022)、配套能源网络建设(何继江等,2021)、微观个体用能成本(Jang,2021)以及政策性转型要求(范英和衣博文,2021)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研究多立足于近年来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能源转型策略,刘平阔等(2019)分析了中国能源转型的驱动因子,包括制度、技术、经济、行为等,以及各因子的交互关系。Zhao等(2020)构建了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和碳税政策交叉监管下的电力市场均衡模型,分析了二者在电力市场资源利用和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余晓钟等(2021)讨论了绿色低碳化能源合作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困境和路径,提出以绿色发展新理念开展高标准绿色能源项目合作的设想。目前对能源转型问题的研究表现为多学科和多方法交叉,对能源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分散。针对国内能源转型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实证检验为主,在用能模式选择和模型构建方面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本研究加入用能企业的阶段化选择以修正AIDS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理论模型方面的不足。
(二)能源消费主体行为研究
作为宏观能源结构研究的行为基础,学者们还广泛讨论了微观个体能源消费决策行为。但由于数据样本的限制,现有文献针对用能主体行为的讨论主要以普查数据中的家庭用户为样本基础。Pegels 和Lutkenhorst(2014)引用早期德国成功普及家庭分布式太阳能项目的案例数据,讨论了配套适度补贴对于刺激家庭单元能源低碳化转型的作用。然而,针对工商业能源消费主体行为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聚焦在企业能源管理和转型激励,主要针对社会环境政策责任(刘晓龙等,2021)、当地能源服务升级(林伯强,2022)和用能效率的提升等因素(张希良等,2022)。当前低碳转型和碳中和路线图均以工商业大用户或宏观的地区数据为主体,受限于样本可得性,尚未发现基于大规模企业数据的研究。得益于较长跨度的样本资源,本研究能够系统性分析包括能源成本、政策导向和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工商业用户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力。
(三)AIDS模型及其延伸研究
针对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研究依赖于不同能源市场份额数据,离散选择模型和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均能较好满足需要,而后者得益于其在消费行为一般性假设和需求弹性计量便捷性上的优势,在消费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曾洁华和钟若愚,2021;顾雨辰和蔡跃洲,2022)。但在随后的模型发展中,传统AIDS 模型暴露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由于价格变量采用了交叉项和多项式模型,为弹性估计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此后期研究普遍采用Stone指数下的LA-AIDS模型进行简化辅助计量。第二,当研究范围覆盖较多品种时,交叉项自变量的数量呈指数型上升,导致计量工作的冗杂。因此,Chaudhuri 等(2006)发展出了阶段化AIDS 模型(Staged AIDS Model),将产品进行两次分类并在不同维度进行计量,提高了模型计量的效率。第三,忽略了需求行为和选择集的跨期差异性,尤其当研究样本扩展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将会误导参数的估计。以本研究涉及的亚太农业深加工产业为例,随着新能源的加速产业化以及综合性能效服务的应用推广,以工商业用户为代表的大型用能主体面对的能源解决方案选择远比之前多样和复杂。参数冗余和选择差异问题会被样本放大,并影响到实证分析的结果,提高传统AIDS 模型的有效性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
二、基于阶段化AIDS模型的实证框架
(一)基于供求结构的阶段化AIDS模型
AIDS 模型的架构是在高曼(Gorman)形式的需求偏好基础上,利用谢泼德引理(Shephard'S Lemma)从消费支出函数推导出基于需求端支出份额的需求函数,可以将其应用于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中能源消费决策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企业能源消费的拟线性特征。一方面,其投入总量基本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生产经营对于能源的需求符合规模效应不变的假设。对比研究期内不同样本产业的产品单位能耗占比情况,也可以证实样本企业能源供求与生产规模呈线性比例关系,AIDS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企业的能源消费决策。
针对样本企业能源需求结构的复杂性,将用能企业的能源消费行为建立在两阶段模型基础之上:企业首先基于当地宏观的能源市场环境和输配网络配置决定供能模式,然后从微观角度选择最具经济性的能源结构。因此,在第一阶段,用能主体需要决策究竟是利用基于公共事业的集中式直供系统满足能源需求,还是自建分布式能源站,抑或通过第三方能源托管模式实现供能。第二阶段,依据当地能源价格、禀赋和供能稳定性等因素决定能源消费的结构。用式(1)架构第一阶段选择行为,位于区域r的企业需要决策在各类能源供应模式k下的支出占比ωkr:

k=c、d、e分别代表集中式(centralized)、分布式(distributed)和第三方(third party)供能模式。r区分了样本区域(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是基于企业每期名义能源支出X且通过Stone 指数P加权平均的各类能源市场成本。lnP=∑FωFlnPF,通过对各类能源F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衡量了能源采购的实际开支规模。μk为扰动项,在第二阶段选择时,将具体到每一项能源i的消费占比ωi模型化为式(2):

其中,i和j分别代表第二阶段选择中具体的能源品类(煤、油气、直购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因变量ωi为在第一阶段特定能源供应模式k下能源i的占比,即ωi=Xi|k/Xk。代表了前述三种能源供应渠道的市场规模,Xk为绝对规模,Pk为加权价格指数,vi为扰动项。在实证计量中,部分沿用传统AIDS模型对系数的两大约束条件,即加总约束(∑iαi=1,∑iβi= 1,∑iγij= 1)和齐次性约束(∑jγij= 1),而不同于传统模型之处在于放松了Slutsky方程下的对称性约束:γij=γji。
当传统AIDS 模型被演化为多阶段情形后,弹性估计和测算模式同样出现了变化。能源产品i自身的价格变化ΔPi通过两个途径影响终端需求:在微观层面,其通过θk|F,r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最终能源消费选择ωkr;在宏观层面,ΔPi同样影响到单个品类的相对价格Pj,从而影响整个品类的消费需求ωi。因此,函数模型是两部分影响的算术加总,见式(3):

(二)附加动态备选集的模型修正
企业的能源消费不仅需要考虑成本因素,当地宏观政策要求、能源禀赋以及能源配套设施等诸多非价格因素都会对企业的用能决策产生影响。尤其当能源供应模式从化石能源转向新能源时,分布式的供应方案将逐步代替之前依托集中式管网输配的模式,能源供应的辐射范围实际在缩小,用能主体面临的能源市场更聚焦于本地。因此,当大宗能源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对不同区域用户产生的影响势必存在较大差异,既反映在选择集层面,又体现在价格弹性层面。若套用统一的AIDS 模型会忽略这一差异性因素,势必带来参数估计和弹性测度上的偏误。对此,利用区域r在时期t的所有能被观测到的能源供应模式组成该地区的能源备选集合,在自变量中除了区域因素和时间虚拟变量以外,再附加当地能源禀赋(统一为标煤),使得传统能源价格(IHS 统计的煤炭、石油和电力)依托离散选择完成相关参数的测度。在测算出特定区域各种能源的可获取性概率Pri以后,能源i对能源j的交叉价格弹性需要在原有的εij上增加能源j的可获得性概率Prj,即εij∗Prj。
(三)核心参数识别
在模型架构过程中,无论是第一阶段的能源供应渠道选择还是第二阶段的具体能源品类采购,Stone价格指数都依赖于市场份额。然而市场份额并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不仅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能源用户消费行为和习惯等非价格因素的制约。当存在能源禀赋约束时,更高的消费占比(ωi)可能直接或间接抬高了能源销售价格(Pi)。如果在需求函数中,AIDS 模型将这些非价格因素都归入随机项μk和υi,包含Stone价格指数的自变量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机项,这将导致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尤为重要。工具变量选择的标准需要既与价格变量Pi相关,又与随机项μk和υi无关。因此,采用两个工具变量:BNEF 年度能源报告中估计的当地各种能源度电成本(cost per kW·h,LCOE)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每个国家(地区)的能源市场份额。不同于原样本中的价格变量,这两个工具变量都属于第三方的技术评估和市场宏观测度,反映不同能源在当地市场的宏观成本和普及程度,在保证原价格Pi相关性的同时,屏蔽微观市场随机因素的影响,以保证随机项μk和υi的独立性。在实证计量中,依托工具变量估计的两步法建立AIDS模型,主体部分参数可以得到有效的呈现,而相应的标准差可以通过软件Stata的Bootstrap过程完成计算。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
(一)样本概况
实证样本源自对四大粮商(艾地盟、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在亚太地区农业深加工工厂运营数据的持续跟踪,粮食深加工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其运营和生产是各国政府重点保障的目标,其能源消费具备极强的代表意义。一方面,农业深加工环节中的能源需求具有很高的刚性,稳定的成本占比符合实证模型的拟线性假设;另一方面,不同于高耗能企业面临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农业深加工企业的能源采购和消费转型策略更贴近纯市场化行为。因此,作为能源替代行为动态研究的样本是非常理想的选择。样本数据包括三部分:农业深加工企业的经营状况来自美国DNB 固定周期提供的企业征信报告汇总①;地区能源价格数据来自BNEF 的全球能源大数据库②;考虑到样本周期跨度达40 年,实证研究同时引用了IHS 的宏观经济数据,用PPI指数对物价水平做了相应的调整,以2010年的物价为标杆,并将货币单位统一为美元③。
(二)模型参数估计
表1 展示了基于区域能源供给可获取性的参数结果,可以解释为宏观区域市场对一次能源的选择行为。化石能源表现为资源禀赋导向型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在发展前期和中期依赖政策扶持,煤油气则更多依仗于当地能源储量形成的区域市场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化石能源相互之间的交叉价格敏感性弱于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价格敏感性,这样的不对称性支持了研究框架对传统AIDS模型中Slutsky方程对称性约束的放松。

表1 离散选择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基于参数估计结果测算的能源需求价格弹性见表2 和表3。表2 对比了单纯的阶段化AIDS 模型(S.AIDS列)和修正差异性选择集以后的模型(修正Pr列)弹性估计结果。与模型架构时的预期一致,在忽略了用能主体不同时期选择集差异的情况下,弹性估计结果被相对低估。尤其是以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为代表的新能源,自价格弹性的估计结果偏差更是达到50%以上。

表2 能源需求的自价格弹性估计结果
表3 对比了不同能源之间的交叉价格弹性,从估计结果看,交叉价格弹性普遍为正,反映出能源之间存在的显著替代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能源之间交叉价格弹性的差异。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普遍高于电力和新能源之间的交叉弹性,这说明对终端用户而言,化石燃料之间的转换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新能源不但对于传统能源的替代相对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还同时受到当地能源政策尤其是电力系统管制政策和能源供应效率与质量的影响,政策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跨区差异上。

表3 能源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估计结果
(三)驱动因素分析
针对价格弹性的估计结果,深入到对能源需求弹性变动的驱动因素的讨论。在样本已有的价格变量之外,引用第三方咨询机构Fitch对全球各国能源市场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年度评分数据,作为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此外,新能源补贴政策变量引用IHS汇总的亚太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数据,单位标准化为美元/千瓦时。能源稳定性指标引用IEEE2018年度报告中对各项能源是否需要辅助服务配套支持的结果并标准化为0~1虚拟变量。表4将能源品类合并为三大类:煤炭、油气和新能源。不难发现煤炭和油气代表的化石能源,其需求弹性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价格和能源禀赋层面,而对于包括政策和设施配套等非价格因素,传统化石能源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需求侧敏感性。但与之相反,新能源需求的驱动因素却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非价格因素。即便随着技术成熟和应用的产业化,成本障碍得到了一定的克服,新能源依然受制于市场准入、输配系统兼容性和用户侧个性化需求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需求弹性驱动因素的实证结果中,新能源面临更多的条件和约束。这一结果承接了动态弹性的计量,同时将实证研究延伸到需求激励层面,在之后的门槛分析部分还将引用这一结果讨论推动新能源未来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因素。

表4 能源需求弹性驱动因素回归结果
(四)动态视角下能源替代的福利效应分析
对于需求层面的福利变化,借鉴补偿变化效应(Compensation Variation,CV)的框架模型,将能源结构性转型带来的影响量化为CV=E(U0,P1)−E(U0,P0)。其中,U0为通过能源单位热值进行等效衡量和对标,即在获得同等热值能量的前提下,通过能源转型对用能主体支出的变动影响。所有的能源供应都依据其热值对标标煤,表5汇总了对照补贴后的实际价格计算的能源采购降本贡献的测算结果。

表5 能源转型对亚太地区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单位:美元/百万千焦
测算结果表明,伴随新型能源的成熟,能源替代可以显著提升用户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但在新能源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能源供求关系和价格均趋于稳定,进一步降本对于用能主体的吸引力和驱动力呈现快速递减的趋势。聚焦消费者福利的计量结果表明,油气、电力和新能源对下游需求端经济价值的贡献普遍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过程,但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预示了不同能源在从幼稚产业向成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差异性的质变点,也可以理解为对标传统能源的平价标准对于不同能源存在不同的要求,而针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需要依赖门槛效应的分析。
(五)门槛效应评估
根据不同能源解决方案的需求特性,针对其动态价格、成本和外部因素等自变量进行门槛回归,见式(4):

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可以体现在两方面:显性层面市场份额的赶超和隐性层面需求弹性的变动。因此,模型因变量yit选择能源i在t期的市场份额和需求弹性,分两个模型进行估计。门槛变量∆Pit为能源i在t期与当时主流能源(以市场份额计)的价差。控制变量Xit主要考虑了市场宏观面的四个因素:能源系统的配套成熟度、当地能源禀赋、政府的能源补贴和当地碳税政策。其中,能源系统配套成熟度主要考察当地市场在输配和终端应用层面的设施覆盖,该变量引用Fitch 咨询每年对各国能源设施评分结果的量化④。能源禀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自1980 年以来持续更新的各国能源已探明存量数据⑤,并借助《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热值参数统一转化为吨标煤⑥。能源补贴和碳税政策存在跨地区差异,可将项目生命周期内预期获得(或缴纳)的总补贴或碳税额度平均到单位能源产出上,单位统一折算为美元/千瓦时。
模型参数计量采用Hansen(2000)自举法,对比门槛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能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新能源,估计的门槛∆Pit为负数。这意味着即便达到和主流能源同等的价格,新能源的需求依然难以被有效启动和激励,而需求行为需要更多来自非价格因素的支撑。表6汇总了参数估计结果。代表能源价差的∆Pit系数估计值在所有能源类别中均表现为负数,这肯定了成本和价格赶超对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作用。那么在后补贴时代,还能够依赖价格杠杆作用推进碳中和吗?结果发现,新能源对于碳税这一因素的敏感性远远超出其他能源类型。这既得益于风光新能源在碳排上的先天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从当前市场结构来看,风光新能源在建设要求和就地消纳方面占有的优势,无疑是能源用户解决碳排指标最具性价比的方式。除了加快能源市场体系改革和配套能源输配设施建设,碳税无疑可以承担“拟价格杠杆”的作用。在碳税政策的持续刺激下,风光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效应有望继续加强,进而加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表6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基于门槛估计的结果可以推算出各种能源的成本竞争力,如果将替代能源需求端平价定义为市场份额或价格敏感性层面与主流能源的持平,那么通过测算当前主流能源成本或价格加上门槛值之和可以作为替代能源的平价成本标准。估计结果汇总在表7 中。表7 同时列举了包括BNEF、IHS 等几家主流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各类能源当前成本的测算,单位统一为度电成本,估计结果普遍介于0.03~0.06美元/千瓦时之间。但模型计算出的门槛值显著低于咨询机构的平价理论值,尤其是风光新能源的平价目标线甚至低于当前成本约50%。尽管当前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完全取消了对风光新能源的补贴,如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亚太国家,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竞价结果完全可以和当地传统火电匹敌,但基于需求模型的测算结果表明,风光新能源的完全普及依然道路漫长。

表7 亚太地区各类能源度电成本估计值 单位:美元/千瓦时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在修正传统AIDS 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亚太地区农业深加工产业的企业层面能源消费样本,实证分析了1980—2020 年能源结构转型的驱动因素和福利效应,并通过门槛效应讨论了新能源去补贴平价后的发展前景,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亚太地区农业深加工企业的能源消费自(交叉)价格弹性中,化石能源比新能源表现出更强的价格敏感性。新能源对于传统能源的冲击表现出典型的双峰特性,前期主要表现为政策导向下的补贴项目对电价补贴的敏感性逐步降低,而后期价格敏感性的反弹主要来源于竞价乃至无补贴下纯市场行为驱动的需求扩张。第二,尽管价格因素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是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重要原动力,但影响力却在持续减弱。尤其2010 年以来,随着风光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得到快速的发展,终端用户对于能源需求的关注突破了传统价格因素的限制,而着眼于更多非价格层面的因素,包括政策驱动的持续性、能源供应稳定性以及当地能源禀赋配套性等。第三,通过门槛模型的深度检验发现,相比油气对煤炭的替代,可再生能源面临更高的价格门槛。长期中立足于碳中和的能源转型不能单纯依赖于绝对成本的竞争,政策引导应该逐步从价格导向转向资源和环境配套方面,在加快新型能源输配网络建设的同时,构建基于碳税的市场体制,进一步发挥新能源在减排增效层面的优势,从而促进内生化的深度能源转型。
(二)政策启示
第一,从能源市场结构和政策稳健性角度看,价格杠杆并不能持续推动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在当下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长期目标,地区能源禀赋和终端用户刚性用能需求的满足应该成为政策制定的立足点。实证样本中核心能源供应具备较强的地区辐射效应,即相对临近的用能主体在能源消费结构和供应方式上存在明显的趋同性。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将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方能有效保障本地用户的安全和经济的稳定。第二,从能源转型的社会成本和政策效率性角度看,新能源代替传统石化能源的转型成本主要来自供应商体系的约束、固定资产置换成本以及新型能源市场配套不成熟等方面。因此,除了强化新能源的经济性,政策制定者需要架构多维度的市场配套环境,降低能源转型的社会成本。一方面,应加快电力市场和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体系完善,打通新能源电力从发输配到用户的最后一道屏障,让绿色能源和传统能源实现同平台竞争。另一方面,完善新能源在电力输配储环节的配套建设,提高新能源市场的流动交易效率,激励终端用户加快用能的转型升级。第三,从产业链环节参与和政策角度看,政策需要引导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在不同产业链环节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防止恶性竞争下的资源浪费。具体而言,在涉及资产投资与顶层设计的大型发电项目和大电网配套建设的环节,要充分发挥央企国企的资金和运营能力优势,使其成为能源产业命脉环节的稳健压舱石。而在涉及用户“最后一公里”配售服务以及设备研发制造环节,应引导民营企业发挥灵活性优势,在细分领域填补产业和市场的真空部分,为能源转型的落地起到润滑剂和加速器的作用,最终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优势和职责的协调互补。
注释:
①DNB数据网站:https://www.dnb.com。
②BNEF数据库网站: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climate-change-data-green/investment.html。
③IHS宏观数据网站:https://connect.ihsmarkit.com/data-browser/buildQuery/Global%20Economy。
④Fitch评分结果来源于EMIS平台:https://info.emis.com/emis-demo-request-landing-page-cn。
⑤能源禀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nergy。
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cbw/201909/t20190924_1699094.html。
————不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