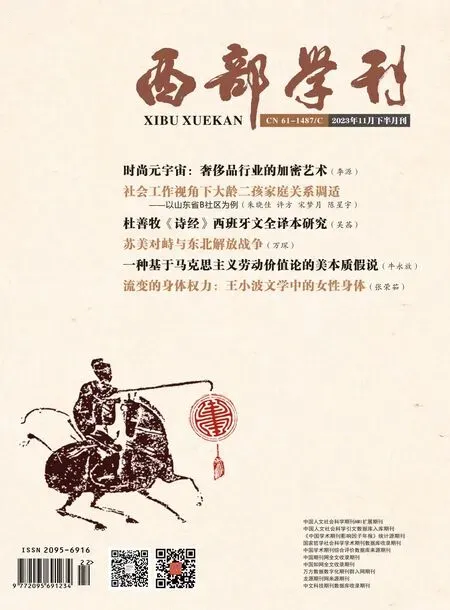纳粹医生与人体实验
——以绝育实验为例
朱 璠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 150080)
1947年纽伦堡审判中战争罪的起诉涉及医学实验,主要医学实验包括高海拔、冰冻、疟疾、磺胺、海水、流行性黄疸、绝育、毒药、燃烧弹等。这些实验大多是应武装部队的要求进行的,在绝育实验中,情况并非如此,其最终目的与拯救生命的医学毫无关系,这些活动很快就落入纳粹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医学界的种族优生学理论和纳粹分子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相互利用。医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进行了罪恶的绝育实验。
一、绝育实验的渊源
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进化论理论的创立,生物科学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使得大多数科学家将人类不平等视为科学上的事实。1853至1855年,阿蒂尔·孔德·德·戈比诺(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出版了种族主义的开创性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标志着“种族”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中有力的工具之一。1905年,由普勒茨与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吕丁(Ernst Ruedin)、律师安纳斯塔西乌斯·诺登霍尔茨(Anastasius Nordenholz)和人类学家理查德·图尔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一同创立的“种族卫生学协会”,是德国种族卫生学兴起的标志,也逐渐代表了所有的优生学家。1904年,普勒茨创办的《种族和生物协会档案》成为德国优生学界唯一的学术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的优生学的研究较为积极。虽然对社会底层人的“退化”表示担忧,对“黄色危险”“斯拉夫威胁”较为关注,但他们对寻求国家支持对“劣等”人进行绝育不抱有希望,而是在增加“优等”人口出生率方面做了积极探究。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种族卫生开始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到了1932年,德国的大学几乎都开设了种族卫生学方面的课程,此类课程多达40余种。希特勒上台后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种族卫生方面的课程。此时,德国各地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优生的机构,种族卫生学的发展得到加速。其中的两个研究中心尤其重要,一个是德国精神病学学院,另一个是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学院。在同一时期美国优生运动衰退的情况下,魏玛共和国的优生学却蓬勃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气候被种族主义所包围,特别是右翼的种族思想,为种族卫生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之而来是1933年,纳粹党取得国家政权,极端种族主义分子的上台使得实施种族卫生的愿景成为现实。
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荣誉:避免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1]
最初,纳粹分子在实施种族卫生主义行动中,把排斥政策放在了首位。排斥最初体现在工作岗位、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而屠杀是是排斥行动最极端的、最终的阶段。最开始,排斥的对象是残疾人,包括身体畸形、精神不正常、智力有缺陷的人。排斥残疾人的政策后来被用来排斥反社会或犯罪的人,如妓女、乞丐、流浪者和惯犯,此后又进一步把这一政策应用在其行为与纳粹社会规范不符的所有人。此后,纳粹还对其他种族的人进行排斥,主要是针对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20世纪30年代排斥政策成为德国的基本国策。
对于不同的群体,排斥方法也各有不同。随着纳粹帝国全面走向战争,希特勒政府开始实施从移民、监禁、绝育走向最终的、最极端的排斥——屠杀等各项排斥政策。绝育计划在后来成为大屠杀早期阶段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确立了大规模优生计划在政治、法律和操作上的可行性。它还表明,每年需要对5万人进行绝育手术的大规模医疗计划在技术上、财务上和专业上都是可行的。战争爆发后,强制绝育政策为纳粹种族方案提供了操作框架,同样的,在大屠杀中达到了最极端的应用[2]。
绝育在德国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优生控制工具。1932年,魏玛政府出台了有关残疾人自愿绝育的法规。1933年7月14日臭名昭著的《预防遗传病法》为强制绝育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法除其他类别外,还包括先天失明、失聪、身体残疾或弱智者,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躁狂抑郁症患者。纳粹当局利用了法律的某些不严格的规定,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在第三帝国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认为不值得生孩子并被绝育。这些实验不是纳粹暴徒所为,而是受人尊敬的医生所为。
二、纳粹种族政策下的绝育实验
大规模的绝育是希姆莱种族理论的一部分,德国对这些绝育实验投入了特别的时间和精力。其中之一的绝育方案包括阉割。然而,对于大规模应用,这个过程被认为太慢、太昂贵。他们还希望找到一种程序,使绝育的效果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当采用大规模绝育策略时,考虑了三种方法,包括药物治疗、X光、宫内刺激。
通过药物“seguinum”进行绝育。波科尔尼博士在1941年10月的一封信中向希姆莱提出了通过使用“seguinum”进行大规模绝育的建议。波科尔尼在信说,马达斯(Madaus)博士在对动物的医学绝育研究的结果中发现,在口服或注射的情况下,seguinum会使动物产生不育。波科尔尼在信中进一步指出:“我意识到这种药物在我国人民目前的斗争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如果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有可能生产出一种药物,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人类产生一种不知不觉的杀菌作用,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可供使用的新型强力武器。”[3]
X光绝育法。对患有遗传疾病的人进行普通的绝育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太长时间和太昂贵。然而,通过X射线进行绝育不仅相对便宜,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数千次。1941年春天,被告布拉克向希姆莱建议用X光手段对犹太人进行绝育。1942年8月,希姆莱向布拉克表示,他很有兴趣在一系列实验中至少尝试一次X射线灭菌。1941年3月28日,布拉克向希姆莱提交了一份关于X光阉割实验结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声称,通过X光进行大规模绝育可以毫无困难地进行。布拉克估计,通过20个X光设备,每天可以为3 000至4 000名受害者进行消毒[4]。
宫内刺激绝育。克劳伯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妇女和吉普赛人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在奥斯维辛,有几千名妇女被克劳伯格绝育。勃兰特本人在他的口供中承认,克劳伯格确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了大规模的绝育实验。他说:“克劳伯格医生进一步开发了一种妇女绝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子宫内注射一种刺激溶液。”[5]1942年5月,克劳伯格博士提议在集中营的女犯人身上进行一项实验,要求“在分娩过程中,从子宫入口进行一次注射”[6]。克劳伯格声称,他发明的方法“无需手术就能使女性器官绝育,效果和受感染的一样好”[7],只要有一个受过充分训练的医生和十个助手,在一个设备齐全的地方,一天就能进行几百次,甚至一千次绝育手术,当然,实验对象不会知道对她做了什么。
三、纳粹医生进行人体实验的心理分析
纳粹医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甘愿接受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原则相冲突的纳粹医学安排,进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医学人体实验,成为纳粹的刽子手?
在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参与大屠杀的医生们这样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受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欧洲反犹太主义的悠久历史,科学和政策的新结合,以及元首号召他们保护自己的种族。正如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等人所指出的,让这些医生做出可怕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在情感上对健康种族受到污染威胁这一生物医学愿景的承诺。医生对纳粹政权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支持为优生学原则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纳粹正是在优生学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种族政策,并在医疗必要性的逻辑下将谋杀合理化。
阿道夫·约斯特1895年出版的《死亡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个人的死亡权利,而是国家为了保持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健康而杀人的权利。尽管约斯特强调了对一个生物学上健康的人民的功利主义关注,但他也声称同情和减轻那些将被杀害的人的痛苦,这一关注得到了帮助实现他的愿景的纳粹医生的响应。作者坚称,他们的提议也是出于对这些不幸的穷人的同情。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的建议是“更高道德”的“治愈工作”。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是一位致力于这种“更高道德”的纳粹医生。他作为德国的首席医疗行政官员,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对计划和实施安乐死计划和各种实验负有“特殊责任”。在审判中,卡尔·勃兰特辩称,为了社会必须牺牲个人。
赫尔穆特·波本迪克(Helmut Poppendick)还描述了他对“严肃科学家的认真努力”的功利主义关注,不仅是为了德国,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他最后的陈述总结道:“经过我的良心的真诚检查,我找不到任何内疚的感觉,并以一种清醒和平静的良心期待法庭的裁决。”[8]波本迪克被判10年监禁。
沃尔弗拉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认为他参加一些实验是为了掩盖他的抵抗活动。在外界证人的支持下,西弗斯和其他几位医生将他们的处境描述为在较小的邪恶之间进行选择:“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权利容忍较小的邪恶以防止更大的邪恶?”[9]西弗斯坚持说,他是在经历了许多“心灵的挣扎”之后才决定继续上诉的。他被绞死了。
维克多·布拉克(Victor Blake)认为,可怕的绝育实验挽救了无数犹太人的生命,否则他们将被灭绝。他恳求道:“然而,没有人能否认我为其辩护时的善意”,并总结道:“我的善意是这些建议的基础,我通过这些建议提供帮助的善意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理解为我有意识地合作灭绝犹太人。”[10]他也被绞死了。
卡尔·格布哈特(Karl Gebhardt)的辩护结合了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考虑。他认为,由于他实验的对象已经被判了死刑,他认为最好是“从恶中生善”。他还辩称,他这样做是希望至少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因为一些“志愿者”得到了如果他们活下来就会得到赦免的承诺。但格布哈特的辩护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康德式扭曲。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主动向法庭提出作为实验对象来代替任何惩罚。确信这样的实验是合理的。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下令将他处以绞刑。
所有纳粹医生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良心和道德上的理由。就连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出于善意”行事的。“早在1933年,德国医生就接受了对纳粹的服从,为国家服务为这个国家服务必须是医学界的唯一目标。”[11]其中一位医生这样写道。由此可见,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虽然不愉快,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优生学手册的作者鲁道夫·拉姆博士认为,每个医生都应该是“人民的医生”,是“生物士兵”。一位前纳粹医生继续拿士兵做类比,他说:“这是一个忠诚和牺牲的问题,因为,正如他逐渐感觉到的那样,‘前线的士兵也不得不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他的责任不在于病人,而在于他的上级、他的国家、他的种族。”[12]
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医生在接受审判时把进行人体实验,服从纳粹不道德的医学指令的行为,解释为是为了服从“党和国家”的命令,是为了完成医学赋予他们的“科学使命”,是利国利民的“有益实验”。抛去这一切的借口和狡辩,纳粹医生是为了实现其意图邪恶的医学“愿景”而随意残害千千万万的无辜被实验者的刽子手,是不折不扣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的积极倡议者,是为希特勒种族主义政策提供“科学性”支撑的帮凶。
四、结束语
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12年里,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Auschwitz)、拉文斯布鲁克(Ravens brueck)、比克瑙(Birkenau)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集中营进行的可怕实验反映了对人类生命和人类苦难的极端漠视。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绝大多数的医生们都是如我们一般的正常人,他们既非聪颖过人,也非天生愚钝;既非生来邪恶,也非过于高尚;他们绝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暴虐成性、狂热盲信、嗜杀如命的“魔鬼化身”,而只是一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13]。但是,正是这些不是魔鬼的人却做出了魔鬼般的行径。当我们在反思这段黑暗的历史时,我们理所应当地会对德国医学界进行谴责,但是“谴责”并非是我们追寻历史的终极目的。相反,只有以史为鉴,彻底总结惨痛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悲剧重演,当后人在经历同样的历史考验时,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才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