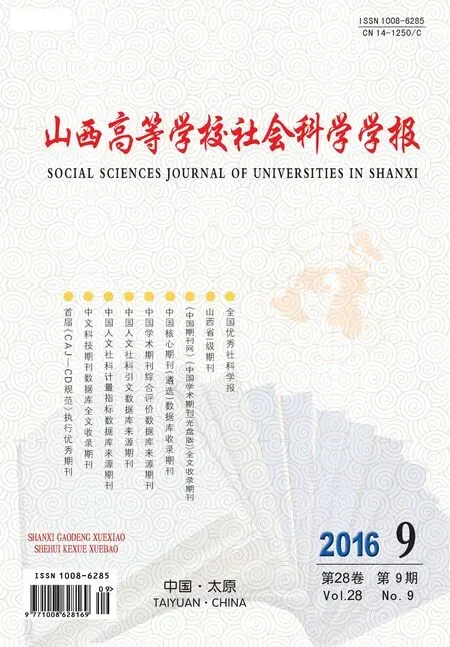自由理论的神学定位:欧洲中世纪的自由观念*
李 洋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自由理论的神学定位:欧洲中世纪的自由观念*
李洋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与神学相关,包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也主要是通过神学的外衣表现出来。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教义、“原罪”说以及“政教分离”的政治实践,都从理论和实践上阐释着自由理念。把握欧洲中世纪的自由观念,对于理解自由思想的发展脉络,了解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中世纪;自由;平等;原罪;政教分离
中世纪对人类自由而言可能是最压抑的时代,但这不代表中世纪就没有自由思想,它主要是通过神学的外衣表达出来。A·布莱克认为,“将人的自由作为某种本质的要求和有价值的东西的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包括古典的遗产、罗马法思想和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等。但在所有因素中,“基督教也许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革命”,在基督教中人们得到了“上帝的儿子的自由”[1]。可见,欧洲中世纪对自由的理解主要是依附于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的诸多神学思想中包含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自由思想在中世纪正是透过神学表达出来的。
一、自由问题神学定位的原初语境
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伴随着整个人类的产生与发展,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开始以哲学的理论化形式探讨自由问题。然而到了希腊化时期,随着希腊哲学在东方地区的传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民族的宗教精神与实用态度的影响。加之,罗马人在征服希腊地区后,又以实用的精神来接受和改造希腊哲学。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晚期希腊哲学的伦理化与宗教化倾向。这种理论倾向表达了人们期待安宁与幸福生活的社会心态,但一旦不能得到满足,则会面临着理论的全面崩溃。我们在罗马后期看到的就是希腊哲学的这种结局:哲学的伦理化使得哲学变为空洞的说教与虚伪的清谈,怀疑主义倾向则使哲学变为文字游戏与诡辩之说,宗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则与巫术迷信互相掺杂。事实表明,面临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内部怀疑精神的破坏,希腊哲学已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它已不能再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必须被吸收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之中才能保存自身的价值。历史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新兴的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初,创始人是耶稣,原本不过是属于犹太教的一支小宗派。基督教的迅速、广泛传播与罗马帝国以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大帝国是分不开的。公元1世纪上半叶,彼得和保罗等人把原始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外邦人中,使其在罗马帝国的广阔地域内得以发展。对罗马帝国的外邦人来说,因长期受到压迫而不再相信自己的保护神,而对罗马人来说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也使他们对罗马民族旧有的宗教与保护神失去信心,转而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寻求寄托。于是在公元2—3世纪,社会中大批的有教养阶层、上层人士等也纷纷皈依基督教,这使得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最终,在公元311年罗马政权公布了《宽容赦令》,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为争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在士兵的盾牌上都画上了象征基督教十字架的符号,最后在基督徒的支持下获得全胜。由此,君士坦丁大帝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基督教从此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罗马境内的300多名主教,在尼西亚召开了全教性会议,制定《尼西亚信经》作为统一教条。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并大肆镇压异端、异教,使得基督教完全取得了精神的统治地位。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基督教也分裂为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此后,罗马帝国衰落并最终被日耳曼人消灭,欧洲由此进入中古时期,基督教不仅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与神学相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一提到中世纪就会浮现出漫长与黑暗感,就会联想到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就会想到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有人会认为在这样一种“黑暗时期”人们是毫无自由可言的,人们也不会去思考自由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中世纪与基督教的一种误解,是人们的一种长期成见。不错,中世纪的确有一个“黑暗时期”,不过这个“黑暗时期”主要指的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百年(公元400—1000年),那并不是基督教的错,主要是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希腊罗马文明被一扫而空所造成的。在物质生活方面,中世纪也许是匮乏的,但从精神层面来看、从信仰上看,中世纪不但不是“黑暗”的,反而应该是光辉灿烂的。在中世纪的诸多神学思想中包含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自由思想在中世纪正是透过神学表达出来的。
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奠定了自由底色
如果说早期基督教是通过忍耐和宽容而俘获人心的,那么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乃至于变为唯一的宗教信仰后,它变得愈来愈暴虐与专断,以至于将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它的绝对控制之下。尤其是对精神生活的控制,在中世纪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切社会意识形式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如此一来,人们对任何问题的论及都需要从基督教的信条与教义出发,需要从神学权威和《圣经》那里演绎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教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很快深入人心,人们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平等。而平等与自由向来是作为孪生兄弟出现的,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勒鲁所说:“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们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而我之所以有这个权利,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2]卢梭也曾指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由此可见,平等与自由是紧密相关的,平等是实现自由的前提,而实现自由是平等的最终目标,充分的平等意味着将获得充分的自由。因此,我们说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教义为人们对自由的思考与追求奠定了底色。这种平等为自由奠定底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表现在人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具有先在地平等性,这为人的自由奠定了终极的合法性依据。《圣经·旧约》在“创世纪”章节中描绘了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人先天具有平等性,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平等性首先表现在人都是由上帝用一样的泥土捏造出来的,在物质属性上具有同一性,这就为平等提供了“事实”依据。正如一位女伯爵在释放女奴时说道:“我们皆是从土造出来的,应当互相可怜……凡所交付我们的,应使他们自由。”[3]97由此,自由人与不自由人在社会身份上的差别,被他们同样的物质属性抹杀了。上帝造人的平等性还表现在上帝给予了人们共同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人们都特别强调血缘和家世,当人们同出一宗时,意味着人们在血缘与家世上的差别被抹平。中世纪的农民代言人约翰·保尔在维护农民利益时就指出:“如果我们同是父亲亚当和母亲夏娃的后代,他们又怎么能断言或证明他们比我们更应当做主人呢?”[4]形象上的平等性也是上帝造人平等性的重要表现。上帝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将人们创造出来,人们在形象上也是平等的,这也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平等的依据。14世纪的一位伯爵在释放其农奴时说:“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故按天然之规例,都应当自由。”[3]96从人的物质属性、祖先血缘以及自身形象,我们都可看出上帝在造人上的平等性,也正是由这种平等性我们可以引出人的自由性,它为人的自由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第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还表现为基督徒身份上的平等,这为人们追求自由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基础。据《圣经·旧约》记载,上帝与人总共进行了三次订约。其中第三次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订约,保证他们有自己的国土。这次合约中也规定了以色列人所必须遵守的戒律与礼仪,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础。以色列人为了维护自己与上帝立约的优越感,他们自始至终坚持着一神教的崇拜。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这种一神教观念,但它却打破了犹太人的狭隘民族意识,提倡普世主义的精神。基督教认为,所有民族在宗教信仰上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且所有基督徒在其身份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不论是王侯贵族还是下等农奴,只要皈依了基督,他们在身份上就是平等的。这种身份的平等主要表现在“基督的肢体”论与耶稣的言行上。所谓“基督的肢体”论是《圣经》中所言,人们在基督中成为一,互相联络作肢体。尽管可能肢体的分工有所不同,但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它们都是平等的。因此,基督徒作为以基督肢体的身份出现,他们之间是同样的、平等的。耶稣的言行也强调了基督徒身份的平等性。在《圣经》中,耶稣指出,凡是遵循神的旨意的人,皆是他的兄弟姊妹。这体现了基督徒在信仰面前的平等性。基督徒在身份上的平等性为他们对自由的思考与追求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基础,只有获得身份上的平等,才获得了在神学世界中追求自由的可能。
三、基督教中的“原罪”说强化了自由思想
中世纪一切都需要通过基督教教义来解释,教义中规定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为人们对自由问题的思考与追求奠定了基础。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体现在基督教的教义与学说中,最主要表现在“原罪”论中。《圣经·旧约》的“创世纪”章中描绘了人们是如何带上“原罪”的。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人类的祖先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创造出夏娃。上帝赋予亚当和夏娃以自由意志、理性和永生,让他们在伊甸园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上帝嘱咐两人不能偷食园中间那颗果树上的智慧果,但受到魔鬼变成的蛇的蛊惑,两人偷食了禁果。偷食禁果后的两人获得了眼睛的明亮与智慧,但却触犯了上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宗教罪孽,这便是“原罪”。犯了“原罪”的二人被驱逐出伊甸园,来到人世,他们与他们的后代失去了永生与不犯罪的能力。由于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人们只能生活在与魔鬼为伍的地狱,但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最终在死后升入天堂。从以上基督教的“原罪”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在基督教神学中的三种形态:“堕落前的自由”“堕落后的自由”与“真正的自由”[5]。
第一,“堕落前的自由”是仅属于亚当一人的自由意志。“堕落前的自由”又可以称为“原初的自由”(prima libertas),它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后赋予他的一种自由意志。一开始亚当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给予了他“可以不犯罪”(posse non peccare)的能力,这便是“堕落前的自由”,属于原初的自由。但当时上帝并没有给予亚当“不能够犯罪”(non posse peccare)的恩典,因此,仅具有“可以不犯罪”能力的亚当仍有可能犯罪,事实上他也偷食了禁果,犯下了罪孽。实际上,亚当在犯下“原罪”前是具有择善的自由的,但他却滥用了上帝赋予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自我而放弃了大善(上帝)。作为对亚当放弃上帝的惩罚,亚当及其后人失去了上帝赋予的“原初的自由”,他们虽然也有“自由”,但却受到“无能”与“无知”的束缚。可见,基督教中的这种“堕落前的自由”,或称“原初的自由”只是属于亚当一人的,是上帝赋予亚当的自由意志,在亚当犯下罪孽后,这种自由就不再存在了。正如奥古斯丁所言:“一个人既已用自由意志犯了罪,为罪所胜,他就丧失了意志的自由。”[6]
第二,“堕落后的自由”是具有“原罪”的人的作恶的自由。亚当犯下“原罪”后,上帝收回了“原初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亚当及他的后代们就没有“自由”,此时他们的“自由”是一种“堕落后的自由”。所谓“堕落后的自由”指的是人们在丧失“原义”(即对上帝的爱)后,因仍保留有上帝的形象而获得“自由”,但这种“自由”只能是选择作恶的自由,是一种颠倒了的“自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提到的无益的自由(fugitiva libertas)、虚无的自由(manca libertas)、空洞的自由(vana libertas)等都属于“堕落后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被罪孽所奴役的自由(servilis libertas)。在“堕落后的自由”中,人们仍然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由于丧失了“原义”,人们只能够爱地上的事物,因此人们的选择只能徘徊于此恶与彼恶之间。从奥古斯丁的“意愿心理学”看,一个人做什么事,只要出于意愿、自愿和爱,就是自由的。对于尘世中堕落的人们来说,他们钟爱地上之物,乃是出自于他们的本心本愿,故他们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恶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的人只能是“罪的奴仆”。
第三,“真正的自由”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受到上帝的恩典。由于犯了“原罪”,人们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堕落后的自由”,这种“恶的自由”使人们生活在地狱与魔鬼为伴。对人们来说,只有获得上帝的恩典,由圣灵发动仁爱之心,使得人们恢复对上帝和邻人的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vera libertas)。由此,“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指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而是要获得上帝的恩典。没有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们生活在罪性的状态之中,被无知和无能束缚着。虽然人们也具有自由的意志,也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但这不过是在不同的恶之间做出的选择。在人们绝望的情况下,上帝带来了恩典的福音,它消除了人们的“无知”“无明”,使得人们能够认识与把握真理。与此同时,圣灵也因上帝的恩典而进入人心,人们消除了“无能”,逐渐达到完善。这就是人们通过上帝的恩典达到“真正的自由”状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定数量的人能获得这种恩典,人是否能获得拯救取决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程度。那么,人们面前就出现了选择拯救或是堕落的两条道路,在道路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以上帝恩典带来的“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它是在人与上帝的互动中实现的,其中介便是信仰。
四、“政教分离”实践了自由学说
“政教分离”的原则最早是由耶稣提出的。据《圣经》记载,在耶稣传道时,有些犹太人故意刁难地问他是否需要向凯撒交税,如果耶稣回答不需缴纳则触犯了王权,如果耶稣回答需要缴纳则会引发犹太人的不满。耶稣智慧地拿出一枚银币(古代的银币上都印着帝王的头像),耶稣问他们上面印着什么?回答是凯撒,耶稣说道:“这样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的这一睿智回答既不是主张政教合一,也不主张谁取代谁,而是要合理划界。具体说来,就是王权用以处理世俗的日常事务,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神权用以负责基督徒的精神生活与宗教生活,使信徒的灵魂得到拯救。耶稣这种“政教分离”的思想在公元8世纪末得到实践,在法兰克国王的支持下建立了教皇国,使得教会有了独立于国王之外的政治中心。公元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教皇革命”,促使了政教二元化的权力体系逐步形成。这种“政教分离”明确地将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划清界限,使得宗教事务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干涉,教会变为了一个独立的实体站在了世俗王权的对面。“政教分离”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人们的自由,一方面“政教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权,使得社会力量增强,公民的自由感增加了;另一方面“政教分离”中凸显的神权高于王权理论成为了近代思想自由的重要渊源。
第一,“政教分离”使得王权削弱,增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将获得多少自由权利,这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大小有着很大关联。在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中的社会力量强大则表示政府、王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范围与控制力会有所削减,就意味着公民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将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在中世纪,充当社会力量的主要有贵族和教会[7]。贵族与国王始终处于既矛盾又统一的地位,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中贵族是实际的统治者,所以贵族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限制王权。虽然贵族的这种角色谈不上现代民主,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来限制王权,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在“政教分离”后,另一种社会力量,也就是教会在中世纪的西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随着教会力量的日趋强大,人们逐渐相信无论是王权还是神权都是由上帝赐予教会的,之后教会将神权留下,将王权赐予国王。因此,人们也相信了教会可以随时收回国王手中的王权。这样教会的力量在社会日渐突出,它建立了宗教裁判所,拥有自己的法庭和法律。由此,教会对王权拥有了实质性的限制,中世纪也因而没有形成极权主义的政府,在权力的让渡与制衡上我们可以管窥到近代议会制的影子,之后的英国还颁布了《自由大宪章》。以上等等都可看出,教会作为社会力量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自由权利。
第二,“政教分离”原则中包含神权高于王权的思想,为西方近代思想自由奠定了基础。中世纪的“政教分离”原则不仅要求将国王与教会的权力分开,也包含着神权高于王权的思想。中世纪的两位神学大师奥古斯丁与阿奎那都为神权高于王权作了理论论证。奥古斯丁指出,人们对上帝要服从,对君主也要服从,但社会的权力体系存在着高低的秩序,“下级要服从上级,天主则凌驾一切之上”[8]。阿奎那则进一步指出,上帝创造了整个社会,“且现存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9]。他们指出神权高于王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王权从人们的精神与信仰领域驱逐出去,这样为人们的精神与信仰的自由保存了一块预留地,这构成了近代西方思想自由的渊源。思想自由是自由的高级阶段,是人皆应具有的本性,是任何人和力量都不应且不可剥夺的。正如一个身披枷锁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而一个暴虐骄纵的皇帝却可能活得痛苦。因此,阿奎那认为人们被奴役的状态只能存在于身体领域,“因为精神始终是自由的”[10]153。阿奎那进一步指出这种思想的力量与精神的自由是上帝赋予的,“在这尘世的状态中,我们由于基督的恩惠得以在精神上没有缺陷”[10]153。这种思想自由的观点被近代思想家们所继承,斯宾诺莎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如果必须有所放弃,那么人们会选择独立思考的自由,而放弃身体行动的自由。可见,思想自由对个人和国家都十分重要,中世纪为人们的思想自由奠定了一定基础。
[1] Antony Black.Guild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
ught: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Methuen&Co.Ltd.1984:41.
[2] 皮埃尔·勒鲁.论平等[M].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5.
[3] 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上卷[M].何新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6.
[5] 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51.
[6]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选集[M].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420.
[7] 启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西方反自由主义至新自由主义学说追溯[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06-133.
[8] 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6.
[9]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75.
[10]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Theological Localization of Freedom: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Middle Ages of Europe
LI Yang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In the Middle Ages when Christianity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people′s behavior and ideas were related to theology, including their yearning and pursuit for freedom, which were also expressed under the cover of theology. In Christian theology, the basic doctrines, like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God",the"original sin"and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ll interpret the idea of freedo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grasp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e Middle Ages of Europ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hought, the liberalism tradition and the liberal movement in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the Middle Ages;freedom;equality;original sins;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2016-05-08
李洋(1989-),男,安徽淮北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问题。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9.023
B97
A
1008-6285(2016)09-0093-05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实践意义研究”(2012BKS001)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