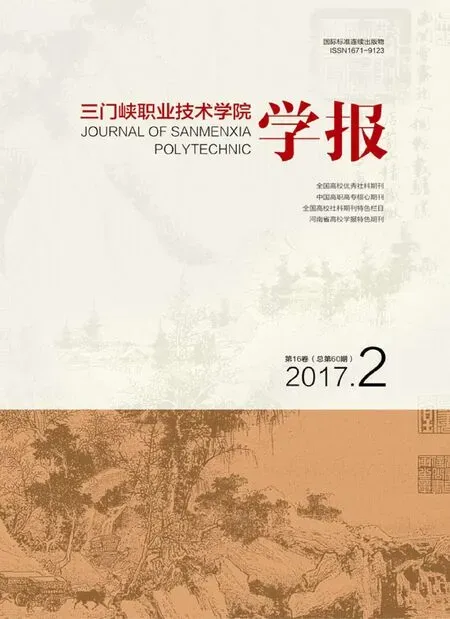余光中散文世界构建路径探析
◎殷宝为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安徽 铜陵 244061)
余光中散文世界构建路径探析
◎殷宝为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安徽 铜陵 244061)
余光中的散文一直备受推崇。他的散文以古今中外的文化积淀作为背景,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及欧洲为地理依托,借鉴诗歌、戏剧、小说等艺术形式经验,在创作题材上广泛涉猎并进行深度开掘,形成具有弹性、密度、质料,感性和知性并重的风格。
余光中;散文;弹性;密度;质料
余光中诗文俱佳,不仅诗歌作品蜚声海内外,其散文追求弹性、密度、质料,以感性和知性并重的风格也一直备受推崇。而这种独特散文世界的形成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古今中外文化背景的交融
“他以自身独有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追求,自由地穿梭与出入于中西古今的文坛中”[1]。余光中在创作时对材料进行广泛涉猎,加上他在中外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方面的积累,使其散文避免了干瘪的抒情和生硬的景物描写,呈现出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充满丰富的知性情感。
余光中从小在四川、南京等地接受国文教育,其父母和二舅父孙有孚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余光中之后在金陵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外文系学习,1958年在梁实秋的推荐下赴美深造,随后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并经常出国游历讲学。古今中外文化的长期浸渍使得余光中的创作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和跨文化、跨民族的开阔视野。这些因素融入到余光中敏感的性格当中,成为他散文写作的文化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台湾文坛西化之风盛行的时候,流派纷杂,口号泛滥。“当诗人置身于文化碰撞之时,这种‘拒绝融化’的宣言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捍卫,使读者感觉到强烈的民族意识”[2]。余光中在经历欧美文化的洗礼后,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他抛开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蛊惑,猛悟“五四”以来散文的诸种流弊,力挺散文的革新,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食古不化”“食洋未化”现象的批判上。
余光中、谭子豪、钟鼎文、思果和画界的刘国松等人,先是被当时的批评派讥讽为“流亡海外的浪子”“西化派”;而另一些致力于古典和传统的现代演绎的人则被扣上“国粹派”的帽子。文学批评流于浅薄的形式主义之争,多是“泛述草评”“情话呓语”“食洋未化”,真正“精警”的批评罕见。在散文集《左手的掌纹》中,像《石城之行》《落枫城》等文章,虽是在国外的游记,却处处交织着对中国的回忆和眷恋,异域人文景观反照的是古典情致的意味隽永。针对“食古不化”的“孝子”,余光中在《掌上雨》中指出,“那些竭力维护传统的‘孝子’”,“踏着平平仄仄的步伐,手持哭丧棒,身穿黄麻衣,浩浩荡荡排着传统的出殡行列,去阻止铁路局在他们的祖坟上铺设轨道。”[3]如此发展下去,“无论孝子或浪子都将成为中国传统的孽子”。[4]
余光中提出艺术家们应该做“回头的浪子”。“对传统文化的秉守抱持……仿佛成了余光中生命中的一种另辟途径的文化精神信仰和美学理念情怀”[5]。他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力图在艺术的横断面上调和古典与现代的关系,致力于中国文艺复兴的理想。他在现代散文里对古典意象的融通不得不使读者联想到苏曼殊的“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欧阳修的“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或委婉低沉,或寂寥荒凉。生死别离,爱恨喜忧,如夜的灵魂般凄厉地飘洒在鬼哭神嚎的雨中。余光中的散文,是构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他散文中的意象、符号才能生成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听听那冷雨》一文中,他对聆听巴山夜雨时意境的描摹也化用古典诗词——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中的意象。
余光中小时候上国文课时带有闽腔吴调的古诗文的曼吟回唱,在他成年后成为生命的记忆,这些记忆在其灵感的触动下发而成声,缀而成文,他的散文也因此显出时而淡雅、时而幽深的古典芳香。他在论及好友刘国松的画时说,“他从油画到水墨,我从虚无到古典,都是在一九六一年左右。”[6]《逍遥游》(1964)、《登楼赋》(1966)、《地图》(1967)等篇目都是这一时期他重新回归古典传统后的代表作。
拥有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化阅历作背景,摒弃了“国粹派”和“西化派”的双重迷雾,余光中开辟了第三条路——“浪子回头”之路。诗集《莲的联想》(1980)为他的回归古典作了总结。
二、抒情、说理、叙事、写景的交错
余光中最终确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指导原则:他在创作题材上广泛涉猎,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手法对古典传统进行整合,寻求传统审美趣味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在新的散文形式中唤醒沉寂在读者内心的对古典意蕴的依恋。散文作为其诗余的无心插柳,所成之荫却像他左手的掌纹和记忆的铁轨一样延伸开来,获得了独立的审美内涵和生命。余光中对生命的这种把握和追求,表现在其散文创作上,可分为抒情、说理、叙事、写景四个方面。
余光中的抒情散文,如他自己所说,“往往寄托在叙事、写景之上”,竭力避免“无端的歌哭的空洞之感”。他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在精神——力图真实地把握自然,重塑自然,让艺术的生命和精神在色彩的流动或宁静,和线条的舒展或收缩中自由显现。这种把握会形成某一艺术流派之间的相似,却很难雷同,因为创作不同于摄影;创作是主观性极强的活动,融入了作者的个性气质,契合或暗合了时代精神,因而会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余光中的抒情散文,在绮靡的情思中往往充满知性的思考。
“作家总是喜欢以他熟悉的、有体验、有感悟的对象作为传情达意的意象。”[7]在《逍遥游》一文中,作者将因漂泊而产生的怅惘之情引入玄缈的太空,联想到黄道十二宫的神秘传说、名为“鲲”的北溟之鱼、“多神的时代”“汉族会唱歌的时代”“自由恋爱的时代”“欧洲中世纪的冬眠”“拉丁文的祈祷”、发生在外国租界的“惨案”“阿Q的辫子”“鸦片的毒氛”、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古老文明的衰败和死亡,以及“战国”“军阀”“太阳旗”……读者跟随这些意象在绚丽的文字间游历,怎能不产生秋转春移的历史沧桑感?余光中在抒情时追求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突破了囿于一己的自伤自怜。他仰慕“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8],“志气”成了统领他文章的关键。
余光中的说理散文注重知性而不失性情,常常显出一种人文关怀下的幽默感。像《猛虎与蔷薇》《书斋·书灾》《鸦片战争和疝气》《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假如我有九条命》等文章,单看题目就足以引起人的期待视野,情趣情味相伴而生。即使在《石城之行》《南半球的冬天》等以叙事为主的散文里,幽默的性情和笔墨也很常见。
“他试图用散文实践不停探求人生的意义、追求理想人格和理想世界”[9]。幽默缘自智慧的头脑对世间万物的人文关照,是一种发自生命底层的幽思。知性和人文情怀诗是余光中散文幽默的内核。当一颗悲悯的心,以睿智的眼光审视世事的无常,反思所谓“情理”的荒唐无稽和自相矛盾时,幽默是不难产生的。试想,眼光开阔、胸怀远大、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却为传统观念和民族隔阂所缚,不肯让洋医生亲自为他治疗疝气;莎士比亚在现代学术规范下竟觅不到一只可以维持生计的饭碗。阅读到此,读者怎么能不会心一笑,有所思悟?
余光中的幽默不同于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的那种俏皮和讥讽的幽默,前者更像是一种善意的玩笑,但都是对古典传统的戏谑式的重读和解构,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对情趣的玩味和追求使得这些散文带有一股书卷气,富有文采自不必说。
回忆构成了余光中叙事散文的主要题材,游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九张床》以床为线索,历数了作者的人生轨迹;《德国之声》以德国音乐为引子,对西欧几个国家的语言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红与黑》则叙述了作者在西班牙看斗牛时,对斗牛士和斗牛的角色命运发出悲悯和感慨,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叙事时穿插对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的诗意的描摹。自然景物、人世百态,在敏感的作家笔下都被赋予生命,作家用笔把握和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宣告了自身文化意义的生成。只有在文化层面上,叙事和写景才显得有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来概括余光中这方面的散文创作。
在追求散文的上述四个功能之外,余光中加上了散文的“表意”功能,表意的散文在他看来是写散文的高境界,随性而发,随情所致。余光中的散文在抒情、说理、叙事、写景方面的分立不是绝对的,而是交织错杂的。在抒发情感时注重感性和知性的统一,说理议论时流露出人文情怀和幽默的文风,俯仰历史、写景状物时充满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构成了余光中散文创作的又一个特点。
三、诗歌、戏剧、小说对余光中散文的裨益
对诗歌、戏剧、小说以及音乐、绘画、建筑等文学艺术经验的借鉴,使得余光中的散文实现了对狭隘散文观的突破和对自身的超越。
余光中是以诗集《舟子的悲歌》开始为文坛所熟知的,迄今已创作诗歌九百多首。在南京青年文学会中学读书时,他读《西厢记》和《断鸿零雁记》,读“旧小说和翻译的帝俄时代名著”[8]。在金陵大学外文系时,教英国小说的老师要求他和同学读“《金银岛》《爱玛》《简·爱》《呼啸山庄》《河上磨坊》《大卫·科波菲尔》《自命不凡》《回乡》”,并翻译西方戏剧[8]。从事外文教学和翻译的经历更是丰富了他在戏剧、小说、诗歌领域的知识,为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素材。
余光中的散文,特别是早期的散文,很多是诗性情感的抒发,文字间流露出作者的诗路文心。收录在《左手的掌纹》中的如《听听那冷雨》《蒲公英的岁月》等篇目可以看作精美的散文诗。“余光中诗人的身份使其散文具有诗化的倾向是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9],在《缪思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中,他提出“诗质的散文”一说,足见诗歌艺术对余光中散文创作的影响。
戏剧和小说对余光中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叙事类的散文中,具体表现为人物对话和叙事结构的安排。这种影响是隐性的,贯穿在余光中的潜意识创作里。
余光中在散文创作中显示出广泛涉猎题材和深度开掘主题的胆识,他说,“一班人总以为作家的才气表现在文字和形式上面,却很少想到,开拓新题材,发掘新主题,更需要才气,甚至见识。一位作家在艺术成熟之后,面对生命的百态,应能就地取材,随手拈来,即使重写以往的题材,也能翻新角度和形式,呈现新的面貌。”[8]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种文体存在互相交织的层面,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几种体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间的有意识整合。
四、弹性、密度、质料与余光中散文风格的形成
在做出上述诸种努力后,余光中在散文创作上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审美取向:追求声色味交织的意象美,即注重文章的色彩和乐律;试图杂糅声、色、味诸种感觉,用多种笔法绘制油彩和水墨山水画;并且在其中融入他对历史人文的独特感知。因而他的文章气势撼人,感情动人,声色迷人。
余光中的诗文“对传统文化素材的大量借鉴与现代翻新,还有对经典艺术手法的匠心独运的灵活运用,无不渗透着中国性的哲理和智慧”[10]。他“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制,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这就是他追求的“弹性”“密度”“质料”的现代散文理念,这里所谓的“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各种文体和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而“质料”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底品质”。[11]
综上,余光中饱享古今中外文化的恩惠,在抒情、说理、叙事、写景、表意时注重知性和感性的统一,并借鉴诗歌、戏剧、小说、批评、翻译等创作活动的经验,在新古典主义理想的框架下,构建了自己的独特的散文世界。
[1]潘水萍.诗意的思想在现代——余光中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重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89-98.
[2]李正.文化认同与原乡归依——论余光中乡愁诗的民族化特色[J].文学研究,2015(9):37-38.
[3]余光中.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C]//余光中集(第七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58.
[4]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185.
[5]潘水萍.余光中与“中国新文学”精神的生发[J].学术探索,2016(9):120-129.
[6]余光中.听听那冷雨[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4:60.
[7]王芹.冷雨中的文化寻根——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解读[J].语文建设,2015(14):32-34.
[8]余光中.十二文集·左手的掌纹[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9]王悦华.大陆地区近十年余光中散文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15(6):128-132.
[10]吴鵾.论余光中诗歌创作中的中华文化因子——以文化认同为参照[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54-60.
[11]郑明娳.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卷5·散文批评[M].台北:正中书局,1993:109-110.
(责任编辑 倪玲玲)
I106.4
A
1671-9123(2017)02-0073-04
2017-04-18
殷宝为(1980-),男,安徽肥西人,铜陵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