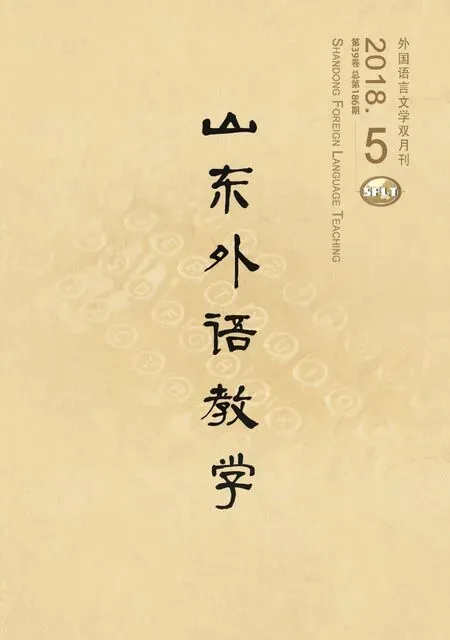当代美国印第安诗歌中的动物形象
邹惠玲 陈晓曦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116)
1.0 引言
动物形象在印第安诗歌中俯拾皆是,究其缘由,印第安人自古以来信奉万物有灵论,对动物视若神灵,崇敬有加。古代印第安人以动物为主角而举行的庆典仪式、表演的谣曲与舞蹈、讲述的神话与传说等,都传达出印第安人的动物崇拜,彰显出他们敬畏生命的深远含蕴以及独特的泛神信仰,这种动物崇拜和泛神信仰在其历史悠久的口头诗歌传统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如鲍比·雷克森所指出的:古印第安口头诗歌中之所以承载了大量动物形象,是因为在印第安人看来,大自然蕴藏着许多从表面上难以理解的智慧和奥秘,只有借助动物发出的“信号和预兆”,才能真正理解大自然的精神和象征意义(Lake-Thom,1997:16)。从这一认识出发,古印第安人以诗歌为载体歌颂动物,通过动物形象“折射出某种特定的意义”(Crawford & Kelley,2005:392),传递出他们的信仰以及尊重万物生灵的态度。古印第安口头诗歌这种抒写动物形象的传统对当代印第安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动物具有人类的各种特性,且不同的动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含蕴,共同构成印第安民族灵魂的核心,昭示出当代印第安人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态度。
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代美国印第安诗歌中的动物元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悄然发生演变和革新。纵观当代美国印第安诗歌作品,有两类动物形象较为常见, 一类是熊、麋鹿、龟和鹰等。它们或者是力量、勇敢的化身,或者是智慧、忠诚的象征,其中尤以熊最具代表性。谙熟自然节律的印第安诗人将这些传统动物形象置于大自然古朴而深邃的协奏曲中,借它们传达出印第安人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文化意旨和对民族精神的崇高追求。在当代印第安诗人中,最擅长塑造熊形象的当属N·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他的诗天马行空、富于想象,描绘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印第安生灵世界。此外,以熊为名的诗人雷·A·小熊(Ray A. Young Bear)、钟爱写鹰的莫里斯·肯尼(Maurice Kenny)、偏爱写牛的伊丽莎白·库克-林(Elizabeth Cook-Lynn )等,也都以描写这类动物形象见长。另一类动物形象则具有特殊的文化定义,包括郊狼、乌鸦、狐狸等。这类动物形象源自传统印第安文化中的“恶作剧者”形象,它们往往违背常理,特立独行,诡计多端,有着双重灵魂。以它们为主角的当代印第安诗歌在曲风上更像是风情小调,以幽默戏谑的旋律歌唱出人生真谛。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当属擅长刻画郊狼的西蒙·奥蒂兹(Simon Ortiz)。在他的诗中,亦正亦邪的逾越边界者郊狼既扮演着文化英雄与导师的角色,同时也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逾越者和边缘化人群。以下笔者将以莫马迪、奥蒂兹等人的作品为例,探究在当代印第安诗人笔下,承继于古印第安口头诗歌的熊、郊狼等动物形象如何表述了当代印第安诗人对于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深邃思考,传达出他们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的独特理解。
2.0 熊——游猎民族的精神寄托
在传统印第安人看来,熊是类人形象和雄壮力量的结合,有时熊和人类几乎一样:“他可以站着、直立地行走;他会哭泣,会呜咽,就像人受伤之后一样。我们在战斗中经常会发出熊一样的声音,讲熊一样的语言……熊和我们一样都有灵魂,他的灵魂在睡梦中和我们对话,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Goble,2005:15)。印第安人把熊视作平等同伴而非普通动物并将熊视作神圣的物种,围绕熊举行形式复杂的典仪。例如,特林吉特族、海达族以及其他西北沿岸部族将熊选作他们的图腾,霍皮人甚至建立了熊族,犹他及其他平原部族有熊舞。在印第安原始捕猎仪式、愈合典仪、成人礼中,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例如,克里族认为猎杀熊不仅充满危险更会因此“付出精神代价”,当熊被猎杀后只有围绕其尸体吟唱颂歌才能安抚其愤怒的灵魂(Rockwell,1991:145)。再如,许多印第安人认为熊的冬眠象征着隔离、死亡、重生,“当冬眠之后的熊在春季出现时,黑脚族、库特奈族和克劳族要举行立春典仪庆祝一元复始、万象更新”(Bol,1998:111)。简言之,象征着“智慧、直觉、自省、保护、愈合”(Lake-Thom,1997:78)的熊不仅一直是印第安口头诗歌中最传统的动物形象之一,而且依然是当代印第安诗歌的主角之一。
在那些满怀深情赞颂熊的当代印第安诗人中,当数基奥瓦族作家莫马迪最享有盛誉。在莫马迪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熊的形象,就诗歌作品而言,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以“熊”(“The Bear”)为题名的诗作。凭借这首将熊神化为大自然缩影与化身的作品,莫马迪获得了1962年美国诗人学会奖。
虽然莫马迪在创作“熊”这首诗时曾经从福克纳小说《熊》得到启发(Stevens,2001:606),但这两部作品中的熊形象及其呈现视角却截然不同。福克纳的《熊》侧重叙述白人奴隶主的儿子艾萨克·麦卡斯林在印第安猎人的教导下学习打猎、多次去山林中捕猎大熊“老本”的故事;而莫马迪在他的诗中则将焦点从艾萨克转到老熊的形象上,从印第安传统文化对熊的诠释出发,浓墨描绘了熊的伟岸形象。诗中这样表现老熊第一次出现在艾萨克面前时的情景:
什么视觉策略
使叶子墙倾斜,
把一道切口撕碎成无数平面。
年事已高、历经沧桑,
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削弱了他的勇气,
从他朦胧欲睡的身躯上是否还能看清当年的胆略和魄力?
看,他并没有走进,
他移动着身躯,却似乎永远停留在原地,
无风的正午,在热辣刺眼的炫光中,
他无形无影,沉默无言。(Momaday,1988:63)
在这三节诗行里,熊在诗中已成为了大自然和荒野的化身,具有灵性和神性。受到心灵震撼的艾萨克不再把熊当做猎物,而是对熊满怀敬畏和仰慕,他那猎杀熊的决心也随之动摇。诗人在写作中使用暗喻的手法,别出心裁地把猎人的暴力行为转化为他在荒野之中的思绪飞扬,把老熊塑造为自然荒野的象征,而艾萨克观察熊的“视觉策略”则对应了捕猎手段。“年事已高、历经沧桑”的老熊显然已经历过数次死里逃生,雄风不再,他疲惫的身躯与其生存的荒野背景环境相呼应。猎人对熊的追猎则象征着人类对原始荒野、大自然的践踏与侵占。然而,纵使衰老疲惫、满身伤口,老熊不怒自威、强大气场足以震慑艾萨克,在老熊身上他切身感受到原始自然的野性和无穷力量。整体来看,这首诗从艾萨克的角度观察熊,从捕猎的初衷到对熊充满崇敬、敬畏。老熊“无形无影”、“沉默无言”的形象充满历史感和神秘感,他像是一个历经岁月变迁、历史之河的圣人,接受世人的拜谒和信奉,而熊的形象在诗中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动物的本体上,而且也上升到了精神层次。正如前文所说,在印第安文化中,熊是神圣的物种,而在这首诗中熊代表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印第安人的大自然,代表着变幻莫测、充满原始气息的荒野。因此,猎人观察熊其实象征着人类观察自然,孱弱的猎人之于苍劲的老熊正如在鬼斧神工的大自然面前渺小的人类,望尘莫及、叹观止矣。老熊的强大意志以及他身上所体现的大自然之变幻莫测在接下来的诗行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自从经历了那次陷阱,他比别人更恐惧,
罗网让他残废,
疼痛带给他的,
是佝偻的脊背和畸形的跛脚。
然后,他不见了,彻底地消失在视线中,
看上去,走得并不那么匆忙,
就像秃鹫控制着滑行,
轻微稳妥,不知不觉。(Momaday,1988:63)
在诗的最后一小节,熊的动作被比作秃鹫在滑翔,它“微微地控制着飞行状态”。大自然中某种未知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引领着熊,老熊已挣脱了肉体的疼痛和局限,超凡脱俗、仙风道骨般的气质使猎人难以捉摸,愈加神往。在这首诗中,老熊不仅是原始荒野的象征,更是一个活图腾,受到猎人的尊崇。诗中熊的形象正契合了熊在印第安远古神话中的地位。它不再只是一只动物,而是原始荒野上的神灵,是叙述者顶礼膜拜的图腾,隐喻着不朽的精神、美德和原始的本真与天性。 老熊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勇敢、自豪、怜悯、坚韧、顽强和恪守自然法则等等,演奏出一首震撼心灵的大自然协奏曲。在这首“协奏曲”中,大自然多种声音的和谐碰撞只为衬托熊之主旋律的雄伟壮美。当描写到老熊充满伤痛的疲惫身躯时,音乐声哀怨颓丧;当描写到老熊奋力挣扎、冲出罗网时,音乐声紧张急促;当描写到老熊在日光下时隐时现、踪迹难寻的庞大身躯时,音乐声神秘神圣,正如悠扬空灵的印第安排箫,诉说着印第安人对大自然的无限崇敬和虔诚。
“熊”这首诗体现了印第安传统文化对莫马迪诗歌创作主题的影响,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作品中引入熊的意象。从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他在诗中赋予了熊形象更深层次的定义:熊是大自然的化身,是荒野记忆的集合,荒野也被理解为在未知领域内的“类熊”存在方式(Stevens,2001:608)。此后,莫马迪在许多首诗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作为荒野精神代表的熊形象。
另一位美国印第安诗人也与熊有着不解之缘,从他的名字“雷·A·小熊”就能探知一二。小熊在他的长诗“熊王的形象挥之不去”(“Nothing Could Take Away the Bear-King’s Image”)中对熊王形象的刻画生动传达出万物有灵的印第安传统观念。在诗中,他将熊王塑造为空灵和大地精华的象征,熊王被猎杀前的一瞬间在他的脑海中久久不能逝去:
虽然你遭遇了不测,
我仍相信会再见到你
你还是原来的模样,
当猎箭在几缕柳枝旁轻擦而过时,
你正在红土地上栖息,
靠近红土地的心脏旁跳动着生命的脉搏。(Bear,1988:262)
这首长诗以回忆熊王被猎杀的一幕为开始,这一幕也在诗中多次出现,成为了贯穿整首诗的线索。熊的坚毅伟岸让诗人叹惋,但诗人同时却又用了不少笔墨描写猎人如何猎杀熊王,这看似矛盾实则与印第安传统文化相一致。印第安人敬畏熊,同时也猎杀熊,因为他们一方面相信人与动物具有亲缘关系、甚至把动物视为神灵,但另一方面又从万事万物平衡统一的宇宙观出发,认为所有生命都可以互相转化和互相分享。在原始印第安生活中,当发生食物短缺时,部族便会举行仪式祈求动物献出生命,以帮助印第安人度过饥馑。然而,印第安人绝不做“多余的滥杀”(Crawford & Kelley,2005:682)。在准备猎杀熊这种被奉为神灵的动物之前,印第安人必定举行复杂的捕猎典仪,以抚慰逝者愤怒的灵魂。这种特殊的捕猎方式也造就了印第安猎人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独特性。在诗中,在捕杀熊的同时,印第安猎人也从熊身上汲取了熊精神的精华,感知到大自然的无穷力量。借助于猎人猎杀老熊的场景,诗人展现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获取其他生命的道德方式”(Crawford & Kelley,2005:392),开掘出印第安捕猎历史的深邃内涵。
诗人在诗中不仅撰写了一出印第安猎人的捕猎历险记,而且描述了自己在当今社会的一系列经历。诗人同自己的几位同伴躺在小山丘上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的他们开始四处游荡。通过对自己以及同伴宿醉后迷糊混沌状态的描绘,诗人从微观视角映射出印第安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迷失、困惑、甚至醉生梦死的生存现状。然而,诗人突然把笔锋转向一把跳入自己眼帘的弓箭,弓箭上那根 “可以触发古老时空信息”的弓弦让处于微醺状态的诗人如梦初醒(Young Bear,1988:266),令他想起远古印第安猎人的光辉形象,想起了坚强伟岸、屹立不倒的熊王,唤起了深藏于内心深处的作为熊性民族后代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诗人感叹时空交错,感悟到印第安远古文明从未消亡,一直对世代子孙产生着深远影响。他百感交集,脑海中再次浮现熊王的身影:
我们就像美国中西部冬季里的风,
无尽地吹动着零落的橡树叶,
诉说着傲天狂尊的合唱,
熊王的形象挥之不去,
他是人,他会行走。( Bear, 1988: 265)
此时,诗人对熊王的形象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他把他的印第安同胞比作“美国中西部冬季里的风”,形象地描绘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在白人社会中飘摇不定、难以立足的生活现状。虽然他们在美国大地上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印第安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感却扎根在每个族人的心中。熊王的形象正是印第安猎人的形象,昔日北美大陆上的主人,今日随风飘摇的流浪者,纵使地位不再,但对印第安身份的认同感根深蒂固。在诗的结尾,诗人又推出一个头束红色发带的印第安猎人形象。诗人穿越时空隧道,回到远古北美大地,描绘出一幅狩猎民族剑拔弩张、指点江山的宏伟画卷。此时,熊和印第安猎人两个对立体仿佛合二为一,这首“协奏曲”也在野外狩猎的原始自然背景下把两个声部的演奏完美地融合进同一旋律,推向最高潮。这正契合了远古印第安神话中人与动物互相转化的传说,熊王虽被利箭刺穿,但他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却永远活在每个印第安猎人的心中,与诗的标题“熊王的形象挥之不去”遥相呼应。借这首长诗,小熊抒发了他对印第安这个游猎民族的勇敢、宽厚的“熊精神”的歌颂和赞美,以及对印第安民族复兴的信念和渴望。
3.0 郊狼——亦正亦邪的恶作剧者
当代美国印第安诗歌中还有一类具有特定文化寓意的动物意象,学界称之为“恶作剧者”,这类动物形象包括郊狼、乌鸦、狐狸等,其中以郊狼(coyote)最具代表性。郊狼是一种生活在北美洲西部原野上的小狼,也是印第安民族最远古的神秘象征之一。“在西南地区、大盆地、高原地区、加州和大平原的各印第安部族口头文学中,最广泛、最经常出现的恶作剧者形象当数郊狼。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研究者常常以郊狼作为印第安恶作剧者的同义词,把两个名称交替使用”(邹惠玲,2005:34)。在印第安口头文学中,郊狼担当着多重角色,有时是文化英雄和人类导师,但更多的时候是既狡诈又笨拙的捣蛋鬼,以“好色、饕餮、傲慢、反叛、贪婪、残忍、卤莽、懒惰”的“恶习和蠢行”而著称(Ballinger,1991:26)。另一方面,郊狼又是诸多印第安创世传说的主角之一。北美各印第安部族的创世传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某位创世神灵创造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灵以及他们居住的世界;从天而降或者来自地下的印第安人把混沌世界改造成人类宜居之地;某位文化英雄为人类创造出生存空间(邹惠玲,2007)。在前两类传说中,郊狼等动物往往是创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而在后一类传说中,郊狼等动物则以文化英雄的身份直接担当创世进程的主导。
作为印第安口头文学中的一个特定文化符码,郊狼深得当代印第安诗人们的偏爱。他们塑造出一个个亦正亦邪的恶作剧者郊狼的形象,继承印第安口头文学的戏谑风格,咏唱出一曲曲洋溢着印第安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的风情小调,彰显着印第安人的生存智慧以及对人生的独特认识与思考。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诗人西蒙·奥蒂兹的诗作不仅经常以郊狼形象为主角,而且鲜明体现出印第安口头叙事诗歌的传统。例如,在“谈郊狼”(“Telling About Coyote”)这首长诗中,奥蒂兹似讲故事般娓娓道来,把恶作剧者郊狼的双面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在这首长达120行的长诗中,奥蒂兹开门见山地把郊狼称为“万物之源,众生之始”。前文提到,有些印第安口头传说讲述的是某位创世神灵创造世界的故事,而另外一些印第安口头传说则把郊狼或者其他动物描述成印第安人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创造者。例如,在克劳族的传说中,在天地混沌的世界之初,郊狼先是把野鸭从水底叼出的几块泥巴变成了大地,又把野鸭从水底衔出的水草变成了人形,从此才有了人类和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因此,克劳人把郊狼奉为他们的创世英雄,认为“现有的一切,或者说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来自‘老人郊狼’” (Erdoes & Ortiz,1984:88)。在这一意义上,奥蒂兹这句“万物之源,众生之始” 不仅表达了对郊狼的肯定和推崇,而且传递出视郊狼为创世者和文化英雄的印第安传统观念。然而,接下来奥蒂兹话题一转,揭示出印第安传统文化中郊狼形象的另一面:“麻烦的缘由,祸患的起因”。作为恶作剧者的典型代表,郊狼具有反叛、贪婪、狡诈、残忍的一面,常常为了一己私欲或一时快活,制造出各种麻烦和祸患。不过,印第安人并没有因此而声讨或者痛斥郊狼的种种恶作剧行为。这正好凸显了印第安人信奉平衡统一的宇宙观,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以两个部分存在,好的和坏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他们互为补充,同属一体”(Brown,1982:23)。在他们看来,恶作剧者郊狼与其他生灵一样,是一个集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于一身的独特形象。另一方面,无论是郊狼利用自己的“超凡技术、策略、欺骗术、哄骗花招”打败敌人,抑或是“被自己的花招所蒙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恶作剧者郊狼的种种行为及其后果教会了印第安人如何明辨是非、如何约束自我(Crawford & Kelley,2005:682)。因而,时而言传身教、时而以身试法的郊狼亦被印第安人奉为导师。
在寥寥数行勾勒出郊狼形象这个矛盾体之后,奥蒂兹运用印第安口头谣曲的形式,吟唱出有关郊狼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读来朗朗上口,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因果关联,共同构成一曲恶作剧者郊狼的风情小调。在前一个故事中,郊狼吹嘘自己拥有“最最光滑、最最柔和的皮毛”,结果成为“所有其他动物嫉妒的对象”,它们在一次赌注中设下圈套,夺走了郊狼引以为荣的皮毛,把它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最后,一群老鼠找来一堆破旧的皮毛碎片,“用松脂粘贴到郊狼身上”(Ortiz,1992:158)。如果说这个故事侧重于表现恶作剧者郊狼自食其果,以其可怜又可笑的结局告诫世人避免重蹈郊狼的覆辙,那么后一个故事则主要展示郊狼略施小计便能轻而易举成功的恶作剧能力。诗中写道,乌鸦原本拥有“最最纯白的羽毛”,这让众多动物艳羡不已,同时也招致郊狼的嫉妒。诗人以带着些许欣赏意味的戏谑口吻,细细述说了郊狼施展其惯用的恶作剧伎俩,借助篝火、松木和狂风,捉弄乌鸦的故事,揭示出郊狼率性妄为、以恶作剧为乐趣的本性,同时也与诗开头对郊狼的界定互为印证,向读者证明经常制造“麻烦”和“祸患”的恶作剧能力。
在另外一些诗作中,奥蒂兹则侧重于刻画郊狼作为印第安人导师的形象。例如,他的“郊狼讲述的创世”(“The Creation, According to Coyote”)以郊狼向诗人讲述普韦布洛族创世神话为主线,突出表现了郊狼之于印第安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在这首诗中,郊狼告诉诗人,印第安人来自地下,之后,郊狼又特别强调,是最早破土而出的优乐亚耶哈和马萨维哈孪生兄弟带领第一代印第安人开拓生存空间:
孪生兄弟说,
“让我们带领这些可怜的生灵
拯救他们”。
后来,历经那一场场
扣人心弦、变幻莫测、惊心惨目的腥风血雨,
他们终于见到天日。
这就是生命,所有这些,所有这些。(Ortiz,1992:42)
在这首诗中,郊狼的形象更接近于一位以讲故事的方式谆谆教导族人、提醒他们不忘本源的部族长者。故事讲述是各个印第安部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讲述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是家庭或部族中的年长者”(Barrett & Markowitz,2004:255)。印第安人相信人与自然界万物生灵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在创世之初,生灵具有变形的能力——从动物变成人,从人变成动物”(Cousins,1997:501),因而郊狼或者其他生灵在印第安口头文学中也常常担当着传承部族文化的导师角色。奥蒂兹在这首诗中刻画的郊狼就是这样一个向族人传授知识、传递历史的长者形象。然而,奥蒂兹并没有忘记郊狼的恶作剧者身份,诗人对他的话秉持几分不信任,不时在郊狼的叙述中插入指向郊狼的怀疑性词句:“他可能吹嘘夸大”、 “他主要是在吹牛”(Ortiz,1992:41-42)。这些风趣幽默的议论冲淡了气势恢宏的部族创世神话的沉重感,使之变得轻松活泼,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恶作剧者郊狼的独特形象。郊狼亦正亦邪、特立独行、令人难以捉摸。他时而通过自身经历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时而又在传授部族历史文化的同时搞笑、吹牛、耍弄他人。不过,尽管深知郊狼的恶作剧天性,诗人在全诗结尾依然写道:“你要知道,我是相信他的”(Ortiz,1992:42)。显然,这最后一行诗句不仅表述了诗人对郊狼所讲授的创世故事的接受,更传达出印第安人对于恶作剧者郊狼的人类导师身份的认可。
郊狼的形象承载着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独特观念。印第安人崇尚万事万物和谐平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并不重视善恶是非的清晰划分,而是追求好与坏之间的协调、统一与共存。从这种观点出发,奥蒂兹笔下的郊狼形象拥有复杂的性格和多变的面孔。然而,无论是表现郊狼那些缺乏道德是非观念的恶作剧行为,还是讲述郊狼传递印第安历史文化的诸多传说和故事,诗人那种戏谑语调之中都发散着对以郊狼为代表的印第安恶作剧者的喜爱和推崇。
4.0 结语
当代美国印第安诗歌中栖息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意象,他们是诗人歌唱的对象,也为诗歌贴上了风格迥异的标签。从以熊为代表的最原始朴素的动物形象,到以郊狼为代表的逾越常规、正邪难分的恶作剧者,印第安诗歌中的动物意象既是印第安诗歌的特色,也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从强悍狂野的熊和亦正亦邪的郊狼这两类代表性动物形象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印第安诗人继承了他们民族的传统精华,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古老智慧的印第安文明,他们的思维模式、创作手法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赞扬熊的智慧、力量、勇敢、神秘,借此歌颂自己的民族和祖先,唱出回归原始、世界大同、返璞归真的传统文明之歌;他们吟诵时而狡黠、时而正直、正邪交错的恶作剧者郊狼,谱写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印第安风情小调。简言之,借助熊、郊狼等充溢着印第安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动物形象,当代印第安诗人向世界昭示着印第安宇宙观和价值观的深邃内涵,咏唱出一曲又一曲生命的诗性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