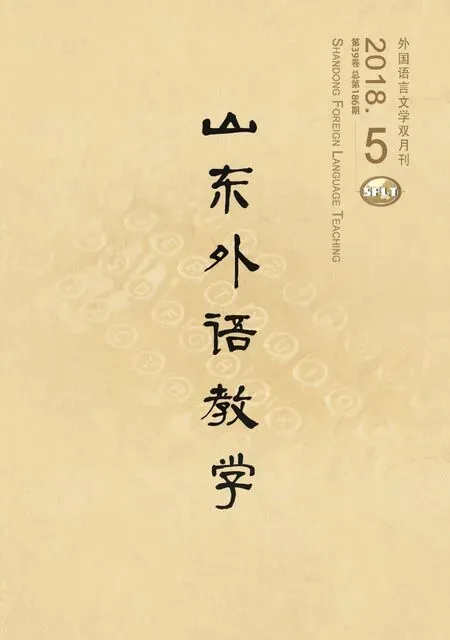从《皮草女王之吻》看北美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教育
刘克东 刘仪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1.0 引言
汤姆森·海威(Tomson Highway,1951—)是一名当代加拿大土著剧作家、小说家和儿童作家,曾于1994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印第安作家。他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一个土著部落,六岁时被送到远离部落的寄宿制学校就读,直到十五岁搬到温尼伯念高中,之后又先后在曼尼托巴大学和西安大略大学修读音乐和英国文学。1990年,海威的弟弟雷内死于艾滋病,痛失手足的悲伤促使他创作了第一部自传小说《皮草女王之吻》(KissoftheFurQueen,1998),此书在加拿大夺得多个奖项,并于2004年被译成法语版本发行。《皮草女王之吻》讲述了一对印第安兄弟从小被送至寄宿制学校接受同化教育,长大后在白人社会中追逐梦想,寻求身份认同的故事。
在征服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上,加拿大与美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强制同化的教育政策。19世纪后半叶起,加拿大白人开始认为印第安人野蛮低级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于是,为了“驯化”他们,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的教育手段逐渐从文明同化发展到了强制同化。19世纪50年代,由政府出资、教会开办管理的保留地外寄宿制学校开始在加拿大崛起。不仅如此,加拿大议会更于1876年通过了《印第安法》,并数次修改,以保证印第安儿童接受寄宿制学校的同化教育(彭雪芳,2012:77)。1894年,“加拿大共有11所寄宿制学校;1912年有3,904名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制学校上学;到了1931年寄宿制学校遍布加拿大各地,达到了高峰,数量猛增到80所,有70%的7-14岁原住民儿童在这些学校就读。1947年寄宿制学校原住民的人数高达9,149人”(陈巴特尔,2015:3)。可以看出,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和强制同化教育在加拿大快速发展,经历了一段顶峰时期。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寄宿制学校开始陆续关门,因为印第安人的融入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生活水平反而越来越糟。再者,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土著们开始在社会上控诉自己在寄宿制学校里遭受的悲惨经历。1996年,随着最后一所学校的关闭,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在加拿大完全消失。
目前,国内尚无对《皮草女王之吻》一书的研究,国外亦寥寥无几。本文结合此背景分析了《皮草女王之吻》一书中北美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同化教育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各种影响。总的来说,同化教育伤害了印第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印第安社会问题。学校里的虐待行为给许多土著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身心伤害,低下的教育质量抑制了印第安儿童身上的个人潜能,使其成年后在社会上的生存情况总体不佳。除此之外,身份认同危机也在这代印第安人身上普遍存在。在本书中,“寄宿制学校力图使兄弟俩抛弃‘落后的’克里族主观意识,来实现‘现代化’,从而给他们造成了精神创伤,兄弟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步入了青年期”(Buzny,2011:1),开始了漫长的抵抗之路,并由此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不可否认,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兴办是一场失败的教育运动。
2.0 对印第安文化造成的巨大破坏
在白人开始殖民美洲前,印第安人有着独特的传统教育方式。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形式以口授历史、讲故事、举行仪式、学习狩猎技术等为主”(代影,2009:11)。通常由部落中德高望重的老人集中传授,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将部落的历史纪事和传统文化教授给儿童。然而,16、17世纪起,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印第安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在征服北美大陆的同时,殖民者们不仅大量屠杀印第安土著并将其驱赶到土地贫瘠的区域,还试图把“野蛮”的印第安人“基督教化”。美国和加拿大建国后,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教育,其中寄宿制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体现。寄宿制学校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一代印第安人身上的传统文化印记,对印第安文化造成了极大伤害。
在《皮草女王之吻》中,克里族印第安儿童杰里迈亚和加布里埃尔便是在就读寄宿制学校的过程中,逐渐淡忘了本族的语言、习俗和信仰,成功被“白人化”。加布里埃尔原本的印第安名字含义为“舞者(Ooneemeetoo)”,在出生后接受洗礼时,神父强制将他的名字改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英文名(Highway,2000:37)。由此可见,从一出生起,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特征就被剥夺。在书中,杰里迈亚来到寄宿制学校的第一天,印第安传统的长发就被统一剪去(Highway,2000:51-55)。不仅如此,在学校里必须使用英语交流,否则将面临惩罚。之外,兄弟俩一年中难得回家一次,几乎完全与印第安部落隔离。印第安部落本都有自己的宗教传统,然而在寄宿制学校里,兄弟俩被全面“基督教化”改造,被灌输基督教教义和价值观。由此可见,寄宿制学校,为了达成摧毁印第安文化的目的,同化印第安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保留外地寄宿制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亨利·普拉特(Richard Henry Pratt)曾说过:“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杀死他们体内的印第安性,才能拯救他们”(Bear,2008)。这段话道出了开办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理念:通过强制同化的方式,使印第安人遗忘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白人化”,或者说是“基督教化”,以达到融入主流社会的目的。
一旦被同化,与传统文化的纽带就很容易被割裂,书中作为同化教育的受害者的兄弟俩便是如此。当时的白人认为,“断绝学生与部落和父母的接触,让他们在隔离的状态中学习白人文化,才能使印第安人放弃野蛮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翟巧相,2005:13)。如此一来,印第安传统文化被完全摒弃,有的印第安孩子甚至连本族的语言都忘记了。在书中,当杰里迈亚搬到温尼伯读高中时,当弟弟用印第安语问他问题时,他已经全然不习惯,也不想用印第安语回答了,经过多年的熏陶,此时他的英语口语已经流利得和一个白人男孩没什么分别了(Highway,2000:160)。同样,当兄弟俩回部落探望病危的父亲时,加布里埃尔的印第安语虽然还能进行对话,却已退步许多了(Highway,2000:226)。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而是有着普遍现实基础。
对于文化破坏的强势入侵,不同的印第安人作出的反应有所不同。在书中,有一次杰里迈亚误入同学阿曼达和她的族人们在温尼伯城中一处定期举行部落仪式的地方,她们穿着本族的传统服饰,跳着某种传统舞蹈,而从小在寄宿制学校里接受白人教育的杰里迈亚全然不知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阿曼达的祖母对杰里迈亚说道:“你们这些北方人啊。你知道吗?你们忘记这些舞蹈实在是太不应该了。难道它们不是优美的舞蹈吗?流传了上千年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它们”(Highway,2000:170-176)。杰里迈亚来自一个克里族部落,这个部落受白人文化入侵很深,部落人民几乎都被变成基督教徒,杰里迈亚的父母更是十分虔诚,从小叮嘱兄弟俩要时刻不忘祷告。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杰里迈亚对待自己所遭受到的同化可以说是毫不反抗,而阿曼达与她的族人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他们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尽己所能保其周全。当杰里迈亚在课堂上作报告时,提到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最暴力血腥的时期,阿曼达提出了强烈反对,她认为在北美大陆上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加害一点也不比法国大革命中的轻,比如著名的切罗基族血泪之路(Highway,2000:148)。由此可见,阿曼达不仅对白人的暴力入侵十分憎恨,对于他们实施的文化入侵手段也是相当抵触。书中的杰里迈亚和阿曼达,是两类对同化政策作出不同反应的印第安人的典型形象,也代表了现实中面对同化不同反应的两个群体。
白人们试图通过寄宿制学校中的一系列手段,剥夺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观取而代之。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错误的。《美国印第安人》的作者威尔科姆·沃什伯恩也意识到强制同化政策的错误,在书中指出:“对印第安人文化的愚昧无知以及对土地的贪婪,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把印第安人踉跄地推入了20世纪,完全失去了维系过去生活的经济来源和文化价值观”(曹彤彤,2016:49)。美洲大陆是印第安人生活了成千上万年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和宗教思想,让他们通过抛弃传统文化的方式来获得“进步发展”的做法绝不可能行得通。
3.0 对印第安儿童造成的不可磨灭的身心伤害与潜能抑制
寄宿制学校实施的同化教育对印第安儿童造成了身心伤害,也抑制了原本存在于每个孩子身上的个人潜能。在《皮草女王之吻》中,杰里迈亚和加布里埃尔在就读寄宿制学校期间,既受到了身体虐待,又留下了心灵创伤,对他们之后的人生负面影响巨大。
在书中,学校里的神父对所有男孩都实施过性侵,对其中长相俊俏的加布里埃尔尤其频繁,作为哥哥的杰里迈亚更是亲眼目睹数次。兄弟俩对此十分憎恨和厌恶,却无处诉说、无处求助,因为他们的父母已被洗脑成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太可能相信神父会做出这般龌龊之事,即便相信,在白人势力的强势压制下,也没有能力替儿子们讨回公道。故而,兄弟俩只能继续默默忍受,这个丑陋的秘密给他们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造成影响一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其结果在杰里迈亚身上的体现就是无法与人有效地建立亲密关系。进入城市生活后,杰里迈亚整日整夜沉浸于自己的钢琴事业中,完全没有社交生活,“钢琴和音乐是他仅有的朋友与陪伴”(Da Cunha,2009:101),这也是他几次与弟弟爆发争吵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杰里迈亚在阿曼达向其表白后与她开始了一段浪漫关系,却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不了了之。在书中,当杰里迈亚第一次和阿曼达发生性行为时,痛苦和快感的交织让他情不自禁地哀号:“是的,神父大人,让我流血吧,请让我流血吧”(Highway,2000:259)。这足以证明寄宿制学校里的性侵经历成为他心底挥之不去的伤痛和阴影。而加布里埃尔受到的身心伤害在其身上造成的结果更为严重,童年的性侵阴影直接导致加布里埃尔踏上万劫不复的堕落道路,最终患艾滋病死去。
事实上,遭受虐待的现象在寄宿制学校里非常普遍。比如上文提到的印第安儿童比尔·赖特在采访中揭露道,学校里的女看守曾用煤油给他洗澡(Bear,2008)。就读于谢尔曼学院的纳瓦霍族女孩露西·托莱多也在采访中提到,在周六晚上的活动时间,印第安学生们被带去观看一部电影,电影的内容是牛仔把印第安人全部杀了(Bear,2008)。在学校里的这些悲惨经历无不给印第安人本就痛苦的人生雪上加霜。
此外,寄宿制学校对儿童的潜能抑制亦是显而易见的。印第安儿童们从小被送到远离部落的寄宿制学校,在完全隔离的环境中学习陌生的白人文化。这种通过切除文化根源的教育方式无法使印第安儿童获得健康的成长和能力发展,导致毕业后在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十分糟糕。在书中,由于生活在温尼伯的印第安人普遍生活情况极其糟糕,酗酒现象普遍,每天都有印第安醉汉倒在街头,作为“温尼伯印第安友谊之家”的成员,杰里迈亚连续六年负责在深夜的大街上巡逻,专门寻找那些醉倒街头的印第安醉汉,将他们拖回(Highway,2000:220-22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杰里迈亚是一个特例,他是钢琴大赛办赛47年以来第一个获得冠军的印第安人,震惊了所有人。在当时的同化教育政策下的印第安人,获得成功的事例是极其罕见的,这也侧面反映了寄宿制学校对印第安儿童的潜能抑制。此外,1928年由刘易斯·梅里亚姆博士牵头从各个方面调查印第安人生存现状而写成的《梅里亚姆报告》也深刻揭露了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教育失败。报告中指出,“寄宿制学校具有程序化的特点,学校里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没有留出时间培养孩子们的积极性,孩子们每时每刻都由信号或命令所指挥着,这让一切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Merriam,1928:32)。另外,在寄宿制学校里,教师的工资微薄,教育质量普遍低下,孩子们每天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从事大量的生产性劳动。因此,事实证明,在寄宿制学校糟糕的教育条件下,印第安儿童无法获得恰当的教育,其潜能没有得到有效开发,致使毕业后在社会中立足对他们而言成为了一件难事。
4.0 造成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所谓身份认同危机,即“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王成兵,2004:97)。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是建立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而对于寄宿制学校里的印第安学生而言,同化教育政策将他们与部落文化的纽带生生撕裂,强行将白人文化灌输到他们脑内,这无疑会使正处于身份认同建立阶段的印第安学生们愈发迷茫、不安和绝望,造成可能祸及一生的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皮草女王之吻》中,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文化认同上。在书中,杰里迈亚自小就显示出了非凡的音乐天赋,幼年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弹奏手风琴,然而,到了寄宿制学校里,他再也无法接触到曾经那日日挂在身前的手风琴,在学校里神职人员的引导下,杰里迈亚学会了弹钢琴,并深深热爱上了它。在这里,钢琴演奏是白人社会价值观中所推崇的一种高雅艺术,是白人文化的代表。杰里迈亚进入寄宿制学校后,弹奏的乐器由幼时的手风琴变成钢琴,象征着他从传统的部落文化中脱离出来并投身于主流的白人文化的过程。杰里迈亚看似是一个同化教育政策的成功案例:他能说一口与白人男孩毫无分别的流利英语,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一举在钢琴大赛中夺冠成名。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士。由于种族歧视等不可避免的原因,印第安人在主流社会中很难真正得到白人的认可,而作为一名在白人世界开过眼界的印第安人,他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早已与部落人群脱轨,甚至无法通过语言表达让父母理解自己的钢琴梦想。这便使他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从寄宿制学校毕业出来的印第安人大都如此,“在白人社会中找不到合适的或是体面的工作,又不得不返回保留地,但由于长时间脱离部落社会生活,很多技能和习惯都被磨灭,无法自如生活在保留地……中,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曹彤彤,2016:48)。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直接导致了印第安人在文化认同上的迷失。
另一方面,寄宿制学校的同化教育对印第安人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在宗教认同上。印第安人拥有自己悠久的宗教信仰传统。然而,自欧洲人开始殖民北美大陆起,从一开始的传教活动到后来的强制同化政策,“许多印第安人,甚至整个印第安人部落都被基督教化了,其结果便是一部分印第安人持守印第安人传统的土著宗教信仰,另一部分则被基督教化”(王宏丽,2010:32)。在《皮草女王之吻》中,兄弟俩出生的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基督教化的部落,他们从小便被父母教育要信奉基督教。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布里埃尔越来越厌恶这个被强加的信仰,其中一个关键的诱因便是在学校里遭受神父性侵的经历,这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基督教信徒的虚伪和丑恶。但他并没有马上寻求对印第安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而是经过土著同学阿曼达的熏陶和普及,亲眼目睹了一群生活在城市中的印第安人对传统土著宗教信仰的坚守,才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对于印第安人的巨大意义。宗教认同是身份认同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对于印第安人整体而言,传统宗教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是他们在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书中,加布里埃尔临死前嘱咐哥哥,死后不想让牧师靠近自己,而是想举办印第安传统仪式。最后,杰里迈亚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拼尽全力成全了弟弟的愿望,他说,“我们是印第安人!和任何人一样,我们有权利举办我们自己的宗教仪式”(Highway,2000:305)。从中可以看出,在白人的同化政策下,当时的印第安人若想要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印第安孩子们自小在寄宿制学校里被灌输基督教信条,疏离了自己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这种宗教自由的剥夺无疑加重了印第安人身上本就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
5.0 结语
总体来说,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发展在19、20世纪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本书作者汤姆森·海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读于加拿大的一所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因此书中描写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但是,寄宿学校的同化教育对印第安人,尤其是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
自白人踏上北美大陆起,印第安人事务便是他们注定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自19世纪中叶起,白人通过兴办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实施同化教育政策,意图让印第安人脱离印第安文化并融入主流社会,然而,他们“忽视了印第安人的传统社会习惯……以文化偏见为出发点……给印第安人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和民族灾难”(喻冰峰,2004:22)。《皮草女王之吻》的主人公便是这场失败的教育运动的受害者,他们的人生受寄宿制学校的同化教育影响深远,并穷其一生都在与之作抵抗。小说的悲剧结尾发人深思,让读者知道,一味的同化,而不顾印第安人的悠久文化历史,只会给他们带来更深重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