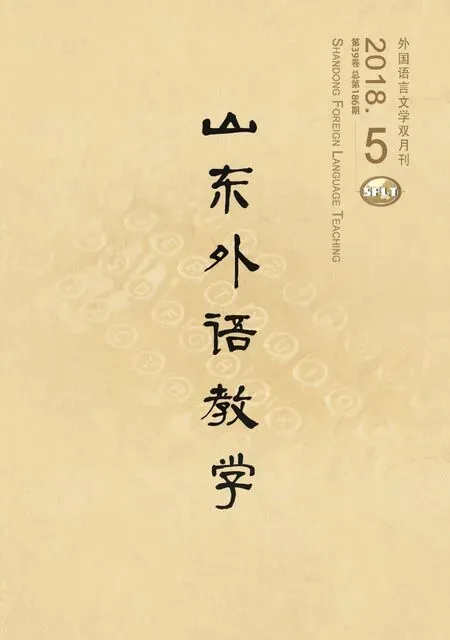双语理论视角下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研究
姜晖 范晓龙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1.0 前言
语用能力在语言能力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二语语用能力的构建和发展也是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问题。刘建达、韩宝成(2018)以交际语言能力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中国英语学习、教学、评测的语言能力理论框架,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语用能力。语用能力,顾名思义,就是运用语言的能力,涉及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之间的关系。从Chomsky(1965)最早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开始,理论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对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各持不同的观点(Hymes,1972;Canale & Swain,1980)。Thomas (1983)从实施交际行为出发,把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前者是在一定语境中通过正确的语言形式来实施交际功能的能力,而后者是遵循一定的社交语用规则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这些关于语用能力的研究都是针对母语说话人的语用能力。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二语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是否和母语的语用能力相关?两种语言的语用能力是否会发生迁移? Kasper (1998)认为语用迁移是母语的语用知识和能力对于二语语用知识的使用与习得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单向的。而Kesckes & Papp(2000)认为语用迁移是双向的,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中语用知识和技能的互动交流。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不同于单语者,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母语语用能力来研究二语语用能力。那么什么是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路径如何?本文在回顾当前语用能力研究的基础上,以Kesckes & Papp(2000)提出的双语理论为框架,探讨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内涵及发展问题, 以期为二语语用能力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0 关于语用能力内涵的相关研究
对语用能力的界定和研究多是以语言学理论、二语习得理论和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和前提的,目前学界对于语用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语用能力的知识观和运用观
Chomsky(1965)最早提出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之分。但Chomsky并没有就语用能力和语法能力之间的不可分离关系以及语言使用的适切条件进行深入研究。 Hymes(1972)提出了交际能力与交际使用二分法,也就是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规则的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随后的研究者也普遍认为语用能力是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Bachman,1990;何自然、陈新仁,2004;卢加伟,2015)。戴沅芳、张绍杰(2015)认为语用能力是外语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的语言知识(口语和书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语用能力,是体现在语言使用者在词汇、语法和语篇层面上的知识选择。外语学习者要先将所学的目的语知识内化,然后把目的语的语法知识和语用规则连接起来,从而做到得体地运用语言。在对国内外语用能力研究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理论框架,韩宝成、黄永亮(2018:95)从应用语言学语言运用的角度,把语用能力(pragmatic ability)界定为“语言使用者结合具体语境,运用各种知识和策略,理解和表达特定意图的能力”。这种界定把语用能力分为语用理解能力和语用表达能力,语言知识和策略是语用能力的基础。语用能力的知识观强调的是语言资源的知识和语言资源在适切的语言环境中得体使用的能力。语言知识始终是语言使用的基础。
2)语用能力的意识观
语用能力的意识观认为语用能力就是一种意识(Ifantidou,2011), 包括语言意识、语用意识和元语用意识。语言意识是指能够识别语言形式,语用意识是指能够识别不同语篇类型的语用效果,元语用意识是指对相关语言形式和语用效果进行元表征和解释的能力。程杰(2017)也认为语用能力包括语用意识和元语用意识两方面。在语用能力研究中,元语用意识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元语用意识是语言使用者在做出语言选择之前,在大脑中对语言形式、交际场景和目的之间如何选择所进行的协商和调整。语用能力实际上就是语用选择的表现,这种选择主要是语言知识和语用规则的选择。语用规则是建立在话语社团的规范、行为模式和规约性基础之上的。Bialystok (1993:54)认为双语成年人所犯的语用失误不是因为不理解语言形式和结构,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的错误选择。造成错误选择的一个原因是缺乏控制注意资源的能力,也就是缺乏对于语言形式、意义和社会语境规则的注意。这种注意和选择实际上就是语言使用者的元语用意识的体现。Vershueren(1999)从语用综观论出发,认为任何社会规约和因素都要经过认知处理才能对语言行为有所影响,人们的语言选择是意识程度的痕迹体现,出现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因此语用能力的意识观强调的是一种认知过程,揭示能力形成的认知机制和能力发展的动态性特征(卢加伟,2015)。
3) 语用能力的体验认知观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应用到二语习得和语用学研究中。在认知语用学的研究框架中,语用能力的认知观主要体现在对语用意义的体验认知和构建中,如通过隐喻、意象和概念等认知方式来完成。二语学习者先体验二语语言形式,获得与二语社会现实相关的概念图式,将其内化后以语用知识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最后再依靠隐喻等认知机制重新理解语言形式与语用意义之间的关系(卢加伟,2015)。毛眺源、戴曼纯(2017)认为语用能力就是交际者借助概念、隐喻等认知手段达成言语理解,促成交际的认知能力。所以,二语语用能力就是一个通过认知手段,依靠普遍认知结构和原则激活或者重构相关经验的过程。由此可见,概念的形成在二语语用能力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虽然以上关于语用能力的观点各有千秋,但是各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之间都是相通的,而且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无论从何种观点出发,语用能力是一种潜在的认知语用机制,是交际者利用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借助概念、隐喻等认知手段,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并不仅仅是对二语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的选择和使用,二语学习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发展的过程(Kesckes,2000),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借助二语的语言形式和母语的概念系统,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中获得二语语用概念意义,重构二语的语用知识体系,发展语用能力。
3.0 双语理论(Dual Language Theory)
双语理论是Kesckes & Papp (2000)针对中介语语用学中的interlanguage提出的,用来解释二语习得者在语言发展和使用过程中一语和二语之间的关系问题。中介语语用学强调二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个中介语的状态,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处于两种语言中间,最终目标是达到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说在二语使用者大脑中出现一套全新的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但实际上多语研究已经证实双语者并不是具备两套完全独立的概念系统(Paradis,1995),语言学习者并不是处于两种语言的中间发展状态,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增加新的信息来改变现有的概念和语言系统,从而在概念系统产生质的变化(Kesckes & Papp,2006)。Kesckes(2010)认为单语者和多语者的语言处理机制最大的不同在于概念而不是语法方面。双语者的语言系统不同于单语者的语言系统,这种独特的多语系统和任何一种单语系统都不一样,是双语者概念发展的结果。这种差异是由于“深层共享概念基础”(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e—CUCB)的存在以及两种语言系统的相互作用。Kesckes & Papp(2000)认为CUCB是所有双语语言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新的语言系统和母语语言系统的思想根植于同一个概念系统,来源于同一概念系统,可以进入两种语言通道。双语者大脑中的深层共享概念基础(CUCB)和双语之间的双向迁移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双语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组合,因此不能简单的用单语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功能。双语能力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种单语能力的总和,因为语言使用不但有普遍性,而且具有文化和语言的特征。双语者并不是指两种语言的独立存在,而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协同作用来影响双语者使用语言(Grosjean,1985),因此双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一直处于动态的概念形成和改变的过程,双语者的认知不具有语码依赖性,而是概念依赖性。
双语理论的关键是概念化,它强调的是概念和语言层面的动态互动,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互相对彼此产生影响。概念知识被词汇化或者匹配一些语言形式如词汇、词组、句子或者话语。在双语模式下,语言产出始于说话人的前语言思想(preverbal thought),在CUCB中或者概念器中以结构的形式预先存在。从CUCB出发,这个前语言思想进入到语言通道,把概念表征和语言表征结合起来,然后进入到语境和由说话人策略结合所形成的语言模式表层。CUCB中包含着三种概念:共同概念(common concepts)、特定文化概念(culture-specific concepts) 和协同概念(synergic concepts)。在双语者记忆中有许多和两种文化相关的共同概念,这些概念的不同只是体现在词汇层面,如“蜜月”和“honeymoon”。特定文化概念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力量,如“春节”和“圣诞节”。协同概念是Kesckes(2003)提出的,指一组独特的双语概念,以两种语言的词汇来表征,但是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不同的文化负荷, 比如“午饭”和“lunch”。对于中国人来说,“午饭”也是一天中很重要的一餐,有主食和副食,但是对于英美人来说,“lunch”只是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三明治。CUCB中的大部分概念和知识是指特定的语言和文化概念,双语者的概念、知识和技能通过两种语言通道进入,因此会保留特定语言和文化特色。双语者的共有概念基础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双语者的语言能力不同于单语者的语言能力。CUCB是一种概念表征,是以语义和概念为基础,而不是形式和符号的表征。
双语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把语言、概念和社会-文化信息整合在一个模式中来解释双语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些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问题,它使双语使用者所获得的概念知识和包含共有CUCB的双语系统相互互动。源于同一个概念基底的思想可以进入到两个语言通道,这对语用技能和表现有重要影响:单语者和双语者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区别不在于用语言来做什么,而是怎么用语言来做事,也就是语言的选择,我们如何去选择,怎样去理解话语,并找到相关性。语言形式的差异是概念化方式的反映,不同语言中概念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语言对应着概念,概念网络对应着认知域(鞠晶、孙启耀,2011)。因此,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概念发展的过程。
4.0 二语语用能力发展中的概念社会化
Kesckes(2014)指出语用能力的发展是语言社会化的一部分,母语语用能力是语言社会化的结果,母语中的语言和社会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不可分割。母语说话人的语用能力是在母语社会环境下自然习得的,说话人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选取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而无需刻意地将语法和语用层面结合起来。但二语语用能力却不能等同于母语语用能力。戴沅芳、张绍杰(2015)指出了中西方学者在界定语用能力时都忽略了母语说话人及外语学习者在语用能力上的区分,二者所处的语言环境和本质内涵不同,因此不能用英语母语说话人的交际能力和语用能力来界定和衡量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双语系统中发生变化的是概念系统,二语语用能力是概念社会化的结果(Kesckes,2014)。概念社会化(conceptual socialization)是Kesckes(2003)提出来的,是为了解释在二语习得中语言社会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从多语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交融中的心理过程变化,解释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概念社会化的过程和CUCB的涌现是密切相关的。Kesckes(2003)把概念社会化定义为“为了适应新文化和语言的功能性需求所经历的一些改变”。在概念社会化过程中,以母语为主导的CUCB共有概念基底在不断的重构,并参与到由二语通道进入新信息的意义构建中”(Kesckes,2003;Ortactepe,2012)。概念社会化的提出扩大了语言社会化的范围,可以帮助双语者意识到文化之间的差异,能反思语言产出中的不同和在双语文化中身份的发展。Kesckes(2003)把概念社会化分为技能层面(skill-side)和内容层面(content-side)。二语习得者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也就是语用能力的发展过程。
(1)概念社会化的技能层面发展
对于多语能力和二语习得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社会文化环境,而忽略了语言系统本身在反映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作用。语言是结构和用法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在语言使用中产生结构,同时语言结构也是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语用能力发展过程中,语言结构知识也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语用能力的知识观所强调的对于语言资源知识的掌握。语用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具体表征形式就是语言选择的结果,语言选择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语言技能和知识的选择,也就是Kesckes(2014)提出的概念社会化的技能层面。正确的语言形式选择是达到语言适切性的前提和基础。语言知识和策略也是语用理解能力和语用表达能力的基础(韩宝成、黄永亮,2018)。
相比Leech(1983)和Thomas(1983) 所提出的语用语言因素,技能层面的范围要相对广泛,指的是语言学习者的实际语言表现主要包括结构正确的句子、对语言的掌控、句子的构成和程式语的使用。这些语言技能是二语学习者能够用来实施和处理具体言语行为的语言实现形式,是学习者语法层面和语用层面的结合。何自然、张巨文(2003)也提到外语学习者在用外语交流时,要有效地连接语用和语法两个层面,实现转化,而作为母语说话人则不需要这一过程,而且二语学习者对于二语的语法知识需要有意识的内化,然后根据具体的语境把语法和语用两个层面连接起来,从而做到得体地运用语言(戴沅芳、张绍杰,2015)。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是二语学习者综合能力的发展和表现,是概念系统意义的重构,这种意义重构体现在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指口头交际的语用能力,而且还体现在书面语篇表达的语用能力。韩宝成、黄永亮(2018:96)也指出“语用能力分为语用理解能力和语用表达能力,语用理解能力包括理解说话人意图和作者意图,语用表达能力包括表达说话意图和写作意图”。夏海鸥(2017)在国内语用能力三十年发展的综述中也发现绝大部分实证研究调查了口语语用能力的不同发展状况,而鲜有对书面语篇语用能力的调查和研究。语篇语法就是书面语篇语用能力的基础,也就是语篇语用知识。戴沅芳、张绍杰(2015)认为语篇语用知识是能够掌握语篇呈现、组织方式、衔接手段与语篇表达意图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Kesckes(2014)提出的本族语者喜好的思维组织方式(ways of thinking)。
除了正确的语言语用知识之外,程式语的使用也是语用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Kesckes(2014)指出使用一种语言并属于某一语言社区意味着要有说话和组织思维的喜好方式。说话的喜好方式就是使用程式语和修辞语言。程式语是母语使用的核心和灵魂(Kesckes,2000)。语用能力和程式语的使用与发展密切相关,因为程式化是群体身份的体现,它们反映了一个社团的共享语言实践,是社团身份特征的表现。Kesckes(2014)认为除了语音之外,情境话语(situation bound utterance,简称SBU)的使用可以显示语言使用者是不是本族语者。SBU是那些高度规约化的程式性语用单位,它们的使用是和语言场景、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密切相关。比如在英美国家,让客人多吃点可以用 “ help yourself”,而在中国就说“多吃点”。就SBU使用而言,概念社会化就是指双语者已经意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会熟练地使用目标语文化中的SBU。
(2)概念社会化的内容层面
概念社会化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既包括二语知识结构的运用又包含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运用二语的知识结构。语言知识只是语用表达和理解能力的基础,内容层面的概念社会化是关于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互动模式、语用策略、目标语文化知识和多文化态度。每个层面的变化是质性的变化而不是量性的变化,包含社会文化语用因素的影响。当前一些学者认为二语的习得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不是质变(De Bot,2008;Hall et al.,2006),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量变和质变同时发生。两种语言会经历从累加期(additive period)到协同期(synergic period)两个阶段。协同期也就是质变的过程,会发生两种语言的概念合成。那么什么是质变?Kesckes (2010)认为质变是指概念的重组和行为发展的完善,这个过程是量变缓慢积累的结果。对于二语习得者来说,当他们掌握一些词汇来表征现存的概念时,这个变化是量变,但是当他们开始重组,完善现存概念的内容,这个过程就变成了质变,最后的概念就变成了CUCB中的协同概念(synergic concepts)。这些概念虽然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征,但是却带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负荷。比如汉语的“午饭”和英语的“lunch”就带有不同的文化负荷。掌握一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知识不仅包括语法体系,而且还应包含概念体系和社会文化负荷。
在概念社会化的内容层面所列因素中,Kesckes(2014)并没有详细解释各个因素在内容层面中的作用,但指出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知识和多文化态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和双语者对目标语文化中社会文化规约的喜好程度密切相关。个体的认知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是对社会互动的内化。在语用能力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个体认知能力和社会文化环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母语语用能力主要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环境,而二语语用能力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喜好,双语使用者可以调控自己对二语的相关社会-文化范式和规范的接受程度(Kesckes,2014)。二语学习者“不可能放弃他自己的文化世界” (Barron et al.,1993:56)。Barron (2003)也解释了学习者的价值信念决定了其向本族语标准接近或者偏离。有些高水平的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有排斥心理,因此拒绝选择文化意味太强的语用表达形式。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个体的责任和付出,个体的态度都会影响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Ortactepe(2012)认为概念社会化主要依靠的是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的投入,而不是和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因此,在二语学习中,语用能力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因素,如信念、动机、意愿和能力等。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在概念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元语言意识是指学习者把目标语本身作为思考的对象,对目标语结构具有反思和调控意识,这种意识属于一种高层次的认知能力。学习者不仅把语言看作一种系统知识,而且还具有调控这种系统知识的能力。例如学习者可以反思和理解句子结构的歧义,并能根据语境正确地推理句子的意义。此外,话语标记语、语用标记语等的使用也是学习者元语言意识的体现。实际上,元语言意识也就是我们在语用能力意识观中所提到的元语用意识,是语用能力发展中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因素。
5.0 结论
对二语语用能力的研究始终是中介语语用学和二语习得领域关心的热点话题。但是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忽略了母语概念在二语语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Kesckes(2010)提出的双语系统模式指出双语学习者并不是两种语言系统的独立存在,而是两种语言的语言系统和概念系统的概念整合。两种语言中的语用规则和文化规约同时作用于二语学习者。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就是概念社会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社会文化规约和语言知识系统的影响之外,母语概念系统以及个体的认知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语语用能力的最终目的是能够恰当地运用语言知识和策略来表达和理解话语意图,实现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