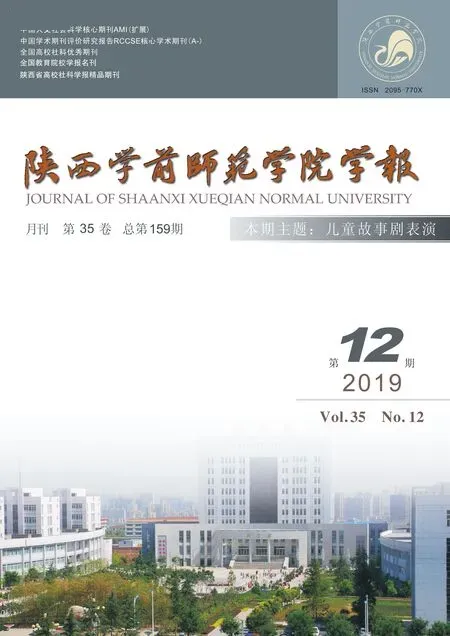幼儿故事剧表演活动的美育价值探析
傅雅萍
(泉州市丰泽幼儿园,福建泉州 362000)
故事剧表演活动指围绕故事中角色、情节、语言等文学要素为载体,以声音表情,面部表情和身段表情来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对于生活和世界的认识、体验和感受的艺术教育活动。而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是积极引导儿童去亲自体验和感受现实世界和艺术作品,使儿童发现客观世界中对称、节奏、重叠、粗细、疏密、统一等美的样式,形成一种对这些样式敏锐的感受能力。笔者认为故事剧表演活动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独特的审美特征,如欢乐徜徉的游戏性、稚拙有趣的冲突性,综合多样的艺术性,有利于促进幼儿审美直觉力、审美创造力、审美态度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是对幼儿进行美育的最佳载体。本文立足于美育角度,对当前幼儿故事剧表演活动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并进一步就幼儿故事剧表演活动的美育价值进行探析。
一、当前幼儿故事剧表演课程中美育缺失现象的剖析
愉悦快乐是幼儿在故事剧表演中最佳的审美体验,是幼儿参与审美过程中审美直觉、审美创造、审美态度等审美经验的总基调,更是美育价值洋溢的最美时刻。这些审美经验,潜藏在故事剧表演角色的对话、动作、情感的点点滴滴里,其发生时既朦胧又形象、既内隐又外显、既短暂又强烈。客观上要求教师去捕捉其中的美育契机,充分发挥故事剧课程的美育作用,但在实践中往往事与愿违。
(一)故事表演对话随意化,缺乏生活体验的审美知觉
要顺利地完成一部完整的故事剧的表演任务,往往需要根据幼儿的实际水平,对故事剧的对话进行适当改编。以美育视角考察教师对故事剧对话的改编工作,不难发现常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奉行童言对话“自然主义”,导致故事剧对话表演平淡化,无韵律之美。二是奉行录音对话“替代主义”,导致故事剧对话表演如哑剧,无意境之感。一句句经过童心过滤的“纯口语”对话,折射出幼儿对故事中所表达事件的生活无感,对话语言的节奏无韵,对话表演自然无法达到共情之趣,索然无味如背书。
究其原因,一方面教师片面地强调儿童口头语言在故事剧对话创作的效用,误将角色艺术对话等同于日常聊天。另一方面教师的功利思想作祟,不允许幼儿出错,所以让幼儿伴随着录音表演,实现表演零误差。教师指导幼儿对话创作“两极化”思维,切断幼儿表演与生活经验的联系与交往,而故事剧对话表演应该去“舞台化”,回归“生活”,以剧本对话的“模版”不断吸纳幼儿个体生活经验,保持个体语言审美图式的生长性,在反映生活或故事的原始色彩的朴素表演中转化为审美直觉。
(二)故事表演动作符号化,缺乏游戏体验的审美想象
身体动作是故事剧表演最基本的媒介,角色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身体动作更多是肢体动作(四肢与躯体),也可以称为身体表情。故事剧里的人、景、物等角色都有典型的身体动作,如兔子蹦蹦跳、大树站不动、女孩跑跳步,肢体动作具有标识角色作用。但在实践中经常会发现,在故事剧表演过程中,要么存在身体造型雷同化现象,现成服装角色快速塑形,无角色认同的动作灌输,导致肢体表达雷同贫乏无张力之核;要么存在身体动作程序化,脱离故事事件情境认知,无切身体验的动作想象,导致肢体表达拘谨生涩无鲜活之趣。一个个手足无措的小孩,身体表征的个性化意识还未开启,如同一个个被束缚的身体,个体专属的审美想象“沉睡”着。
究其原因,教师过分强调故事剧表演的观众视角,且往往以成人“好看的”视角评判故事剧表演效果,忽略了幼儿在故事剧表演中的感受与创造性的发挥。因而,在身体动作的创作上注重结果,而忽略了幼儿对审美对象的“感受与欣赏”的体验,以教授表演为主,简单移植角色动作,导致幼儿表演动作整齐划一。注重角色形象包装,追求表演观赏性,错误理解幼儿对故事剧表演的喜爱,其更多源于爱玩的游戏心理,而不是爱美。笔者认为故事剧造型动作的表演,只有在游戏活动中,用游戏的方式去感受去体验去对话审美对象,身体才能在放松中觉醒,在冲动中释放原始力,渐进审美想象的愉悦状态,拥有身体变奏变形地表达角色形象的审美创造力。
(三)故事表演情感浅表化,缺乏艺术体验的审美理解
故事剧表演的情感指幼儿在角色表达过程中,共鸣与表现要基于情感的体验与理解[1]165,它包括自然表现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幼儿情感因年龄小体验浅表不深刻,外显能力有限,常常出现一些尴尬局面。如在表演过程中,无论是配角、正角、丑角、恶角,幼儿脸上的表情要么一笑到底,导致表演无感染力;要么全凭喜好,无论故事情节多么蜿蜒曲折、荡气回肠,只要不感兴趣均无表情,若遇上喜欢的情节,瞬间眉飞色舞,导致表演情绪化。
究其原因,教师指导幼儿进行角色情感表达中,认为幼儿受年龄制约不能辨别角色的不同性格或情感,对其情绪情感的艺术导引方法不足。一方面,忽视语言、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的感受与欣赏,缺少以审美的视角去品味、体验、思考角色的艺术情感表达的内容、形式等,导致表演时幼儿常常以生理情感状态代替角色情感表达。另一方面,过度重视幼儿表演情感的外显效果,嫁接节奏快的音乐、色彩亮的场景、口号式的对话等形式,导致幼儿角色表现处于高亢兴奋的情感状态,忽视对角色情感的深度理解。笔者认为在故事剧表演中,情感伴随整个审美过程,教师应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尊重幼儿各自的审美偏好,使其专注于角色情绪的丰富与变化,畅通无阻地表达自己的审美理解。
二、幼儿故事剧表演课程中美育价值的挖掘
美学家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一书中,将审美按其形态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方面[2]169。笔者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择取“悦耳”“悦目”“悦心”审美形态为依据,结合我园故事剧表演课程的实践探索,阐述幼儿在故事剧表演活动中感官、身体、心灵的愉悦享受,探析教师如何把握和挖掘其中的美育价值。
(一)对话“悦耳”,提升审美直觉能力的敏锐性
优美的对话,稚气的对白,让幼儿欢乐、自在,沉浸在梦幻弥散、跌宕回环的故事情节中,获得动人心魄之感,便是故事剧对话创作达“悦耳”之境。故事剧对话创作要达“悦耳”之境,教师要引导幼儿将生活中看到的熟悉的事物、听到的美的声音等审美经历进行加工改造,转变为拟声语、象声词,如飞禽走兽、风雨雷电的模仿声,增加各种对话音效的音感、语义、节奏等审美经验,从而使对话对白的美感来源于听觉,又超越听觉,迅速导入其它感官引发愉悦感,提升幼儿语言审美直觉能力的敏锐性。
1.优美的剧本对话,引发语境多感的审美知觉
审美感知是对审美对象的形、音、色、光、空间、张力等要素组成的形象的整体性把握[3]。一部故事剧对话具有“优美”的张力,来自于教师以“咬文嚼字”的方式,与幼儿一起赏析生活美景,润泽幼儿对话的色韵、节奏,使其描绘故事角色的直接感受,或亲切、或空灵、或活泼、或浪漫……让幼儿在质朴、纯美的故事剧对话欣赏中,获得听声入境、闻声见景的愉悦感,增进幼儿细致的审美观察力。
案例一:《敲门》(节选自大班故事剧表演《珍珠龙须粥》)
幼儿创编的对话:
武将:我先去敲门,咚咚咚,怎么没有人?
文臣:你到别家敲一敲。
(三个人走到第二家)
武将:咚咚咚,这家也没有人。
文臣:怎么都没人?
皇帝:你看,那家有人。
师幼共构下的对话:
武将:我先去敲门,咚咚咚,里面可有人家?
文臣:我看是你敲得太重了。我来敲敲看,咚咚咚,里面可有人家?唉,一出手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三人走到第二家)
武将:还是我来敲,咚咚咚,唉呀,这家也没有人,我也喝了一个“闭门汤”。
皇帝:好一个“闭门汤”。
文臣:是“闭门羹”,不是“闭门汤”。
武将:“闭门羹”就“闭门羹”吧。你们看,前面的房子有炊烟。
文臣:没错,那家肯定有人,我们快去看看。
皇帝: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案例中教师接纳幼儿的创作建议,把原来“怎么没有人?”“怎么都没人?”的平淡对话里加入了“闭门羹”、“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妙趣的语言,轻松地表现出文臣斯文、认真的处事习惯,衬托武将粗犷、威武的行事做派,还有皇帝在剧中的主角形象。当然幼儿对“一波三折”“闭门羹”等妙语的共鸣,得益于教师与幼儿大量阅读经典的成语故事、传说故事、人物传记,教师以优秀文学作品帮助幼儿积累丰富的语言审美经验,形成生动有趣的剧本对话。
2.稚气的角色对白,引发妙语趣言的审美直觉
审美直觉是一种形式性直觉,通过对物体的形状、体积和造型的富有个性色彩的情感体验[4]72-76。在故事剧角色对白表演中,幼儿往往表现出浓浓的稚气感,这份稚气感恰到好处地保留了“稚”与“拙”的形象张力,让幼儿角色对白创作既有改造的空间,又不失孩童的视野,幼儿在愉悦感中,便拥有塑造人物的语言直觉力。
案例二:《躲哪》(节选自中班故事剧《捉迷藏》剧本)
幼儿创编的对话:“很大很大的地方”“树后面”“花的那边”……
师幼共构下的对话:
妮卡说:哇呜,公园好大呀!可以躲在哪里。(丰富象声词表达对捉迷藏环境空间大小听觉感受)
巴特说:看,有大大的树,可以躲在大树后面。(丰富视觉动词表达对捉迷藏空间方位视觉判断)
乔治说:花儿一朵连一朵,可以藏在花丛的后面。(丰富量词表达对捉迷藏环境内容、距离的视觉判断)
艾米说:假山里有山洞,可以钻进去,谁也看不见。(丰富方位词表达对空间方位视觉判断)
妮卡说:不要太远了,我们去藏起来吧!
故事剧《捉迷藏》剧本中,既有大量重复、词意不明的对话,又潜藏着幼儿的朴素经验。教师反复品读孩子的每一句话,遇上对话语句重复冗长,去除繁复之语,选取一两句能生动描述故事场景的对话即可;遇上对话语句不连贯或词不达意,可引导幼儿再次运用想象、拟人、夸张、比喻等言语形式将口语化的对话延展,其语言的画意感快速勾勒出“假山、密林、花丛”等捉迷藏的生活情景。教师与幼儿以对话为媒介,交流与调整各自的思想和情感,并以听觉为源点联合触觉、动觉、味觉等统整的审美知觉,使身体感觉通道活跃起来,迅速带幼儿回忆与共情捉迷藏的全部生活经验,生动地表达幼儿的所闻所想所乐。
(二)动作“悦目”,激发审美创造力的独特性
拟真的形象、多变的造型,幼儿的身体表演灵动吸睛,仿若进入了复制模仿、审美意象、神与象游的描述状态,使其故事剧动作造型创作入了“悦目”之界。教师借以故事剧角色身份,开启幼儿扮丑扮萌、嬉戏打闹的游戏天性,点燃了他们内心的活力,使其拥有表达自己、表现角色、主宰环境的畅快感,审美创造力呼之欲出,更具独特性。
1.拟真的角色造型,引发和而不同的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即指个体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情趣、性格、情感等直接移注于物,通过想象,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教师应呵护幼儿扮丑扮萌的游戏天性,唤醒幼儿在生活中对“原型意象”的认知,使其焕发活力,生动地塑造故事角色外形特征,诱发同一故事角色“和而不同”的审美意象。
案例三:《大灰狼的N种死法》(节选自中班故事剧表演《小熊请客》)
在不同的故事里,大灰狼越是凶恶,结局一定是越发离奇地倒霉。
楷楷大灰狼拿了张地垫,躺在地上“睡死”了。看着大灰狼安静的样子,小动物们傻眼了。(运用生活经验的感知表现大灰狼倒霉)
凡凡大灰狼倚着墙根,头戴遮眼布,扎坑“撞死”了。看到大灰狼倒立贴墙的样子,小动物捂着嘴笑。(运用动画片《灰太狼》欣赏经验的联想表现大灰狼倒霉)
蒋蒋大灰狼拿着玩具方筐,啊——,扑通进篮“摔死”了。大灰狼肚子贴在篮底,头与四肢被篮筐缘空架吊着,太倒霉!小动物们笑弯了腰,还轮流到篮筐里“死”了一回。(运用故事剧情景《小熊请客》的想象表现大灰狼倒霉)
大灰狼,反面角色的经典代表。故事剧中的大灰狼有多倒霉,幼儿就有多喜欢它。幼儿自备的草席、遮眼布、篮子等简易道具,能快速、逼真、生动地将自己装扮成倒霉的大灰狼,游戏感十足的欢乐,不仅带给同伴视觉上的共鸣与享受,更清晰地展现了幼儿对大灰狼从“死”与“倒霉”之间的审美想象水平差,即楷楷模仿人死的模样、凡凡再现丑角“灰太狼”、蒋蒋巧借篮筐装死。其中,最具感染力的造型就数蒋蒋大灰狼,蒋蒋的造型汇聚了自己在生活中、动画片中、绘本中,无数次对该角色造型的知觉而形成的审美灵感,身体任由玩具框雕刻出“死”比“活”还有精气神的“洋相”,大灰狼双眼紧闭,造型多变,尽显诙谐,引来一帮小家伙们互相逗趣“倒霉”。
2.特定的事件动作,引发狂喜专注的神与象游
游戏是充满幻想的,它在幼儿的主观世界和外部客观世界之间搭建了桥梁,将梦想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5],让幼儿“自我”能自由出入“剧里”与“剧外”。孔起英教授在《儿童审美心理研究》一书中称之为“神与象游”,指审美活动中个体的情意伴随着具体可感的形象而不受时空的限制,进入物我不分的境界[6]8-10。在故事剧表演中常见幼儿自发“嬉戏打闹”的游戏行为,而在自主选择角色的氛围下,当故事角色形象或情节事件,吻合了幼儿自己特定的愿望、满足了心理某部分需求时,幼儿控制自己、控制他人、控制环境的欲望,便在故事角色表演中被满足,幼儿在自我欣赏的同时,全情投入,动作奔放,狂喜且专注。
案例四:《泽泽与水蟑螂》(节选自大班故事剧表演《101只蝌蚪》)
泽泽是个安静腼腆的小男孩,平时话少声音小,多数时候总是自己一个人玩。(生活中的泽泽小朋友)
水蟑螂,故事剧中捉了青蛙妈妈和蝌蚪宝宝的大坏蛋,这个角色却是泽泽的最爱。
故事剧《101只蝌蚪》里有六只水蟑螂,舞台上泽泽扮演的水蟑螂最威武,最强悍。每到“小龙虾与水蟑螂为争夺青蛙妈妈而吵架打斗”的情节时,泽泽扮演的水蟑螂总是第一个冲到小龙虾的阵营中,狠狠地说:“这是我的地盘,青蛙是我的食物。”双手在空中做出舞枪弄棒的动作,时而腾空跳,时而伏地趴,时而旋转手臂,不时张嘴发出怪叫声,扮着各种鬼脸。(故事剧《101只蝌蚪》中的泽泽小朋友)
案例中,水蟑螂的故事角色将泽泽带入了幻想的世界,腼腆的泽泽身体开始觉醒,它释放身体潜在的“攻击力”不由自主地在自我与角色之间“走出走进”,当泽泽完全投入到故事剧表演“里面”,身体随心而动,“腾空跳”“伏地趴”“旋转”,动作流畅自如地表现出“水蟑螂”的艺术形象,每个动作都奔放有力,拥有了角色的霸道力量,生活中的弱小感完全地得到补偿,满足后他从角色走出来,又恢复了安静腼腆,“神与象游”的想象让幼儿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张扬自己的行为,获得主宰自我,控制角色的愉悦感,创作出一个生活中未成出现的崭新“自我”形象。
(三)情感“悦心”,萌发审美态度的意向性
恶毒巫婆走神一笑,稚气娃娃装老太,无邪表情自如切换,便是故事剧情感表达“悦心”之境。因为幼儿审美态度不成熟,所以他们是以审美移情、偏爱的方式,执著于自己喜欢的角色。教师如能接纳这种不成熟,善用美术、音乐、雕塑、文学等艺术表现形式,引导幼儿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表演创作的每一个过程,便能映照出幼儿本真的内心冲突,使其在自然情感与角色情感不协调间,外显内在心灵的愉悦与自在。
1.纯粹的自然情感,引发节律重复的审美偏爱
审美偏爱是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倾向性感情评价。幼儿偏爱节律重复的情节,如经典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灰姑娘》都是在重复的桥段中,让幼儿感到熟悉,不紧张,有自信,能把握。教师如能尊重幼儿的审美偏爱,采用“节律重复”致情节冲突的创作,再辅于幼儿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如舞蹈、唱歌、美术、雕塑等,幼儿的自然情感能伴随故事情节地推进,流畅自在地表达。
案例五:《打嗝》(节选自中班故事剧《捉迷藏》剧本)
第一次情节设计:
乔治:你们藏在哪里呢?
伙伴:我在这里……
第二次情节设计:
乔治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朋友,伙伴们决定跟她开一个玩笑。
妮卡:嗝!
乔治:什么声音?
艾莎:嗝嗝!
乔治:你们躲在哪里?
大家:嗝!嗝!嗝!(随机)。
乔治:哈哈,找到你们啦!找到你们啦!
故事剧《捉迷藏》的冲突创作,缘起乔治找不到伙伴的着急。可是第一次设计时,那种一问了之的桥段,未能满足幼儿在捉与藏矛盾冲突的“着急”体验。“着急”的情感并不是让幼儿真的着急,而是要表达捉迷藏的乐趣。教师效仿经典故事剧情节重复,对话变奏,配上乐曲《咕嘟嘟》更显生气,打“嗝”音效的空间移位里夹杂着同伴熟悉的音色,细细的、粗粗的、嗲嗲的童声此起彼伏,铺设忍而不发的情感状态,表演趣味十足,使幼儿不仅替乔治着急,也觉得好玩有趣。在这样满足他们偏好的故事表演里,使他们不仅喜爱故事剧表演,也喜爱生活的美好。
2.错综的角色情感,引发喜爱角色的审美移情
审美移情是主体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品质等赋予给不具有人的感情色彩的外物,结果外物似乎也有了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品质等[7]。在故事剧中,鲜活的艺术形象、激烈的情节冲突诱发了幼儿的审美移情,幼儿从害怕、恐惧、无奈到惊喜、好奇、满足等不同情感的变化,获得对角色多元的审美认知与理解。
案例六:《勇敢的小鲤鱼》(节选自大班故事剧表演《小鲤鱼跳龙门》)
最近,班上的孩子总是三三两两围着绘本《小鲤鱼跳龙门》聊天,强强指着锋利的岩石,说:“如果小鲤鱼跳到岩石上,一定很疼。”多多说:“对,这是大禹用斧头劈下的石头,石头的边沿像刀子一样。”琪琪说:“你看水草也是很坏的,会把小鲤鱼缠住……”很快,这幕场景出现在故事剧的表演中。
强强、多多礁石躺在地上,双手做出山尖手势停至在腰旁,一脸坏笑地说:“我的礁石有棱角,你敢试一试吗。”小鲤鱼游来游去,说“我好害怕!”于是,她又邀来一群小鲤鱼,小鲤鱼站在椅子上跳过去了,大家哈哈大笑。
强强礁石生气地变换礁石棱角的位置,挑战小鲤鱼。……(引发了小鲤鱼的惧怕、生气、无奈、惊奇等情感表现)
刚刚、俊俊、杰杰水草蹲站相依着,说:这里有很多高高低低的水草,你跳下去就缠住你,你们敢跳吗?小鲤鱼游来游去,找到了最矮的地方跳过去,很满足地游走了。(引发了小鲤鱼的犹豫、惊喜、满足等情感表现)
案例中,孩子们在绘本故事《小鲤鱼跃龙门》欣赏中,既关心小鲤鱼是否能顺利跃龙门,又希望看到小鲤鱼是如何面对一个个困难?因此海浪、礁石等成人世界的外物在幼儿的“关心”中被活化,诱发幼儿自己扮演海浪、礁石与小鲤鱼搏斗,从而感受到小鲤鱼从刚一开始的紧张害怕、到小心翼翼、再到最后的大胆挑战,勇跃龙门。其角色情感转换,有迂回、有变奏、有反复,直到“鱼跃龙门”那时刻,矛盾的情感体验生发充沛的生命活力。彭运石曾细致地描述过,这种审美愉悦的体验状态就是一种高峰体验的情感状态,是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自我与自然、社会合一的“剧烈的同一性体验”[8]。
在故事剧表演课程实施中,幼儿积极热切地投入其中,身心在游戏的世界里、在艺术的世界里尽情飞翔,让所有的梦想变成了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使其成为一个精神丰富而快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