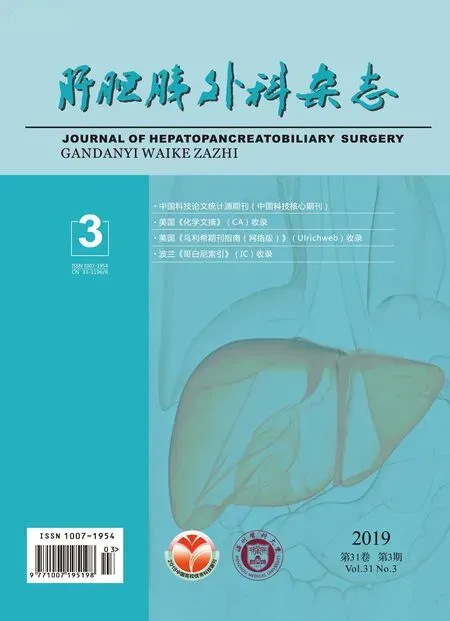基于肝细胞癌微环境和生物标志物特点构建靶向性纳米载体的研究与应用
李镇利,吴寒,杨田,吴孟超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肝胆外科,上海 200438)
随着纳米技术的不断发展,纳米材料在肿瘤的诊疗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鉴于纳米材料的尺度效应、表面效应以及光、声、电、磁等方面的特性,相比于传统的治疗模式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1-3]。肿瘤血管的病理生理特性,是纳米颗粒发挥其优势的结构基础。肿瘤区域血管相比于正常血管,结构完整性差,具有更宽的血管内皮间隙。通常将载体粒径在10~200 nm可较好地通透血管壁并滞留在肿瘤组织中的过程称之为肿瘤血管的高通透长滞留效应(EPR效应),这是纳米药物能在肿瘤组织中选择性分布,具有较好靶向性和低毒副作用的前提[4]。纳米材料的靶向作用主要包括被动靶向和主动靶向效应[5]。被动靶向效应指的是基于EPR效应使纳米级别的生物材料被动富集于肿瘤区域,而主动靶向效应则指的是通过在纳米材料上连接特异性的配体,与肿瘤微环境中的特征性受体结合,进一步提高肿瘤富集量,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随着纳米材料在医学领域研究越来越广,基于EPR的被动靶向效应并不能满足目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需要,而基于肿瘤微环境特点设计的主动靶向纳米载体被越来越多地设计出来,并且与传统被动靶向相比,在基础研究中展现出了更加优越的效果。
原发性肝癌(主要指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第五大高发的恶性肿瘤,其致死性更是高居第二位[6]。作为恶性程度较高,预后差的恶性肿瘤,肝癌在肿瘤微环境和生物标志物方面有其特征性的表现,并且已有研究基于这些特征性靶点设计出了许多分子靶向性的药物[7],如索拉菲尼、瑞格菲尼等[8]。尽管在患者生存时间方面优于传统的化疗药物(中位生存时间仅延长3个月),但仍然无法避免全身毒副作用大,远期疗效不佳的问题[9]。所以,靶向性强、毒副作用小的纳米载体与肝癌微环境和生物标志物的结合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并在基础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将对肝脏摄取纳米颗粒的特性以及基于肝癌微环境和生物标志物特点构建靶向性纳米载体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肝脏摄取纳米颗粒的特性及结构调控
尽管纳米颗粒相比于传统药物,具有较好的肿瘤富集特性,但肝脏对于外来物质的屏障作用是其面临的一大问题。研究表明,通过口服或静脉注射的纳米药物,会大部分沉积在肝脾部位,并被代谢排出体外,导致生物利用度降低,治疗效果远低于预期,甚至会造成肝脏毒性,引起一系列代谢性的问题。肝脏摄取纳米颗粒的结构基础是由Kupffer细胞组成的网状内皮吞噬系统(RES),进入血液循环的纳米颗粒首先会与血浆蛋白结合,接着被迅速调理素化,并进一步介导巨噬细胞的内吞作用,使其在肝内沉积,不能再次进入血液循环[10],具体的步骤如图1所示[10]。

图1 肝脏吞噬纳米粒子的结构基础(左)和PEG化修饰逃逸RES示意图(右)[10]
为了实现RES逃逸,科学家对纳米载体进行了多种功能化的修饰,削弱肝脏对纳米颗粒的屏障作用,以更好的发挥其效果。目前,聚乙二醇(PEG)化是纳米材料最普遍的修饰策略,能避免与血浆蛋白的结合,进而阻断调理素化过程,逃逸RES的吞噬作用。PEG化还能延长血液循环时间,改善生物相容性,已成为公认有效的改性方法[5]。此外,研究通过多光子荧光显微镜实时观察肝脏摄取纳米颗粒后发现,肝脏的清除作用还与纳米粒子的疏水性、表面电荷及大小有关[11],带负电荷的颗粒更易被RES吞噬,造成肝脏毒性,而亲水性基团则有利于逃逸肝脏的屏障作用。另一项研究系统评估了纳米颗粒的大小对肝脏摄取的影响[12],发现直径为60 nm的纳米颗粒最有利于肿瘤的富集,直径的增加或减少均会一定程度增加RES的沉积。近期研究从器官结构、血流动力学和细胞表型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肝脏作为纳米颗粒屏障的原因和策略,结果表明,纳米颗粒更容易在血管入路周围富集;肝血窦内血运丰富,血流交换面积大导致血流速度慢是纳米颗粒易于在肝内沉积的重要原因;此外,肝脾脏器内巨噬细胞的表型对纳米颗粒的摄取量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巨噬细胞在肝脾内分别分化成Kupffer细胞和红髓细胞,相比于普通巨噬细胞,其吞噬作用明显增强[13]。
因此,肝脏作为纳米颗粒沉积的主要器官,是制约纳米药物发挥作用的主要屏障,而随着现有技术对肝脏摄取纳米颗粒的机制研究以及相对应的结构调控,能够找到更加合理的改进手段。现有研究正是得益于这类技术的发展,才进一步针对肝癌微环境特点,设计出特异性更强的纳米载体,拓宽了纳米医学在肝癌诊疗领域的应用前景。
2 肝癌微环境的特点与相应的纳米载体功能化设计
纳米颗粒的功能化设计的目的一方面在于逃逸RES的吞噬,延长血液循环时间,提高生物利用效率,如上述所示;另一方面在于结合肝癌微环境的特性,赋予纳米颗粒相应的功能化修饰,实现更好的肿瘤响应性和靶向性。除上述提到的肿瘤血管区域的特征性变化外,目前还从根据肝癌肿瘤的酸性环境、谷胱甘肽含量高、肿瘤间质的高渗透压、肿瘤组织乏氧性等特点进行功能化设计。
2.1 酸性环境
肿瘤区域的pH(6.5)略低于正常组织(7.4),而肿瘤细胞内的内涵体或溶酶体则更低(5.0~5.5)[14-16]。在正常的组织内,H+由糖酵解,谷氨酰胺分解以及ATP水解产生,能够通过转运进入血流,保证组织内的中性环境,而在肿瘤组织内,高负荷的糖酵解过程导致乳酸堆积,形成酸性环境。此种差异为设计pH相应药物输运系统提供了基础,研究通过在纳米载体表面包覆聚电解质层,使其结构在酸性条件下遭到破坏,进而实现药物的响应性释放[17]。近期研究发现,以纳米材料为化疗药物载体的载药体系能在酸性环境下显著加速药物释放,并且在肝癌细胞系和肝癌模型上系统验证了该体系响应性释药特性和靶向输运性能[18]。
2.2 谷胱甘肽含量高
谷胱甘肽(GSH)是人体细胞内具有重要功能的还原性天然活性肽,在肿瘤细胞内和正常细胞内的浓度差异较大(4∶1)。二硫键能稳定存在于人体血液中,而在肿瘤细胞内则被高浓度GSH降解。因此,利用二硫键对肿瘤高浓度GSH的降解性而设计的纳米载体具有广阔的前景[19-21]。研究通过合成有机无机杂化纳米硅球(掺杂二硫键结构),能得到肿瘤区域内GSH响应性降解的药物载体[22]。在此基础上,通过连接肝癌特异性配体,设计出了靶向性强,并且具有GSH响应性降解+释药性质的纳米载体,有效地增强了肝癌化疗的疗效,降低了全身毒副反应[23]。
2.3 肿瘤间质的高渗透压
肝癌组织渗透压(IFP)的升高主要源于血管、淋巴管道的异常、EPR效应等导致肿瘤间质过度增长引起[24-25],肿瘤中心位置往往压力最高,向外周逐渐降低[26-27]。IFP升高一方面促进了肿瘤生成和转移,另一方面导致药物和纳米载体很难进入肿瘤细胞发挥作用,影响其治疗效果[28-31]。研究发现,通过抑制肝癌间质成纤维细胞(形成肿瘤间质的主要成分)的生长,能够有效降低IFP,并且提高纳米载体的摄取率,增强药物治疗的效果[32]。此类研究说明纳米载体不但在增强肿瘤药物靶向性方面意义重大,在改善肿瘤微环境方面同样优于传统的治疗手段。
2.4 肿瘤组织乏氧性
肿瘤组织的乏氧特性主要是由于肿瘤细胞高负荷的糖代谢,使葡萄糖转运体异常活跃,远远超过正常组织的氧气供应导致。乏氧特性参与了包括肝癌细胞增殖、血管形成、转移、化疗耐药在内等多个重要的过程:一方面乏氧状态可能会加剧肿瘤增殖和转移;另一方面通过联合乏氧特异性药物,可以实现提高肿瘤化疗的疗效。有研究将乏氧响应性物质偶氮苯修饰的纳米颗粒应用于肿瘤的基因治疗,在提高药物靶向作用的同时,还有效地增加了肿瘤细胞对siRNA的吞噬效率,达到了可观的抗肿瘤效果[33]。
3 肝癌生物标记物与纳米材料表面功能化设计的结合
上述微环境特点多是肿瘤组织所共有,缺乏肝癌特异性。相比于其他肿瘤,肝癌细胞会特征性表达多种膜蛋白分子,如图2[34]所示。这种特异性的蛋白常常用于肝癌的早期检测,而在纳米医学领域,这种特性对于纳米载体的表面修饰和功能化设计同样至关重要,以下将重点阐述几种广泛应用于纳米载体的肝癌特异性膜蛋白分子。

图2 肝癌细胞表面特征性膜蛋白受体示意图[34]
3.1 聚糖蛋白-3(GPC-3)
GPC-3是属于硫酸肝素蛋白多糖家族的一种膜蛋白,常在肝癌组织中异常表达。据报道,74.8%的HCC会出现GPC3 mRNA的异常表达,而仅有3.2%在正常肝组织表达,证明了其高度的特异性,可作为纳米载体的高效靶点。研究发现,基于GPC-3单克隆抗体GC33修饰的纳米材料,能显著抑制GPC-3阳性的Hep G2和Huh 7细胞系的肿瘤生长,而对于GPC-3阴性的SK-HEP-1细胞系,则没有明显的改变[35-36]。另外一项以HepG2(GPC3表达上调)和HLF(GPC3表达含量低)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也证实了GPC-3良好的靶向性[37-38]。
3.2 生长抑素受体(SSTRs)
SSTRs是G蛋白偶联的一类跨膜蛋白,在不同组织中表达含量差异较大。研究显示,SSTRs常见于肝脏疾病比如急慢性肝炎、肝硬化和HCC,其中HCC占据41%,而极少表达于正常肝组织[39]。鉴于SSTRs良好的肿瘤特异性,有研究将奥曲肽作为SSTRs的特异性配体,并共价修饰在载有阿霉素的纳米载体-脂质体上,利用奥曲肽和SSTRs的特异性识别和结合过程,成功从体外和体内实验验证了其对肝癌组织良好的靶向效果[40]。
3.3 整合素相关蛋白(CD47)
CD47是一种膜蛋白,常在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能够与巨噬细胞表面的信号通路蛋白(SIRP-α)特异性结合,介导细胞吞噬作用,这可作为纳米材料与肝癌细胞特征性结合的分子基础。有研究将纳米载体修饰上CD47配体片段4N1K后,将其作为肝癌组织荧光染色的工具,并在肝癌细胞和患者病理组织中验证了其应用价值[41]。相比于传统的免疫荧光法,该手段更加经济高效,具有很高的临床转化价值。
3.4 αvβ3整合蛋白
αvβ3是血管生成和肿瘤形成过程中,血管内皮细胞高表达的一种最普遍的蛋白[42],而少见于正常的血管内皮细胞,其作用在于能够招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血管形成[43]。研究已证实这类蛋白可在多个肝癌细胞系中高表达,成为应用较多的治疗靶点[44]。三氨基酸肽(RGD)可以作为该靶点的有效配体,研究发现RGD修饰的纳米载体能首先聚集在肿瘤血管周围[45],并进一步介导肿瘤细胞的内吞作用,增加肿瘤细胞的吞噬量,提高治疗的效果[46]。此外,近期研究通过对MXene纳米片进行介孔氧化硅包裹,成功地将RGD共价连接到了MXene载体上,并且在肝癌细胞和动物模型上系统地验证了其优越的靶向性能,可以比对照组的肿瘤靶向效率提高1.6倍[18]。
综上所述,目前基于肝癌特有的微环境特点(酸性,高浓度谷胱甘肽,间质高渗透压和乏氧状态等)以及细胞表面分子标志物(GPC-3,SSTRs,CD47和αvβ3蛋白等),已成功构建出一系列具有优越靶向性能的纳米载体,并且在基础实验阶段已经证实其良好的靶向作用,在肝癌的高效诊断和治疗领域具有很高的临床转化前景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