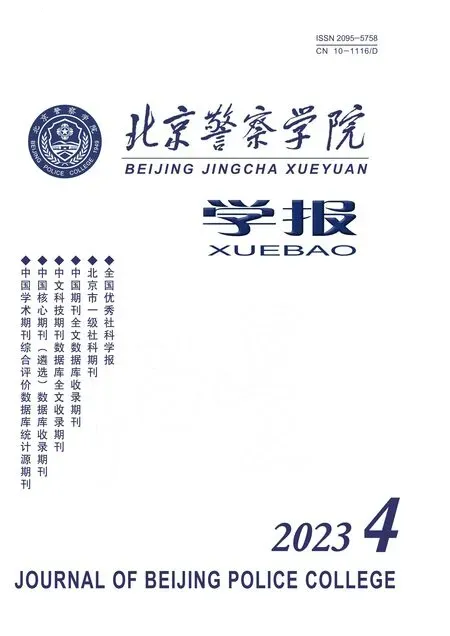传销犯罪隐语分析
欧阳国亮,祁维超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沈阳 110035)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1]近年来,传销犯罪依然高发,对传销活动的治理依然形势严峻。一方面,传销活动不断改头换面,特别是借助电信网络实现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手段更加多样,令人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传销组织大量使用秘密语(即传销隐语)进行交流,使得作案过程更加隐蔽。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从资本运行监管、法律机制建设、网络信息监管、社会综合治理等角度不断探索根除传销犯罪的有效路径,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对而言,公安机关对传销过程中所用的隐语则关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传销犯罪隐语的性质、特点、产生规律以及应对策略进行探讨,以便为公安机关惩治传销犯罪,宣传教育群众防范传销陷阱提供有益参考。
一、传销犯罪隐语的界定及研究材料的来源
(一)传销犯罪隐语的界定
隐语是特定的社会集团或组织,出于内部保密交际的需要而创造使用的一种言语符号系统。任何犯罪集团在其内部都会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秘密话语系统,例如毒品犯罪隐语、电信诈骗隐语、盗窃隐语、赌博隐语,公安机关一般将这类用语统称为犯罪隐语。[2]145在传销犯罪活动中,传销人员为了掩人耳目、躲避打击以及误导公众,也创造了一些专门用于其内部交流的秘密用语,例如“1040 工程”“西部大开发”“做生意”“讲工作”“三菜一汤”等,这些都披着普通词语的外衣,而指代的内容却与传销有关。本文根据公安机关对犯罪隐语的有关界定,结合传销犯罪的性质特点,将这种由传销团伙内部使用的各类与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秘密用语称为传销犯罪隐语。
(二)研究材料的来源
近年来,为了研究传销犯罪隐语的特点、规律以及识别的方法,我们对传销犯罪隐语进行了持续的收集整理,并进行了跟踪调查,收集的条目超过1000 条。在调查手段上,一是通过向长沙、桂林、南昌、广州、贵阳、南宁、秦皇岛、沈阳等地公安机关发函或采用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收集。二是通过网络检索的方式整理各类媒体报道中提到的这类隐语。例如《人民日报》曾设置专栏向公众介绍防范传销的内容,其中介绍了不少传销犯罪隐语。三是通过对一些有过传销经历的人员进行访谈,收集了一部分传销犯罪隐语。这三条渠道是本文研究素材的主要来源。
二、传销犯罪隐语的分类
在对传销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时,对于侦查人员而言,他们最急需的就是了解各类传销犯罪隐语的含义,从中获得侦查的线索或者情报。为此,首先对调查收集的传销犯罪隐语进行了分类,建立了基础数据库,并解释了每一条传销犯罪隐语的具体含义以及标注了它们所使用的场合等信息。从类型上来看,传销犯罪隐语可以根据其形成的路径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其词语形式进行分类。当然,公安机关普遍根据这些隐语所指的内容种属进行分类。[3]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本文将传销犯罪隐语分为四大类,即业务隐语、身份隐语、生活隐语和宣传隐语。
(一)业务隐语
业务隐语是指关于传销活动本身以及传销活动中各项具体活动的用语。例如,传销团伙将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叫做“1040 工程”“1080 工程”“北部湾经济区”“商务商会”“自愿连锁”“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资本运作”“生意”。传销人员的这类用语可谓是琳琅满目,但就是决口不提“传销”二字。又如,“讲工作”指传销人员向新人介绍工作内容和理想目标的整个过程,好比上课;“正班”指传销人员向新人讲的工作内容,好比上课的内容;“走工作”指新人加入传销组织后推荐人带他熟悉工作内容;“铺垫”指在正式洗脑前带新人在城市内参观;“五级三晋制”指传销组织内部晋升的分配制度;“结案”指促成新人加入行业。业务隐语是传销活动中数量最多、使用频率最高的隐语,在收集到的1305 条传销犯罪隐语中,业务隐语有416条,占比32%。而且随着网络传销活动的猖獗,与网络传销业务有关的隐语也很多,它们与互联网术语交织在一起,识别难度很大,例如“电子商务”(指网络传销)、B2C(指点对点发展下线)、020(指线上线下混合传销行为)等等。
(二)身份隐语
身份隐语就是在传销犯罪活动中用来指代身份的秘密用语。一般来说,传销组织中的人员构成复杂,存在非常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身份,而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专门的用语用来称呼。例如:“实习业务员”指传销组织分级中第一级人员;“推荐人”指传销活动的发起人和招募人;“新人”指新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大领导”指同时管理几个宿舍的人;“伞尖”指资本运作体系中对高级头目的一种称呼,按级别不同还可分为大伞尖和小伞尖;“伞下”指资本运作体系中对下线的称呼。传销活动中的这类身份用语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局外人看到这类词语常常以为它们指的是正常的公司职员,而实际上这类用语都是暗语,传销组织就是为了起到挂羊头卖狗肉的效果,以此迷惑外人,并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正名。
(三)生活隐语
生活用语就是在日常交际生活中对某些日常事物的称呼,最为常见的就是餐饮用语。传销组织为了节约成本,最大程度的压榨下面的人,给“员工”提供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衣、食、住等方面的条件都极差。但传销组织者为了蒙蔽、迷惑参与者,经常采用“指鹿为马”的手段为一些简陋的饭菜取一个华丽的名字。例如,“白金大米饭”指粗糙的大米饭,大米又硬又糙,但传销组织者却给他们灌输,大米相当于白金,吃了就能赚更多的钱。“白兰地”指白开水。“白玉金鸡蛋”指大白菜汤里加一个鸡蛋,白菜相当于钱,寓意吃了能赚的更多。“鲍鱼片”指面条,主要指宽刀削面。“翡翠黄金汤”指南瓜汤里放点葱花,寓意翡翠黄金汤,喝了富得快。“满汉全席”指普通的饭菜。“茅台酒”即白开水,有时将其称为陈酿20 年的茅台酒。“牛奶”指早晨清汤寡水的大米粥。“青龙过江”指一大盆盐水汤里放一根大葱。“咸鱼翻身”指煎一条鱼翻一下面,寓意转运。这些餐饮用语表面看上去都十分的高大上,在向不知情的人介绍加入“公司”后的生活条件时,张口就说餐餐有“三菜一汤”“鲍鱼”“白金大米饭”“水煮大甲鱼”,让人充满憧憬并信以为真。实际上这只是传销组织者惯用的语言手段,这类词语是典型的隐语黑话。
(四)宣传隐语
宣传隐语就是传销组织专门给社会公众或新加入组织的人进行洗脑宣传的隐语。这类隐语比起前面三类隐语来相对特殊,它大部分都是一些标语口号,而不是词语。有的采用的是励志式的口号,例如“会吃苦吃一阵子苦,不会吃苦吃一辈子苦”“人人出局,人人赚钱”“一个人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最慢需要一年”“这是一个改变你一家三代人命运的事业”“今天吃萝卜咸菜,明天开奔驰宝马”。有的采用的是警醒式的口号,例如“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行业没有失败者,只有放弃者”“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来到这里你就会知道你以前的梦想是多么渺小”。有的采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号,例如“听话照做,服从配合”“想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不准低头,不准退缩”。传销组织的宣传隐语多出现在网络贴吧和一些聊天群中,经常是一组一组出现,如同一首诗歌,读上去朗朗上口。但其字面宣传的意思和真实宣传的内容大相径庭,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类标语口号仍然带有隐语的性质,值得警惕。
三、传销犯罪隐语的基本特征分析
传销犯罪隐语蕴含着与传销有关的犯罪性质、犯罪事实、犯罪身份等各方面的信息,和其他犯罪领域的隐语相比,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复指性极强
复指性是各类型犯罪隐语的共性特征之一,它是指同一个事物用多个不同的隐语来表示。[2]166例如毒品犯罪领域,指代海洛因的就有“双狮地球”“四号”“四哥”“三合一”“小白”“面粉”等多个隐语。[4]传销犯罪隐语的复指性较之其他领域的犯罪隐语更强。根据不完全统计,光指传销这种行为的隐语就不少于30 条,如“阳光工程”“阳光投资”“1040”“520+520”“西部大开发”“西部商务”“国家项目”等。指代邀请人加入传销组织这种行为的有“钓鱼”“抓羊”“打豆”“请客”“带客”“请人”“邀约”“招新”“纳贤”“做市场”“放线”等10余条隐语。指代给新人洗脑也有大量的隐语,常见的就有“喝汤”“烧开水”“喝咖啡”“讲思想”“除旧”“施肥”等隐语。即便是同一个传销组织的内部,对同一个事物所用的隐语也很多。这种复指性特征不但使传销犯罪隐语的数量变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增强了隐语的保密性,使外人无法轻易掌握这些隐语。
(二)衍生速度快
各个领域的犯罪隐语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言语系统,其发展变化通常和犯罪形式、手段的变化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犯罪隐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根据形势变化和犯罪需求不断更新。传销犯罪隐语也是如此,也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新隐语源源不断产生。例如近年来传销人员给传销这种行为穿上了很多新的马甲,把以前的“1040 工程”“西部大开发工程”改名叫做“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家庭创业工程”。尤其是随着微信、自媒体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以打着“虚拟货币”“期货投资”“科技创新”“区块链”“慈善互助”“电子商务”等新概念为幌子的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经济犯罪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网上创业式传销、连锁加盟式传销、慈善式传销、虚拟货币传销、网络博弈式传销等新型传销也日渐增多,并由此衍生了很多新的传销犯罪隐语。例如,百川币、SMI、MBI、马克币、贝塔币、暗黑币等都是对一些传销骗局的内部用语。又如,“消费满500 元返利100%”“消费不用花钱,免费购买商品”“消费=存钱=免费”“一边上网娱乐,一边上网赚钱”等新的传销宣传口号也大量滋生。总之,旧的传销犯罪隐语在不断消亡,新的传销犯罪隐语又在不断滋生,特别是借着互联网这个温床,其滋生的速度很快,值得关注。
(三)派系差异大
我国境内的传销可以分为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两大类型,二者的划分最初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是南派传销,典型代表就是两广地区;长江以北是北派传销,典型代表就是东北地区。[5]然而随着传销的发展以及国家打击力度的持续增大,两派传销不断跑路和搬家,寻找新的适合传销生存的土壤,传销就渐渐失去了地域之分,如今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主要的区别是在操作模式上。传销操作模式的不同,管理方式和“工作”内容也不同,从而造就了不同的传销犯罪隐语。正因如此,尽管传销已经打破了地域之分,但是在传销犯罪隐语上依然有明显的南北差异。其中,南派传销主要打着“自愿连锁经营”“特许连锁经营”“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民间资本运作”“国家秘密项目”“消费投资”“商务商会”“1040 阳光工程”“西北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旗号,因此传销犯罪隐语多与投资、理财、开发、连锁等有关,例如国家项目(传销投资)、阳光理财(传销入伙收人头费)、商会(传销组织)。北派传销则打着“直销”“网络营销”“人际网络”等旗号,通常限制人身自由,因此,传销犯罪隐语多与直销、网络、营销有关。北派传销还有一套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的专用语,例如住宾馆(把人关起来)、按摩(给不听话的人打一顿)、站岗(看守放哨)、睡地铺(10 人以上关一起)等。有时候根据传销犯罪隐语的这些差异可以起到辨别传销派系的作用。
(四)内容蛊惑性强
其他犯罪领域的隐语,内容上主要突出保密性,限于内部交流使用。相比之下,传销犯罪隐语有相当一部分是面向社会不明真相的人使用,具有极强蛊惑性,让人听了之后很容易被洗脑。一方面,大部分隐语都冠以“投资”“工程”“开发”“理财”“项目”“金融”之名,甚至打上“国家扶持”“政府鼓励”的标签,让人信以为真。另一方面,编造一些蛊惑性宣传口号,如“开发北部湾,共享中国梦”“我们的事业,国家的未来”“在家打牌,轻松百万”“国家打击,旨在保护”“没有传销,只有营业”,冲击人们的心理底线,让“传销是合法行为”这种认知深深扎根在不明真相的人的脑海中。传销人员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通过大量隐语、欺骗性语言,不断地给被发展者灌输着传销致富的理念,使其一步步地沉迷于其编织的美梦,在内心深处对传销实现了认同,从而在传销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传销犯罪隐语的蛊惑性由此可见一斑。
四、传销犯罪隐语的形成理据分析
隐语从使用目的上来说是为了增强信息交流的保密性,防止内容被局外人知晓,因此隐语常常被视为语言交际密码。作为“密码”,隐语并不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一套体系,而是基于汉语普通话词汇或方言词汇而形成的,也即隐语具有依附性。[6]由于隐语依附于汉语词汇,因此在形成方式上都有一定的规则可循,而非杂乱无章,否则创造者或使用者自身也会难以记忆。传销犯罪隐语同样也是基于一定的方法或规则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形成理据。
(一)比喻法
即以一事物比喻与传销某方面相似的另一事物,从而形成隐语。具体而言,有的隐语是通过形象比喻,例如“放单线”指一个人出去走走,“走双线”指乘坐火车,其中的“双线”是根据火车轨道的特性比喻而来。有的隐语是类比而来,例如“上课”指传输传销业务知识,类似于在教室里上课;“钓鱼”指引人上钩。有的是通过转喻的方式形成的,这类隐语带有明显的“指鹿为马”的特点,往往是对不好的事物进行美化,例如将传销行为美化为“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将传销人员美化为“业务员”“组长”“科长”,把粗茶淡饭叫做“三菜一汤”,把白菜汤叫做“金枝玉叶汤”,把土豆萝卜西红柿做的菜叫做“满汉全席”,把白开水叫做“茅台酒”等。有的隐语则是在比喻的基础上通过联想延伸而来,例如“喝汤”“烧开水”都是指给新招纳的人员洗脑,“汤”“开水”都是液体,这就跟“洗”产生联系,喻指洗脑。比喻法是传销行业最常用的隐语创造方法,用这种方式形成的隐语其字面意思和真实含义之间一般都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借代法
传销犯罪隐语很多是通过借代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借用一个与某个事物相关的词语来代替这个事物。常见的有用标志代替整体,例如把警察叫做“两道拐”,因为见习警察或辅警的肩章是两道拐弯符号,故被代指警察。又如“闪光灯”指警车,理据是警车的上部装有红蓝爆闪灯,以此代指警车。还有一种是部分代整体,例如“阳光投资”“西部大开发”“1040 工程”都是指传销活动,这些隐语被社会揭露后,传销组织就借用原来隐语中的第一个字来指代原意,于是用“阳工程”“西工程”“1工程”之类的叫法来指代传销行为。这种借代实际上是对原来隐语的缩略,相较于此前的隐语,其隐蔽性更强。
(三)谐音法
谐音是隐语常见的形成方式之一,传销领域也经常用这种方法创造隐语。例如“龙井”指警察,因为“龙井”是“龙井茶”的简称,这个词语中的“井茶”与“警察”谐音。“抓羊”指邀请新人加入传销组织,“羊”在粤语中和“人”谐音,“抓羊”实际上就是“抓人”。广东一带的传销组织还将警察叫做“大嫂”,因为香港习惯把警察叫做“sir”,这个单词和“嫂”谐音。传销行业还有一种通过数字读音和某个词语的谐音关系形成的隐语,也即数字谐音隐语。例如“98”代表“走吧”“酒吧”,“68”代表“溜吧(即逃跑)”,“07”代表“你去”,“31”代表“生意(即传销)”。
(四)统称法
传销组织内部经常会有一些“数字+名词”格式的隐语,例如“一汤”“三课”“四大学习”“五子登科”“五级三晋”“八字方针”等。这些隐语都是对一种或者几种具体事物的统称。其中“一汤”指思想洗脑课,“三菜”指制度课、剖析课、发展课,“四大学习”指听课技巧、邀请技巧、推荐技巧、配合技巧,“五子登科”是指拥有车子、房子、妻子、票子、孩子,“五级三晋”是指五个身份级别、三种晋级制度,“八字方针”是指听话照做、服从配合。除此之外还有“八大交流”“十六字箴言”“六大工程”“四条原则”“三严”“四请”“七律”等内部隐语,都是对几类具体事物的统称。相对而言,这类隐语破译难度很大,因为它们只是一种统称归纳,字面上并没有表现具体所指的内容,仅仅能够推导每条隐语所指的事物数量。例如,“五子登科”能推断出五个“子”,但“子”具体指代何物,则需要了解其内部背景,否则很难破译。
(五)拆字法
拆字就是将某个字拆开来表示某个真实意思,或者将拆开的偏旁部首通过会意的方式组合为一个意思。例如“田里力工”指男性,“田”和“力”合为“男”。“好人左边”指女性,“好”的左边即为“女”。传销组织内部在称呼某些人员的头衔时,一般不直接称呼其真实姓氏(传销人员几乎都不知道头目们的真实姓名),而是将真实姓氏拆分为几个部分来称呼,例如将吴姓经理称为“口经理”“天经理”或者“口天经理”,将李姓主管称呼为“木总”“木子主管”,将廖姓主管称为“广总”“广羽主管”,等等。这样就不会轻易将传销组织内部的头目或组织者的姓名泄露,从而起到隐藏身份的作用。
(六)笔画法
笔画法基本上只用于数字的表示。众所周知,汉语中的“一”“二”“三”所代表的数字与这个字本身的笔画数量是对应的。传销组织内部受此启发,也借用一些笔画数量分别是1-10 的字来代表具体某个数字。例如,“乙、丁、丈、心、禾、竹、我、金、禹、哥”分别代表1-10,因为这些字的笔画数量分别是1-10 画。广西警方曾打掉的一个传销组织中,他们的手机短信里就有一行文字“乙乂已以仪亦矣宜奕益”,这些字的声母和韵母都相同,只是声调不同,办案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破案后才明白这十个字分别代表的是数字1-10,其规则就是每个字的笔画数量。
五、传销犯罪隐语的应对策略
传销犯罪隐语是传销违法犯罪分子的交际工具,本质上是基于普通汉语词汇形成的一套秘密用语。我们没法控制这类隐语的产生和发展,毕竟它们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是传销组织,只要有传销犯罪行为的存在,传销犯罪隐语就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但是通过探索它们产生的规律、传播的路径,进而尽可能的去破译它们的内容,阻断它们的传播路径,为打击传销犯罪行为以及为公众防范传销陷阱提供智力支持。为此,提出如下几方面应对策略:
(一)把握传销犯罪隐语的形成规则破译其内容
从前文介绍的传销犯罪隐语形成的词语理据可以看出,传销犯罪隐语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大机制:修辞手法和认知手段。传销人员一方面借助比喻、借代、谐音等修辞手法创造隐语,在此基础上进行同类隐语衍生,从而形成一定规模体系的传销犯罪隐语。另一方面,他们也基于不同事物之间相似性、关联性这一认知模式,把生活中的一些普通名词同传销领域的一些具体事物结合起来,从而将普通名词术语为其所用。这也客观上说明传销犯罪隐语的形成是有一定模式的,它们总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路径进行衍生和派生,万变不离其宗是这类隐语的基本特点之一。正因如此,有时只要掌握了某一条传销犯罪隐语的含义就可以破译一串隐语,例如2021年我们协助辽宁某地侦办一起传销案件,嫌疑人的微信中有“风”“刮风”“起风了”“风来了”“被风刮跑了”这类的隐语。“风”指警察,因此类推出“刮风”“起风了”“风来了”是指警察来了,而“被风刮跑了”指被警察抓走了。
(二)运用大数据手段对传销犯罪隐语进行即时监测识别
传销组织在进行传销活动时,都会运用一些即时通讯工具如电话、微信、QQ、短信、电子邮箱、阿里旺旺等进行信息传递,在传递的内容中经常包含有大量的传销犯罪隐语。在掌握线索的基础上,公安机关可采用大数据手段和技术侦查手段对传销组织和传销人员的即时通讯工具中的传销犯罪隐语进行监测识别。具体来说包括两个工作:第一,建立传销犯罪隐语数据库。公安机关在办理传销案件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传销组织的各类隐语黑话进行收集,对其含义、使用的地区进行标注,建立传销犯罪隐语电子档案,然后将其整合为数据库。第二,将传销犯罪隐语数据库同舆情监测手段结合起来,对即时通讯工具上的传销言语信息进行自动监测识别。其具体做法是将传销犯罪隐语运用字典树的方法,把它们处理为敏感主题词并进行关联,然后导入信息监测系统中,系统通过即时匹配跟踪实现对涉及传销内容的监测。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库建设是关键,公安机关要常态化收集辖区内的传销犯罪隐语,动态更新数据库内容。
(三)对网站上的传销犯罪隐语进行专项清理
近年来,传销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传销组织不但依托网络技术人员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网站,[7]而且还经常利用网络贴吧、论坛、抖音、快手、百家号、头条号等交际媒介发布与传销有关的内容。以至于网络上大量充斥着传销犯罪隐语,一些门户网站和自媒体账号,已然成为传销人员学习传销犯罪隐语的平台。因此,网信部门、公安机关有必要基于传销犯罪隐语数据库,利用舆情监测手段中的话题跟踪、信息过滤、内容筛查等技术,对互联网上的各类传销隐语行话进行清理、屏蔽,阻断其传播的路径。在这一方面已经有现实的案例参考,例如2015 年,针对网络上大量充斥的涉毒隐语黑话问题,公安部、国家禁毒办会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信部等部门开展了专项清理行动,取缔了832 家涉毒网站,封堵了1471 家境外涉毒网站,清理删除了涉毒隐语黑话6.5 万多条,成效十分显著。[8]治理网络上的各类传销隐语也可参考这一思路,通过多部门联动实现“清网”。
(四)面向公众揭露传销犯罪隐语的本质
传销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明暗结合,即以合法经营之名进行光明正大的宣传、策划,然后暗地里进行非法活动。在此过程中,传销组织者都会运用大量貌似合法的术语来引诱公众上钩,这些术语实际上就是披着合法外衣的犯罪隐语而已。公安机关应该借助国家和地方媒体的反传销专栏,加强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宣传,揭露传销活动中隐语黑话的性质和真实含义,让公众透过现象窥视其本质,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例如几年前广西、广东等地的公安机关就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以科普专文的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揭露了大量的传销隐语黑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9]这也客观上启示我们应该通过宣传手段,瞄准目标对象,构建全警反传销、全社会反传销的治理格局,从思想和认知上提升公众的防范能力。
六、结语
近年来,传销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传统的以“洗脑”为主的聚集型传销转变为网络型传销。传销人员通过自己构建或者租借第三方服务器来设置传销网站开展传销活动,通过即时聊天工具与下线联系,无需实际接触。伴随着这种变化,传销犯罪隐语大部分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网络已经成为传销犯罪隐语滋生的温床。今后应对传销犯罪隐语更要侧重从网络监管入手,阻断其传播渠道。公安理论研究也应加强对这种隐语的研究,深入分析它们的形成机制和形成规律,解析它们的含义,将侦查学、语言学、舆情监测等学科理论结合起来,构建跨学科研究框架,为传销犯罪隐语破译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更好地服务于公安机关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