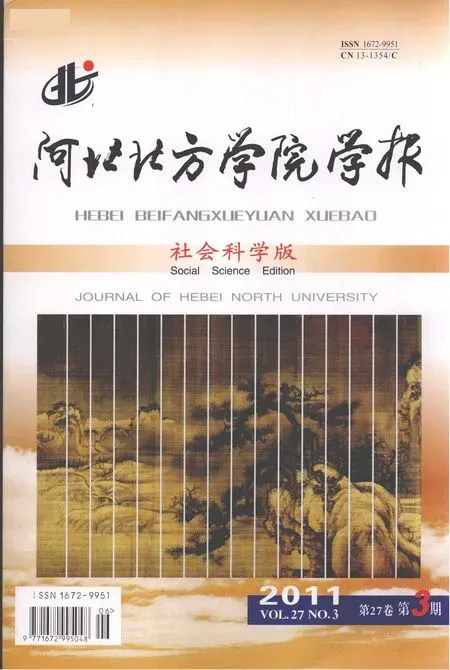保留宾语把字句的句法生成研究
黄新强,黄婷婷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目前,关于保留宾语句式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以下两种句式:一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式,如早期汉语语法主宾论战以来人们已耳熟能详的例句:“王冕七岁死了父亲”;二是某些被字句动词带宾语的句式,如“张三被杀了父亲”。这两种句式是汉语中独具特色的结构,不少学者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关于另外一种带保留宾语的句式——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却鲜有系统、全面的论述与研究,例如:“她把橘子剥了皮”,“李四把纸门踢了一个洞”等。
本文借鉴吸收前人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之合理论述,综合运用“非宾格假定”(Unaccusative Hypothesis),“题元理论”(Thematic Theo ry),“格语法”(Case Grammar)等相关理论,对保留宾语把字句的句法生成机制进行探究,力求为该句式找到一种统一有效的生成模式,以期丰富、完善现有的把字句生成研究及保留宾语句式研究。
一、保留宾语句式研究现状及问题
学界广泛讨论并普遍认可的保留宾语句式主要包括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式和被字句动词带宾语句式。这两种句式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注意①,但他们对这两种句式的分析大都是独立进行的,不曾发现这两种句式的相似性及关联性,因为这两种句式表面上看来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徐杰[1](P23),[2](P72)首先观察到这两种句式有着诸多的共性,并将两种句式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最终提出一套统一的理论解释,对后来的保留宾语句式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与推动作用。近年来涉及保留宾语句式研究的学者有邓思颖、潘海华、韩景泉、朱行帆、沈家煊、黄正德等,其中涉及以上两种句式分析的主要是是潘海华、韩景泉。本文综合各家论述,并主要以徐杰和潘海华、韩景泉之研究为参照,简要论述保留宾语句式研究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两种保留宾语句式的共性
根据徐杰[1]和潘海华、韩景泉[3]对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及被字句动词带宾语句的研究,这两种句式的共同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两类句式中动词前后两个名词性成分必须具有广义的“领有/隶属”关系,既包括一般意义的“领有/隶属”关系,也包括“部分/整体”关系和“亲属”关系。
2.两类句式中动词后名词性成分既可出现在动词之前,也可出现在动词之后。例如:
(1)a.张三死了父亲。/张三的父亲死了。
b.张三被杀了父亲。/张三的父亲被杀了。
3.两种句式中宾语不能提升到句子主语之前。例如:
(2)a.他断了一条腿。/*一条腿他断了。
b.他被绑了一条腿。/*一条腿他被绑了。
4.两种句式中动词都不具备给宾语指派格位的能力,而动词后面又都有要求获得格位的名词性成分。
事实证明,两种句式中前后两个名词性成分不一定具有广义的“领有/隶属”关系,这一点对后面的分析很重要。黄正德[4]也指出“历事主语与受事宾语虽然常有某种领属的语义关系,但这绝不是这种经验式非宾格句的必要条件”②,“主语与宾语之间至少在有关事件发生之前也谈不上什么关系”。例如:
(3)a.他家来了许多要饭的。
b.他们发生了一起车祸。
c.墙上被人涂了很多颜料。
d.桌子被人砸了一个洞。
(二)对于共性特征的语法解释
“非宾格假定”理论与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Perlmutter[5](P157-189)首先提出单元述词应分为“非作格”(unergative)与“非宾格”(unaccusative)两种。Burzio[6]进一步指出双元述词也应平行地分为“及物”(transitive)与“致使”(causative)两类动词。李艳惠、吕叔湘、黄正德③曾对汉语动词做过类似区分。例如:
(4)a. 非作格动词 :cry,laugh,talk,哭 ,笑 ,跳等表示动作的自动词
b.非宾格动词:exist,appear,arrive,来,死,发生等存现动词
c. 及物动词 :eat,drink,kick,打 ,骂 ,吃等
d. 致使动词 :break,sink,open,开 ,关 ,摇等
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在深层结构中是句子的逻辑主语,在表层结构中也是句子的语法主语,属于外部论元;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在深层结构中是句子的逻辑宾语,在表层结构中是句子的语法主语,属于内部论元。根据非宾格假定,这里所讨论的不及物动词带保留宾语句式中的不及物动词主要就是非宾格动词,而非宾格动词不具备给深层逻辑宾语指派结构格的能力。被字句中动词经被动化之后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的能力让“被”给吸收了,同样不具备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的能力,而且深层主语也被抑制掉。所以,这两种句式在深层结构中也都是无主句。
徐杰[1,2]认为,生成这两种句式的主要手段是领有名词移位。领有名词移位的主要动因是为了满足“格鉴别式”(Case Filter)的要求,即为了获得格位。领有名词前移至主语位置并获得主格,保留宾语留在原位获得“部分格”。而深层主语(PRO)的非论元位置为已获得题元角色(领有)但却无法获得格位的领有名词移位提供了落脚点(landing site)。
潘海华、韩景泉[3]认为,部分格假说存在严重缺陷,领有名词移位说同样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了全新的处理方法,认为句首名词性成分属于非论元,不是句子的主语,而是话题(topic),话题不是移位产生的,而是基础生成(base-generated)的。句首名词性成分位于CP的Spec位置,而通常所谓的主语位置,即 TP的Spec位置是一个空位。“张三死了父亲”和“张三被杀了父亲”具有如下深层结构:
(5)a.[CP张三 [TPe[VP死了父亲]]]
b.[CP张三 [TPe[VP被杀了父亲]]]
受格要求的驱动,在动词后基础生成的客体论元通过显性移位移入e处,获得主格,再向右移位,移出VP嫁接在 TP位置上,这种句法操作称为“外置”。再次移位的动因是语用原则,即为了生成句末焦点。在(5)基础上的进一步移位生成如下结构:
(6)a.[CP张三 [TPti[VP死了ti]父亲i]]
b.[CP张三 [TPti[VP被杀了ti]父亲i]]
(三)现有研究的主要问题
领有名词移位说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重复赋格”和“格冲突”[3,7]。领有名词本身有“所有格”,移位后又获得“主格”,造成“格位重复”和“格冲突”。另外,“的”字的消失缺乏合理的解释,违反了“充分诠释性原则”(Princip le of Full Interp retation);领有名词的落脚点同其语迹分属不同的投射层次,违反了“语链一致性原则”(Chain Uniformity Princip le)。“部分格”假说也存在严重问题,“部分格”获得者要求是无定性质的成分,然而事实并不尽然,而且引入“部分格”将使“非宾格假定”原有的解释力失效,甚至使整个格理论的解释力失效。
面临这种状况,朱行帆[8]用核心动词向轻动词EXPERIENCE的移位来解释句子的生成,但这种移位缺乏有说服力的动因,而且设置这样的轻动词会排除很多合格的句子,生成很多不合格的句子。沈家煊[7]提出用“糅合”(blending)理论来解决各种问题,“糅合”说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却回避了保留宾语句式研究在生成语法框架下面临的难题,因为“糅合”操作在本质上属于认知范畴。
笔者基本认同潘海华、韩景泉[3]的解释办法,话题及空主语假定可以较好地解释下面两个基本问题:
1.“张三,父亲死了”和“张三死了父亲”的关联。这两句话在结构合法性方面不存在差异,只因语用表达力不同,后一种结构形式使“父亲”成了焦点,从而得到强调。
2.“客人来了”和“来了客人”的关联。既然“来了”无法为“客人”赋格,为何“来了客人”仍是合格句式呢?按照他们的理论,“来了客人”中的“客人”是经过了句法移位而外置的,已获得主格,并成为焦点;“客人来了”中“客人”移位至空主语处没有成为焦点而已。
二、保留宾语把字句的生成
目前,关于保留宾语句式的研究很少涉及把字句中动词带宾语的现象,邹科[9]、黄正德[10,4]等曾讨论过类似“他把橘子剥了皮”的句子,但并未针对此类句式进行详细论述。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很多,例如:
(7)a.他把橘子剥了皮。
b.他们把苹果吃了8个。
c.他把门踹了1个洞。
d.我把墙上刷了漆。
这种句式在把字句中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别,无论是从把字句生成研究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保留宾语句式生成研究的角度着想,都很有必要对保留宾语把字句进行系统的考察。
(一)保留宾语把字句与上述两种保留宾语句式的比较
保留宾语把字句是否具备另外两种保留宾语句式的共性?如果答案肯定,能不能用统一的方法来处理这三种句式?发现不同句式的共性,并试图用一套统一的句法理论加以解释,这完全符合生成语法的经济原则:即用尽可能少的理论或规则去解释尽可能多的语言现象。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1.关于动词前后名词性成分具有广义的“领有/隶属”关系一说,本文持否定意见,很多保留宾语把字句同样不具备这一特征。如例(7)中的c、d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已足证移位说的不可行,Hole[11](P365-386)提出以约束理论来刻画主宾之领属关系,但却无法解释没有领属关系的句子④。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句式中参与比较的名词性成分位置不同,前两种句式是句首与句末名词性成分比较,而保留宾语把字句是句中与句末名词性成分比较。因此,邹科[9]将例(7a)中“橘子”和“皮”看成是由最初的单一名词词组“橘子皮”经移位得来的分析并不合理,“他把门踹了一个洞”和“我把墙上刷了漆”永远不可能有“*他踹了门的一个洞”和“*他刷了墙上的漆”这样的对应句。
2.关于前两种句式的第二点共性,保留宾语把字句与之相差甚远。这主要是因为保留宾语把字句中名词性成分同另两种句式中名词性成分所担当的题元角色不同。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属非宾格句)和被字句动词带宾语句中句首是历事,句末是受事,而保留宾语把字句中句首是施事,句中是蒙事,句末是受事。历事与受事可以一起出现也可以分开出现,但施事与受事总要分于动词前后。保留宾语把字句具备第三点共性,不过与本文的讨论关系不大。
3.不像无法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的非宾格动词,也不同于让“被”吸收了赋格能力的被字句中的动词,保留宾语把字句中动词属二元非作格动词(本文采用黄正德[4]对汉语动词进行的分类方式,将汉语一至三元动词都分为非作格与非宾格动词),可以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前面已经提到,动词无法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是前两种句式生成过程中句法操作的主要动因,而保留宾语把字句中动词不具备这一特征,因此从根本上否定了采用同一套理论解释保留宾语把字句的可行性。
(二)保留宾语把字句的主要句法特征
保留宾语把字句中的动词一般属二元非作格动词,保留宾语把字句属非作格句。非作格句的本质特征是以施事论元为其外在论元,即非宾格句的主语是基础生成的,这同潘海华、韩景泉的空主语假设无法相容。一元非作格句是个无宾句,二元非作格句在动词后有受事成分,保留宾语把字句属含二元非作格动词的三元非作格句。二元非作格句只需两个论元就已满足动词对论元数目的要求,第三个论元的题元角色是由谁指派的呢?该论元的格位又是由谁赋予的呢?
一个自然的假定认为“把”赋予该论元以一定的题元角色,并为该论元赋格。黄正德[12](P167-174)详细地论证了“把”不具备赋予句中论元题元角色的能力,并认为“把”是特殊的功能语类,唯一作用是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事实上,“把”并不能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来研究和分析“把”的词类归属。传统汉语语法一直将“把”看作介词,这并不合适,因为“把”虽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介词,但同样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有悖于介词的特征,如“把 NP”不能移动;不能省略;否定词可以置于 PP和VP之间,却不能置于“把NP”和 VP之间;跟把字句关系最密切的不是主动宾句,而是受事主语句等。“把”更不是动词,因为“把”在语法化过程中已明显丧失了动词的大部分特征。不少人将“把”看做具备致使义的轻动词,是轻动词v的语音实现。将“把”看做轻动词最难以解释的就是状语成分的位置问题。例如:
(8)a.小王小心地把杯子拿给小李。
b.小王把杯子小心地拿给小李。
c.小王小心地拿杯子给小李。
d.*小王拿杯子小心地给小李。
(8a-b)中方式状语“小心地”可以出现在“把”前或“把”后,但(8c-d)中状语却只能出现在动词之前。这说明“把”的位置应高于主要动词提升后的落点v,即“把”在 vP之上。邹科[9]、张杰[13]、黄正德[12](P176-195)等认为只能将“把”看作是汉语中除核心功能语类外的特殊功能语类⑤。能够为名词词性成分赋格的主要是具备一致性特征的核心功能语类、及物动词和介词,“把”作为不具备一致性特征的特殊功能语类,是不能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的。如果将“把”视为赋格成分,下述现象将难以解释:
(9)a.她把水喝了。
b.她喝了水。
(9b)中“水”由“喝”指派宾格 ,那么(9a)中“水”也应由“喝”指派,而非“把”。若是这样,“把”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已获得格位的NP只能移到非格位处,“把”后NP位置应该是非格位位置。如果“水”由“把”指派宾格,则“喝”不能为“水”赋格,这又如何解释呢?可见,“把”的作用并不在于格位指派。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把”既不具备为动词论元指派题元角色的能力,也不具备赋格能力,“把”是可以引入域外论元、含“控制性致使”义的功能语类。那么,回到上面的问题,保留宾语把字句中第三个论元的题元角色到底是由谁指派的呢?该论元的格位又是由谁赋予的呢?
笔者认同黄正德[4]的观点:非作格结构具备中间论元,语义上指涉蒙受者(Affectee)或者间接受事(Indirect Patient),处于“外宾语”(outer object)位置。以“他把橘子剥了皮”为例,“他剥了皮”已是二元非作格句,而“橘子”作为第三个论元,也即中间论元,出现在“把”和V之间,其题元角色是由“剥+皮”这一动词短语赋予的,其角色是“蒙事”。而其格位则是在其与轻动词v的一致性特征进行核查时由v赋予的。
(三)保留宾语把字句的生成分析
以“他把橘子剥了皮”为例,详细分析保留宾语把字句的生成过程。首先,从词库中提取动词词组“剥了”和具有受事题元角色的名词性成分DP1“皮”合并形成 VP’,VP’与作为 VP指示语的 DP2“橘子”合并形成V P;轻动词v选择V P为补足语,形成v’,v’与其指示语合并形成vP。在本运算阶段,共有如下非诠释性特征(uninterp retable feature)需要核查:v的强[-V]特征,v的一致性特征,v的 P特征,DP1和DP2的结构格特征。V为DP1赋宾格,消除DP1的格位特征;v的强[-V]特征激发V移位至v,消除该特征;v的一致性特征作为探头,探测到目标DP2后,匹配的特征就建立了一致关系,二者的非诠释性特征得以消除;v的P特征致使DP2移至v的Spec处核查该特征,P特征消除。推导继续进行,功能词“把”选择vP为补足语,并在词汇矩阵中选择代词“他”作为它的域外论元;T与BaP合并,并投射成 TP。至此,三个非诠释性特征需要核查:T的一致性特征,T的 EPP特征和域外论元的一致性特征。T的一致性特征作为探头,探测到EA的一致性特征,一致操作消除二者的非诠释性特征;T的EPP特征激发EA移位至其Spec位置,消除该特征,推导成功。关于句中名词性成分的题元角色,V给DP1和 EA分别指派受事和施事的题元角色,VP为DP2指派蒙事的题元角色。由此可见,vP的Spec位置是一个非论元、非格位位置,这才使得已获得格位和题元角色的DP2的移位成为可能。推导过程如(10)所示:

综上所述,本文在生成语法普遍语法理论原则的框架下,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保留宾语把字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保留宾语把字句同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和被字句动词带宾语句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无法应用现有的保留宾语句式的生成模式,进而提出一套新的解释理论,对保留宾语把字句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有益探索,并得出如下基本观点:保留宾语把字句中具备三个论元,“把”后名词性成分属于中间论元,并由VP指派“蒙事”的题元角色;中间论元的格位特征通过与轻动词v的一致性特征匹配得以消除;“把”属特殊功能语类,具备“控制性致使”义,可以引入域外论元,但既不能为前后名词性成分指派题元角色,也不能为其后名词性成分赋格。当然,还需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工作,才能对本文提出的保留宾语把字句的句法生成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注 释:
① 关于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句式早期可见于吕冀平(1955)、邢公畹 (1955)、曹伯韩 (1956)、徐重人 (1956)、素父(1956)、李钻娘(1987)、郭继懋(1990)等;关于被字句动词带宾语句式早期可见于吕叔湘(1948,1965)、丁树生(1961)、李临定(1980)、朱德熙(1982)等。
② 历事、受事属动词论元的题元角色;关于非宾格句下文另有讨论,这里指不及物动词带保留宾语句。
③ 黄正德[4]认为,汉语三元述词和与其相关的句法结构同样可以分为非作格、非宾格两类。
④ 详见黄正德[4](P8)注解[10]。
⑤ 从“核心”这一术语出发,有核心必有边缘,核心功能语类具有跨语言普遍性,特殊(边缘)功能语类则具备语言个性[14](P217-229)。
[1] 徐杰.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 [J].当代语言学,1999,(1):16-29;1-19.
[2] 徐杰.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潘海华,韩景泉.汉语保留宾语结构的句法生成机制[J].中国语文,2008,(6):512;514-517.
[4] 黄正德.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 [J].语言科学,2007,(4):8.
[5] Perlmutter D.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D].Proceedingsof BLS,1978.
[6] Burzio L.Italian Syntax[M].Do 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6.
[7] 沈家煊.“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 [J].中国语文,2006,(4):292-294.
[8] 朱行帆.轻动词和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J].现代外语,2005,(3):221-231.
[9] Zou K.The Syntax of the Chinese Ba-constructions and Verb Compounds:A Morpho-Syntactic Analysis[D].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95.
[10] Huang C-TJ.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D].Cambridge:MA :M IT,1982.
[11] Hole D.Extra argumentality-a binding account of“possessor raising”in German,English and Mandarin,in Possessivesand beyond:semanticsand syntax,ed.by Ji-yung Kim,Lander Yand Partee B A.MA:GLSA Publications,2005.
[12] Huang CT J,Li YH A,Li YF.The Syntax of Chines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3] 张杰.最简方案新框架下把字句的生成与推导 [J].外国语言文学,2006,(2):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