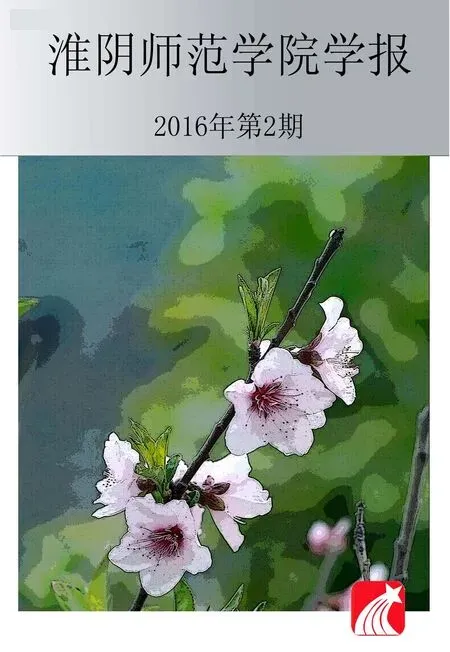课程的理解:专家与实践者的维度
孙文书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课程的理解:专家与实践者的维度
孙文书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课程改革决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是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改革运动,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范式的根本转换。课程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每一个与课程有关的人员都秉持着自己的课程概念。然而,认识上的分歧,使新课程改革在理论探究与教学实践中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非议、抵制与排斥。基于此,文章从专家和教师视角对传统课程认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基础上,探索了当代课程的品质。
课程;课程专家;课程实践者;思维方式
0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课程语义的源流
新课程改革要求增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愿望以及思考和探究未知世界的动机,并从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角度,全面设计课程目标,从而使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新课程改革,不仅具有了崭新的时代依据,而且具有了更丰富的科学内涵。
对课程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指引、支配着甚至决定着不同价值主体的课程行为方式。课程一词作为课程论学科的核心术语,其概念不仅是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更是课程实践的航标。但是,课程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课程一词的界定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在见仁见智的阐释中使其处于歧义丛生的境地。在课程本质的认识上,曾经受到批判和摒弃的历史观点仍在一些课程实践者的观念中徘徊,干扰和误导着对于今天学校课程的理解。因此关于“课程是什么”的追问,无论从理论建构的逻辑必要性,还是课程变革实践的吁求来看,都有必要重新给予回答。明确“课程是什么”的问题是课程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它规定着课程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课程编制模式以及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的范围、方向、策略等问题。
在西方英语世界里,课程(curriculum)一词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它是从拉丁语“currere”一词派生出来的,意为“跑道”(race-course)。根据这个词源,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currere”一词的名词形式意为“跑道”,由此课程就是为不同学生设计的不同轨道,从而引出了一种传统的课程体系。课程是比较标准的场地,学生在上面跑向终线(获取文凭)。而“currere”的动词形式是指“奔跑”,这样理解课程的着眼点就会放在个体认识的独特性和经验的自我建构上,就会得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课程理论和实践。
1 专家的课程观:分类学的考察
课程研究领域中学派林立、异说纷呈,如儿童中心论课程观、学科中心论课程观、社会中心论课程观之间的冲突;课程编制的工学模式、过程模式之间的对峙等无不是起源于对课程本质内涵的不同理解。
奥利佛对课程本质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1)课程是在学校中所传授的东西;2)课程是一系列的学科;3)课程是教材内容;4)课程是学习计划;5)课程是一系列的材料;6)课程是科目顺序;7)课程是一系列的行为目标;8)课程是学习进程;9)课程是在学校中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课外活动、辅导及人际交往;10)课程是在学校指导下,在校内外所传授的东西;11)课程是学校全体职工所设计的任何事情;12)课程是个体学习者在学校教育中所获得的一系列经验;13)课程是学习者在学校所经历的经验……
我国课程学者施良方教授曾对课程概念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和梳理,把近百种的课程概念归结为六种类型,即: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
台湾课程学者黄政杰考察了众多的课程定义后,把课程定义归纳为四类:第一,课程是学科和教材;第二,课程是经验;第三,课程是目标;第四,课程是计划。
郝德永教授根据其具体表现围绕目标、经验、活动、计划几个维度对课程进行限定:主张将“预期的学习结果和目标”视为课程,而内容或经验则被看作是课程的手段;强调从学生学的角度确定课程的内涵,这种课程观起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把活动纳入课程的组成部分,这种课程观并不反对学科课程,只是考虑到学生在除了教学活动之外的其它活动中也能获取某些知识、经验,而这些知识经验又是传统的学科课程所无法包容和解释的,于是,以堆积的方式把这部分活动也纳入到课程含义中,这样便有了“课程是指有计划的学科或其他活动”的课程定义;把课程定义为一种计划。
关于课程本质问题持续至今争论,体现了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对传统课程本质观的辩护与修缮,体现为在课程实践中坚持以学科课程为主,辅之一些课外活动;另一种则提出各种全新的课程本质观,试图超越传统的学科课程教育内容的局限,赋予课程以新的姿态和面貌。上述两种取向的共同旨趣在于视课程的本质为知识。
现代课程专家对课程的探讨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学视角,对传统课程论进行反思和批判。比如,从课程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课程(本身)”就是作为教育知识之法定基本形式的“课程文本”,亦即作为教师与学生教学活动之基本依据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材。作为社会控制的中介,课程是社会向教师与学生提供的教与学的基本依据。
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倡议者认为,课程的运行过程,是一种开放性的形成过程,它不断地进行“自组织”或自建构的调整,那种封闭的、永恒的、稳定的课程运行机制或认知范式不符合教育的特性。这样,后现代课程观坚持建构性、探究性的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赋予了每个人建构与探究的权利,从而使教师由“布道者”、“控制者”、“代圣人传言者”转为组织者、探究者,与学生具有平等的地位。
2 实践者的课程观:被束缚的教师
课程改革所产生的更为深刻的变化,反映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的改变上。教师对课程的理解也即教师的课程意识,是教师的“课程哲学”,是以课程观为核心形成的,是对教育活动体系中课程系统的一种整体认识,是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课程观与方法论。
目前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其一就是在前苏联凯洛夫教学影响下的经典“课程知识观”。学校设置课程,是为学生提供认识的客体,以便学生作用于这个客体,发生教学认识过程。所以,课程本质上就是教学认识的客体,也就是人类认识成果,也就是知识。教学活动就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领(主)导学生,学习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即现成知识,使学生认识世界并发展自身的活动。教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知识打开,内化,外化。知识中心或知识居于课程的中心地位,是课程的本质决定的,知识传授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教师的神圣职责。因而,教学中“注重知识传授”,永远不存在“过”的问题,而是永远不够并且要不断加强的问题。
明确的课程意识支配着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方式、教师角色乃至教师在教育中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而没有明确课程意识的教师,总是把课程视为一种“法定的教育要素”或“法定的知识”,并在课程系统面前无所作为,即管理主义课程观。这种课程观强调课程中的国家权力、国家意志和专家权威,认为课程是由教育权力部门制定,并由指定或委托的专家设计的。从而,课程成为具有法定意义的教育要素,教师乃至学校在课程中的基本权力特别是教育专业自主权被无情地剥夺,或者教师不自觉地放弃,教师和学校被排斥在课程的形成过程之外。教师把课程作为“法定的知识”来接受和传递,教师依附于权力,依附于课程设计专家。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把课程及相关法定的课程载体(如教学大纲、教科书等)奉为“圣经”,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教师是课程的“忠实执行者”,它不希望也不要求教师在课程面前有所作为。其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教师和学校的课程权力。要体现“课程对地方、学校和学生的适应性”必须尊重教师和学校的课程权力,增强教师的课程意识,确立生成的课程观。
3 二种课程观的差异及其表现
课程本质作为课程理论探讨的一个“逻辑起点”,对此能否取得一致理解,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把握当前课程研究的主要问题领域,转变课程思维,而且将直接影响与国际课程同行的对话。当对方说的“课程”与我们意识中的“课程”不是一码事的时候,真正的对话很难持续下去。
在漫长的课程理论求索中,几乎所有课程研究者的课程概念都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每种概念大都是在认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每种概念都隐含着某些认识论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课程专家与实践者的认识是有交叉和共鸣的,但是课程改革在深入,课程专家对课程的探讨在不断地深入,而教师的课程意识似乎难以与研究者的观念同步,而是停留在传统的课程观念上。具有课程意识的教师以自己对课程的独特理解为基础,从目标、课程、教学、评价等维度来整体规划教育活动和行为方式。
课程是一种文化生成与创造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探究活动中意义、精神、经验、观念、能力的生成过程,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师生通过平等对话、交流与协商的方式,共同营造一种探究式的教育氛围。教师应该主动承担建立“自组织”的教育过程与机制的重任,使课程实施从“输入一产出”式的认同式学习转向创造式的、探究式的学习,从而实现课程的知识传递逻辑向知识建构逻辑的转换。
4 结语
总之,课程改革决不仅仅是课程内容的更新或教材的变换,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一种新思维方式的课程概念重建问题。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类文化各个领域里的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观念的更新和课程探究逻辑的转换也成为必然。因而,无论是教育理论研究者,还是教育实践工作者,都必须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探索与实践新思路与新举措。任何抱守残缺、僵化固执的课程认识,不仅因其生命力的枯竭而被时代所淘汰,而且也难以阻挡课程改革的步伐。
[1] 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7.
[2] 程天君.课程:“私人事件”还是“法定知识”?——基于社会学的课程概念重申[J].教育科学研究,2006(6):16-17.
[3] 郝德永.课程认识论的冲突与澄清[J].全球教育展望,2005(1):15-19.
[4] 黄甫全.课程本质新探[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6(1):21-25.
[5] 寇平平.课程概念的文化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9(1):35-37.
[6] 熊和平.论课程的私人性品质[J].教育参考,2006(2):12-13.
[责任编辑:张超]
G652
A
1671-6876(2012)02-0165-03
2012-03-10
孙文书(1985-),女,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