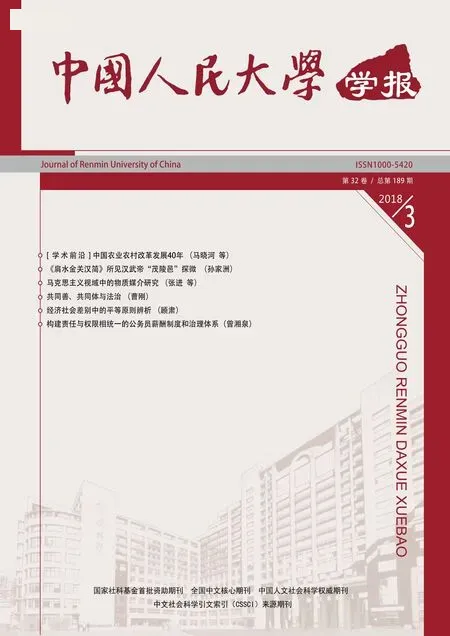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再思考
聂敏里
一、 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概述
中西文化比较是西学东渐以来,无论是在中国思想者这里,还是在西方思想者那里,都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思考。在这一比较中,人们很自然会得出种种有关中西文化、中西哲学、中西思维的差异与不同来。而在比较的方法论上,长期以来基础和主导的思考路径不外乎是以下三种,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体西用”最早的提出是在1895年,时任上海中西书院掌教的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用笔名发表《匡时策》一文,其中说道:“夫中西学问,本自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吴一泉:《“中体西用”说及其历史作用》,载《文史知识》,1990(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为“中体西用”的来源出处。自然,沈寿康的这一提法是对自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以来便盛行于清末知识分子中的有关中西之学本末、道器、主辅之论的总结和概括,而至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体西用”说遂成滥觞。*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12-31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西体中用”是李泽厚在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提出的,该书初版于1987年,其后,李泽厚又在《再说“西体中用”》*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载《原道》(第三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一文中对之予以重申。概而言之,李泽厚所提出的“西体中用”是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以胡适、吴稚晖、殷海光等人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说的纠偏之论,它意在表明,在将西方先进的文化、制度等引进中国时,应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谓“以现代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而“中西互为体用”则是傅伟勋于1984年10月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候选博士周阳山的学术对话中提出的。*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4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他用这个概念意在表明对异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吸收,所以,或许对这个概念更为贴切的表达是他所谓的“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即将西方思想“创造地转化而为我们中国本位的思想文化遗产”。*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4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近几年来,又有刘笑敢在上述中西体用模式基础上提出“反向格义”的概念*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2)。,认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框架来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他对此持否定态度。
总之,西学东渐以来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基本的思考路径不外乎就是上述这些。如果全面地观察、同情地理解,它们每一个都不能说没有一得之见,也不能说完全缺乏平衡的考虑,但是,在根本上,这些思考路径都或多或少分有一个相同的前提预设,这就是,中西文化是两种独立而异质的地方性文化传统,二者的差异是根本的,而相似或互补之处则是局部的和外在的。它们都在中西文化扞格抵牾的前提下来处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
但是,这一前提预设本身是成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忽略了文化比较中必不可少的时间参考坐标因素,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没有把它们各自放入彼此对应的时间序列中去。而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考虑文化比较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则除了有共时差异外,还有历时差异,从而在文化比较中就不仅有中西问题,还有古今问题。据此,当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正确的比较方式应当是:以古代西方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作比较,以现代西方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作比较。一旦建立起这样一种在正确的时间参考坐标中的文化比较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在文化比较中古今的差异是主要的,而中西的差异是次要的。古代西方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具有较多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古代文化类型,在这里,古代文化类型是普遍,而中西古代文化相对于它是特殊和普遍、具体和一般的关系。同样,现代西方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具有较多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现代文化类型,在这里,现代文化类型是普遍,而中西现代文化相对于它是特殊和普遍、具体和一般的关系。只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到共同作为古代文化类型,中西古代文化在一致性下又具有什么差异性,共同作为现代文化类型,中西现代文化在一致性下又具有什么差异性。但显然,这时,这些差异就是次要的,不能够改变和抹杀它们共同作为古代文化类型或现代文化类型的本质一致之处。与通常文化比较中人们对差异的重视和寻求不同,文化比较也可以去寻求和发现相同,而这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将中西文化各自特殊化为绝对的异质性、塑造成两种绝对不可沟通的地方性文化的比较模式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成见之际,这甚至具有思想上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
上述观点并不试图否认中西文化存在差别,它承认人们可以去讨论中西文化差别这一主题,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不是无效和无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差别是古今文化差别,相较于此,不仅中西文化差别是次要的,而且对中西文化差别的比较必须建立在对古今文化差别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就难免会犯时代混乱的错误,以西方之今比较中国之古,或以中国之今比较西方之古。一旦我们基于正确的时间关系来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中西文化各自基于古代或现代文化类型的共性因素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就不仅可以在比较之中发现差异,而且也可以在比较中发现相同。当然,如此一来,上述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思考路径也就失效了。因为,我们完全不必基于中西文化绝对异质性这一前提预设来就中西文化比较的可能路径加以思考,相反,我们倒是可以基于中西文化作为古代或现代文化类型的相同来从事中西文化的比较。上述各种路径是从异出发,而我们可以从同出发。
二、明末清初第一次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
在从文化比较的一般原理层面对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一些问题做了澄清之后,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来审查上述那种将中西文化特殊化为两种绝对异质的地方性文化从而加以比较的思考路径形成的根源。简单来说,这是中西文化在接触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彼此时间上错位的结果。
在历史上,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碰撞与融合有三个大的时段。第一次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是在明末清初,它始自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进行文化交流,而终于1715年发生在康熙朝的“礼仪之争”。*张西平:《中国与西欧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28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第二次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是在清末民初,它始自鸦片战争前后,而由于特殊历史原因终止于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则是在当代,它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现在仍在发展过程中。
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明朝末年。当时,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西方所开启的地理大发现的总体历史格局下辗转来到中国,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但是,在与中国知识阶层亦即士大夫阶层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文化上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以文化交流的正常方式即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平等对话进行的,而且交流双方的文化都属于古代文化类型,从而在撇开了礼俗方面的一些基本差异之后,双方更多发现的是彼此之间文化上的相近和相通之处,而不是差别与抵触之处。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仍属于古代文化类型这一点无须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西方文化和来华进行西方文化传播的主体耶稣会士他们的文化身份。西方文化从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在文化观念上重新塑造了人与上帝、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但是,这是一个对西方社会来说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新的文化势力在增长,而旧的文化势力在社会上依然居于统治地位,只是通过发生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才根本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因此,16世纪随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并不就是一种现代文化,相反,它的古代色彩仍很鲜明,在主体上仍旧属于古代文化类型。而作为这一文化传播主体的耶稣会士在西方社会更是一个保守的宗教组织。它虽然是一个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新修士团体,但它并不是一个新教团体,而是一个天主教团体,是宗教改革运动中南欧天主教会改革的产物,其基本宗旨就是效忠教皇,并在传播基督教信仰上与新教竞争。*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192-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因此,在文化上,尽管耶稣会士不排斥自然科学、文学和伦理学等世俗学问,许多耶稣会士在这些方面还有精深造诣,但是,他们学术的基础却始终是神学和经院哲学,这也就决定了以他们为主体传播的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仍属于西方古代文化。
对此,我们只要大体了解一下由来华传教士译介过来的西方文化经典就可以明白了。例如,利玛窦除了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外,还取材西塞罗、塞涅卡和其他许多古典作家的道德著作,以中文形式写作了一部《交友论》(1595),并在翻译爱比克泰德道德格言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二十五言》(1605),其目的就是向中国士大夫阶层说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同等水平的文明、享有相似的文化观念。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其他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也纷纷效仿这一著作形式,在摘编西方古典作家文献的基础上写成了诸如《求友篇》《五十言余》《修身西学》《达道纪言》等著作。而除了这样一些属于伦理学性质的西方古典思想的译介外,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宇宙论方面的西方古典哲学著作也被陆续译介过来。例如,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同明朝学者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寰有诠》(1628),其中的第2~5卷是对亚里士多德《论天》的一个古代评注的翻译,而《名理探》(1631—1639)是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前分析篇》以及波菲利所写《导论》的翻译。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和徐光启所著的《灵言蠡勺》(1624)反映的是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思想,艾儒略(Giulio Aleni)的《性学觕述》(1624)则是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和《自然短论集》的一个综述。此外,高一志还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一起合作完成了《空际格致》(1633)一书,这是对亚里士多德《论天》、《论宇宙》以及《气象学》的一个编译。*Nicolas Standaert(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I.Leiden: Brill, 2001, pp.604-605, pp.606-608.只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才有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那部可谓总其大成的《穷理学》(1683)一著的编纂。这部著作共六十卷,分理推(Logica)、形性(Physica)、默大费西伽(Metaphysica)、马得马第加(Mathematica)、厄第加(Ethica)五个部分,将已有的耶稣会传教士所编译的著作分类编辑在一起。*梅谦立:《明末清初的西哲东渐》,载《西学东渐研究》第一辑,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显然,上述五个部分实际上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南怀仁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体系系统地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介绍给当时对西学颇有兴趣的康熙帝,以为天主教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建立较为牢固的知识基础。
一旦我们对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所绍介过来的西方文化典籍有了上述了解,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第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两种地方性古代文化的交流,它们在文化发展的时间性上基本上是对等和平行的,因此,双方在交流过程中经常能够发现彼此之间有许多相近和相通之处就不足为怪了。例如,针对儒家文化,利玛窦曾这样写道:“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他们古代哲学家的那些罕见的智慧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书仍然存在,上面满都是训导人们要有德行的最有益的忠告。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和我们自己最杰出的哲学家相匹敌。”“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利玛窦的上述文字是在他生命晚年私人所撰的《中国札记》中写的,该书以意大利文写成,原来的目的是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并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利玛窦、金尼阁:《中国札记》,31、100、104页,“中译者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3。也就是说,它并不像他的以中文撰写的书籍那样,目的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传播基督教,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其中有关儒家思想的说法是为了有意取悦中国文人*列文森即持有这样的看法,他没有意识到耶稣会士文化上保守的特征。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40-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而可以认为是利玛窦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真实看法。但我们由此却可以发现,其中鲜明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中西文化相通与相近的一面,而非差异与抵触的一面。
而作为平行的比较,我们也可以考察最初接触利玛窦撰写的中文书籍的一些明代知识分子的观感。这些人由于与利玛窦是一种宾主友好的关系,自然不会刻意通过发现书中一些相同的东西来讨好或取悦什么人,因而他们的观感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进行接触与交流的中西文化彼此的基本情况。例如,李之藻在为利玛窦《天主实义》一书所写的“天主实义重刻序”中这样说:“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至其检身事心,严翼匪懈,则世所谓皋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在这段话中,他针对西方科学而首先产生的“不类近儒”的感受当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儒家缺少的正是自然科学。但即便如此,李之藻也不认为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所没有的,因为中国古代当然也有自己的自然科学著作,所以他认为甚至这样一些东西也是“粹然不诡于正”。而接下来涉及西方的道德文明,他更是认为同儒家的追求没有区别,从而得出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结论。再如,徐光启在为利玛窦《二十五言》一书所写的“跋二十五言”中曾有这样的话:“闲尝反覆送难,以至杂语燕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100、13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这就是从儒家的道德教化出发考察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发现它们在基本的伦常观念上的一致。
明代部分知识分子在同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中之所以能够产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感,究其实质是由于这一时期进行交流的中西文化同属古代文化类型,它们在最基本的宇宙观、道德观上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当它们作为两种地方性文化相遇、交流时,在发现彼此由于风俗、信仰而来的文化差异之外,也能够发现彼此同属古代文化在宇宙观、道德观上的相通、相近之处。
三、第二次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特殊复杂性
西方文化第二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清末民初,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之始。但是,仔细分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明确在这一时期进行文化交流的双方各自所处的时代及在文化类型上的归属。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化仍然属于古代文化类型,这也是无疑义的。但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却已经经过近三百年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尤其是在文化上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基本上完成了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除了农、兵、机械等著作外,在思想文化上被绍介进来的主要还是西方古代经典,但到了戊戌维新之后,思想文化上大量传播的就是西方现代经典了。
例如,在这一时期交流的最初阶段,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鸦片战争后由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同李善兰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即所谓《续几何原本》(1857)。1865年,曾国藩将此书同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一起付印,由此中国知识界才得以一睹此书的全貌。此外,在伟烈亚力所主编的《六合丛谈》(1857—1858)杂志上,另一位来华传教士艾约瑟还撰写了一系列专门介绍西方古典文化的文章,如《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古罗马风俗礼教》《百拉多传》《和马传》等。*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0-191、2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也对西方古典学术思想做了初步的清理,其中首推王韬。王韬撰有《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西学图说》三本介绍西方学术的著作,并笔译了由伟烈亚力所口述的《西国天学源流》。在《西学原始考》和《西国天学源流》这两本著作中,他对古希腊的哲学史从泰勒斯到斯多亚学派都做了广泛地涉猎和介绍。戊戌变法失败后,西方的文化典籍更是以迅猛之势进入中国。当然,最初时候,它仍然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探求。所以,在1902—1904年之间,便有梁启超所著《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公猛所著《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王国维所著《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希腊圣人柏拉图传》《柏拉图之政治学说》等。*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142-143、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这些书籍的意义在于,它们已经不再是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迻译和绍介,而是带有主动研究的性质,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西方文化有了学术上的较为深入的了解。但是,毫无疑问,它们仍属西方的传统文化,亦即古代经典。
根本转变的标志是严复从1898年到1909年十年间翻译出来的那八本现代西方经典著作,它们分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名学》(1905),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这些著作广泛涉及了现代西方新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例如进化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它们在思想上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冲击,我们只需要提到《天演论》就可以明白了。正是在《天演论》中,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法则,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由所谓的“严译八大名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独由此而知西学之根底究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知有现代西方思想。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们的认识也逐渐超越了中西、体用的范式,而进至古今、新旧的范畴。以严复为例,他不仅在1902年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直接批评了“中体西用”论,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16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而且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一系列论文中还明确指出,中西之不同更多的是在文化的古今差异上。这一思路到了梁启超那里则被更进一步地落实在“新民”上,他认识到,在中西文化的近代碰撞与交流中,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中国文化顺应时代的自我更新和更生。所谓“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者也”*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四》,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省的意识。
但是,行文至此,我们也就必须对这一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复杂性加以说明。实际上,上文已经表明,在这一阶段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以西方现代思想为主,特别是在戊戌维新之后,大量西方现代思想论著被纷纷译介过来,我们接触到的实际上是所谓“新学”。但是,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仍旧是古代文化类型。这也就意味着,此时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根据仍旧是三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古代儒家文化,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文化比较在时间上的错位和不对称。像严复、梁启超等人只是由于曾经求学于海外,从而能够知道文化的新旧之分,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缺乏历史意识和时代观念的普遍思想背景下,所直观把握到的就仍旧是中西之别。而在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内部虽然从17世纪以来也经历了所谓的“古今之争”*1688年,法国学者Charles Perrault发表《古今比较》(Parallèle des et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是这一讨论的一个标志性著作。维柯1708发表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以及他的一系列演讲也集中了这一主题上的讨论。扩而言之,像培根的《伟大的复兴》、笛卡尔的《谈谈方法》等著作,都是开古今之争风气之先的著作。,也有旧学与新学之分,但是,要说这一时期接触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能够仔细分辨中国文化的类型归属,明确与之进行碰撞、交流的中国文化属于古代文化类型,显然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对于双方来说,由于这一时间上的错位和不对称,当简单而不加分辨地进行文化比较时,所发现的自然更多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且还是趋向于绝对异质性的差异。
此外,使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更加特殊复杂的还有双方交流的方式。在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特征,并且是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服务的,因此,双方的文化交流就不再像明清之际那样是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而是被很自然地置于了民族对抗、民族冲突的模式之中。
这样,我们就必须谈到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属于现代化的普遍问题。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形成民族国家统一国内市场,以此为母体进行全球扩张,建立以自己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实质。任何一个国家当它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现代化,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必然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于率先完成民族国家统一从而进入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国家如英国、法国来说,由于它们的民族国家统一体没有受到挑战,因而其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扩张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防御型的民族主义。但是,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由于它们的现代化是在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全球殖民扩张的冲击下应变、受激产生的,它们一方面要在被殖民、被侵略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这一现代化又要以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统一体为前提,因而其民族主义就会突出地表现为防御型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上也就会伴随地形成排外型的民族文化,以与自身现代民族国家统一体的构建相配合。这样,既要维新启蒙,又要救亡图存,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正是在这一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局中,以保守主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一条极其自然的文化必经之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跳出中西之别的地方性文化比较的藩篱,而立足于古今之争的属于人类历史的普遍思想范式来就中西文化进行考察,是那么的困难。
列文森已经指出了这一困难。他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尽管在整个儒家思想传统内部充满了争论,而且还是新与旧的争论,例如陆王心学之于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复兴又之于上述二者,但是,一旦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威胁,这种思想上的新与旧的争论就转变成了中与西的争论,也就是说,从“从思考时间到思考空间”。*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9-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艾恺则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困难不仅存在于中西文化之间,而且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整个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面对先发的现代化国家的强势挑战,在文化上总是存在着这一普遍的焦虑感和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过激反应。他在详尽地考察了随之而来的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文化上的反现代性思潮之后,得出了一个普遍的文化观点:“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由于现代化国家明显的军事与经济优越性,他们感到被迫做文化引借以保护(或强化)一个新兴的效忠与心理认同的焦点——民族国家。”*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90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一般地解释了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知识分子群体中所普遍具有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文化选择的历史与社会成因。这样,现代化和反现代化,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进步与保守,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纠结在一起,就造成了在中西文化比较上特殊复杂的情况,这个情况在今天并没有更多的改善。
四、在中西古代文化中发现同
在对中西文化比较常常陷入两种特殊地方性文化比较范式的历史成因做了上述分析和说明之后,我们将针对西方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就它们同属古代文化类型在一些基本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的一致和共同之处做一些举例说明和论证,以证明我们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不仅可以思考异,也可以发现同。而之所以选取中西古代文化而非中西现代文化来进行比较,一个原因是,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它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缘的,亦即是在应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中非自发产生的,人们往往会简单地将中国的现代文化等同于西化或西方文化的殖民,因此,在文化比较中就不认可把中国的现代文化拿来同西方现代文化作对比,而仍旧拘执于传统的文化比较模式,即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一方,而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另一方。鉴于此,一个破除上述思维误区的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古代文化来对比西方古代文化,这里既不会有文化殖民的问题,也不会有时代错位的问题,可以做到平心静气。
这样,我们将对向来被宣称构成中国文化独特性的三个基本思想观念在中西古代文化比较的背景下做一讨论,这就是天人合一、气、阴阳。
“天人合一”在总体上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它与现代哲学的主体性立场或人本主义立场的显著差别就在于,它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更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而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完满表达。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个主导思想倾向就是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最根本的特征。他们经常忽略了例如在荀子那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传统,而经常拿来进行对比的实际上是现代西方思想,例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以及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所宣扬的“改造自然”。同时,他们也忘记了“天人合一”实际上反映的是古代普遍的由于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薄弱,因而人从属于自然这一基本的社会生活状况。一旦我们认识到后一点,我们便可以发现,事实上在古代西方思想中也处处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想法。
以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为例,区别于现代技术中心主义,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技术模仿自然”*。他的名言“技术在一些方面完成自然不能够完成的事情,在一些方面模仿自然”*W.D.Ross.Aristotle’s Physics,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p.146,159.,其重点就是对技术加以限制,表明技术始终是在自然的范围内活动。而作为比较,我们只要稍微提到《中庸》中对人功的限定,即所谓“参赞天地之化育”,把人的作用限制在参与、协助天地完成自然之化育上,两者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就显明了,同时,也根本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斯多亚学派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按照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它们在基本的构成成分和运行法则上是一致的。整个宇宙是一个活生生的、处于运动之中的、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个特殊的个体都从属于这个整体,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宇宙论和形而上学层面上,人与自然是和谐的。而相应地在伦理学上,对于人来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合于自然的生活,自然构成了人的本性,而遵从这个本性生活,就是人的德性。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在《论人的本性》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合乎自然而生活”的伦理原则,而克里西普在《论目的》一书中则说:“有德性地生活等于根据自然的实际过程中的经验而生活。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的本性的一部分。因而目的就可定义为顺从自然而生活;换句话说,顺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以及宇宙的本性而生活。”*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VII,87,载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6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这样,“顺从自然而生活”就是斯多亚学派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而这与“天人合一”观念的一致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气的思想,人们公认中国拥有悠久的气论传统,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很早就已经从气一元论的角度来解释整个自然了。例如,《国语》中已经记载有根据阴阳二气变化对自然现象(地震)进行解释。《左传》则进一步讲到了六气的思想,将气的阴阳变化平衡理解为健康和疾病的根源。《国语》《左传》都是中国古代较早的文献资料,这充分证明气的宇宙论思想在中国发生时代之早。而这种思想在汉代同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气本论的宇宙论思想体系。这主要体现在《淮南子》和《论衡》中。《淮南子·本经训》说:“天地和合,阴阳陶化,万物,皆乘一气也。”王充在《论衡·谈天》中则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这种气本论的思想构成了汉唐以后中国古代宇宙论、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内核。而经过此后宋明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同理气二元论相关的一系列讨论,气不仅成为宇宙论的本体概念,而且成为形而上学的本体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道德现象和政治现象。我们看到,甚至到了清代王夫之、顾炎武、戴震那里,都有气本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引申。
而当研究者将中国古代的气论思想与肇始于古希腊的元素论思想相对比,尤其是将它与现代原子论思想相对比,一个很自然的看法就是,中西在对自然与宇宙的理解上是极其不同的,它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者是生机论的,一者是机械论的;一者是整体论的,一者是还原论的;一者是直觉的、活泼泼的,一者是分析的、僵死的,等等。但是,恰恰是在这里,比较者忽略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复杂性,而只是用一种单一的思想传统来理解西方的自然观,尤其是通过现代自然科学。他们普遍不了解元素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古典希腊时代的产物,而不属于早期希腊宇宙论的思想范式。只是在巴门尼德以后,由于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的发展,在巴门尼德存在概念的基础上,首先是在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那里元素论的思想发展起来了,然后在古典希腊时代的原子论学派那里,把世界和事物分析为原子和原子的结合与分离的思想才发展起来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聂敏里:《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68-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但是,在巴门尼德之前,并不存在元素论的思想范式,相反,在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美尼那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气本论的宇宙论体系。
例如,希波吕特记载阿那克西美尼的观点说:“阿那克西美尼……说无限的气是本原,从其中方生者、已成者、将在者、诸神和神圣者被生成,其余的东西从它的这些产物中被生成。”*在这里,气的本体论的地位是明确的。而气生成万物也不是像后来的元素或原子生成万物那样,是通过例如气的微粒的机械运动的结合与分离。在阿那克西美尼那里,气是对世界整体变化的经验性表达,气就是世界的原始形态,而气的流转、运行就是世界万物的生灭变化,就是我们可见世界的一切生动的、活泼泼的现象。因此,气生成万物的根本机制就不是元素的结合与分离,而是气本身的凝聚与疏散。希波吕特对此的记载是:“因为当它被凝聚和疏散时它就显得不同;因为一当它被分散为更稀疏的东西,火就被生成了,而反过来风就是凝聚的气,而从气中通过紧压云被产生出来,而再次当更凝聚时水就被产生出来,当被凝聚得更多时土就被产生出来,而当达到最大的凝聚时石头就被产生出来。”*G.S.基尔克、J.E.拉文、M.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218、218-21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在这里,凝聚和疏散机制的提出就表明气在阿那克西美尼那里根本不是元素,相反,它是世界的基本物质形态,而世界的万事万物、各种变化都可以归因于它变得更紧密一些或者更稀疏一些,也就是说,归因于气本身的变化。
当我们这样来理解阿那克西美尼的思想,它和中国古代气本论思想的一致性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中国古代在提出气是世界基本物质形态的基础上,同样讨论了气生成万物的机制问题,其中关键性的正是凝聚和疏散。例如,张载《正蒙·太和》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又说:“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结,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张载:《张载集》,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在这里,赫然在目的正是气的凝聚和疏散,而与阿那克西美尼思想更显一致的恰恰就是气凝聚生成风雨、雪霜、山川等自然万物。
以气的方式来看待宇宙,并且以此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这并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独有的,相反,它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具有悠久的传统。实际上,它是古人很素朴地看待自然的一种普遍的方式。把它特殊化为中国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思想传统悠久,另一方面则无疑是因为中西思想的比较者看待问题不全面、比较视角选取片面的缘故。
最后,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向来被视为中国古代宇宙观最独特的“阴—阳”概念。关于“阴—阳”,中西学者都一致同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是中国古人观察宇宙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李约瑟说:“在理论上,阴阳在自然界中是处于更深的一个层次,并且是古代中国人能够构想的最终原理。”*对此,中国学者自然是无异议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即便是李约瑟也发现,由“阴—阳”所展现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甚至在早期希腊哲学中也能找到。他提到了毕达戈拉斯学派的对立表,在这个表里,十对对立面被列在一张表里,例如,一与多、奇与偶、光明与黑暗等。但是,他武断地认为二者之间毫无关联。*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254、301-302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劳埃德基于他对中西古代思维方式的熟悉,曾经建议可以把“阴—阳”思想与早期希腊哲学中的对立面理论相对比,但他仍然坚持认为“阴—阳”是中国思想的一种独特模式。*G.E.R.Lloyd.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18-140.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事实上,正是他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学术论文《古希腊哲学中的热与冷、干与湿》*⑧ G.E.R.Lloyd.“The Hot and the Cold, the Dry and the Wet in Greek Philosophy”.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64(84):92-106.,为我们在中国古代宇宙论基于“阴—阳”的思想与早期希腊宇宙论基于“热—冷”的思想之间寻求内在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为了论述的简略,我们仅就古代有关阿那克西曼德思想的一段证言做些简单分析。
伪普鲁塔克《汇编》2曾记载阿那克西曼德的一个思想:“出于永恒的那热与冷的创生者在这个世界生成时被分离开来,并且一个出于它的火球包裹着环绕大地的空气被生成,就像树皮包裹着树一样;当它被破裂开来并被关闭进一些圈环中时,太阳、月亮和星辰便造成了。”*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阿那克西曼德构想了一个出于永恒的创生者,它在世界生成时被分离开来,而这个创生者之所以是创生者,不是首先在于世界从它生成,而是在于它是热与冷的创生者,热与冷是它创生整个世界的基本原则和物理机制。所以,在此基础上,从物理学的角度,阿那克西曼德就构想了一个世界实际被创生的过程:它是一个火包裹着气、而气包裹着大地的球体,这个球体破裂之后,便产生了日、月、星辰,它们是一些被包裹在气中的火。*G.S.基尔克、J.E.拉文、M.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196、20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这样,对于阿那克西曼德来说,热与冷构成了宇宙创生的基本原则和物理机制,正是热与冷的相互作用实际地产生了整个世界和世界万物。
假如我们把阿那克西曼德这里的思想同他的其他思想联系在一起,例如,埃修斯所记载的“阿那克西曼德说天由热与冷的混合物构成”*Hermann Diels,and Walther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cratiker.Erster Band.Berlin:Weidmann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60,p.86.(DK 12 A 17a),并进一步把这里的“热与冷”同“阴与阳”联系在一起,因为“阴与阳”所涵盖的最基本的一对对立面就是“热与冷”,那么,它与中国古代宇宙论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就显露出来了。至少,在《道德经·四十二章》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中,作为“一”的统一体,统一体中所内含的对立面——阴与阳,阴与阳的相互作用产生万物,万物的本质是阴气和阳气的平衡协调,所有这些思想要素显然和阿那克西曼德上述思想的基本内容存在着明显可比较的相似之处。
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早期希腊宇宙论中的这种热与冷、干与湿等对立面相互作用造成一切宇宙万物的思想在古代希腊医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果我们观察其中的一些思想会发现,它们和同样基于这些对立面相互作用的中医传统思想没有多少差别。例如,在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一篇医学文献《论人身上的部位》中有这样一段话:“疼痛是由冷、由热所造成的,是由二者的过多和过少。”而另一篇医学文献《论症状》也说:“在人身上,所有疾病都是由胆汁和黏液造成的。胆汁和黏液,当它们在身体中变得过干或过湿,过热或过冷,就引起了疾病。”⑧也就是说,身体中的冷热、干湿的平衡和这种平衡的被破坏是健康和疾病的原因。对于希波克拉底学派医学文献中所展现的这种思想,熟悉中医传统理论的人们难道不会多少产生一些似曾相识之感吗?
因此,甚至在“阴—阳”这种向来被视为中国古代独特思维方式的观念中,我们也能发现中西古代思想的一致性,因为这里的关键和重点不是中西,而是古代。在一种朴素、直观的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下,像“天人合一”、“气”、“阴—阳”等恰恰就是古人对世界的最基本的认识。在这里,“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所以,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上,我们不仅要重视异,也要重视同,既要学会在同中发现异,也要学会在异中发现同,关键是要把中西文化放到正确的时间参考系中来对比,并且始终坚信处于相同历史时代的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