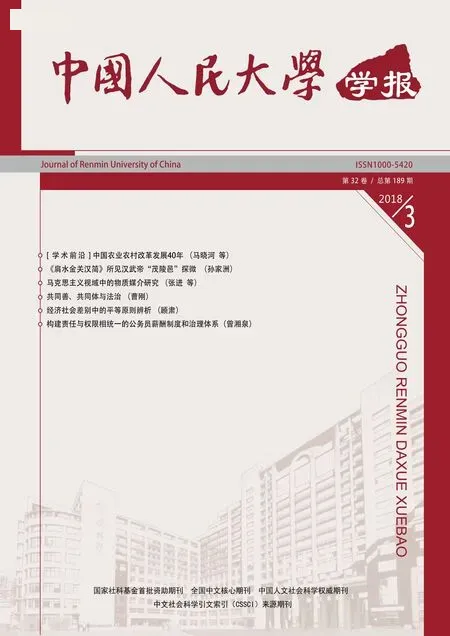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及其新动向与挑战
郭庆民
话语是一种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的社会实践表达方式。话语结构是被制度化、意识形态化、自然化的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反映并塑造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辩证关系,必然与其他理论发生联系,因此难免具有跨学科性质”*辛斌:《语言的建构性和话语的异质性》,载《现代外语》,2016(1)。。批评话语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向其他学科的渗透、融合和延伸。但是,其研究范围和领域的延展也向研究者提出诸多学术挑战。本文通过厘清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谈到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时,有时使用interdisciplinary(交叉学科的),有时则使用transdisciplinary(跨学科的),比如沃达克(Ruth Wodak)和约翰斯通(Barbara Johnstone)通常使用前者,而费尔克劳的话语研究属于后者。一般来说,transdisciplinary研究强调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融合,而interdisciplinary研究虽然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但研究还是在一个主体学科框架内进行。另外还有人使用multidisciplinary,它通常指各学科运用相关概念和方法研究同样的问题,但彼此保持独立性。由于这三个词经常在相关文献中混用,本文也不做细分。,评述其跨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及其挑战,并提出应对挑战的跨学科策略。
一、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两个交叉维度
根据沃达克的定义,批评话语分析或批评话语研究探讨“权力、身份政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变化或文化变革等方面的符号学维度”*R.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K.Hyland & B.Paltridge (eds.).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p.38.。它具有两方面的复杂性:一是它涵盖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二是社会符号形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研究范围的广度。再加上批评话语研究所借助的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使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谈到其源头,有人把它与功能语言学相联系,有人则认为它借助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而兴起。但是,无论把它看作是一种语言研究还是社会批评,学者们都不否认其跨学科性质。
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领域和应用的理论与方法决定的。如果给这种研究找出几个关键词,最重要的莫过于“话语”(或“语篇”)“语境”“社会实践”“权力”“意识形态”与“批评”。单独来看,每个概念都不专属于批评话语研究,但是,当把它们放入同一个体系并重新界定它们的含义与深层逻辑联系时,它们就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话语”是研究对象,它的使用自身带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被系统性地使用的语言才能被称作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代表研究的目的,其中“权力”决定着话语使用的方式,可以被看作是话语生产者导向的行为,反映话语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体系,代表话语使用的结果,更多地涉及话语接受者的行为,即话语的使用对话语接受者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批评”是研究视角或手段,指对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使用做出分析与解释,即“使用理性思维对一些论点和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提出质疑”*R.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K.Hyland & B.Paltridge (eds.).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p.40.。
在论证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时,韦斯(Gilbert Weiss)和沃达克提到五个方面的必然性:(1)社会身份和种族主义研究等都是复杂的社会新问题;(2)学科自身——包括大学教育也在走向融合;(3)新知识的建构需要突破单一学科带来的局限;(4)现代社会关系变得更复杂;(5)批评性思维需要新型知识以及新的知识组织方式。*G.Weiss & R.Wodak (ed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pp.19-20.他们借用了纳普(G.A.Knapp)和兰德韦尔(H.Landweer)1995年谈到女性主义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时总结出的五个特点。可见,它产生于客观需要。
那么,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约翰斯通认为,批评话语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甚至也不能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套系统的方法,研究的问题跨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甚至深入到其他领域。*她提到,在美国,大部分话语研究者不是语言学系的人,他们从事的是英语、人类学、文化、传媒、教育学、外语、修辞学、文艺批评、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法律等领域的研究。*B.Johnstone.Discourse Analysis.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2008,p.XIII、XV.
第二,相关理论的多源性。沃达克提到,批评话语研究的诞生与多个传统学科相联系,其中包括修辞学、语篇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用学。*R.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K.Hyland & B.Paltridge (eds.).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p.38.她使用“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杂糅”*来指称这个研究领域,她坚持认为,批评话语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并列出该领域共有的十个特征为其独立性辩护。*R.Wodak.“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J.Zienkowski, J.Östman & J.Verschueren (eds.).Discursive Pragmatics.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1,p.51,54-55.
第三,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其中包括话语和非话语的社会符号或者二者的结合物,而研究非语言的社会符号需要借助传播学、信息学、网络研究、艺术研究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
由于它跨越的学科众多,范戴克(Teun.A.van Dijk)等认为,“分析”(analysis)一词已经不足以涵盖它研究的各种话题和研究对象、借用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他们建议用“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代替“批评话语分析”,或简称“话语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想突出跨学科性,并提升其学科地位,让它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语言研究等取得同等地位。
无论怎样指称这个领域,从其发源和学科交叉状态来看,它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是语言研究的维度,二是其他学科知识的维度。无论是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的三维模式、 范戴克的社会认知方法和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还是其他话语研究传统,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上进行的。其中,对语言的分析是手段,在这个维度上,研究者主要对话语生产者使用的语言形式或表达的概念内容进行描述,这些描述可以是微观的用词层面,更多的是语篇和语类层面;也可以是各种语言修辞手段和其他符号的运用,在研究者看来,各层次语言特点的使用都具有符号学意义。相比之下,第二个维度是目的,即通过批评性分析,揭示藏匿在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披露话语生产者的社会政治意图,进而提出突破现行话语结构或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
两个维度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别。韦斯和沃达克列出三种跨学科模式:(1)累加型模式(additive model):把语言研究和其他研究领域叠加,比如拉波夫(William Labov)把复杂的语言学知识和静态的社会学变量结合;(2)折中的随机模式(eclectic ad hoc model):为研究的目的把语言研究和各种理论结合,不管其认识论根源和兼容性如何,比如把福柯、拉克劳、哈贝马斯的宏大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结合;(3)综合型/问题导向型模式(integrative/problem-oriented model):从研究的问题入手,应用各种方法和理论研究语言问题。*G.Weiss & R.Wodak (ed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pp.19-20.他们认为,自己的话语历史研究法属于此类研究。这类研究的关键,是对相关概念和方法做出重新界定,而且要在第二个维度上对核心文献的选择和相关理论的运用进行合理论证。但他们提到的交叉方式仍然不能反映话语研究的全貌。尽管研究者都把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相结合,但他们对二者的关注程度和方式不同。
二、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方式
对于两个维度的交叉方式,范戴克的区分更加合理。他提到两个研究传统:一个是语言学为导向的话语研究(linguistically oriented studies),另一个是社会科学的各种话语研究(variou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它们有各自的不足,“第一种研究经常忽视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有关权力滥用、不平等的概念和理论,而第二种研究很少从事具体的话语分析”*T.A.van Dijk.Discourse and Powe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p.99.。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把话语研究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也被称作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既关注吉(James Paul Gee)所说的“discourse”(即语言形式的具体使用),也关注“Discourse”(即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语结构)。*J.P.Gee.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pp.6-8.研究者认为,“语篇的一系列特征都被看作具有潜在的意识形态效果,包括词汇、隐喻、语法、预设和含意、礼貌习惯、语言交换(话轮)方式、语类结构和文体”*N.Fairclough.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1995,p.2.,还包括各种话语策略和修辞手段。他们多数有语言学背景,在修辞学、语篇语言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或语用学领域受过学术训练。
这些学科都研究语言在社会文化情景下的使用,但与批评话语研究在侧重点上存在重要区别:第一,批评话语研究是多学科交叉,而传统语言学科多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社会语言学主要是语言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第二,批评话语研究更具有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任何具体话语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下生成的,语境的变化造成话语参与者角色的转变,从而赋予话语不同的意义;二是社会结构不仅把话语制度化,而且受着话语的塑造。传统的语言研究更静态化,比如心理语言学研究各个年龄段语言的形成及其特点,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使用语言的特点。第三,批评话语研究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传统语言研究缺乏批评的维度*,话语研究者也分析语言的形式特征,但是这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语言结构、语篇结构和话语策略如何被用来表达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
鉴于以上提到的传统语言学分支已经涉及语言和其他符号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教育等领域的交叉,像费尔克劳、沃达克、范戴克、奇尔顿(Paul Chilton)、范莱文(Theo van Leeuwen)等一批长期从事话语研究的著名学者,重点研究的领域就是话语与符号如何反映和塑造各种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身份建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视角等社会现象。
第二类研究,不应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形式,主要关注吉所说的“Discourse”,即话语的系统使用方式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法国人主导的研究传统,代表人物包括福柯、阿尔都塞、佩舍(Michel Pêcheux)等。在他们看来,“话语是语言与意识形态的交汇处,话语分析就是对语言的使用进行意识形态维度的分析,话语是意识形态在语言中的物化”*R.Wodak.“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J.Zienkowski, J.Östman & J.Verschueren (eds.).Discursive Pragmatics.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1,p.65,63.。对福柯来说,话语本身既是被争夺的对象,也是开展斗争的场所,话语研究在于揭示藏匿在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其目的在于改变话语结构,打破它对思想的控制;这同时也是围绕合法性开展的斗争,这种合法性体现在谁有权力决定语言的使用,并进而决定在学术界和学校使用哪种话语体系。*虽然福柯等不从事具体的语言形式分析,但也会研究某些用词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倾向,考察它的起源、在历史过程中使用频率的变化、用词和指称上的演变、使用模式,因为这些都反映社会群体关系的变化和斗争过程。福柯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权力、知识、真理,跨越多个学科,以至于“很难把他具体称作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或批评理论家”*S.Mills.Discours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7,pp.42-46,16.。
第三类研究,重点分析话语所表达的概念和意识形态内容,是一种内容分析,而不是语言形式分析。研究者也谈论话语与权力,却更多地把话语看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福柯那样认为话语本身就是斗争的目标和场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话语权”,而不是话语霸权(hegemony)。聂筱谕把话语权定义为“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其世界观、价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传播于社会,并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影响力”*聂筱谕:《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基于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审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3)。。他认为话语权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而在乔根森(Marianne Jørgensen)和菲利普斯(Louise Phillips)看来,话语霸权指“每个代表谈论和理解社会的特定方式”为取得主导地位“彼此之间开展的持续斗争”*M.Jørgensen & L.Phillips.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p.7.。显然,他们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遵循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后者研究殖民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和话语结构的影响。张康之认为:“人们今天在谈论话语的问题时,基本上是在话语权的意义上使用‘话语’概念的,只有在严格的学术探讨的意义上才会将‘话语’与‘话语权’加以区分。”*运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对中国道路的怀疑”*张康之:《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建构》,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1)。。
三类研究可以互相借鉴,但是它们存在两个关键区别:一是话语研究与相关学科的结合程度和方式不同;二是他们对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及其关系的定义不同,如杨文星讨论了不同学术视野下“话语”的定义和使用方式。*杨文星:《“话语”在不同视角下的阐释》,载《理论月刊》,2016(9)。弄清三类研究的区别,既有助于明确批评话语研究的学科定位,也有助于研究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做的到底是哪一类交叉研究,并保持应有的学术谨慎。
三、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新动向及面临的挑战
从事外语研究的中国学者做的基本属于上述三类研究中的第一类研究。下面主要讨论这类研究的跨学科新动向及其挑战。这类研究多集中在话语体现的各种社会不平等,新的研究并没有脱离这个基本视角,但其跨学科领域和方法有所拓展。我们主要围绕沃达克提到的六个新动向*R.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K.Hyland & B.Paltridge (eds.).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p.41.进行讨论和评述。
第一,研究知识型经济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其中包括知识型经济向其他国家和社会领域的转移。这实际上是对费尔克劳研究方向的延伸。费尔克劳认为:“现代社会是‘基于知识’的或‘知识驱动’的社会……在当代社会经济的变化中,语言比以往起着更显著的作用”*转引自L.Young & B.Fitzgerald.The Power of Language: How Discourse Influences Society.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6,p.7.。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社会福利国家向市场驱动型国家的转变,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球体系内取得霸权地位。费尔克劳一直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如何重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致使经济领域对政治和社会领域进行“殖民化”。经济话语侵入学校、医院等非经济的社会领域,结果大学教师变成“具有开创精神和自我推销的知识工人”,比如他们在描述自己时会使用team objectives(团队目标),business effectiveness(业务高效),business enhancement(业务增强),maintenance of customer-focus(坚持以顾客为中心,这里“顾客”指学生),而这些都是典型的管理学话语。*A.Mayr.“Institutional Discourse”.In D.Tannen, H.E.Hamilton & D.Schiffrin (eds.).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Second Edition.Vol.II.Malden and Oxford: Wiley Blackwell,2015,p.767.显然,要鉴别出这类话语,研究者不仅需要语言分析能力,还要熟悉管理学的概念,甚至熟悉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
第二,把认知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话语研究,这不仅需要新的研究工具,而且需要在认识论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这是对范戴克等的社会认知研究的延伸,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认识是如何通过话语转变成社会共识的。为了研究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搞清楚语言与社会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范戴克指出,“话语结构与区域和全球社会语境之间的结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现在只停留在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探讨上*;即研究话语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揭露社会歧视行为,更重要的是揭示话语控制心智、塑造社会信念和态度的方式,因为一旦形成这样的信念体系和认知模式,就会产生系统性的、持续的歧视行为。*T.A.van Dijk.Discourse and Powe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p.99,106.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学者可以探索如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实现认识论上的转变,为话语研究带来创新。
第三,新媒体和区域与全球新形势正在改变人们的政治生活,其中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活中的“去政治化”现象特别值得研究。政治家可以通过网络“聊天”这种非正式的话语形式完成意识形态的灌输。政治和专业知识的权威在表面上被消解,使政治话语更容易被自然化。这些变化“对话语分析者看待语篇和社会交往、甚至看待语言自身性质的方式提出了诸多挑战”*R.H.Jones, A.Chik & C.A.Hafner (eds.).Discourse and Digital Practices: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Digital Ag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5,p.1.,其中包括:(1)网络社交的多模态化使基于口头和笔头语篇分析而形成的传统话语研究方法受到挑战;(2)网站上存在大量无法追溯来源或来源混杂的语篇,这给研究话语参与者和语篇间性*指intertextuality,周流溪教授对“语篇间性”和“互文性”做了辨析。参见周流溪:《互文与“互文性”》,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造成严重困难;(3)这种混杂性特点造成话语权力的分散,使研究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关系更加困难;(4)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过程及效果变得更复杂、更微妙、更难测量;(5)语境变得更复杂,话语参与者游离于线上和线下语境,且跨越时空谈论同一个话题。李桔元等提到,批评话语研究在研究途径和方法、多样化理论基础上的开放性,本来就“导致其核心概念长期以来缺乏统一、合理的界定”*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载《外国语》,2014(4)。。人类社交方式的改变使这一状况变得更复杂,研究者需要对“话语”“权力”“意识形态”“语境”等与政治领域相关的核心概念及其表现形式进行重新认识。
第四,研究多媒体和新语类带来的影响。网络语篇经常是由语言、图像、视频、音频、表情等各类符号元素构成的多媒体、多模态混合体,在其中,语言甚至不再占主导地位。范莱文指出,由于某些多模态语篇在设计时具有层次性,某些元素被突出、被前景化,读者甚至都不需要按照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线性方式阅读,从而形成了新的语类结构。*T.van Leeuwen.“Multimodality”.In D.Tannen, H.E.Hamilton & D.Schiffrin (eds.).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Second Edition.Vol.I.Malden and Oxford: Wiley Blackwell,2015,p.457.琼斯(Rodney Jones)等指出,与借助衔接手段组织起来的传统语篇不同,很多网络语篇表面上看起来结构松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连贯性差。*R.H.Jones, A.Chik & C.A.Hafner (eds.).Discourse and Digital Practices: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Digital Ag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5,p.6.虽然如此,分析这样的“松散结构”语篇,需要沃达克所说的“新的多模态理论和方法”。而且,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是跨学科的。范莱文指出,多模态研究不仅需要借用话语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还要从其他相关学科汲取灵感,比如艺术和设计理论”*T.van Leeuwen.“Multimodality”.In D.Tannen, H.E.Hamilton & D.Schiffrin (eds.).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Second Edition.Vol.I.Malden and Oxford: Wiley Blackwell.2015,p.447.。而究竟应该借用哪些学科的哪些概念和方法,他认为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五,研究话语结构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过程,预测话语的未来走向。这实际上是沃达克等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延伸,他们起初用这种方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反犹主义话语。他们认为,研究这类话语必须分析其历史形成过程,强调各类语境对它们的塑造作用。最近几年,随着右翼势力在法国、奥地利、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崛起,各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纳粹主义等歧视性话语也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和《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等批评话语研究的主流杂志发表了很多涉及此类话题的文章。“语篇间性”“话语间性”(interdiscursivity)“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等成为核心概念*R.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K.Hyland & B.Paltridge (eds.).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p.41.,使系统地运用跨学科的话语历史方法显得更加重要。
第六,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数据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克服研究的随机性(cherry-picking),使研究过程变得可追溯(retroductable),分析结果可验证。沃达克这里所说的“随机性”,主要指生硬地套用某种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一些话语实例。批评话语分析经常被指缺乏明晰性、客观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克服方法论上的这些缺陷也要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四、应对挑战的跨学科策略
既然话语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应对学术挑战的策略也应该是跨学科的,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适应话语使用方式的变化,加强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力度。扬(Lynne Young)和菲茨杰拉德(Brigid Fitzgerald)总结出四个话语变化趋势:专业技术化、会话化、市场化和全球化。*L.Young & B.Fitzgerald.The Power of Language: How Discourse Influences Society.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6,pp.261-264.专业技术化指技术和专业语言进入社会政策,专业化词汇和名物化结构的使用令公共话语听起来多了一些专业性和合法性,少了一些主观价值,但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会话化走向反面,使话语带上非正式的个人色彩,更容易在无意识中完成意识形态灌输,如政治家的网络“聊天”。市场化指借用商品交换的话语来谈论教育和政治等非经济领域的话题,结果使正常的社会沟通变成类似广告推销。全球化的话语更强调一些所谓“普世价值”,如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强调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依赖和一体化,热衷全球化的人用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语气,极力把它描述为“不可逆转的”“没有其他选择的”“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淡化全球化趋势对地方经济和文化特色造成的破坏。
这些趋势不仅需要研究者重新认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传导方式,而且需要拓展自己的跨学科知识。要分析更加专业化的语言,必须具有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要分析会话化的语言特点,应该掌握语用学或会话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要分析市场化的语言,需要懂得一些营销学和广告学的知识和策略;要分析全球化的语言,需要知道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应用。否则,在“批评的”层面就难以从理论上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严谨的结论。
第二,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克服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约翰斯通对话语分析的定义强调了它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性质。从方法论上来看,沃达克的话语历史研究法、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模式和范戴克的社会认知研究法,都仅仅是“途径”(approach),而不是“方法”(method)。可喜的是,研究者已经在使用各种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汇语法分析、逻辑语义分析、语篇结构分析、语料库、语言统计、语言认知实验等方法,试图对话语的结构、功能、心理认知过程进行形式化和量化的分析。但是它们多数涉及“(容易量化的)词汇层面分析”*T.A.van Dijk.Discourse and Powe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p.96.,而不是宏观的语篇层面,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更是局限于主观判断和归纳。
面对跨学科的研究,沃达克主张应该根据不同的话题和研究对象借鉴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田海龙也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是兼收并蓄的,依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所观察的语料而定,没有固定的模式”*田海龙:《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2)。。这提醒我们,在跨越不同学科时,除了相关领域的知识外,我们还应该清楚这些学科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比如在研究对语篇和其他符号的认知时,我们也可以采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使用各种认知和心理测验仪器,来克服访谈和调查表研究的缺陷——比如被调查者可能回避一些话题或言不由衷。另外,“如何在多模态研究领域建立学科融合是多模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李战子、陆丹云:《多模态符号学:理论基础,研究途径与发展前景》,载《外语研究》,2012(2)。,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助研究艺术和传媒的方法实现创新。
第三,要把握前沿课题,但也要在进入不熟悉的跨学科领域时保持学术谨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虽然我们能解读日常话语的意义,但是,知识分子和学者高度专业化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来解释的权威性问题”*J.Angermuller.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 Subjectivity in Enunciative Pragmatics.UK: Palgrave Macmillan.2014,p.55.。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公认的“解释的权威性”(interpretive authority)只可能产生于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博学广闻,能自由徜徉于多个学科,比如福柯;二是虽然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是语言研究,但通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已经对语言之外的相关学科领域相当熟悉。像沃达克长期研究欧洲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关心欧盟内部的政治格局变化;范莱文是媒体与传媒学教授,还是《视觉传媒》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他对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和视觉符号有深入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这些专家才能搞跨学科研究,只是说在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研究者应该对研究的切入点保持学术上的警觉。比如,研究医学话语时,可以通过分析病人与医护人员和亲属等的会话,研究病人对“病人”“医生”“生病”等的概念如何被塑造,因为这是有语言学背景的人通过学习一些基本医学知识能驾轻就熟的研究。但是,如果将研究扩展到美国的医疗体制和医疗队伍在管理病人上使用的话语,就要对美国的医疗体制,比如美国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可支付医疗选择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又称作Obamacare),甚至包括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极力推翻Obamacare等相当熟悉。*T.Halkowski.“Medical Discourse”.In K.Hyland & B.Paltridge (eds.).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pp.321-331.
第四,寻求相关领域专家的合作,使研究过程真正体现跨学科性质。这无疑是跨学科研究的最理想模式。比如韦斯和沃达克提到,他们在研究失业和就业政策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参与其中。*G.Weiss & R.Wodak (ed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pp.20-21.合作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知识交流的过程,语言学家要学习跨文化交际和社会学理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要了解语言学和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经济学顾问和国际问题专家也被邀请参加相关讨论或举办讲座。研究宏大的前沿问题更需要这样做。吴鹏等提到,由于目前“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占主导地位……跨学科合作就成了问题导向型话语研究的必然选择”*吴鹏、王海啸:《当代西方话语研究述评与本土化反思》,载《现代外语》,2014(2)。。沃达克等近期在研究欧盟组织内的身份政治与决策模式,作为语言专家的他们与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合作,提出了一些模型,用来解释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欧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关系。他们收集的语料包括采访、政策文献、政治演讲、媒体报道、欧盟官员的内部观点*R.Wodak.“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J.Zienkowski, J.Östman & J.Verschueren (eds.).Discursive Pragmatics.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1,p.62.,等等。可以设想,这样的研究能够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五、结语
应该承认,国内的话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很少像沃达克那样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分工合作,这显然与其跨学科性质不相称。这也是国内学者难以产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其政治经济大国地位不相称,这种“失语”状态正在伤害我们的民族自信和自尊。杨光斌指出:“对自己的‘硬成就’如果没有相应的概念、理论、观念去建构,就会依然用基于异域的理论甚至意识形态来‘关照’中国,结果必然失去心理上的优势。”*杨光斌:《如何更客观地认识中国政治:世界大历史维度与国际大空间视野》,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1)。他认为,用早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去看待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西方中心论下的中国政治。他提升到认识论上来分析这一问题,指出:“中国不应该是‘观念世界’的理论试验场,而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杨光斌:《如何更客观地认识中国政治:世界大历史维度与国际大空间视野》,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1)。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多次提到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他指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8。。这一重要讲话启示我们,对话语的研究在中国大有可为,而这需要研究者增强民族自信,开拓跨学科的视野,掌握跨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去创造高质量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