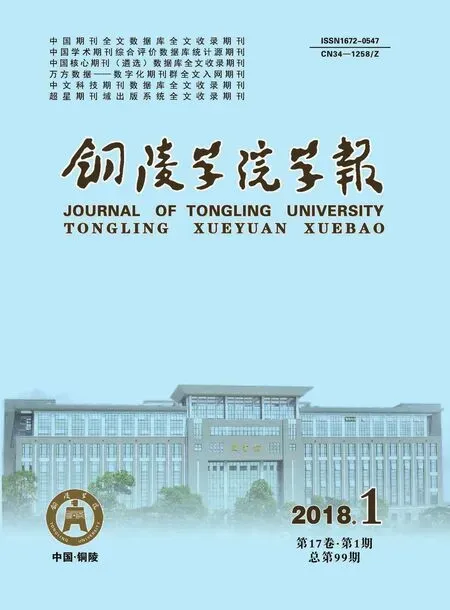中小城市空间形态设计中的地域文化反思
——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孙洪伟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近年来,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一些中小型城市也迈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当各地城市的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事实上就意味着城市间竞争的开始,包括经济、文化的竞争,以及资源、人才的竞争。北上广这类一线城市,因其巨大的城市体量,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对于二三线的中小型城市来说,要想竞争剩余不多的资源和人才,只能不断的提升自身竞争力。其中,城市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就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城市空间的发展。布局规划合理的城市空间,能够极大的便利城市生活,同时也会积极地提升城市形象。然而,在一个日趋均质化的时代,如何在升级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能保持与众不同的城市形象呢?地域文化的介入,开始成为一个普遍选项。大致来说,几乎每个城市都分属不同的地域文化,并且或多或少都接受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对于一个希望通过差异化设计去实现竞争优势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工具。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总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的案例分析,探讨一些相对普遍且典型的问题,以备参考。
一、城市与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是各类建筑物共同组成的城市。城市中的所有建筑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特定需求而存在,如住宅、商铺、行政机构,甚至街道、广场等。这些建筑物因功能的区别而形态各异,共同描绘了城市的基本面貌。然而,对人来说,建筑物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建筑物而获得的各类空间——封闭或开放的空间。因此,我们所谓的城市空间形态,首先是指由各类建筑物的形体所直接呈现的城市形态;其次,是由建筑物所分隔出的各类城市空间,这种空间以某种可见、可感的形式存在,也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与阳,前者是城市的阳形,而后者是城市的阴形,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往往受两大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和建筑物因素。具体来说,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包括山体、地势、水体、气温、降水等因素;建筑物因素主要是指构成一座城市的所有建筑及设施,大致可分为城市的平面布局、街道网络体系、街区与公共空间、公共及住宅类建筑[1]。抛开人为因素,城市空间形态中的自然因素几乎是静止的。然而,城市中的建筑物则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城市的空间形态接受自然因素和建筑物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是前者是常量而后者是变量,后者在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城市中建筑物变化的根源在于人,在于人需求的多样化及易变性。马斯洛心理学认为人的需求大致分为两大类:生理性需求与社会性需求。最早的建筑,就是为满足人生理与安全的需求而出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也在社会化。相应而来的,是建筑设计的社会化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建筑类型的分化(如住宅、宗教、商业、官署等建筑),不同的建筑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其次,是建筑形制的分化(如建筑的高度、开间的数量、屋顶的形制等),即使是同类型的建筑,也会因不同形制而有等级之分;另外,各种建筑及建筑空间集合体——城市的出现,也是建筑设计社会化发展的直接体现。并且,作为多样化的空间集合体,城市是成熟社会的物质载体。正是由于城市的存在,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才有实现的物质空间。城市与社会的结合,也使城市及空间设计能够摆脱纯粹的物质形态,从而进入文化领域。
无论是作为物质形态的城市空间,还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城市空间,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接受地域的塑造和影响。首先,任何一座城市,都是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城市。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地理特征,这是城市空间形态设计的物质基础,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在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地域与文化往往会有微妙的互动,从而形成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对于城市空间形态的要求,又经常展示出不同的态度。
二、城市空间设计与地域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城市形象问题开始备受关注。千城一面的城市空间设计导致城市特色、文化的缺失,受到广泛批评。作为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城市空间形态设计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对于很多中小型城市来说,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去彰显城市空间设计,开始逐渐成为热门选项之一。
然而,何谓“地域文化”?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半世纪之前,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就曾提出类似的概念——文明的地域体系[2]。近年来,地域文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备受关注,学界也多有探讨[3-5]。
城市空间设计与地域文化之间存在天然关系,两者的结合是顺其自然的结果。然而,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却是近年之事[6-7]。本文无意执着于复杂的概念,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概括来说,“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的,且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地理空间有大小、广狭之分,并不是所有的地理空间内都会产生对应的地域文化。除了地理因素外,历史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才会产生特定地域文化,如楚文化、齐鲁文化、吴文化、皖江文化等都是如此。这些文化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会逐渐辐射至一片广大的区域。在这片区域中,还会存在各种亚区域文化。另外,地域文化具有相对性。在对比条件下,地域文化的特殊价值才会凸显。对于中小城市的空间设计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类城市,大多属于大型区域文化内(如楚文化、皖江文化等)的亚地域文化,之所以关注于城市空间设计,更多的是出于竞争的目的,尤其是与周边同类型城市的竞争,文化的竞争、经济的竞争,甚至人力资源的竞争。城市自身的地域文化(亚地域文化)为城市间的竞争提供了直观的参照,也为城市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城市空间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大致涉及三个层面:首先,城市自然条件层面,主要涉及地理、气候条件与城市空间设计的关系。任何城市都处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空间设计首先要考虑城市的地理特征,根据地形地貌合理的设计。大致来说,位于山地、丘陵地区的城市地势多起伏,城市空间中建筑物的纵向尺度与组合需要更多的考虑地形因素;而平原地区的城市则相对自由,更多的考虑建筑物自身的空间需求。同样,湖泊水系众多的城市,需要对平面空间进行合理分割,使建筑物与水系互相匹配,以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转;而水系较少的干旱地区则无需担心这类问题。
其次,城市历史层面,主要涉及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沿革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一座城市的历史,首先是关于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城市历史,是被特定地域文化所塑造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地域文化在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所遗留的历史印记。这种历史印记,可以是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如区域、道路、水系的规划;也可以是城市空间中的某些重要历史元素,如重要的历史建筑物,甚至是建筑物所普遍使用的材料、颜色等。这都是城市空间中可见可感的物质性元素,直接塑造着一座城市的外貌。
另外,城市生活层面,主要涉及地域性城市生活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与影响。城市生活与地域文化有紧密的关系,生活的内容、形式都接受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甚至塑造,是地域文化的直接呈现。这首先是因为城市生活强烈的物质属性,城市生活要满足居民的各种物质需求,如衣食住行等。这些物质需求的满足又与城市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如水土肥美之地生活多求安逸,而水陆交通便利之地则生活多讲利益。城市是满足人各类需求的城市,不同的需求必然决定了城市空间设计中的差别。这种差别有时会以显性的姿态呈现,如城市的规划,建筑物的遗存等;更多的时候则是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存在,如生活的便利性,城市的认同感等。
三、铜陵城市空间设计的文化反思
铜陵市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下游,是皖南城市中面积最小却又极具特色的城市。从地理位置来看,铜陵属于典型的皖南城市,地貌起伏多山,丘陵纵横交结,且全年气候温暖湿润。
皖南诸城中,以徽州(黄山市)、宣州(宣城市)和芜湖最为知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皖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城市的声誉和地位,是与其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其中,商业的成功及商业文化的繁荣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铜陵的历史却截然不同。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铜矿资源聚集区,这里的历史始终都与铜矿紧密相关。众所周知,重要的矿产资源历来都是被政府垄断,这在铜矿资源的管理中尤为突出①。事实上,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矿区,历史上的铜陵并没有因此获益,反而却因采矿而忽视了其它领域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都直接导致铜陵虽位于长江南岸,但是其发展轨迹却与安徽的江南诸城判然不同,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工矿业文化。
工矿业文化是铜陵地域文化的基本因素,事实上已经深入到城市空间的方方面面。只是随着近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扩张,原有的城市空间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于是铜陵市也出现了“拆、挖、建”,这一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的城市扩建现象。客观的说,拆与挖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如何建设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于是,地域文化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
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如何将两者完美的融合,并不容易。在铜陵近年的城市空间建设中,可以很好的诠释这一点。并且,铜陵城建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在同类城市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城市空间的改扩建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城市本身的地理特点。
从城市的纵向尺度来说,铜陵市区多山,且多位于中心位置,螺狮山、笔架山、板栗山均如此。一般来说,在山体周围建设,要考虑建筑物与山体的关系,其中建筑物的高度是重点考量之一。
在铜陵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之前,山体周围都已建有建筑物,如公园、居民小区等。客观来说,原有建筑物中,公园大致是经过规划的;但是公园周边居民区的建设却未必如此②。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是历史遗留的既成事实,我们无法改变,甚至也无需改变,因为这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这些建筑物大多高度有限,一般都是五层楼,所以从纵向尺度来说对山体的影响不大。我们大致能够想象当时铜陵城市空间的基本面貌——在高低错落的山体之间,城市建筑群依次展开。当时城市天际线的主体,也必然是山体所勾画的轮廓,建筑物坐落其间。然而经过几年大规模城市改造之后,我们讶异的发现,山体“消失”了。尤其是身处城市之中的时候,原本举目所及的景观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建筑物。
从平面空间来看,目前铜陵的城市空间大致分为两部分:以长江路为核心的区域和以天井湖为核心的区域。天井湖的存在,使得这一区域的平面空间得以自然分割,建筑物的组合大致依照湖岸的走势而展开,形成良好的城市景观。然而在另一片区域中,问题则严峻的多。这里是城市最繁华的地段,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商铺、学校和住宅。这是一片拥堵的区域。我们相信在任何城市中,都有这样的区域,都会面临空间规划问题。越是拥堵的地方,越是需要精心的设计。然而,当你站在高点俯视这片区域的时候,你会发现密密麻麻全是房子,或高或矮、或新或旧。除了拥堵不堪的道路外,几乎看不出这里的地貌特征,一切都被建筑物所覆盖。设计在此已无立锥之地。
虽然各方都在强调城市特色、地域文化,但是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作为城市特色和地域文化基础的地理信息却被忽视、抹杀。其结果,就是原本由湖光与山色共同组成的城市自然景观的消失。如果说城市(尤其是市中心)建筑物密度和高度的增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城市发展与城市地理特征的保存之间,也一定能够取得某种平衡。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重点在于城市的规划者一定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从制度上对城市的新修建筑物予以规范。
其次,在城市空间的改造中,城市历史是地域文化的最佳切入点,也是最大的陷阱。
明代时,曾筑铜陵县城池,“初无城。明万历三年,兵备副使冯叔吉、知县姜天衢筑。周围七百丈,高二丈一尺,门四。”[8]然而时间久远,历史上的城池早已荡然无存。现有的城市建筑及空间,基本上是解放后逐渐形成的③。这使我们对这座城市地域文化历史的追溯失去了物质基础,所以只能将思路转向抽象层面,如符号、色彩、材料。对于城市空间的改造来说,这最容易操作,如风火山墙、白墙黑瓦,已经成为徽派、江南建筑的典型符号与色彩。但是,这同时又是最大的陷阱。正因为易操作及典型,所以也容易流于形式,陷于僵化的困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普遍流行的“大屋顶”式建筑,就是典型案例。
对铜陵来说,绵延数千年的工矿文化,开始成为城市空间改造的最佳诉求对象。身处铜陵,你会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出入城市的门户(火车站、城市入口等),还是城市的地标,抑或是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公园、博物馆、公交站台等),你都会发现“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以铜为材料的雕塑,到与铜相关的各种历史符号;从历史器皿的放大复制,到采矿历史的形象化复述;从铜圆雕,到铜浮雕,甚至还有一座专门为铜雕准备的公园——翠湖公园(国际铜雕园)。“铜”在这座城市的空间中已无处不在,但是作为金属材料的“铜”却消失了。充斥在这座城市中的,只是一个个与铜相关的符号,一个个内容(物理属性)被抽空,却又被大量复制且诉诸于感官刺激的符号。
难道这就是铜陵的地域文化,其历史只能以如此方式如此“现身”?事实上,当这座城市(包括大多数同类型城市)的历史被抽象为某一(且唯一)具体符号的时候,它已经深陷关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陷阱。铜陵“最大”的历史,确实是“铜”,是关于铜的采掘、冶炼的历史,是关于在此过程中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也是关于这座城市中生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是真实而丰富的历史而非各种符号拼贴的历史。
那么,历史存在于何处呢?这是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一般语境中,一旦涉及到“历史”问题,潜意识中我们就会自动将其转化为一个“久远而又辉煌年代”的问题。但是当这个“久远而又辉煌年代”无迹可寻的时候,我们又会陷于迷茫。对城市历史的符号拼凑,就是处于迷茫状态的无奈之举。
殊不知,昨日即历史,真正历史存在于每一个平凡的日日夜夜中。千年前的城池无迹可寻,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城市却依然存在。我们对一座城市空间历史的追寻,也未必一定是对其“久远而又辉煌年代”的追寻。对铜陵来说,解放后逐渐形成的城市空间,是一个更具价值的研究对象。那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工矿企业的厂房、职工宿舍,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历史。那些由铜陵有色金属集团④投资规划、修建的街道、景观,才是这座城市地域文化的真实形态。舍近求远,只是出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历史想象。拆除、重建,只会抹除这座城市真正的历史。最终的结果,只会形成历史符号的大杂烩,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另外,在任何城市中,生活的需要是空间改造的原动力。而地域文化与城市生活的天然关系,又使其成为城市空间改造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讽刺的是,这通常也会使地域文化陷于又一个困境,面临严重的反噬危机。
铜陵是一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解放后,为了支援铜工业的发展,一些技术骨干被迁移到这里,并逐渐形成一个产业中心。快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然而本地人口有限,于是各地的移民逐渐成为这座城市中重要群体。时至今日,这种本地人数量少,而移民数量多的人口结构依然没有改变。一般来说,移民多的城市,其生活会更加多元化。然而铜陵是个例外。首先,铜陵的城市空间实在是太小,没有为多元化留下充足的空间;其次,这些多元化的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成为产业工人。因此,这是一座充满了工人生活气息的城市。这一点,通过这座城市中的很多地名都能发现,如工人新村(小区)、铜化新村(小区)、工人医院(现市立医院)、井巷新村(小区)等。这些都是这座城市地域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呈现,也是关于这座城市地域文化的鲜活记忆。
然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随着各商业性地产项目的开发,更随着历任政府市政政策的不断调整,最终我们悲哀的发现:道路越来越宽、楼房越来越高、公园越来越新,但铜陵与其它城市的相似度也越来越大。这就像“南辕北辙”故事,一方面我们无比虔诚的相信,地域文化能够使这座城市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真诚的亲手将其葬送。这在城市交通系统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铁路运输无疑曾经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原材料的输入与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铁路。然而,对铜陵人来说,铁路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在那个逐渐远去的年代,在每一个在雾气弥漫的清晨,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在呜呜作响的汽笛声中,701厂⑤的工人曾经成群结队的登上小火车,神气活现地穿越城市边缘,驶向群山深处的工厂。这是其它城市难得一见的景观,却曾经是铜陵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至今日,铁路犹在,曾经的盛况却早已不见,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抱怨和投诉。其原因在于,原本蜿蜒在城市边缘的铁路线,已经被各大住宅小区所吞噬。日夜不停货运列车穿梭于居民楼下,无疑会对周围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噪音污染。然而,居民的投诉与抱怨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因为建好的铁路不会轻易拆除,其管辖权也不属于铜陵。
铁路还是那条铁路,人还是那群人,是什么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如此窘境呢?根源无疑不在于铁路,也不在于人,而在于城市空间的不合理扩展。任何城市都需要发展,然而发展首先要考虑城市生活的现实需求。在新建小区的规划审批过程中,不考虑已有的空间划分(铁路),不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噪音),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城市的地域特征被吞噬,居民的正常生活被干扰。
如果说铁路的例子不具有普遍性意义。那么在新建小区、新修道路名称命名的随意性中,我们发现了更加典型的例子。经济开发区是铜陵城市空间向外拓展的代表性区域,周边聚集了大量新建小区和城市人口,同样也规划建设了笔直宽阔的街道。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从地图上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跟铜陵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恒大绿洲(小区)、万泰水晶城(小区)、五环国际(小区)等时髦洋气的名称。如果说这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自由,是市场行为,政府无权干涉。那么,穿插在这些小区周围的街道更让人瞠目结舌,东西走向的是翠湖一路、翠湖二路……翠湖六路,南北走向的是泰山大道、华山大道……衡山大道。这种命名方式,最大优点就是方便记忆。然而,在我们瞬间记住这些街道的同时,也会瞬间忘记自己身处何方。我相信,这样的故事绝不会只发生在铜陵这座城市中。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对每一座急需空间改造的城市来说,地域文化的介入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很多城市已经将其付诸于实践。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才发现最终的成果与最初的意愿背道而驰,铜陵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是一个相对固定且稳定的空间,其形成、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然而,对当代的中国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一切都在急速变化。慢,似乎成为一种罪过。各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将城市裹挟进入快车道,城市空间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同时,城市又是一个复杂综合体,其发展不能无目标、无规划。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总要有一个目的地。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个写着地名的指示牌,但是这块带字的小铁皮却为这辆车指明前进的方向。地域文化就是那块小铁皮。在很多城市的空间改造中,都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告诉自己,更重要的是告诉公众:看,这就是我们的方向!然而,就如同铁皮上的地名,尽管可能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但若你从未去过,那么它也仅仅是个地名而已。地域文化究竟是什么,很多城市的规划者并没有真正了解,甚至根本就不关心。因为它只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被信手拈来的一个符号,听起来很熟悉,看起来很诱人。
于是在人声鼎沸中,一座座城市迅速的旧貌换新颜,并且迫不及待的宣告地域文化的降临。城市中的居民也翘首以待,迎接崭新的城市。然而,感官的刺激会迅速消退。短暂的热情之后,恢复理性的公众也会迅速的发现,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内,他们的城市早已是狼藉一片。
无论如何,城市还将是那座城市。就像铜陵那条早已“不合时宜”的货运铁路,无论你是爱是恨,它将长久的横亘在那里。而我们的生活,也始终在某座城市中展开,无论是好是坏。
注释:
①作为战略性金属,铜矿的采掘和冶炼一直都为官府垄断。这主要是与铜在中国历史上的用途有关:先秦时期,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礼器制作的主要材料;秦代之后,铜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制作货币的主要材料。
②此类居民区中,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工矿企业自行建设的家属楼。在其建设过程中,更多是考虑解决职工们的居住问题,而无力关注其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③在这一点上,以铜陵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因为国内的中小型城市中,绝大多数历史上曾经有城池,但是解放后又被拆除。并且,都面临着近年来的城市改扩建需求。
④铜陵有色金属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恢复建设的铜官山矿,是新中国最早的铜工业基地。经过60多年的建设,这家企业始终是铜陵的支柱性企业,其影响已深入铜陵的各个方面。
⑤即现在的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主要生产铁路货车。早期分别隶属于上海铁路局、交通部、铁道部,厂名701。701的名字使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改名后铜陵人依然称其为701厂。
参考文献:
[1]吴薇.近代武昌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2.
[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339-379.
[3]张凤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8(4):63-66.
[4]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及其时代价值[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0(3):52-57.
[5]白欲晓.“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1(1):76-80.
[6]朱光亚.城市特色与地域文化的挖掘[J].建筑学报,2001(11):49-51.
[7]王纪武.地域文化视野的城市空间形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5.
[8][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第20卷)池州府[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