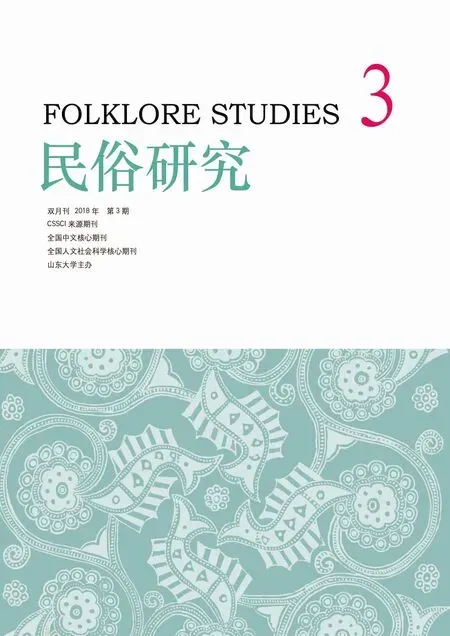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
——实践民俗学的愿景
户晓辉
博物馆与民俗学以及二者联姻的结果——民俗博物馆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在18世纪末,德语地区的民俗学,尤其德国民俗学也曾是“边界学”(Grenzkunde)、“国别地理学”(Länderkunde)、“国家学”(Staatenkunde)、“文化地理学”(Geographie der Kultur)、“财政学”(Kameralistik)和“统计学”(Statistik)的一部分。*参见Andreas Hartmann, “Die Anfänge der Volkskunde”,in Rolf W. Brednich (Hg.), Grundriβ der Volkskunde: Einführung in die FXorschungsfelder der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Dietrich Reimer Verlag, Berlin, 2001, S.14-15。至少可以说,民俗学最初既有自由民主的浪漫理想,又有经世致用的现实诉求。德语国家的民俗学在起源时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出于国家财政的需要而登记资源,是为了解救“民众的困苦”(Not des Volkes)。只不过这个动机虽然在后来的民俗学中一再出现,却又经常被人们忘在脑后。*参见Helmut P. Fielhauer, Volkskunde als demokratische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Ausgewählte Aufsätze aus zwei Jahrzehnten, Wien, 1987, S.363。更少有人意识到,所谓“民众的困苦”,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而且前者往往又是由后者导致的。也就是说,在民众那里,由物质贫困所导致的精神痛苦,远远赶不上由精神上被剥夺了自由、权利和尊严所导致的物质贫困。
从民俗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俗学的浪漫理想与现实诉求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过程。具体而言,欧洲大规模的民俗收集始于19世纪,为此才建立了各门文化科学和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参见Cristoph Asendorf, Batteries of Life: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 and Their Perception in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Don Renea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50;德语原著名为《生命力的电池:论物的历史及其在19世纪的感知》(Batterien der Lebenskraft. Zur Geschichte der Dinge und ihrer 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Gießen, 1984)。德语地区的民俗博物馆则以各个地方的家乡博物馆为主。显然,民俗博物馆为了收集、整理并展示民俗的需要应运而生,而且,在最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作为收集对象的民俗常常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无用的产品。就像废弃的邮票、空酒瓶等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废物一样,民俗在历史上也被如此看待”*[美]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户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与此相应的是,民俗博物馆被视为历史遗留物的储藏室和陈列馆,这里主要是物的叙事和“物的语言”(Die Sprache der Dinge)*Wolfgang Kaschuba, Einführung in die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Verlag C.H.Beck, 2006, S.224.,人们在这里听到的仿佛总是历史的余音绕梁,体会到的仿佛也只是怅然若失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民俗博物馆最典型地体现了民俗学的现实诉求与浪漫理想相互分离的学科征候。民俗博物馆不仅与民俗学研究一起经历了长期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过程,而且本身在民俗学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少得到理论的反思。在经验实证研究倾向的主导之下,民俗学者们往往关注和批判的是民俗博物馆将民俗孤立化和非语境化的具体做法,只是近几十年来才开始重新考虑再语境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问题意识聚焦的仍然是作为物的民俗,而不是作为物的主人和使用者的民众。
放眼整个世界博物馆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似乎也不应单独苛求于民俗博物馆的研究与实践。因为从旧博物馆学到新博物馆学的发展历程在总体上也是从物到人回归的过程,不仅实物在博物馆中的中心地位在逐渐被虚拟物体和智能物体(smart object)取代,而且也同样体现为一个转变过程:从见物不见人,到逐渐看见人,直至看到大写的人。我们可以比较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The 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在界定“博物馆”时的措辞变化:
1961年:
ICOM shall recognize as a museum any permanent institution which conserves and displays, for purposes of a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collections of objects of cultural or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把为了某种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而保存、展示、收集具有文化重要性和科学重要性的物品的任何常设机构确认为博物馆。)
1974年: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making,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the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open to the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for purposes of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material evidence of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公众开放,为教育、研究和欣赏之目的征集、保存、探究、传播并展示人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
1989年: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making,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open to the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for purposes of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material evidence of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公众开放,为教育、研究和欣赏之目的征集、保存、探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
1995年(2001年的与此措辞相同,只是增加了几个逗号):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making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of its development, and open to the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for purposes of study,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material evidence of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公众开放,为教育、研究和欣赏之目的征集、保存、探究、传播并展示人们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
2007年: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公众开放,为教育、研究和欣赏之目的征集、保存、探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参见网址: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Definition according to ICOM Statutes (1946 - 2001),http://archives.icom.museum/hist_def_eng.html [2017年10月22日]。
从1961年根本不出现“公众”和“人”的字眼,到1974年出现了“公众”(public)和“人”(man),再到1989-2001年出现了“公众”和“人们”(people),直到2007年出现了“公众”和“人类”(humanity),其中的重点转移和问题意识的变化至少包括:从物到人,从“物质证据”到有形遗产(物质遗产)再到无形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泛泛而谈的人到具有人性的人。人的因素在逐渐增强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和重视。因此,近年来才逐渐发展出以人为中心的博物馆学(people-centred museology)。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博物馆的中心不是物,而是文化,博物馆是人与物、人与人发生文化对话的场所。“随时光流转,当代博物馆已完成了从古时为祭祀之用的对珍玩奇观的收藏,以及为扬威之用的赫赫战功的展示,逐渐演变到现代意义上为审美之用的灿烂文明的复现,以及为体验之用的仪式缔造的圣地的过程。”*施旭升、苑笑颜:《仪式·政治·诗学:当代博物馆艺术品展示的叙述策略》,《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与其他博物馆相比,民俗博物馆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去精英化色彩和平民化倾向。恰恰在民俗博物馆里,民俗学最初的两种实践动机——自由民主的浪漫理想与经世致用的现实诉求——不仅可以得到认识的统一,而且应该得到实践的结合。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审美启蒙的公共领域
博物馆类似一个凝视装置,它以特定的方式吸引并决定着观众如何凝视以及凝视什么。民俗博物馆所展示的民俗之物固然常常已经被抽离了具体的语境和文化环境,但恰恰因为这样,它们在民俗博物馆里才可能得到观众的重新审视和深入审思。例如,民俗博物馆常常要陈列过去的生活用品和生活用具。无论观众是否使用过或者见过这些用具,他们都会想象它们曾经的那个世界,这些用具为观众与那个过往世界的照面提供了契机和媒介,也就为不同观众进行不同的记忆联想和理解意义上的对话展示了平台。
当然,民俗博物馆展示的是历史之物却并非历史本身,因为历史并非过去了的东西,因为过去了的东西恰恰是不再演历的东西,但它也不是单纯今天的东西,因为单纯今天的东西也不会演历。相反,历史是从将来得到规定并且穿过现在的往事和曾经的存在。*参见[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4页。这就意味着,民俗博物馆的展示仿佛是从未来的自由立场投向过去和现在的器物和生活用具的一束光线。这束光线不仅可以为这些器物和生活用具找回那个已经失落了的、曾经的世界,更是为了让它们重新斩获另一个世界,使它们获得新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含义。因此,一方面,民俗博物馆“不应该仅仅采取‘过去时’的方式来展现一个民俗资料构成的世界,而更应该考虑这些民俗资料和现在的地域史、地方史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必须给这些民俗资料赋予现在的意义与价值。过去的展示都是把地方上由历史而形成的民俗世界与民俗认同除掉了,没有把与特定的土地和大地相关联的人民形象投射在民俗文化这个屏幕上,因此造成了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民俗展示的现况”*[日]大冢和义:《博物馆展示的理念与评价的方法》,陈文玲译,参见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41页。,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把某物视为艺术就意味着从自由的立场来看*参见Harm-Peer Zimmermann, sthetische Aufklärung. Zur Revision der Romantik in volkskundlicher Absicht,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GmbH, Würzburg, 2001, S.291.,那么,日常生活用品进入博物馆就意味着把它们变成了艺术品。观众进入博物馆就仿佛进入了一种仪式的阈限状态,博物馆在时间和空间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种阈限区域(liminal zone)*参见Carol Duncan, 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 Routledge, 1995, p.20。,“博物馆像一个神奇空间,物进入到博物馆里,就不再是原来的物,而是成为特有的信息载体与象征符号,要和人重新结成一种新型关系。博物馆也像一个神奇的画框,在这里观看物,观者和物之间也必然会形成一种特定博物馆语法的修辞关系”*曹兵武:《博物馆是什么?——物人关系视野中的博物馆生成与演变》,《中国博物馆》2017年第1期。。这也就意味着,只有站在自由的立场来看待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我们才能把它们看作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当然,观众在博物馆中可以获得审美、娱乐、怀旧等各种体验。博物馆中的凝视,与其说来自观众的眼光,不如说来自投注在展品身上的那一束光。或者说,投注在展品身上的那一束光才是现代性的凝视之光,它照亮了展品,使博物馆中的农具或日常用品脱离了实用性,使观众有可能以无功利的审美来看待并且反思它们。恰恰是这种审美的启蒙需要观众运用先验的反思判断力,即把特殊归摄于普遍的能力,达至审美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建构一种具有共同感的叙事(a consensual narrative),让原本只能以单数形式存在的记忆也能够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参见Silke Arnold-de Simine,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17.,进而培养观众“对公共事务的感受性,也是一种关乎主体间交往的实践性的德性”*周黄正蜜:《论康德的审美共通感》,《云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这实际上是为公民素质的培养创造了审美的契机。因此,民俗博物馆也是感性启蒙或审美启蒙的公共领域,而不仅仅是文化猎奇和民俗展示的场所。欧洲的博物馆一直是推行“实践的启蒙”(praktische Aufklärung)的一种公共领域*参见Wolfgang Kaschuba, Einführung in die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Verlag C. H. Beck, 2006, S.25-26;周飞强:《公共性与博物馆的转型及实践》,《新美术》2008年第1期。,民俗博物馆当然是实现民俗学的学科抱负的绝佳途径:即通过各种实物形象(Bild)进行人文教化(Bildung)和审美(感性)启蒙,“由此可见,中西方博物馆历史发展脉络虽然不尽相同,但是美育都曾作为一种民主意识的代表,被当做实现公民自身权益的渠道”*周冬梅:《论美育在博物馆公共教育中的重要性》,《艺术教育》2017年第Z3期。。当然,这种启蒙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宣传和独白,而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平等的相互启蒙和公共对话*曹兵武指出:“从用品、葬品、祭品、礼品,到缪斯神庙,到博学园,到皇室贵胄的私密的神奇橱柜以及文人雅玩,物之于人,不断延伸出新的功能和情感系连。而公共性则是博物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基因突变或者催生婆。”参见曹兵武:《博物馆是什么?——物人关系视野中的博物馆生成与演变》,《中国博物馆》2017年第1期。,“这是因为博物馆还有一种重要的启蒙和民主化的价值”*施旭升、苑笑颜:《仪式·政治·诗学:当代博物馆艺术品展示的叙述策略》,《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关于审美共通感及其公共启蒙作用,康德曾写道:
但是,人们必须把sensuscommunis理解为一种共同感的理念(die Idee einesgemeinschaftlichenSinnes),即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对表象方式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任何他人在思想中的{表象方式*大括号内的文字系译者根据文义补充,下同。},由此使自己的判断仿佛接近了全部人类理性,由此避开了从主观的私人条件出发可能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可能被轻易看作客观的。那么,发生这种事情的途径就是,人们使自己的判断接近别人的那些虽然并非现实的、却毋宁仅仅是可能的判断,摆脱以偶然的方式附着在我们自己的评判上的种种局限,并以此置身于每个他人的位置上;而这又是由这样的方式造成的,即人们把在表象状态中是质料即感觉的东西尽可能除去,仅仅注意自己的表象或表象状态的形式上的特性。*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44-145.
在我们借以宣布某物为美的一切判断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有别的意见;但我们仍然不把我们的判断建立在概念之上,而是仅仅建立在我们的情感之上,因此,我们不是把这种情感作为私人情感,而是作为一种共同情感(ein gemeinschaftliches)奠定为基础的。那么,为此目的,这种共同感(Gemeinsinn)就不能被建立在经验之上;因为它要授权人们做出包含着一个应当的判断:它说的不是每个人都将与我们的判断一致,而是每个人都应当与它一致。因此,我在这里把我的鉴赏判断说成是共通感的判断的一个实例,因而我赋予它示范的有效性,{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理想范式,在它的前提之下,人们就能够有理由使一个与它一致的判断以及在该判断中表达出来的对一个客体的愉悦对每个人都成为规则:因为虽然原则仅仅是主观的,却仍然被假定为主观上普遍的(一个对每个人都必然的理念),在涉及不同的判断者的一致性时,只要人们肯定已经正确地将之归摄于这个原则之下了,就能够像一个客观的{原则}那样要求普遍的赞同。*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81.
阿伦特主张把gemeinschaftlicher Sinn译为“共同体感”。*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115页。当然,康德意义上的共同体首先指人类的共同体,只不过康德也把这种共同体描述为“公众”(das Publikum)和“观众”(die Zuschauer)。*参见Johannes Keienburg, Immanuel Kant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der Vernunft,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S.149。如果说审美判断“通过公共性进入公共性”(in der Öffentlichkeit durch die Öffentlichkeit)*Johannes Keienburg, Immanuel Kant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der Vernunft,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S.149.,那么,做出这种审美判断的观众也同样能够“通过公共性进入公共性”,由此获得一种被扩展的思维方式(eine erweiterte Denkungsart)。
显然,民俗博物馆也是一个交互主体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恰恰是培育观众审美共通感的公开场域,因为无功利和超功利的审美有助于培养观众以不偏不倚的和客观中立的理性立场来看待和思考公共事物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康德所谓公共的思维方式(die öffentliche Denkungsart),它体现为三个准则,即作为知性准则的自行思考(Selbstdenken)、作为判断力准则的站在每一个别人的位置上思考(an der Stelle jedes anderen denken)和作为理性准则的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的思考(jederzeit mit sich selbst einstimmig denken)。康德在此指出,真正的启蒙之所以非常艰难,恰恰因为要在思维方式中确立并保持对被动性、盲目性和仅仅考虑自己的目的等习惯的单纯否定是非常艰难的,而这种单纯的否定恰恰构成了真正的启蒙。限于题旨,也为了便于理解,这里不对康德的细致区分和微言大义展开论述。*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45-146以及注释。
从理想状态来说,中国民俗博物馆的启蒙先锋作用和意义主要在于,即使在民主匮乏的情况下,也让观众首先学会用理性来管理自己,这是我们在目前甚至未来需要学习和实践的自由能力。换言之,每个人都需要自我启蒙,都需要不断地摆脱精神上的未成年状态,因为“启蒙就是人脱离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的出路。未成年状态就是不经另一个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知性*康德在这里指的是作为理性构成部分的知性,下同。。如果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不经另一个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这种未成年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我们作为公众需要认识到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为“公众要启蒙自己,是更为可能的;只要允许公众自由,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参见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in Immanuel Kants Werke, Band IV, Herausgegeben von Ernst Cassirer, Verlegt bei Bruno Cassirer, 1922, S.169-170;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8期。每个人摆脱未成年状态的精神启蒙都是无止境的过程。这是一场自己与自己展开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人的理性能力不是一种神秘的本质,而是需要通过公共使用加以培育和维护的素质。在一个大家都纷纷放弃自己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转而追求不思考的安逸的时代,一个人单独保持自己的理性是困难的,但却又是必须的”*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二、公共对话的实践场域
当然,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物品常常来自偶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提供的信息和知识也具有碎片化、零散化的特点,因而博物馆的展示总要以特定的方式随物赋形,力求使这些碎片化、零散化的信息和知识趋于系统化和整体化。尽管民俗博物馆首先有物的叙事和物的语言,但这种叙事和语言必须依靠观众来完成,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人通过物来叙事和对话。“在博物馆的参观活动中,通过观看、理解和与讲解员的互动,与展品的互动,参观者与展品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动仪式的相互关联”*娜文:《民俗博物馆实物模型互动展示系统HanikaParadise》,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页。。民俗博物馆以展出的物的形式重组了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参见Cristoph Asendorf, Batteries of Life: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 and Their Perception in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Don Reneau, University of Clifornia Press, 1993, p.47。,这就需要观众来理解、建构并参与这种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因此,民俗博物馆是对话和实践的场域,而不是单纯的储物间和陈列室。对意义的理解本来就不是独白和独占,而是对话。传统也并非未经触碰地待在过去的博物馆里,而是被纳入了活生生的当下。*参见Jürgen Becker, Begegnung-Gadamer und Levinas: 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und die Alteritas, Ein ethisches Geschehen, Peter D. Lang, 1981, S.31。因此,民俗博物馆就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发生交织和碰撞的文化空间,也是不同理解视域发生融合的对话空间。“博物馆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它为物与物的关联和物与人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框架。在这里,物的信息被最大化发掘,物的价值被最大化利用,物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因为物而延伸、发展,物因为人而具有了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在博物馆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曹兵武:《博物馆是什么?——物人关系视野中的博物馆生成与演变》,《中国博物馆》2017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民俗博物馆还是自我与他者相遇的地方,“民俗物品进入博物馆展示,也是通过对生活模式的神圣化重塑,推进了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民俗文化可参观性生产的魅力就在于与人相遇,穿越人们想象当中的环境,即普通自我的过去世界——成了‘他者’的自我”*关昕:《民俗展品与观众体验》,《博物馆研究》2017年第3期。。
如今,民俗博物馆是文化空间和叙事空间,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场域。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应该指出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汉文本将英文的cultural spaces对应于“文化场所”,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术语使作为关系场域的“文化空间”显得过于实体化和物质化。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上提供了一个英、法文对照的非遗术语表,将“文化空间”解释为“人们一起实施、分享或交流社会实践或想法的一种物理的或象征的空间”*英语原文是“A physical or symbolic space in which people meet to enact, share or exchange social practices or ideas”,参见网址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0265.pdf [2016年10月16日];另可参见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单霁翔:《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这种文化空间当然需要有具体的场所或场地,但它的根本特征是关系场域。这就表明,民俗博物馆的“公共空间应该是民主的,可以包容不同的声音,并将这些不同的声音凝聚为一种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公共空间”*严啸:《博物馆的媒体化:一种公共话语的阐释》,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3页。。
三、转向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给观众带来的不能“只是在一种被设计的展示或表演中得到的虚假体验”*安德明:《生活着的古代城市博物馆——有关平遥古城文化展示的考察报告》,《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6期。,而是需要把观众的体验纳入展示,让观众共同参与意义建构,实现从物到人以及从物质到故事、信仰和价值的转换。这样的要求与近年来的新博物馆学趋势(new museological trends)不谋而合,因为新博物馆实践恰恰试图使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更加民主化,它的目标不是提供权威性的宏大叙事,而是关注日常生活、个人故事和传记,以便呈现多元的记忆。*参见Silke Arnold-de Simine,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2。
尽管民俗博物馆的条件有限,而且不同的民俗博物馆也会受到不同条件的种种限制,但在不同理念的指导下,民俗博物馆的陈设方式、布展格局会有大不一样的面貌。在这方面,也许私人博物馆比公立博物馆更容易有新的突破,也具有更多的变通性、灵活性、先锋性和创造性,有可能率先成为民主实验室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换言之,“博物馆不是为了行政,也不是为了一部分的研究人员而存在,更不是为了里面的学艺员而存在。博物馆是为了使用者,即地方而存在的。因此,博物馆的调查、研究、展示、教育都是地方本位的,必须是站在居民的立场、角度而进行”*[日]武士田忠:《论地方博物馆存在的问题》,陈文玲译,参见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这在中国许多公立的博物馆可能还无法完全做到,但私人博物馆则相对容易做到,或者可以先行一步。私人博物馆尽管可能受到资金、场地、人员等方面的限制,但在实践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方面可以捷足先登,而民俗博物馆尤其应该比其他类型的博物馆率先从独白式博物馆走向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对话式博物馆”(dialogic museums)这个术语来自Annette B. Fromm,“Ethnographic museum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turn to our roots”,in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2016) 5, p.93。,逐步推进并实践博物馆思想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 des Museumsgedanken)*Helmut P. Fielhauer, Volkskunde als demokratische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Ausgewählte Aufsätze aus zwei Jahrzehnten, Wien, 1987, S.267.。常言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有首先在博物馆的理念上想到并且追求民主化,才可能在实践上逐步做到一点,即不仅鼓励观众之间的平等对话,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促成观众、博物馆管理者与展品原初使用者之间的多元对话和互动实践。正如日本学者大冢和义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博物馆的展示本身不是目的,“展示,不应该成为学艺员自我满足的终了;同时,参观者也一样,不单只是观看东西,还要以自己的意识提出批判的见解并对博物馆提出要求与意见,必须要有相互的交流,还要有使这项功能成为可能的制度”,另一方面,还应尽可能使博物馆的信息公开化,“由于博物馆并没有对于民众公开有关博物馆的信息,民众方面也无法对此感到关心,因此,诸如民众主动努力使博物馆成为知性与美的感动的源泉,为此而献计献策,或是对相关行政部门提出要求表达不满等,都很难做到。博物馆必须要把自身的问题、苦恼与民众共享,一同构筑解决的机制,唯有民众与博物馆携手合作,博物馆才有可能成为终身教育社会的核心设施”。*[日]大冢和义:《博物馆展示的理念与评价的方法》,陈文玲译,参见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43、346页。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至少需要考虑如下一些问题:
(一)在主体方面:谁进入博物馆?谁不去博物馆?谁的目光?谁的凝视?谁被博物馆的陈列排除在外?
(二)在对象方面:谁应该了解什么?博物馆在选择什么,排斥什么?
(三)在对象的性质方面:能否重新思考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博物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四)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方面,是否具有以下明确的实践目的:
1.能否重建人(包括社区和文化实践者)与物的实践关系,建立民俗文化转向公共文化的有效机制,并且为非遗的表演和动态展示创造空间?
2.在文化记忆的政治上能否为普通观众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叙事”声音和访谈录音提供文化展示的空间与对话的空间,并且充分显示对它们的尊重?
3.能否采用多媒体互动手段把讲故事环节纳入博物馆展厅?能否让不同观众听到别人不同的回忆与讲述?能否为观众的讲述、回忆和评论提供多媒体交流的平台?多媒体的数字化博物馆在展示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使博物馆成为多声部回忆和多元记忆的时空连接点,让观众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这些做法在奥地利等德语国家的民俗博物馆中已经有所尝试。*参见网址:Was kann Kultur? | Cultural Broadcasting Archive https://cba.fro.at/314300 [2017年11月3日]。韩国民俗村也以活态博物馆的形式促进观众的互动和参与体验(参见图1)。2017年10月6日,在德国慕尼黑的现代绘画陈列馆召开的一个博物馆主题会议,议题就是“数字空间中的博物馆:机遇与挑战”(Museen im digitalen Raum. Chancen und Herausforderungen)。这次会议表明,社会的数字化转变也引起了博物馆观众的角色转变以及对博物馆与观众互动的不同期待。*参见网址:“Museen im digitalen Raum”-Tagung am 06. Oktober 2017 | DIE PINAKOTHEKEN https://www.pinakothek.de/musmuc17[2017年11月3日]。

图1 观众在韩国民俗村的县衙前体验传统的刑具,拍摄于2012年12月8日
4.能否让不同观众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记忆和认同感?博物馆能否有助于普通观众个人参与自己的历史书写并且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5.是否尊重普通观众的人权和文化权利?能否让他们形成个人的独立判断?如何增强活态非遗的能见度(visibility)?比如,利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和3D建模等技术手段,增强观众对环境的感知性以及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互性和自主性。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对话过程恰恰是新媒体的基石。*参见Andrew Dewdney, David Dibosa and Victoria Walsh, Post-critical Muse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Art Museum, Routledge, 2013, p.193。例如,清华大学研究生娜文为民俗博物馆设计的以达斡尔族纸偶哈尼卡实物空间模型为基础的互动故事体验和衍生品开发系统,就为观众在模型展台上的互动操作提供了主题故事的互动演绎契机。*参见娜文:《民俗博物馆实物模型互动展示系统HanikaParadise》,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2-43页。国内也已经有人尝试在民俗博物馆展示设计中“导入叙事的理念,将展示空间转化为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叙事’过程。将各个民俗文化的知识点纳入时间的流程中,以时间为主线贯穿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按照民俗文化事件产生、发展到结束的先后顺序来编排,组成完整的叙事过程。民俗博物馆展示设计采用顺叙的故事脉络和叙事结构,通过具有因果联系的情节将民俗故事联系起来,故事的表述脉络清晰、自然贯通。顺叙的叙事方式符合观众的认知习惯,使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获取连续的叙事线索,感受传统民俗产生、流传的历史背景”*李女仙:《民俗博物馆展示设计的叙事特征与空间建构——以新会陈皮文化体验馆为例》,《装饰》2017年第8期。。民俗博物馆的目标在于让普通观众不仅成为旁观者,而且成为参与者,也就是成为博物馆意义诠释与价值生产的主体,“下一步的趋势是建立个性化的‘人人’数字民俗博物馆,即参与数字民俗博物馆的创建、管理和发展的主体将由政府转移至草根大众,信息传播的方式将发生新的变化,由民俗博物馆和民众之间的双向传播转变为民众之间的多项传播,将会有更多的民俗文化展品通过‘人人’民俗博物馆聚合到网络中,未来呈现给民众的将是一道‘满汉全席’式的数字民俗博物馆”。*周蕊、戚桂杰:《数字民俗博物馆的建设与推广》,《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
6.能否给普通观众带来独特的、前所未有的陌生化体验?能否有助于在他们之间形成新型的民主化社会关系?
如果说公共民俗学工作需要民俗学者脚踏实地、头顶云端*民俗学家史蒂夫·斯波林(Steve Siporin)的原话是“Public folklore work requires folklorists to have their feet on the ground and their heads in the clouds”,参见Robert Baron and Nick Spitzer (eds.), Public Folklor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 2007, p.242。,那么,民俗博物馆的实践同样需要民俗学者以心中的道德律为头顶的星空和实践法则,并把它贯彻到脚踏实地的日常实践中去。民俗博物馆的这种实践可以成为而且应该成为实践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实践民俗学恰恰不是要匍匐在现实的脚下,而是要用自由意志引导并改变现实,开辟并创造崭新的现实”*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因此,“民俗学不是没有人文关怀的客观知识学,而是通过对民俗和生活世界的理解最终推动民众(包括学者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实践科学。实际上,民俗学在许多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实践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学者对民和民俗理解得越好,就越有助于推动民俗生活的正当化和由民转变为公民或自由人的社会进程”*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8期。。奥地利民俗学者赫尔穆特·保罗·菲尔豪尔在30年前的《家乡博物馆——历史的废物间?》(Heimatmuseen-Rumpelkammern der Geschichte?)一文中说得好:我们现在需要真正民主化的博物馆,让民众在其中也能找到他们的历史认同,让他们能够为现在和将来的文化遗产做出衡量并达至成年。*参见Helmut P. Fielhauer, Von der Heimatkunde zur Alltagsforschung. Beiträge zur Währinger Kulturgeschichte, Eingel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erbert Nikitsch, Wien, 1988, S.34。可喜的是,国外民俗学者已经在认识和实践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比如,“在德国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的兴起时期,博物馆被视为学术研究机构,博物馆馆长通常也同时担任大学教授。博物馆是高高在上、远离尘世的象牙塔,博物馆的藏品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学。向学术圈子以外的普通受众介绍展品,既非博物馆工作人员能力所长,也非他们的兴趣所在。……[但是,]在向公众开放和与公众交流方面,德国博物馆在最近的十几年内有重大的改变。面向普通受众,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组织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已经被列入大型的、公立博物馆的常规活动日程当中。”*吴秀杰:《多元化博物馆视野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德国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的历史与现状概述》,《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更重要的是,民俗博物馆的日常实践可以实施那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活动,正如卡舒巴在柏林的相关社区为居民参与城市事务的协商与管理提供平台所实践的那样。*参见[德]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安德明:《从“民俗学”到“欧洲民族学”:研究对象与理论视角的转换——德国民俗学家沃尔夫冈·卡舒巴教授访谈》,《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因此,“在运用我们的田野工作训练将传统的传承人与物件关联起来,在找寻新的方式将博物馆的新技术用来让传承人的声音被听到这两方面,民俗学者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民俗学者能够并且确实在创建更为‘在文化上民主的’博物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田野工作、馆藏发展、展品和教育推广方案都与社区共同决定”。*参见[美]C. Kurt Dewhurst:《民间生活与博物馆:一种建立新的文化生态的力量》,陈熙译,《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如果说民俗学是一种“民主的文化史书写”*参见Helmut P. Fielhauer, Volkskunde als demokratische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Ausgewählte Aufsätze aus zwei Jahrzehnten, Wien, 1987, S.360-377。,那么,民俗博物馆恰恰应该成为这种书写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要尽可能地容纳许多不同的声音,而且有责任为这种多样性提供共同的基础,其展示的方式所激励的不仅是观众的观看,而且是他们的参与。这也就意味着从为了观众记忆转向由观众来记忆,从为了观众讲述转向由观众自己来讲述。*参见Ekaterina Haskins, “Between Archive and Participation: Public Memory in a Digital Age,” in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007, Vol.37, p.408, p.403。按有些学者的分类,“民俗展示无论对于成年/童年-自我类型,还是祖先-自我类型的参观者来说,实际上是看到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旅程(或他们祖先的生活),在公共的集体历史叙事当中,‘占据一席之地’。于是,遗产允许私人自我成为公共叙述——取代独自翻看个人影集的形式,使参观者得以把这些记录下的瞬间当成史诗般的叙述和戏剧化的情景而得到公开认可和展示。对于其他类型的参观者而言,则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进行比较,‘勾起我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怀念,在刹那间成为自己生活的观众’。于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通过展示被重新塑造为奇幻而特别的。”*关昕:《民俗展品与观众体验》,《博物馆研究》2017年第3期。实践民俗学期望建设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其中不仅有人与物的单向“对话”,更有人与人通过物的双向对话,这才是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的在于为普通观众自己的不同叙事、讲述和记忆提供平等表达与公开展示的平台,让不同于正统和官方的叙事形式与记忆方式能够获得公共表达的机会,由此使普通观众相互进行审美启蒙,共同培养公民习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