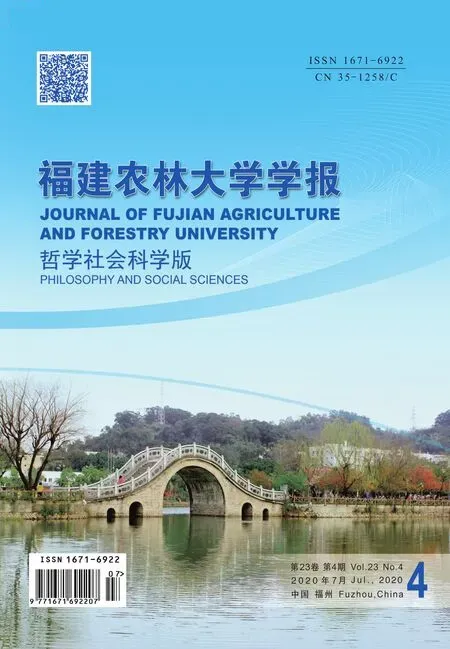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差异性影响
——基于CFPS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实证分析
张斌昌,兰可雄,林丽琼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贸易摩擦的加剧,出口和投资受到抑制,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收入的增速下滑使得降低储蓄成为刺激居民消费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居民的储蓄一直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从2000年的28.2%提高到2008年的37.3%,2018年达到44.91%,处于较高水平。但高储蓄率不利于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数字金融的诞生,对居民消费方式的变革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为增加居民消费带来了契机,改变了居民的支付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消费;依托于数字金融产生的各类消费信贷平台,通过透支未来储蓄的方式改变了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观;数字金融发展也促进了理财市场的发展,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促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变储蓄为投资。因此,厘清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收入层次差异,丰富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有助于为政府制定刺激消费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家庭储蓄的研究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其中,宏观层面侧重于分析金融发展和住房价格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微观层面侧重于分析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1.从宏观层面来看,侧重于分析金融发展和住房价格对家庭储蓄的影响。金融发展主要从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和金融排斥的角度展开研究。其中,部分学者研究指出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家庭储蓄。如高宏霞等认为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负向影响居民储蓄,且具有异质性影响[1];汪伟等研究发现居民的投资行为受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约束,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居民投资热情,从而降低家庭储蓄[2]。部分学者研究指出居民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而受到的金融排斥与家庭储蓄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臧旭恒和裴春霞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居民受到金融排斥的概率,从而降低了家庭储蓄[3-4];叶海云认为金融排斥现象越严重,家庭越倾向于压缩消费和增加预防性储蓄[5]。部分学者认为住房价格与家庭储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陈彦斌等研究指出房价的快速增长使得房地产的投资性质突显,投资性房地产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房价的快速上涨[6];李雪松和陈斌开等研究指出房价持续上涨促使人们为购房而增加储蓄[7-8]。可见,学界较多学者从宏观层面研究金融发展和住房价格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结论也基本统一,但较少有学者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2.从微观层面来看,侧重于分析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预期寿命和个人经历等。如Chamon等研究发现年龄和家庭储蓄之间呈U型关系[9];章元等研究指出预期寿命的延长会提高城镇家庭的储蓄,降低农村家庭的储蓄[10];程令国等研究发现经历过饥荒的居民更容易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11]。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人口结构和居住模式等。如甘犁等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比高收入家庭高,因此,低收入家庭会选择提高储蓄来减少未来的流动性约束[12];金烨等研究指出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差距对家庭储蓄具有激励作用[13];苏华山等研究指出未婚男性家庭成员数量越多,则家庭储蓄越高[14];尹志超等研究指出家中女性劳动力参与劳动会显著增加家庭储蓄[15];王树等研究指出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储蓄,而老年抚养比则相反[16];易行健等研究发现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的储蓄率比独住的年轻人高[17]。可见,学界较多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既丰富了家庭储蓄的相关理论,也为政府制定刺激消费等相关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但忽视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应将数字金融纳入家庭储蓄的分析框架中。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2015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下简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5”)的数据,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收入层次差异等,以丰富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从而为政府制定刺激消费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
根据经济学理论,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差额等于家庭储蓄。储蓄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转化为投资,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同时影响储蓄和投资。即一方面,降低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刺激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居民的投资倾向,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
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相对的,即家庭储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变化,而家庭消费水平往往与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有关。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分为硬约束和软约束,硬约束指家庭无法通过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软约束指家庭获得资金的成本较高,两种约束都会导致家庭降低消费,提高家庭预防性储蓄。而数字金融依托互联网技术跨越时空障碍,基于支付、转账、借贷等功能降低了家庭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变了家庭难以获得资金的尴尬局面。因此,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有助于改善家庭的消费结构,从而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
而资本市场改革滞后、投资渠道狭窄、投资风险高等降低了家庭的投资意愿,严重制约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字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业态给传统金融系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给银行类传统金融机构带来服务模式和技术转型升级的机遇;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理财市场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在数字金融的推动下,金融市场能够提供大量流动性更快、安全性更高和收益性更稳定的金融产品,增加了居民的投资机会,降低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同时,数字金融以其独特的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优势打破了以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市场环境,降低了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提高了家庭的投资倾向,从而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
综上,数字金融发展降低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有助于提高家庭消费支出,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同时,数字金融发展推动金融市场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家庭投资意愿,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FPS 2016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5。其中,自变量数字金融发展的数据来自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5,该指数包括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港澳台地区除外)的数字金融发展。因变量家庭储蓄来源于CFPS 2016,该调查覆盖中国25个省,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等3个层面的数据反映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5中剔除与CFPS 2016覆盖不一致的6个省份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和配比,最终获得8 819个有效数据。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Yi=α0+β1Xi+β2Oi+ui
(1)
其中,Yi表示第i个家庭的家庭储蓄,Xi表示第i个家庭所处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Oi表示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层面等控制变量,α0、β1和β2表示待估参数,ui表示残差项。
(三)变量的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具体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Table 1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1.自变量。自变量为数字金融发展。其均值为5.381 9、标准差为0.009 2,表明研究的25个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不是非常好,且数字金融发展的差异不大。
2.因变量。因变量为家庭储蓄。为保证模型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尹志超和Sandom等的研究[15,18],根据经济学理论对储蓄率的定义,将家庭储蓄1界定为:
(2)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弹性关系,将家庭储蓄2界定为:
S2=lnS1
(3)
在实证分析中将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作为主要的回归模型分别进行OLS回归分析和2SLS回归分析。其中,家庭储蓄1的均值为0.462 3、标准差为0.238 4,表明家庭储蓄1的差异不大;家庭储蓄2的均值为-0.975 4、标准差为0.699 4,表明家庭储蓄2的差异不大,进一步消除了弹性关系中的异方差问题。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层面。由于研究对象家庭储蓄是家庭层面的决策,户主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为避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个体层面主要选取户主年龄作为代理变量。户主年龄的均值为42.431 5岁,标准差为11.532 9,表明被调查家庭户主年龄不大,以中年人为主,但户主之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为8.554 2,标准差为1.245 4,表明家庭人均收入较高,且差异较大;老年人数量的均值为0.024 6个,表明被调查家庭中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有可能会影响家庭为老年人养老的储蓄决策;子女数量的均值为1.451 6个,表明被调查家庭大部分拥有1个小孩,有可能会影响家庭为子女教育、结婚和买房的储蓄决策;慢性病患者比例的均值为11.781 2,标准差为25.053 5,表明被调查家庭中患有慢性病的家庭成员较少,且被调查家庭的慢性病患者比例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28.471 7,表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均值分别为0.436 7、0.288 0和0.275 4,表明来自东部地区的被调查家庭占比较大。
(四)内生性分析
由于模型(1)中能够控制的变量有限,所以可能因为遗漏重要变量导致数字金融发展和家庭储蓄之间产生内生性。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互联网普及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互联网普及程度代表数字金融发展的技术基础,和数字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符合相关性原则;同时,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家庭储蓄不直接相关,符合外生性原则。因此,选取互联网普及程度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前文建立的模型(1)的基础上,采用OLS方法和2SLS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2。
1.OLS回归下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关系。由表2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家庭储蓄1中,数字金融发展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416,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家庭储蓄越少。这主要是缘于数字金融发展改变了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在家庭储蓄2中,数字金融发展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1.386,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家庭储蓄降低1.386%。这主要是缘于数字金融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和理财产品结构。
2.2SLS回归下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关系。由表2的2SLS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一阶段回归F值远大于临界值(10),表明互联网普及程度通过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在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中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410和-1.501。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家庭储蓄越少;且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家庭储蓄降低1.501%。同时,在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的情况下,家庭储蓄2在2SLS回归分析中下降的幅度比OLS回归分析中下降的幅度大,这主要是缘于互联网普及程度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促使传统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进一步改变了服务模式和产品结构。

表2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household savings
3.控制变量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关系。户主年龄在家庭储蓄1中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在家庭储蓄2中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则家庭储蓄越少。这可能是缘于老年人生活随着养老保险的完善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促使居民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家庭人均收入在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中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与经济学上储蓄和收入的正相关关系相符,表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则家庭储蓄越多。这主要是缘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促使家庭储蓄不断增加。老年人数量在家庭储蓄1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家庭储蓄2中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老年人数量越多,则家庭储蓄越多。这主要是缘于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日益提升的照料需求导致家庭为了照料老年人需要增加储蓄。子女数量在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中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子女数量越多,则家庭储蓄越多。这可能是缘于子女上大学、结婚、买房产生的费用较多,户主为此必须增加教育储蓄和住房储蓄等。慢性病患者比例在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中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表明慢性病患者比例越大,则家庭储蓄越少。这可能是缘于国家财政向公共医疗投入的增加,有效改善了居民的医疗问题,促使家庭的医疗储蓄随之减少。经济发展水平在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中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则家庭储蓄越多。这主要是缘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进一步增加了家庭储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中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越好,则家庭储蓄越少。这主要是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推出的数字金融产品较多,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促使这些地区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数字金融产品,导致家庭储蓄减少。
(二)稳健性检验
家庭储蓄行为存在一定的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改变样本区间和家庭储蓄定义来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尹志超等的做法[15],将家庭储蓄3定义为家庭人均储蓄率(S3=家庭储蓄1/家庭人口数),具体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详见表3。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改变样本区间后分别针对家庭储蓄1和家庭储蓄2的稳健性检验;模型3是针对家庭储蓄3的稳健性检验。同时,由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且控制变量并非该部分的论述重点,故下文中未对其展开分析。
由表3可知,在模型1中,剔除样本上下约10%后得到7 132个有效数据,数字金融发展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309;在模型2中,剔除样本上下约10%后得到7 064个有效数据,数字金融发展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807。可见,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表明上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在模型3中,数字金融发展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061。可见,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在改变储蓄率定义的情况下回归结果依旧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结果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三)差异性分析
鉴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两极化和家庭贫富差距显著等对数字金融发展存在影响,本研究进一步从区域、城乡和收入层次等方面,对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差异性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4。
1.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区域差异。由表4可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家庭储蓄1中的系数分别为-0.474和-1.557,在家庭储蓄2中的系数分别为-1.615和-4.241,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家庭储蓄越少。这主要是缘于东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普遍较好,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随着近年来政府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而不断优化,家庭可以选择的数字金融理财产品逐步增多,促使家庭提高投资积极性,从而降低家庭储蓄。中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家庭储蓄1中的系数为8.564,在家庭储蓄2中的系数为22.980,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中部地区的家庭储蓄越多。这可能是缘于东部地区相关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使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数字金融发展速度。
2.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城乡差异。由表4可知,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家庭储蓄1中的系数分别为-0.446和-0.197,在家庭储蓄2中的系数分别为-1.439和-1.014,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家庭储蓄越少。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城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降低1.439%;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农村居民的家庭储蓄降低1.014%。这可能是缘于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金融在城镇地区的普及程度优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居民受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更明显。
3.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收入层次差异。参考尹志超等的研究,根据收入水平的差异将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15]。由表4可知,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低收入家庭在家庭储蓄1中的数字金融发展仅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191,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低收入家庭的家庭储蓄越少,但数字金融发展对低收入家庭的家庭储蓄影响的显著性较弱。这可能是缘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储蓄相对较低,数字金融发展对其消费的刺激作用不明显。在家庭储蓄2中的数字金融发展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711,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低收入家庭的储蓄降低0.711%。这主要是缘于数字金融发展主要是改变了低收入家庭的支付方式,但并未对低收入家庭的投资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家庭储蓄1中的数字金融发展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319和-0.270;在家庭储蓄2中的数字金融发展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1.335和-0.705。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中等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家庭储蓄越少,这主要是缘于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有更多的富余资金可以通过购买数字金融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导致家庭储蓄减少。

表4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差异性的回归分析结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household savings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CFPS 2016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5的数据,运用OLS模型和2SLS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收入层次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整体上呈负相关,数字金融发展越好,则家庭储蓄越少。从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弹性关系来看,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家庭储蓄降低1.501%。
2.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差异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收入层次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即数字金融发展每提高1%,则城镇地区的家庭储蓄比农村地区多降低0.425%;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储蓄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数字金融发展对低收入家庭影响的显著性较弱。
(二)建议
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降低家庭储蓄以刺激消费和带动经济增长,应加强数字金融的宣传教育、推进数字金融的队伍建设和健全金融行业的协会制度,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1.加强数字金融的宣传教育。金融素养是金融消费者作出正确的财务决定和防范金融诈骗的基础,应加强数字金融的宣传教育以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加强数字金融的宣传教育,要注重完善金融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应以村居为单位推进金融信息服务点的建设和完善,如设立专门的金融信息小教室,组织数字金融领域相关专家、大学生等定期下乡为村民开展数字金融知识宣讲;同时,要注重丰富数字金融宣传教育渠道,将传统宣传教育渠道(如信息服务站、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点等)和新兴传播媒介(如微博、微信等)有效融合,以加强数字金融的宣传和推广。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力度,如以村居为单位注册专门的数字金融服务公众号和数字金融信息微博,让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在多元化的数字金融宣传教育渠道中有效提高金融素养。
2.推进数字金融的队伍建设。数字金融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金融市场的环境和金融行业的服务模式,应大力推进数字金融队伍建设以优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在员工培训过程中要着重于数字金融技术的培训,通过聘请数字金融领域相关专家定期进行数字金融技术培训,以提升员工的数字金融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从而推进数字金融队伍的人才建设;同时,金融机构内部应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技术部门,通过吸纳相关专业人才组建数字金融技术部门,专门为金融机构开发以数字金融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如数字化的小额定期存单和小额定投基金等,以优化数字金融服务。
3.健全金融行业的协会制度。数字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业态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应增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数字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通过建立健全金融行业的协会制度,积极搭建数字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交流平台,有效引导和推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数字金融机构定期开展交流会、人才合作培养项目等,以规避传统金融机构与数字金融机构的恶性竞争,推进二者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