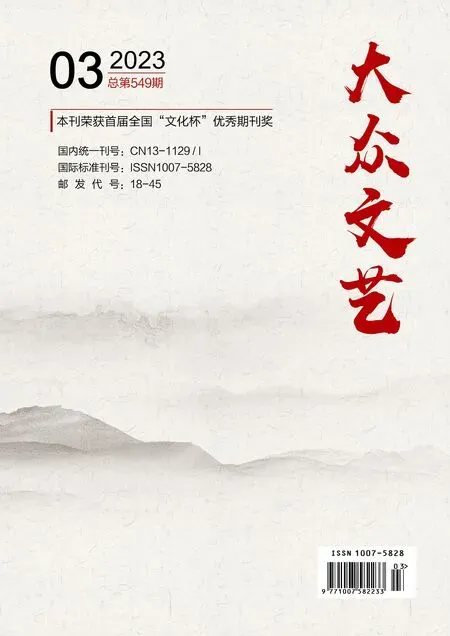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长恨歌》:一个女人和一座城
许梦娇
(杭州西子实验学校,浙江杭州 310000)
自1995年《长恨歌》载于《钟山》杂志始,文坛上对于《长恨歌》及其作者王安忆的讨论就未曾停止,直到2000年,《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争议之声更是铺天盖地。有人将王安忆定义为“张爱玲的接班人”“文坛的弄潮儿”,将《长恨歌》定义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等等,但是不管外界是如何定义这本书,是如何定义王安忆自己,作者本人始终不曾承认——“我总觉得我非常被动”[1]。而王安忆自己则是这样评价《长恨歌》的:“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一、一个女人如何表现一座城
许多人认为,将一座城市的历史以一个女人的生活作为表现形式实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谬的。城市的历史应该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通过男性社会权利政治的动荡来加以表现。但是在《长恨歌》中,读者不仅看不到历史的重大变革,甚至连主导历史发展走向的男性身影也几乎消失不见。实际上这与王安忆的创作理念有关,王安忆曾在1982年的一篇自述中说道:“我现在很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写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到很多年的历史,很大的一个社会,就像高晓声的陈奂生一样。”[2]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王安忆创作《长恨歌》的初步动因。等到1985年的时候,王安忆在思及初期写徐州时的经历时说道:“我想放弃写徐州,反而倒写出了徐州。为什么?后来,我悟到,虽然写的是文工团,小小的院子里,一百多人,但它是在徐州的,这里发生的一切悲欢喜乐,都带有徐州的气息,都带有徐州的历史和它的文化。”[3]这样的一种小说观不妨套用到《长恨歌》的创作上,或许这正是王安忆所说的借一个女人写出了一座城市的原因,因为这个女人身处于这座城市之中,她的一举一动都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她的整个人生都是这座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但是还是会有人质疑,仅仅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可以反映整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吗?对此,王安忆在2000年的《文学报》上对于历史概念的阐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所以,在作者看来,历史的面目不是由众多重大事件堆砌而成的,而是在平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逐渐积淀形成的,而生活的主体是“人”,换言之,历史的主体也是“人”,所以,想要展现历史,首先得肯定“人”的地位。因此在《长恨歌》中作者塑造了“王琦瑶”这一形象,希望借“王琦瑶”这个女人前后四十年的人生来反映上海这座城市最值得被铭记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的选择,在作者看来则是非“弄堂”不可,因为“城市无故事”[4],只有“在那些居住拥挤的棚户或老式弄堂里,还遗留着一些故事的残余。”[5]
可是为何非要把这段历史的主人公限定为一个女人呢?在惯常的思维习惯中,我们更偏向于选择男性作为历史的主宰者,女性大多时候只能乖乖的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即便是花木兰替父从军也只是老百姓们美好的愿望罢了。但是王安忆偏偏为她的历史选择了一位女性作为主人公,不仅如此,这个女性还是极具世俗性的,她是由形形色色的上海弄堂、淮海路、花园洋房和细心细意的小日子堆砌而成的。那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上海是富有女性气息的,上海历史在那些美丽女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最终这些重重叠叠的女性的影子纠结成了王琦瑶的形象。
那么王安忆又是如何借王琦瑶这一人物来展现历史的呢?在“人”与“历史”之间,“城市”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城市”是“人”生活的所在,同时又是“历史”变迁的载体,所以如果想要借“人”来表现“历史”最关键的就是写好这座“城”。在《长恨歌》中,作家选择了“弄堂”作为结构整座城的切入点,上海的弄堂是这座城市的芯子,王琦瑶则是弄堂孕育出来的女儿,至此,人与城紧密相连。
在《长恨歌》中,小说的故事性和城市生活的世俗性表达松散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似乎更愿意从某一点生发开来,由点及面、缓缓而言、渲染全篇,从而在散文化的叙述中包裹住小说的故事性,将“人”与“城”通过语言的桥梁联系起来。但有些论者认为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将《长恨歌》割裂了,使得小说中似乎有两个王安忆,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甚至于大量的散文化笔触造成了一种“语言暴力”,作者的主观意识充斥于字里行间,压抑了读者再创造的空间。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看王安忆的小说观,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这一叙事风格其实是有意为之。在王安忆看来,小说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反映,既然是作家个体的主观化思想的表达,其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个体认知的表现,而那些散文化的语言实际上就是幕后的作者借语言文字这一媒介向读者的缓缓倾诉。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是历史文献,如何能苛责小说家将一座城市的历史用纪实的方式表现,当小说以一种文学性的笔触阐述的时候就已经烙上了作家的个人风格色彩,至于读者怎么进行再创造,那已经不是作家该管的事了,作家只需忠实地表达自己便已经是尽到了应有的责任。王安忆曾在一篇对话录中说道:“是谁规定了小说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难道不是先有这样那样的小说然后才有了我们关于小说的观念吗?谁能说小说不能用议论的文字写,用抽象的语言写?……其实,小说之所谓怎么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好’。”[6]所以,这样的一种“洇染”式的叙事风格并没有将小说割裂,相反,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作家在表达小说的故事性的同时兼顾了城市历史的展现和作家主观意识的表达,从而将人——城——历史三者紧密联系起来,最终达到作者所说的“借一个女人写一座城”的目的。
二、女人对城市:长恨
小说名为“长恨歌”历来引起了众多读者的猜测,为何王安忆会借鉴白居易的长诗同样也将自己的小说以此命名呢?在论者看来,“长恨”实际上是作家借王琦瑶对这座城市的一个感叹,一种情感。那么,何为“长恨”?
实际上,此“恨”并非指“仇恨”,而是“遗恨”,即遗憾。在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中直至篇末才始现一“恨”——“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同样也是“遗恨”,而非“仇恨”,或许王安忆将其小说命名为“长恨歌”借鉴的便是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恨”的是李、杨二人生死相隔的爱情故事,那么王安忆的《长恨歌》“恨”的又是些什么呢?这一“长”字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一)何为长“恨”?
无可否认,《长恨歌》这样一部以女性视角展现上海的小说中充溢着对柔美但不柔弱、坚强而有担当的上海女性的无声歌颂。无论是王琦瑶也好,还是严师母,甚至小说中一笔带过的蒋丽莉的母亲,这些女性一边极尽所能的花着心思享受着生活的美好,一边对生活的苦难忍耐着、承受着、解决着,比如王琦瑶人前是漂亮得体、不露声色的“沪上淑媛”,人后又是历尽艰辛、含辛茹苦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的单身母亲。她们有悲有喜但是从来淡然处之不怨不艾,该浪漫时浪漫,该务实时务实,分得清缓急,拎得清轻重,然后在生活的沉淀下绽放出自己的美好。在这些蛰居于弄堂、安稳于现世、被柴米油盐浸泡着的上海女性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柔美、坚韧、强大让读者为之赞叹不已。
然则,单就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而言,她的忍耐力、坚韧性固然令人赞叹,但是当一个人在遭受了种种变化和磨难之后还是只学会了忍耐和默默承受,那么就应该对此进行反思了。王安忆基本上是以爱情的方式来讲述王琦瑶的一生的,不论是李主任、康明逊还是老克腊,结局都是那么不尽如人意的,而王琦瑶似乎从来都不曾接受教训,只是将自己的爱情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哪怕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情。和李主任,不过是“有恩有义”的依赖;和康明逊,地位不对等、身份不对等,连爱情的付出和回报都是不对等的;等到老克腊,垂垂老矣的王琦瑶已经糊涂了,她错将老克腊的怀念当作是旧时代的重现,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新时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可否认,男权对女性命运的掌控是造成女性命途多舛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并非必然原因,命运的多难和不可知虽说是客观的,但是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可是王琦瑶却没能好好理解什么叫事在人为,只是被动地接受命运带来的结果,随波逐流而无所作为。李静将王安忆小说中的人都定义为“一种历史在其中处于匿名状态的不自由的人”[7],在这里或许可以拿来借用一下。
再则,王琦瑶的“不自由”不仅仅表现在她对于爱情的不作为上,更是贯穿了她整个的人生。追求时尚是王琦瑶生命的重要意义,王琦瑶的时尚不仅仅是单纯的追赶潮流,而是要成为潮流里的中流砥柱,而“三小姐”的称号似乎将她的这样一种愿望落到了实处。自从在选美比赛中获得了“三小姐”的桂冠起,王琦瑶似乎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在常规的思维模式下,“三小姐”是王琦瑶时尚人生的起点,她本应该接着这股风势继续将自己的时尚之路走得更加辉煌,结果比赛之后她就投入了李主任的金丝笼里,仓促的结束了这段还没来得及开始的旅程。等到王琦瑶被放出金丝笼,再调整好自己的心情重新回归上海生活,这个时候的时尚却已经不再为王琦瑶留位置。而王琦瑶一边难以接受现有时尚的粗糙,一边又沉溺于缅怀旧时尚而难以自拔。王琦瑶似乎总是在做着不属于这个时代事情,成了一个错位人生的缔造者。并且同时,王琦瑶在拒绝现时生活而沉溺于旧日时尚的同时,使得周围的人也在不经意中就带着“三小姐”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她,至此,旧日的风光对此时的王琦瑶来说并非光辉的荣耀,而是一种无形的拘束和枷锁,它将王琦瑶束缚在旧日时尚中,将她的形象固化为40年前的“三小姐”,而拒绝王琦瑶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尚之中,使得王琦瑶脱离了这顶帽子就什么也不是。所以,最终在“内遗”(王琦瑶自己对现时时尚的拒绝)和“外遗”(现时环境对王琦瑶的排斥)的双重作用下,王琦瑶终于成了新时代的“遗民”,迎接她的必然只有死亡的结局。
王安忆在谈及自己创作《长恨歌》的灵感来源时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曾经听说一件事情……说一个上海小姐在七十年代中期被一个上海小流氓杀了。”[8]或许正是因为《长恨歌》的成形是源于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从而冥冥中注定了满篇的“遗恨”。
(二)何为“长”恨?
“内遗”和“外遗”的双重作用不仅使王琦瑶成了新时代的“遗民”,还使她身上弥漫着一股恒久不散的孤独感。三十年代的王琦瑶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而七八十年代的王琦瑶是不属于新时代的孤独。虽说造成这种孤独状态分内外二重原因,但是个体内心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种隔绝状态不仅使王琦瑶在前后四十多年的人生中陷于孤独,还使其不论在什么年代与周边世界都是格格不入。所以,在时代隔绝(纵向孤独状态)和环境隔绝(横向孤独状态)的相互作用下,这种孤独感将永不消散。
并且,在《长恨歌》中,始终都弥漫着宿命的味道。从开篇起,不管是“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阴森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9]这样的暗示性语言,还是类似王琦瑶、严师母、萨沙、康明逊和王琦瑶、张永红、老克腊、长脚这样时间前后相距四十年但是情境相似的人事变换,或者是王琦瑶和张永红这样高度相似的人物轮回,都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宿命的味道。个体生命的努力在历史和时代的作用下似乎化为虚无,四十年前与四十年后的重叠,更凸显了生命的悲凉与哀怨。
而弄堂上洁白的鸽子,以其血红的目光见证着这一切,它们的繁衍也意味着这段悲凉的历史将会长长久久的轮回、再现。
结语
透过王琦瑶及其周边的人事变换,我们看到了王安忆想要呈现给我们的上海,这样的上海实际、功利、精明而又有着独特的美。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上海写进了一个女人之中,又通过这个女人展现给读者看。对上海,王安忆是又爱又恨的,爱的是曾经的上海的精致、务实,恨的是现在的上海的粗鲁、鄙陋,在王安忆看来,“这城市的心啊,已经歪曲的不成样了,眉眼也斜了,看什么,不像什么。”[10]所以最后,王琦瑶,这个四十年前的上海代言人在作者的笔下随着那逝去的上海一同死去,以此来祭奠曾经的上海心。
或许自从王安忆在未满周岁时乘火车在一个痰盂上进入上海开始,就注定了她与上海的不解之缘。《长恨歌》的问世完成了王安忆对上海的致敬,而王琦瑶的死去或许也标志着那个王安忆最爱的上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者用闲言碎语、残丛小语构筑了一个记忆中的上海,用语言描绘了一幅上海的“清明上河图”。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