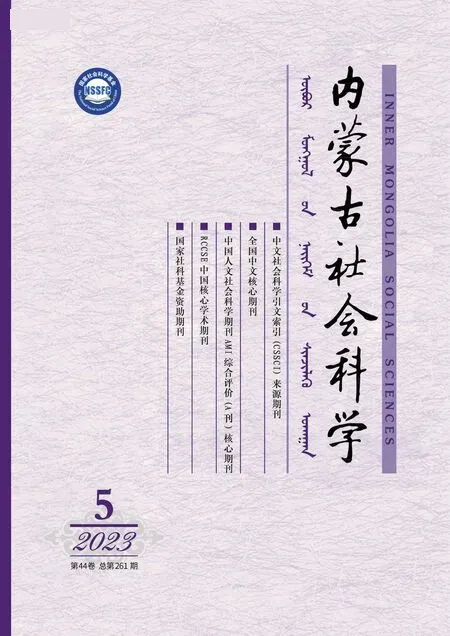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郭晨光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引言
西晋末叶,匈奴、鲜卑、氐、羌、羯五胡民族趁机占据中原,出现了“十六国”政权,从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洛阳被匈奴刘聪占领,一直持续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重新统一北方。十六国和北魏不仅在社会史上前后相连,北魏前三帝实际仍处于十六国时期,而且二者在文学史上也彼此联系,从十六国到北魏初期(1)本文所说的北魏初期指自北魏立国至拓跋焘结束十六国纷争、统一北方的这一时期,与十六国大致处于同一阶段。形成的文学风貌一直延续至孝文帝改制。相比南方重诗赋,十六国和北朝则以应用文自许。其中诏令(2)诏令是以帝王名义颁布的各类下行文书的统称,东汉蔡邕《独断》将其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戒书四种,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诏令大抵不出以上规模,以册书、制书、敕书、诏书、令书、玺书为主。地位最高,作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因文书行政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成为中古北方最具示范效应的文学文本。
目前学界对这一文学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朝后期,诏令撰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学传统,而对于奠定这种制度化写作的十六国和北魏初期,学界研究仍有较大欠缺,对当时的文献状况、文风演变及背后的成因等并不十分清晰。以诏令为代表的北方文学的复兴与民族政权密不可分。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既是中古北方民族文学的起始,也预示着北朝文学的发展方向,是古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一、十六国诏令对魏晋文风的承继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载:“既而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畴,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1](卷41P.743)有关当时“章奏符檄”的数量,严可均据《晋书》《魏书》及明代屠乔孙汇辑的《十六国春秋》共辑出322篇,其中诏令敕制110篇、章奏表启93篇、书信48篇、经序经记40篇、经论等15篇、诫子书4篇、檄文8篇、符命4篇,其中以各民族首领的诏令数量最多。
由于十六国政权被后世史官斥为“偏霸”“僭伪”政权,各民族首领的“下诏”在《晋书》等史书中被史官用“春秋笔法”改为“下书”[2],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原始诏令的数量及其本来面貌。各民族首领的诏令数量远多于严可均所辑,如《太平御览·偏霸部》(关于《太平御览》,以下简称《御览》)承袭北齐祖珽《修文殿御览》分部,是抄录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最多的类书。此外,《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取材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及残存的十六国旧史,“保留了许多十六国独家史料,可作为一手史料”[3]。笔者据相关类书、史书直接收录或辗转相抄又辑出的部分,略举几例。如《御览》卷六七二《器物部七》引范亨《燕书》:“昭武帝营新殿,昌黎大棘城县河岸崩,出铁筑杵头一千一百七十枚。永乐民郭陵见之,诣阙言状,(慕容盛)诏曰:‘经始崇殿,而筑具出,人神允协之应也’。”[4](第4册P.3383)《燕书》是十六国旧史,范亨曾为燕尚书,记述的史料往往取自亲身经历,比较可靠。又如:
刘曜敕刘熙及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5](卷94“简文帝咸和三年”P.3015)
石勒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5](卷91“元帝太兴三年”P.2926)
石勒诏:“且敕停作,申吾直臣之气。”[4](卷120P.586)
石虎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辨者以斩论。”[6](卷106P.2773)
苻坚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6](卷113P.2889)
苻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郡县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5](卷103P.3306)
慕容儁令:“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闻也。”[4](卷122P.584)
慕容德令:“今假顺来议,且依燕元故事,统符行帝制奏诏而已。”[4](卷126P.610)
吕光诏:“吾疾病不济,吾终之后,使(吕)纂统六军,(吕)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今外有强寇,民心未宁,汝兄弟辑睦,则贻厥万世,若内相图,则祸不旋踵。”[4](卷125P.604)
含上述文字记载在内的十六国诏令的作者多不明确。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僭伪诸君有文学”条专论民族首领的文学素养[7](PP.164~165),严可均《全晋文》《全宋文》也将诏令的著作权归于各首领名下(3)严可均据《通鉴》卷103“简文帝咸安元年”,(苻坚)“因命王猛为书谕天锡”,将《为书谕张天锡》置于王猛名下。。有学者则认为十六国君主的赞美之词大多出自后世史官对十六国史的“华夏式过滤”[8]。当时各民族的封建化水平差异较大,如三国时期氐族就“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9](P.858)。据此姚薇元指出:“氐族固久通中国,以与汉族杂居,渐趋融合,姓汉姓,习汉语,并精通汉人之生产技术与礼俗文字。”[10](P.232)如《御览》卷九四四引车频《秦书》有“苻坚欲敕与王猛……坚亲为敕文”[4](第4册P.4194)的记载。其写给昔日爱侣、臣子的《诏慕容冲》很可能为亲作。魏晋时期,君主手诏、手令开始流行。此风亦波及十六国时期的各政权,民族首领以手诏、手令的形式亲自起草诏令,如前燕慕容儁《手令敕常炜》、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等,施用于军情紧急或赐予重臣亲信。还有使用“口占”形式,即不打草稿,进行口头叙说。战乱频繁需快速处理军务,加之民族首领多“不修书传”,使诏令有了口头述说的可能性。口占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还能起到炫耀才华的效果。如大夏赫连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刘)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6](卷130P.3208),同卷又载其自言(《通鉴》作“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同条《御览》卷一九二《居处部》引《十六国春秋·夏录》作勃勃“下书”,多出“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义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远,宜有美名”[4](第1册P.927)。前者应属口占,后经文士润色,以写定在册的面貌呈现。
在大多数情况下,诏令的作者可能是《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的汉族士人,其身份主要是参管机密并代民族首领发号施令的文书之士。魏晋时形成了以中书监、中书令掌诏令的制度,如《初学记》卷一一《中书令第九》引“晋令”,“中书为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也”[11](P.273),从法律上将此职固定下来。十六国与北魏沿袭魏晋制度,仍以中书令、中书监、中书郎掌诏令,如后赵中书令徐光、王波,前燕中书令韩恒、中书监宋该,后秦中书令韦华、中书监王周、中书侍郎王尚,大夏中书侍郎胡方回等。这些士人凭借博文丽藻入职,如苻坚《下书征王猛辅政》称其“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而拜为中书令、前燕封弈、宋该“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后秦给事黄门侍郎古成冼、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这些代拟者亦以诗赋知名,据曹道衡《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一文考证,徐光、宋该、封弈、朱彤、梁谠等作品不存,但曾作诗赋或有时人称赏的记载。[12](PP.328~392)出现在吐鲁番高昌郡时代的上揭《前秦拟古诗》残本(Дx.11414+Dx·02947)保存了前秦文学的珍贵样本,是苻坚殿前中书侍郎朱彤、韦谭、阙名秘书郎模仿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作的五言诗,“是魏晋拟古诗风在前秦的延续”[13](P.216)。乱世之中文人始终未能遗忘风骚传统,只是将其退居到相对次要的地位。
十六国是北方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宋叶适云:“刘、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国,虽族类不同,而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原不甚异。”[14](P.468)五胡的核心族群并非远徙而来的入塞部族,汉晋时他们就已经居住在华北、太行山两侧,涵化于中原士人群体中的五胡民族,其文化水平、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原化了。汉族士人出于建功立业、维持门第、移风易俗等原因出仕民族政权,如张宾之于石勒、王猛之于苻坚、尹纬之于姚兴,逐渐接纳并认同其统治,主动调试于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对诏令的文体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当时南北阻隔导致的文化交流几乎绝迹(4)《晋书·成帝纪》载咸和八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拒绝与北方往来。东晋与刘、石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南北拒绝往来。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东晋盛行的玄风在北方缺乏成长的土壤,加上十六国自身的图籍资源较为匮乏,“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15](卷32P.1027),“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可能是旧有魏晋皇帝诏书的遗存(5)晋制,皇帝的诏令一般用青纸书写,如《晋书·楚王玮传》载,“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参见《晋书》卷59(第5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1597页。《晋书·赵王伦传》载,孙秀“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参见《晋书》卷59(第5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2页。,内阁存档的前代诏书成了仅有的文学遗产。诏令移檄的撰制既有较强的时效要求,又有突出的模式化、程式化特征。代拟者在撰构之前,这些诏令范本自然成为可供借鉴的对象。十六国文学的起步不存在所谓的“南化”倾向,而是表现出对中原本土产生的魏晋文风的因袭,下面略举几例进行比较。
前赵刘曜《下书封乔豫、和苞》:“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6)房玄龄等《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9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9页。后文所引此诏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晋武帝司马炎《下傅玄皇甫陶诏》:“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7)房玄龄等《晋书》卷47《傅玄传》(第5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0页。后文所引此诏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刘曜《下书封乔豫、和苞》:“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
晋武帝司马炎《下傅玄皇甫陶诏》:“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
行文中大量使用反问句、语气词连接,刘曜《下书封乔豫、和苞》“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况朕之暗眇,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皆步趋蹈袭司马炎《下傅玄皇甫陶诏》之“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出付外者,宁纵刻峻是信邪”。
前燕诏令也呈现出向魏晋复归的倾向,如慕容皝《下令赐封裕》“夫人臣关于人主,至难也”,化用司马炎诏中“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减也”,形成了两组“4∶4∶4∶6”的排比句,具有浓厚的骈俪气息。结尾“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诗》不云乎:‘无言不酬’”[6](卷109P.2825),化用《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过”及引《诗》论证,展现出对经典的熟稔。无怪乎被认为是“慕容氏于五胡之中受汉化程度最深”[16](P.280)。
此外,还有典故与文字化用者,如刘曜《下书追赠崔岳等》“魏武勒兵梁宋,追恸于桥公之墓”[6](卷103P.2687)、苻坚《下书召徐统子孙》“故桥公一言,魏祖追恸”[4](卷122P.588)等,皆化用曹操《祀故太尉桥玄文》追念恩师桥玄之典。苻坚“士死知己,由来格谟”亦是对曹操《祀故太尉桥玄文》“士死知己,怀思无忘”“士思令谟”的袭用。同一时期的北魏诏令也有向魏晋复归的倾向。曹道衡指出,崔浩《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遣辞典雅,略带骈文气息,基本上模仿三国时期潘勖《册魏公九锡文》”[12](P.83),也是对中原魏晋文风传统的承继。
某些民族政权还吸收了魏晋的文书制度,如石勒《下书八座书八座》中的“八座”即指尚书令、仆射和六曹尚书,或指尚书令、左右仆射和五曹尚书。后赵在立国之初仿效西晋东堂评决尚书奏事的制度,重要的行政事务通常由八座集议然后具名上奏、待批。后赵由五胡中封建化水平最低的羯人所建,设置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相当完备。石勒《又下书》“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石虎《下书清定选制》“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施行之”,诏书要发到或经过门下,经门下审署、封驳等流程的目的就是防止皇帝的失政和暴政,与“东晋以后诏书通过门下之举被制度化、固定化”[17](PP.295~299)几乎同步。石勒《下书招贤》开辟了地方大族子弟入仕的道路,恢复了九品制度。其《下书复议寒食》是臣子之间有关寒食的一场争论。中书令徐光则认为周汉魏晋皆有灾害,是“天地之常事”。石勒下书敦促尚书实施详议,其结果产生了“有司奏”,“有司”指尚书省,黄门郎韦謏驳了“有司奏”。石勒听从其建议,把冰室迁移到阴寒之地,并州同以前一样过寒食节。两晋南朝的门下省一直拥有对尚书奏章的封驳权,君主常将一些待议之事交给门下议决。后赵“下书”已接近后世的“门下型诏书”,吸收了魏晋制度的某些特点,表现出与东晋南朝近似的政治制度特征。
二、异质文化与北魏诏令的嬗变
北魏建立之初,北方尚处于十六国时期,文学气象、文化气质与十六国一脉相承。作为民族政权,北魏与十六国又有诸多不同之处。《魏书·崔浩传》载:“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汉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18](卷35P.81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亦言:“独拓跋以真匈奴入据诸夏,纯用胡俗强变华人。”[14](P.468)“变”字说明北魏早期在文化政策上的倾向。拓跋鲜卑久居塞北,早年称“代国”时被苻坚征服,此时鲜卑还处在“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的游牧阶段,习俗异于中土,言语需要翻译,统治者对中原的礼仪文化不感兴趣,如贺狄干在后秦习读书、史,精通《论语》《尚书》,举止风流,有似儒者。返国后,拓跋珪“见其语言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18](卷28P.686)。内迁的鲜卑文化圈与汉文化圈在同一时空内的碰撞,必然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载:“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1](卷41P.744)
北魏在南征北战中全盘接纳了十六国的文学遗产,如许谦是前秦文人,崔宏是十六国遗民,邓渊其祖、父分别仕于前秦、前燕。十六国“有时而间出”的诗赋在此时“呈现出一种真正彻底的萧条”[19](P.61),文士完全成为诏令的代拟者,对诗赋避而远之。如崔宏“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18](卷24P.623)、崔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18](卷35P.812),受崔浩案牵连,高允《征士赋·序》自叹“不为文二十余年矣”,其实这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现象。面对残酷的杀戮,“惧罪”心态是导致其文体选择由诗赋完全转向诏令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诏令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一是北魏诏令的繁盛程度发生显著变化。北魏诏令的使用频率之高以及写作数量之多,远超十六国和前代政权。就使用频率而言,《魏书》中引用或提及诏令多达两千余次,超过前四史的总和。其中太祖拓跋珪卷38次、太宗拓跋嗣卷42次、世祖拓跋焘两卷98次、高祖拓跋宏两卷多达248次,其他志、传还提及其诏、敕等180余次。很多个“诏”字意味着一份诏令录入史册,其中一些诏书事情寻常、内容多元,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之高。就数量而言,《全后魏文》共60卷收录诏令14卷,同时期的两晋仅有12卷。北魏出现了很多诏令专书和总集,如延昌初,常景受敕撰《门下诏书》40卷。《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收录北魏诏令有佚名《魏朝杂诏》2卷、《后魏诏集》16卷。宗幹《诏集区分》20卷、李德林《霸朝杂集》5卷,分别汇编于北周和隋代,其中很多为北魏诏令。《门下诏书》作为诏令专书和《诏集区分》分体总集的出现,说明至少在北魏中期以前,士人对诏令就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此外,《隋书·经籍志》别集类收录《后魏孝文帝集》《后魏司空高允集》《后魏司农卿李谐集》《后魏太常卿卢元明集》《后魏司空祭酒袁跃集》《后魏著作佐郎韩显宗集》《后魏散骑常侍温子升集》《后魏太常卿阳固集》,现存诏令及其他应用文占压倒性比重,诗赋只有寥寥几首。
二是鲜卑文化初入中原,鲜卑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通用的情况明显。“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17](卷32P.1069)这里的“国语”就是鲜卑语。《隋书·经籍志》收录有《国语号令》4卷、《鲜卑号令》1卷以及《杂号令》1卷。官方为此设置了专门的翻译官员,如“(天兴四年)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18](卷113P.2973)。此种情况持续至北魏迁都后,孝文帝以强令禁止的形式对语言进行统一要求,“(太和十九年)六月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18](卷7P.177),由此可知朝堂上政令的传达仍以鲜卑语为主。魏初诏令受其影响,呈现出质朴少文的面貌,文学水平甚至落后于前燕、前秦和后秦。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褒奖大臣的《诏赐王洛儿爵》就大量使用“王洛儿”“洛儿等”“不然”等口语,不够庄重得体。还有拓跋焘写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两封书信,纯属口语,几同谩骂。曹道衡认为,这可能更接近于北魏朝廷中通用文体的原貌。[12](P.451)北魏拓跋珪、前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前秦苻坚、晋孝武帝司马曜与名僧竺僧朗的几封书信最能体现此种差异。其中司马曜之文篇幅最长,文采最优。慕容垂、慕容德、苻坚之文部分使用骈体,与东晋文风差异不大。拓跋珪文共有三句,除了首句问候和末句遣使贡物,主体部分仅一句,“冀助威谋,克宁洪荒”,向僧朗占卜凶吉,求其庇佑,表现出对文学形式技巧的忽视。究其原因,可能与拓跋鲜卑本身汉文化水平较低,以及试图以鲜卑风俗文化变汉人的国策有关。
三是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等魏初帝王,基本不具备亲撰诏令的能力,需要完全委任汉族士人。《周书》中“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的名单记录了从昭成帝到孝文帝前期诏令的代拟者,反映出代拟这一行为在北魏初期已经趋于例行化、制度化。如许谦“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18](卷24P.610)、崔宏于道武帝时“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18](卷24P.623)、崔浩于太武帝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18](卷35P.812)、高允自文成帝至献文帝时“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18](卷48P.1086)、高闾于孝文帝太和十年前“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18](卷54P.1198)等即是如此。道武帝时期还有邓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18](卷24P.635),严可均据此将邓渊之名补入《全后魏文》拓跋珪文中。如天兴年间的《定国号为魏诏》《天命诏》《官号诏》就可能出自邓渊之手。诏书委于“专人之手”,促使代拟者身份的独立,较高的身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著作的署名权。“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指面对统治者的猜忌和防范,汉族士人凭借其典正文雅的诏书(而非诗赋)获得恩宠,声望日高。(8)在这一长串名单中,能够算得上诗赋作家的只有高允一人,但《高允集》二十一卷今已不存,其所存诗赋只有寥寥数首。凉州士人入魏后境遇不佳或可提供一个反面例证。张湛、宗钦、胡叟、胡方回、段承根擅长诗赋,其文学造诣较崔浩、高允等河北士人更为成熟,只有胡方回制掌丝纶的经历被拓跋焘雅重,“召为中书侍郎,赐爵临泾子”。
四是北魏士人依据诏令开始构建新型士人关系网络。北魏尚书省仍然是总理全国事务的宰相机构,门下多以鲜卑贵族、武人担任,以文采见长的汉族士人多充任中书省。拓跋焘在神麚四年(431)大量征召汉族士人,征召的标准是“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即北方的高门望族。卢玄、杜诠、崔绰、李灵、李熙、邢颖、刘遐、高允、游雅、张伟、张诞等应征进入平城的中书省,“皆拜中书博士”或“中书侍郎”。他们“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18](卷48P.1081),由此促成的短暂的文学繁荣因崔浩案而终结,但中书省作为北朝汉族文官的中心却得以确立,“掌诏诰”和修史成为其标志性的权力。此职在鲜卑集团中虽不受重视,但中书监、令、中书侍郎、舍人、给事黄门侍郎、给事中等成为汉族士人竞相争夺的“热官”[20](卷24P.890),成为其突破仕途之捷径。“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不仅指这一群体在前后相连的时间段内“掌诏诰”,而且反映了士人关系网络的建立向依赖血缘、家族、婚姻的转变。除崔宏、崔浩父子外,《魏书·崔玄伯传》载崔宏次子崔览、崔宏弟崔徽都曾于拓跋嗣和拓跋焘年间任中书侍郎。同卷还记载崔宽家族与崔宏同属清河崔氏,但两家关系疏远,只能算是同姓望家族。崔宽长子崔衡学崔浩书法,“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迹也”[18](卷24P.625),魏收称崔宏“世家隽伟,仍属权舆,总机任重”[18](卷24P.638),是因文书而显贵的家族。游明根、高聪为中书博士在于同族游雅、高允的引荐,郑羲为中书博士应为“李孝伯以女妻之”的关系。故有的血缘关系和门阀体系在选官制度上占据主导,乃至成为“家人父子之事业”[21](P.19)。
随着以诏令为依据的职官选任制度的日渐成熟,士人开始构建新型的关系网络。其中高允成为扭转时风的关键人物。高允历事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四朝,从太武帝到文成帝的27年间一直任中书侍郎一职,文明太后“引允禁中,参决大政”。与崔浩荐人“各起家郡守”不同,高允重视汉族士人对文化机构的掌握,如孝文帝时发挥重要作用的青齐士人,“允收其才能,表奏申用”,很多汉族士人都受到过高允的接济或举荐。高允晚年提携了一大批在献文帝、孝文帝时执掌文书的士人,如中书侍郎高闾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18](卷54P.1198)、李璨迁为中书侍郎是“雅为高允所知”、高允晚年的助手刘模由其引荐并迁为中书博士。诏令由此成为北朝士人的“行卷”,通过干谒有名望、有影响力的官员,以获得其推荐、提携,使仕途更加平顺。如高闾任中书令期间,“(中书)博士、学生百有余人,有所于求者,无不受其财货”[18](卷54P.1210),可见向其行贿、请托的人数之多。
总之,相对于难以改变的血缘关系和门阀体系,这一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充满开放性和流动性。诏令在其中承担着两项职能:一是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实现士人之间关系网络的普遍勾连,乃至于这一网络在北朝后期几乎覆盖了各地域、各阶层、各民族的士人;二是直观地反映士人的知识素养和文学才能,如博综经史、为文敏速、文风典雅且富于文采等,从而塑造士人的精神面貌,直接影响北朝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三、诏令的文学史意义
以上对十六国和北魏初期诏令的特质进行了探讨,诏令作为一种实用文体,相较于史学界在诏令体制、生成机制以及政治功能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其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上很少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考虑到“知制诰为文士之极任”[22](第2册P.564)的社会心态,诏令作为政治文本在当世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远过于后世的理解。诏令不仅提供了新的文学文本,为改变长期以来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亦有较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由以往重视经典作家、名作的研究思路拓展至社会日常生活,以诏令为中心展开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演变的研究,或可以使那些长期被遮蔽的文本重新焕发光彩,为北朝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北朝文学研究若仅集中于王褒、庾信、颜之推等移民文人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经典文本,必然会给人以中古北方文坛的荒漠化印象。诏令作为现存数量最多的应用文体,倘若我们转换研究视角,将这些新材料作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坛予以关注,则有助于北朝本土文学原生状态的展示。十六国和北魏诏令中保存了各政权即位大赦、刑法律例、礼乐制度、风俗习惯等的第一手资料,如石勒《下书国人》禁止报嫂婚、在丧娶婚与汉族礼仪相冲突的部分,但又允许羯人保留火葬的习惯,是记载历史上其他民族自然观、生命观的珍贵文献。赫连勃勃《下书改姓赫连氏》改掉刘姓,却又“大兴宗法之制”。《晋书·刘曜载记》后附唐代史臣曰,“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6](卷103P.2702),“习以华风”“兼其旧俗”是当时各民族积极融入中原礼制又保留北土旧俗的真实记载。
诚然,从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来看,崔浩、高允、高闾等并不算一流的文学家,但非一流文学家的文学创造力并非乏善可陈,他们的文学创造力主要表现在诏令的写作上,也奠定了其在北朝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刘师培《南北文风不同论》一文称崔浩、高允之文“咸硗确自雄”[23](P.561),其诏书写作呈现出不追求辞藻华美但气势逼人的战斗文风。实际上,北朝诏令既有共性,又因代拟者自身的文学素养而呈现出微妙的嬗变特征,如高闾与高允文风相近,被称为“二高”。《魏书》本传载其“强果,敢直谏,其在私室,言裁闻耳,及于朝廷广众之中,则谈论锋起,人莫能敌”[18](卷54《高闾传》P.1210),这是与高允文风相近的一面。本传又称其“文章富逸”,“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优礼之”[18](卷54《高闾传》P.1198),在追求浩大声势之外,还有华丽、富有文采的另一面。《文馆词林》载录了太和三年(479)系于孝文帝名下的《后魏孝文帝戒师诏》,考之《魏书·高闾传》载其于太和三年,上表反对北魏出师淮北,理由与诏书中“兴师动戎,必须豫策;振威举旆,实待储伏……介胄戈矟之用,皆令修备”[24](P.452)相同,此诏可能为高闾代拟。全文近四百字,篇幅是崔浩《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的两倍,几乎通篇使用骈体,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的高要求,追求张皇威武、忠义奋发之效,洋溢着北魏作为“正邦之象”的豪情与霸气。这说明北朝诏令宏壮、贞刚的美学风格在北魏初期就已奠定。
其次,文书之士的文学活动促使原有的文学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中国文学版图自中古起就形成了重组的态势。长期以来,汉语文学的地域发展并不均衡,中原、江南、巴蜀一代相对发达,河朔地区(今河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较为薄弱。晋室南渡之后,中原文学中心遭到破坏,被称为“文章殄灭”“经籍道尽”,长期动荡导致文学的衰落之态。十六国和北魏初期,北方的文化建设不断加强,士人的诏令写作有效填补了此地域的文学空白,北方文士的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虽然不能与同一时期的南方地区相比,但将区域文学中心推向今甘肃、关中、内蒙古和辽东等地。史念海《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一书统计了《晋书》各列传所记载的汉族文士有70人,而这些汉族文士就源于以上区域[25](P.268),在带动边地文学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河北籍卢玄、高允、邢颖、游雅等“神麚征士”被征入平城后,以其文书写作发挥政治作用,形成的文学传统和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北朝末期,邢邵、邢昕、卢明宣、卢元明等人来自“神麚征士”同一个家族,或有较为密切的家族姻亲关系,夯实了北方文学的发展基础。《隋书·经籍志》将河朔文化视作典型的北朝文化,使其与“江南”形成二元对举,初步实现了南北地域文学的均衡发展,改写了中华文学的地理格局。
最后,从中国古代民族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考察,诏令的文学意义在于对民族书面文学形式和表现主题的开拓。在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期,诏令是传统文学断层再生的新生事物,使文学发展的脉络延绵不绝。从存世文献来看,能够确定属于两汉民族书面文学的作品仅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匈奴歌》《行人歌》《白狼歌》等31篇,且主要是乐府诗。[26]无论是民族首领亲撰,还是由汉族士人代拟,诏令都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拓跋鲜卑本无文字,记录事情依靠图形和绳结,道武帝、明元帝时只有少数鲜卑贵族通晓汉文。现存的海量诏令却以汉语文字作为载体,可见朝廷政令的传达、官方和民间的交往已经主要依靠汉语文字,不仅保证了汉族文学传统在北方的继承、延续,而且促进了鲜卑族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从献文帝、孝文帝父子开始,北朝帝王形成了亲自作诏的传统,特别是孝文帝,“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18](第一册·卷七《高祖记》P.187)。《文馆词林》保存着北魏孝文帝、孝静帝,北齐文宣帝、孝昭帝、武成帝、后主,北周武帝、明帝八位帝王的诏书二十余篇。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以汉语文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逐渐超过其本民族的语言,获得了优势地位。这样,北方少数民族就有了与汉王朝“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27](P.169)的基础,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
——论汉文帝诏令的个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