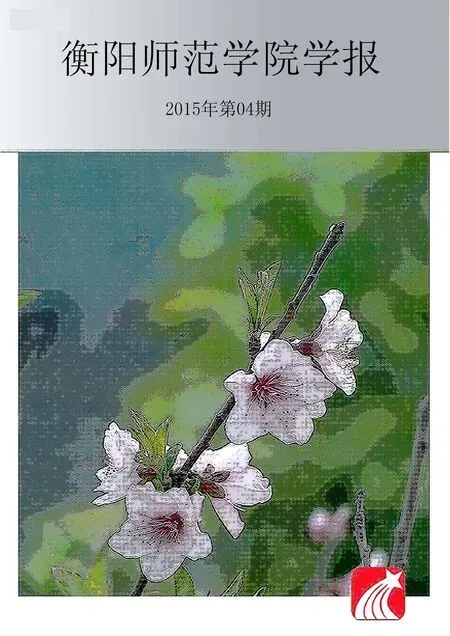近百年来王船山《读通鉴论》研究述评
刘 荣
近百年来王船山《读通鉴论》研究述评
刘 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学界以往甚少有对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的某一部作品予以专门、系统、严谨之研究者。历来为人评价甚高的《读通鉴论》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该书在被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曾经经历了曲折又复杂的问世以及流行的过程,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成为学界80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成就硕果累累。因此,对以往学界关于《读通鉴论》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综合性的叙述和评价就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弥补学界以往在此项工作上的空白,更是期望今后的《读通鉴论》研究以及船山学研究能够在此综述所揭示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深化。
研究述评;《读通鉴论》;近百年来;王船山
学界公认,明清学术、思想研究乃20世纪以来的显学之一。生当明、清鼎革之际的大学者王船山,因其毕生著作数量之多、堂庑之广和议论之深①,尤为后世所推重,“船山学”研究方兴未艾且大有可为。但是,以往甚少有对船山某一部作品予以专门、系统、严谨之研究者。②历来为人评价甚高的《读通鉴论》便是其中之一。
从形式上看,该书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为文本依据,对其中记述的部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政策制度等内容予以评说和论断,间或从中引出或发表自己的见地。很多学者据此判定其为史论专书。但实际上,深入阅读和思考一下该书便会发现,《读通鉴论》可以从史学、哲学、政治、民族、军事等等多个视角和层次进行解读和诠释,绝非史论一项内容所能涵盖。是书始撰于1687年,写成于1691年③,值船山离世的前一年。越明年正月,船山卒于湘西草堂,享寿74。从时间上看,该书乃船山生前仅次于其最后一本著作《宋论》而完成的作品④。然而,《读通鉴论》一书在写成后的170余年,即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问世;其后便脱颖而出,迎来一段昙花一现般的绚烂光华,在半个世纪里为世乐道和追捧;20世纪30年代起才以寻常的姿态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对此,笔者另有专文具体考论了该书在被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经历的曲折又复杂的问世以及流行的情况,此不赘述⑤。
20世纪30年代直至今天的80多年是对或者围绕着《读通鉴论》一书开展专业化的学术研究的时期,成就硕果累累。因此,对以往学界关于《读通鉴论》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综合性的叙述和评价就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弥补学界以往在此项工作上的空白,更是期望今后的《读通鉴论》研究能够在此综述所揭示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深化。对是书近百年来研究综述的展示将是本文的重点,所述地域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也将被收录。在资料的选取上以代表性的资料为主。在论述思路上,主要通过两大层次分别展开:针对性研究综述和相关性研究综述。前者是对《读通鉴论》一书作针对性的专门研究的论述,后者则就围绕着该书的不同方面或角度开展研究而做的成果描述。
一、针对性研究综述
首先是专著方面。截至目前,所见的仅有两部以《读通鉴论》为题的著作。第一部是出版于1982年的李季平的《王夫之与读通鉴论》。该书的篇幅并不大,《读通鉴论》也并非作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因而只在书中的最后部分有所涉及。作者首先揭示了王夫之从事著史、论史的四条一般原则和宗旨:实录精神、公正不“挟私”、反对记载邪妄以附会人事和以史为鉴。其次,作者认为,王夫之在批判理学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中建立了发展进化的的历史观,而且,历史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的趋势和规律的,即“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理论。以这种进化史观为思想基础,王夫之在政治主张上提倡厚今薄古,主张变法革新,从而驳斥了理学家的复古主张和历史倒退论。第三,王夫之在评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时采取的分析的态度也是其坚持的进化史观的反映,从而在某些方面揭示了长期以来被歪曲了的历史真相。
另外一本是香港学者宋小庄的《读〈读通鉴论〉》, 1991年出版。总体而言,该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借鉴西方历史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总结了《读通鉴论》中包含的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历史观等历史理论。作者从史鉴、史识和史德三个方面概括了历史认识论;把《读通鉴论》使用的史学方法归结为因果法、比较法、考辨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五种;作者认为,王夫之“对历史观的主要课题都进行了探索,并给予回答。对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他以进化史观和治乱分合史观来解释;对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原因,他以天理史观来解释;对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以圣贤英雄史观和民本史观来解释,达到我国当时历史哲学的最高峰。”⑥其中,王船山的治乱分合史观并非循环史观,是变化的进步的循环,套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螺旋式上升。他所论之“天”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一)敬畏天命,兼顾人事;(二)探求天理,关注民心;(三)人凭天时,成其大业诸义等三个涵义。而且,其“天理史观并不限于天理两个概念。对历史发展的可知的规律,他以‘理’解释;对历史发展必然趋向,他以‘势’解释;对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机,他以‘时’‘数’解释;对人顺应历史的作用,他以‘几’解释。”⑦王船山既没有片面鼓吹帝王创造历史,也没有片面断定人民推动社会。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读通鉴论》所包含的900余篇史论作有机地归类、分析和综合,从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和法律思想六个方面分别再现了《读通鉴论》体现出的治国思想。作者对这一部分的处理用功颇深,试图将船山的近千篇史论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不过,作者在此也仅仅对《读通鉴论》一书的字面意思作了解读,换句话说,作者只是把王夫之《读通鉴论》的文本内容用现代话语翻译并分类整理、罗列了一番,没有深入、有效地进行理解和诠释。
李季平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宏观地捕捉到了一些《读通鉴论》体现出来的史学思想,缺乏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分析和理解。宋小庄意在全面探讨《读通鉴论》一书,不管是对其中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探究,还是建立体系分述各类治国思想的努力,都足以表明他对该书价值的认可和重视。但整体地看,除了在运用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框架范围船山历史理论上见出一些新意外,作者对该书的挖掘仍然比较单薄,欠缺深度。总之,这两部著作毕竟是《读通鉴论》研究领域里的难得的专门之作,其选题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眼光,代表了上个世纪后期《读通鉴论》研究的水平。
论文方面。以《读通鉴论》为中心的专题论文计有20余篇,我们选取代表性的成果予以论述。雷敢在《略论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历史观》(《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中论述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关政治历史方面的观点。他不仅认为王夫之坚持进化史观,而且认为这种历史进化的思想是以其“日新盛德”为哲学基础的;进一步地,王船山在政治上主张革新。王船山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的标准和依据: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其中,“严夷夏之防”尤其是通古今的大义,是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最高准则。陈斯风则在《试从〈读通鉴论〉探船山进化史观》(《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专门探讨了王船山的进化史观及其局限性。认为虽然王船山在批判传统史观缺点的基础上又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进化史观,但他只承认社会运动的渐变,反对各种形式的革命性的变化。其次,其史论还停留在尽可能客观的描述史实水平上,远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阶段,特别是对历史进化的动力没有深究。最后,船山史评的标准仍未脱出礼乐伦常之类的儒家道德框架。王彦霞在《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史论价值》(《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中高度评价了《读通鉴论》一书的史论价值,认为该书对历史的评论达到了相当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史论的最高水平。但该书也未能避免中国古代史论的普遍缺陷,即“以文饰史”,作者所掇取的史实有的经不起推敲。胡刚、唐泽映的文章《从〈读通鉴论〉看王船山的民族观》(《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则就《读通鉴论》的民族观作了初步的剖析。在作者看来,王夫之的民族观表现为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种族偏见,严防夷夏之辨。比如,他不主张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少数民族不能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等。这种民族观是同他的一些正确方面的历史观相矛盾的。但作者并没有谈及王船山的历史观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以及同民族观的矛盾之处。刘德春则从“士”的视角入手研究《读通鉴论》,他视王船山所论之士、君子、君子儒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认为《读通鉴论》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在《知识分子的拯世情怀——〈读通鉴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中,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救世使命主要表现为:对天道的体察认知,对治道的维护拯持,对学道的传承光大。三者密不可分。发现和认识社会历史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是救世的基础,开物成务、经世致用、治理国家是救世的目的,而传承文化、光大人文精神则是救世的命脉所在。还有论者从《读通鉴论》中挖掘到了王夫之的战争伦理观,认为王夫之基本的战争伦理思想是:在战争权利上,以正统的国家意识为准则,强调战争参与和发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在战争行为上,以传统的人本思想为准则,强调战争过程的道德性和合目的性;在战争主体上,反对国家投降主义,强调“与人争战”的伦理原则以及基本道德固持。这些思想既与其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也与他的遗民心态及其伦理归属感息息相关。见宋雪玲《论王夫之的战争伦理观——以〈读通鉴论〉三国史评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此外,宋小庄专门撰文《〈读通鉴论〉所论史事举误》(《船山学刊》1991年第12期),以《资治通鉴》为据指出了《读通鉴论》中出现的七处史事错误。但认为此乃大醇小疵。欧厚钊注意到了《读通鉴论》中出现的“清贞”一词⑧,认为这是个全新和有意义的概念。王夫之虽然未对这一概念下过定义,但基本等同于“清正”。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政治品格,是清德在政治领域里的体现。徐麟以《读通鉴论》中的人物刘琨为切入点⑨,通过分析王夫之对他的评价,进而对王夫之的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的理解:我怀抱刘越石那样的孤愤,力图匡复华夏民族的社稷,但同他一样把路选歪了,没有办法实现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所幸的是我的下场比他要好一点,得终天年;但我心里的这口气终究不能平复。
综上所述,以往论者以论文的形式展开对《读通鉴论》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较晚,成果不多。从研究的内容和领域上看,大部分集中于对该书蕴含的史观、史论和民族思想的探讨,虽有个别新见,但在具体内容的阐述上多有相似之处;很少拓展其他领域和面向的研究。研究方法方面也无足观。这些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基本体现在针对《读通鉴论》研究的专著上面。总而言之,学界以往有关《读通鉴论》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全面或部分地对其进行诠释或者探讨其与王船山其他思想或著作的关系,应当成为今后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方向。
二、相关性研究综述
我们一直强调,该部分是围绕着《读通鉴论》一书的不同方面或采取不同的角度而开展的研究工作,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此项研究没有边界可言。前辈学者事实上已经点出了或者通过自己的开创性工作揭示了该书可能包含的研究范围:梁启超认为该书和《宋论》虽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⑩嵇文甫认为“在他那看似不成统系的许多经义史论里面,实蕴藏着很微妙的一种历史哲学。”○11杨昌济认为“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我辈所当知也。”○12而钱穆则主张:“观其最后著作《读通鉴论》、《宋论》两书,今人皆以史论目之,不知其乃一部政治学通论,于历代政治上之大得大失,以及出仕者之大志大节所在,阐发无遗。”○13由是可以看出以往学人看待和理解该书的四个角度:历史学、历史哲学、民族思想以及政治思想。而纵观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由以切入的视角或侧面也基本没有走出上述的矩矱。因此,下面对有关《读通鉴论》研究综述的论列将分别从历史学、历史哲学、民族思想以及政治思想四个方面进行。
1.历史学的角度
不可否认,除《读通鉴论》外,船山尚有其余几部历史著作。萧萐父将王夫之的史学著作分为早期和晚期所写,并认为晚年所写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才是他的史论的代表作○14,可谓的见。但其中又有别,王夫之在《宋论》中只论评了有宋一代的史事和人物,而对《读通鉴论》的评论则涵盖了中国历史上十几个朝代的1000多年的历史。从篇幅上讲,后者无疑更广大。这其实也暗示着,议论纵横千余年宽广历史的《读通鉴论》更充分、自如和深刻地灌注了王船山的历史思想。一句话,《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论著。除史学思想外,其包含的历史哲学、民族思想和政治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也在船山著作中最具典型性。
鉴于该书的写作性质,从史学角度研究《读通鉴论》的学者在数量上是最多的,成果也是最丰富的。最早着手研究的当是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集中体现其船山学研究的《船山学案》一书。该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后在1982年由岳麓书社再版。作者曾在“序”中自述写作缘起:王船山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学术界对他的丰富思想遗产也还缺乏真切的了解。所以,作者在书中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掘发船山遗留的思想宝库。作者认为,王船山的人类社会历史观的基础理论建筑在他“氤氲生化论”的自然进化史观上。但同时,“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和自然史演变相等的,而有其具体的法则”○15。这一法则是“理”,他把理看做客观历史的发展律,把握到了理势统一。对这一法则的把握是王夫之在历史理论上“破天荒”的创见之一。王夫之的另一创见是,他说明了历史研究的任务重在明了历史的得失成败,以为人类的借鉴。同时,王船山还批判了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秦汉以下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历史观。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王船山的历史观。认为,王船山对中国历史三种离合阶段的分期法是进步的,对打破古人的三统说是有力的,而在质的移行法则上讲来,却是贫乏的。“明末清初的时代还没有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中心力量”○16则是这一贫乏观点的原因。该书实际上开启和奠定了建国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船山史观的范式。
作为建国后船山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萧萐父先生的研究成果一直备受学界重视。他曾于不同时期写作了许多有关船山及其研究的论著和论文,以《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17和《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18为代表。到了晚年,萧萐父又将自己以往关于船山学研究的成果汇总进《王夫之评传》一书。这本出版于2002年的著作,实际上囊括和最终代表了萧先生毕生研究王船山的成果。该书体例谨严、论述全面,且立意鲜明,把王夫之定位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重在挖掘其思想中反映和体现出来的早期启蒙思想。该书特意辟出一章专论船山的“史学思想”。作者看来,“依人建极”的原则,是王夫之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在社会历史的领域中,王夫之主要是从‘类’的观点,而不是从个体的人的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19他不仅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作出了考察,还“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去探寻具体的社会关系、制度、设施与依附于它们的政治立法原则、伦理规范及其一般原理的关系问题,即社会生活和实践领域中的‘器’与‘道’的关系问题。”○20王夫之创立了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即“理势合一”、“理势相成”的学说;还深刻阐述了“天理”与“假手”,即历史的客观规律性通过人的历史实践而展现的观点。王夫之思想中“天”这一概念的存在,基本上摆脱了神学史观和天理史观,也力图摆脱英雄天才史观。总之,作者认为,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以“人”为起点,又以“人”为归宿。不过,作者也指出了王夫之史学的缺陷和不足,歧视劳动群众是其历史观的根本缺陷。其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论,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循环论的束缚。其“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说,基本还停留在用人的“意见”、尤其是圣人的“意见”来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水平上。萧萐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其研究工作更有着前人不曾具备的哲学思维和视野,充分体现了其哲学家的识见。
台湾学者杜维运有《王夫之与中国史学》一文,后被收进其主编并于197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中。为了回应西方史家认为中国史学只有叙事而无历史解释之艺术的误解,作者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专门从事于历史解释之史学作品,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便是其中的代表。该书较正史论赞更接近西方史学中之历史解释者,表现在:“一曰渊源之追溯也,二曰原因之阐释也,三曰背景之分析也,四曰变迁之缕述也,五曰影响之探究也。”○21除此外,作者认为王氏有一套极高明之史学方法论。总之,作者通过介绍王夫之的历史解释艺术、历史哲学、归纳史实与比较史实、历史解释之基本思想、史学方法论等内容,不仅回击了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一直以来的偏见和歧视,论证了西方史学所有者,中国史学亦不遑多让。同时,指出了王氏对中国史学的诸多贡献,认为其应该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作者采取的比较史学的视角很新颖,能更好地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夫之的史学并在世界史学的范围中反思中国史学。
冯天瑜的著作《明清文化史散论》主要探讨了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历史领域的表现则以“王夫之理性主义历史观探微”为题予以论述。作者同样注意到了王船山对中国历史上各种命定论历史观的批判,并详细列举了这些历史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三国时流行的“正统说”、唐宋的“道统相继沦”、邵雍的“元会运世说”和朱熹的“划运说”。并认为,“夫之本身并未全然冲决气数史观的罗网”○22。同时,作者认为夫之的“理”与黑格尔的理性颇有近似之处。在作者看来,王夫之之所以能够批判各种历史观,原因在于他使用了理性主义的武器。这也是王船山历史观的特色。
围绕《读通鉴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王船山的历史观和史论的当推黄明同、吕锡琛二位学者合著的《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一书。是书出版于1986年,内容上分为两大块。作者先是阐述了王夫之在历史观上的贡献和内在矛盾以及归宿,后又介绍了王船山的史论。王船山的历史观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有其内在的逻辑。综观作者对王夫之历史观的贡献的论述,不难发现其基本框架和思路乃是建立在借鉴、吸收前贤特别是萧萐父等观点的基础上的。但作者在具体内容的论断上仍然突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王船山的历史观,从研究人的本质开始,建立其历史观的理论大厦”○23,“王船山历史观中的人,是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统一”○24。“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表现是一治一乱的循环,但他的循环论已不同于以往的治乱循环论,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以气释社会治乱,把社会治乱归结为气的变化,气盛则治,气衰则乱。社会治乱的内在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25其治乱循环并非简单、机械的重复,是以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为基础的,不是封闭式的历史循环论。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上,“王船山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着内在必然性,强调其规律性,但没有正确揭示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26王船山历史观的突出贡献是,比较合理地回答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客观必然的关系,人的能动作用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其历史观也存在着一些内在矛盾:他一方面承认客观的理、势为社会发展自身的必然,人不可违抗;另一方面又把天理说成人心所固有,过分夸大心的作用。“王船山在他的历史观的终点树起了‘尊君’的旗号,从而使之终于陷入了圣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27作者对船山史论的论述并无新意可言,基本是陈陈相因了前人的观点。虽然该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仍然不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窠臼,但其建立船山史观体系的努力和其中闪现的一些经过辩证分析的见解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
此外,台湾学者林聪舜也在其《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1990年出版)一书中谈到王船山的历史观。他认为,船山对“理”、“势”、“天”概念的分析显示了一种辩证的历史观,原因何在?这与船山的身世有关。此辩证的历史观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天道的信赖以及对历史变迁之光明面的肯定;而船山所处的时代却是天崩地解和价值理想失落的时代。故而,肯定天道的存在和历史的光明面,将其所处的时代视为“天”,曲折表现其自己的暂时历程。如此,既未漠视当前所处环境的晦否,又能维系自己对历史前途的希望。
以上论者皆承认船山有一套独特的或者完整、自成体系的历史观,其史学思想和理论的某些内容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突破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部分学者在指出其史论贡献时,也比较客观地探讨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但与以上论者的观点相左,也有个别学者并不认可《读通鉴论》的价值,或者不满于前人对其价值的过高评价,从而严厉批评并指出了船山史观中的缺陷。前者如严复,他曾说,“王夫之之为通鉴论也,吾之所谓然,二三策而已”○28。也许,严复对该书价值的评判和取舍有着自己的标准,我们对此不得而知。后者如蔡尚思。他在1985年出版的《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中公然声称:“对于清末以来的‘学术权威’对王船山的评价,不要过于迷信,以免束缚自己的思想”。显然,作者是不同意对王船山的过高评价的。作者企图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王船山的整个思想并且抓住其中心,认为虽然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最大贡献而占重要地位,但其落后思想也很突出。表现在史学上,有时承认历史进化,但主要是宣扬历史退化论;宣扬历史循环论和地理决定论;且往往不顾及历史事实而发议论。作者在研究中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前人对王船山的评价、勇于质疑的做法值得赞许。但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只是通过摘抄部分一目了然的资料而得出比较浅显的结论来,缺少对船山思想的深入解读和挖掘。
散见在各种期刊上的专题论文也从史学的角度对该书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吴怀祺和王记录均注意到了易学和王夫之史学的关系。二人均认为,王夫之的易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紧密相联,他以史证易,又以易论史。吴文《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6期)总结了王夫之易学对其史论的深刻影响:一,通变思想影响了其对历史兴衰的总结;二,重人事思想,人事在历史兴衰中有重要作用。王文《论易学对王夫之史学思想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对王夫之将历史变化看做一治一乱一离一合的循环论的看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只注意到王夫之的一些词句而没有注意分析这些词句背后的深刻内涵”。因为在王夫之看来,这种治乱往复的简单循环,绝非普遍现象。是历史以断续形式表现出来的发展状况,他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继承关系,更非机械的重复与循环。范阳《论王船山历史观主要范畴的脉络》(《哲学研究》1983年第9期)通过阐明王船山历史观范畴的内容及其相互连结,意在揭示其历史观的总体轮廓。王夫之历史观中的主要范畴,是有层次可分的,大体上是从“理”与“势”开始,上溯“天”与“道”,下连“时”与“几”,以及联系其他范畴如“象”与“数”、“隐”和“显”、“常”和“变”等组成一个体系。但前三对范畴实际清理出了王船山历史观范畴体系的脉络,他们分别用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及其本质以及认识和把握王船山提到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规律。张岱年与汪学群则分别在《王船山的理势论》(《船山学报》1985年第1期)和《王夫之的理势观》(《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中专门就船山的“理”与“势”做了辨析。前者阐释了理势论的基本要义,认为船山析理为二:必然之理(条理)和当然之理(至理)。在理势关系的涵义上,除了意识到前人常讲的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历史的客观规律关系外,张岱年认为还包括现实与理想的问题以及强权与公理的问题。在汪文看来,理势观的提出乃是王船山借经义阐发己义的经学阐释模式的范例。但作者对理与势及二者关系的讨论仍旧延续了前人的见解,无甚新见。孙钦香重新思考了《读通鉴论》中提到的“三代之治”的问题。她认为,船山封建、井田之论不是在证明和解说历史进化与否,而是在此史论中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封建、井田之制作为三代之良法其得失何在,以及后世该不该效法此等制度设置问题○29。叶建华认为王夫之对史学的本体理论做过较多的论述,自成一定的体系。书中的《绪论》四篇堪称史学理论名篇○30。其史学本体论包括:史学目的论、史书编纂论和史学评价论。
李锦全撰文专门探讨了王夫之历史观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在《论王夫之历史观的内在矛盾》(《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中,作者强调,王夫之历史观中有着三对深刻的内在矛盾:王夫之虽然承认社会的进化发展,并有着必然趋势和规律,但也只是抽象的逻辑推衍,是理论上的突破,至于现实社会向何处去,他却感到迷惘,从中也暴露出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在如何处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王夫之的思想也是存在矛盾的;第三对矛盾体现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认识历史的创造者问题上。作者最后同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前,一切进步思想家包括王船山历史观的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还有论者采用比较的眼光讨论船山史学思想的特点。施丁和严衡山是将王船山与司马光的史论拿来比较的代表○31。施文通过大量举例《读通鉴论》中的史实,比较二人在认识、分析、见解等方面高低、深浅和优劣。认为,王夫之的批判,不仅有认识史实之纠弊,还有史论之观点与方法之针砭;司马光史论的主观性较重,而王船山的则比较客观。严文分析了两位史学家史学思想的异同及其产生异同的原因:二人都有提倡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等共性,但是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评价社会历史的标准等方面二人有显著的不同。导致这些异同的原因包括二人在政治观点、写史的直接动机和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张世英则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对船山的“天”作了解读○32。伽达默尔主张的融合过去与现在、古与今的“大视域”,即将历史事件与人物置于其后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从整体上去理解的做法,深契王船山那种对以“势”为基础的“天”的理解。“天”是其历史研究的一种视域,要求人们从历史流变过程的整体看待历史。同时,观看历史的“天”和“大视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二者一中一西,相互辉映。
美国学者S.Y.Teng在《Wang Fu-Chih’s Views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8,No.1,Nov.1968)文章中对王船山的历史观与历史撰述有所阐发。作者主张,王夫之的历史观无疑受到了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也与其社会和道德思想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却明显的具有开创性。作者赞同王夫之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谈及为何王船山的历史理解如此深刻和特别时,作者认为其早期波澜壮阔的生活经历才是他得以对历史有着深刻理解的原因。
2.哲学的角度
准确地讲,该部分主要是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讨论《读通鉴论》的。虽然第一部分中也有着类似历史哲学的理论和观点,但应该说,“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是有区别的”○33。依贺麟的观点,“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是以哲学的原理为主,而以历史的事实作为例证和参考,因此它是哲学而非历史。”○34因此,前人特别是大陆学人在阐述船山历史哲学时,很多便遵从了这一思路:先讲船山一般的哲学见解,再讲他的历史哲学。我们在此只是处理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
最早注意到《读通鉴论》蕴含船山的历史哲学并着手进行研究的当是嵇文甫。他在1935年写有《船山哲学》一书(后被收进其1962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论丛》),里面提到,“在他那看似不成系统的许多经义史论里面,实蕴藏着很微妙的一种历史哲学。”○35他从古今因革论、朝代兴亡论和华夷文野论三方面阐述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其中,古今制度的因革被他视为船山最卓绝的历史见解。在作者看来,船山的历史哲学终归是其“新天理史观”的体现,把天理和人情事势打成一片,拿活生生的现实历史去充实天理的内容。虽然是书乃船山历史哲学研究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但真正从哲学的理趣而非历史的观念出发去阐释船山历史哲学的,贺麟算是第一人。
贺麟《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一文写于1946年(后被收进其《文化与人生》一书,1988年出版)。作者总结了王船山研究历史哲学的三个方法:第一、先得出哲学原则,再应用、发挥于其历史哲学;第二是现象学的方法;第三是体验方法。在作者看来,船山在历史哲学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的辩证的历史观。特别是,他对于天道的矛盾进展或辩证法观点,默契于黑格尔理性的机巧的历史观。但却早于黑格尔而提出。也即,作者认为王船山的天或理是类似于黑格尔的理性或上帝的思想。贺麟的这种将船山之天比作黑格尔理性的机巧的思想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深刻的启发和影响。
港台地区的大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将其《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的论述止于王船山。作者虽然没有在书中专门阐述船山历史哲学的内容,但将其置于自己构建的船山思想体系中之一环的位置予以概述,这同样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大致了解船山的历史哲学观念及其与船山整个思想体系的内在关联。作者对历史哲学的涉及集中在“人文化成论”一章。由于重“气”,船山善论历史文化。“船山将历史文化不只视为吾心之理之例证,而视之为客观存在”○36,“乃指个人精神和行事表现和影响于客观社会,能化成乎天下后世。”○37这当中,船山的历史哲学便充当了其中一个角色或者说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船山“论历史不止于褒贬,而可论一事之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世运之升降。”○38他“重观一史事之特殊性,于一一之事见一一之理;重论一史事之时势;亦重论一事影响之社会价值、文化历史价值。”○39总之,作者眼中的船山,“本其哲学思想之根本观念,以论经世之学,由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事业,通性与天道与治化之方而一之者”○40,而历史哲学便是船山外王事业之一端。唐君毅的这一研究理路对上个世纪70年代后的台湾船山学界有着深远影响,台湾船山学研究领域里的知名学者,如曾昭旭、林安梧等人,均受到了唐先生研究旨趣的莫大影响。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船山学研究思路基本上就是在接踵唐君毅,只是在具体的语言表述和成果的表达方面有所不同。
台湾学者罗光亦对王船山有着比较独到的研究。他在《罗光全书·王船山形而上学思想历史哲学》(1996年出版)中肯定《读通鉴论》乃中国历史上少数基本讲历史哲学的书。认为,“王船山的历史哲学,承继《春秋》的思想,以天命史观和伦理史观为主”○41,并且创立气运史观。《读通鉴论》一书的历史哲学有三个观点:(一)历史的时代意义;(二)历史为天理人道的历史;(三)历史以民为本。
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1985年版)中曾涉及王船山“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但作者主要把着眼点放在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上。认为,王船山对历史演化过程的描绘同柳宗元相似,但又在后者“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并进一步阐明了柳宗元已经指出的不能用历史上个别人物的动机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的这一思想。同时,作者指出,“王夫之讲理势统一,接近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42
台湾学者曾昭旭的大作《王船山哲学》初版于1983年、再版于2008年,是船山学研究领域里很有成就和影响的一本专著。是书第二编介绍了船山历史哲学。前已提,曾昭旭和接下来要介绍的林安梧作为台湾地区的船山学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旨趣深受唐君毅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曾文看来,船山“重在更从此道德主体向外发以成就具体的道德事业,使其学之趋向,乃不是由末反本而是由本贯彻于末的……由本贯末,则即体致用而全体在用。”○43船山即由此而建立其史论,《读通鉴论》便是代表之一。作者认为,船山历史哲学的根本要义是“道德的天命观”。“既重天命,而天命下贯,于人则为大公至正而无私,于事则为各当其时而顺势”○44,“其论史亦是以天命之大公至正为大纲,而降论人之公私,事之顺逆,而终于论法物之同具道德庄严者。”○45不难看出,船山之历史哲学乃是“由本贯末”之末之一段,即道德事业之一表现。
另一位台湾学者林安梧将船山历史哲学等同于狭义上的人性史哲学。在其1987年出版的《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中,作者对人性史哲学做了解释:人是天地之心,宇宙经人之创造成为人之宇宙,即历史文化的宇宙,人即于此历史文化宇宙中长养自己,复以之参赞此历史文化宇宙。作者不同意大陆侯外庐等学者的主张,即先建构一套自然史的哲学(天道论),然后再由此演绎而生出一套历史人性学(人性论),之后再将之运用于历史的解释下;相反,整个船山系统即是一历史哲学的系统(自然史哲学,历史人性学及人性史哲学),此系统中充满着浓烈的历史意识。“史论史评并不是理论建构的导生物,而是参与整个船山学的理论建构的。”○46理势合一论是船山人性史哲学的核心论题,是船山经由人性史世界的通观而寻得的一个历史的法则。
最后,是大陆学者邓辉的《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 2004年出版。作者认为,船山历史哲学有广、狭两义之分。广义上可以将其称之为历史性哲学,即宏观的历史哲学系统。狭义上则是其具体的历史哲学思想,即将其历史性哲学贯彻于人类历史研究所体现的思想。它直接体现于其史论史评中。作者首先着力阐发了其一般哲学思想,并将其贯彻和应用于具体的历史哲学。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具体来说,就是“时亟变而道皆常”的历史规律论、“人极立而道术正”的历史动力论、“一治一乱、一合一离”的历史形态论、“理势相成”的历史趋势论和“凝道生德而全质备文”的历史意义论。作者也构建了一套船山思想解释体系,从船山对宇宙生化的认识开始,继之考察其历史性哲学,然后再研究历史性哲学之历史实践——具体的历史哲学。不难看出,邓辉的思路是属于大陆嵇文甫、侯外庐和贺麟等这一论述体系的。探讨过程中,作者借鉴了不少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如现象学等;与此同时,也有意识地展开中西比较,通过西学彰显船山哲学的一些特点。论及船山具体的历史哲学时,作者似乎没有讲清楚“道”具体何所指、人极的具体表现有哪些等问题,只是泛泛而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
通过历史哲学的角度探研《读通鉴论》一书的论文却不多。黄明同有《王夫之历史哲学的逻辑路径初探》(《哲学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王夫之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实际上,该文充当了我们上面曾提及的《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一书的提纲挈领式的作用。为此不再具体展开论述。段塔丽的《王船山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船山学刊》1998年第2期)几乎就是在复述贺麟《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一文的看法。
与上述学人认可并努力挖掘船山历史哲学的做法针锋相对,台湾哲学史家劳思光认为船山的史论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因他对“历史规律”、“历史知识”、“历史之意义”等观念缺乏论断。只可说,在广义的标准上船山有某种“历史哲学”矣,因他毕竟也论及过历史演变的性质等问题。依作者之见,“船山史论中的文字一部分只能划归文人议论之列,大抵依于臆测,随意发挥,既无史学价值,亦与哲学无干。一部分属于对史事作价值判断之风气,只是价值理论或道德理论之应用,均不足视为‘历史哲学’之资料”○47。
3.政治学的角度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对船山的政治思想有很高的评价,其《读通鉴论》中含蕴着船山重要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且“乃汉唐以来诸儒所不能发”○48。熊十力曾举一例说明,他将“有圣人起,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这句话理解为,此乃虚君共和制。尤其是前一句,表明船山主张制定宪法。应当说,熊先生有意从船山著作中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寻找能提供政治制度建设之借鉴的传统思想来源,但他只是孤立地抓住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没有虑及具体的语境及船山整体思想的趋向。
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对船山政治思想有所论及。他认为,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虽然泛论史事,但其中对政治问题别有见解,且贯注着他一贯的精思。作者提到了船山论政的要点有二:“一曰法制之不能泥古,船山本此而论封建与郡县之不同,及于井田、取士、兵农分合诸端;二曰为治之不可恃于法。”○49作者于是书论及船山部分甚为简要,且只关注到了船山政治思想中的极少的一部分。
牟宗三在其《历史哲学》和《政道与治道》二书中均援引过《读通鉴论》的部分内容,为己所用。在《历史哲学》中,他通过王船山的一些看法来表达他自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见解,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意味。在后书里,作者实际上以王船山为例,说明明末诸儒虽反省外王之道,重经世致用之学,“然一触及而不能把握此问题之肯要与症结,故亦不能审思而明辨之”,“不能从义理上开出应然之理路”○50。作者的评价是,“其识量与心愿,可谓深远宏大”,但“船山心思至此而穷”○51。
萧萐父、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一点。首先,作者断定,“王夫之的政治思想,肇因于对明王朝灭亡之教训的总结”○52。其次,王夫之批判了3000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指出了其本质上的非道德性。进而,他提出了以集权和分权相结合为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以法律限制君主权力、实行分权制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保其族、卫其类”,实现民族之振兴是其立论之归宿。既然帝王的“私天下”是导致汉民族不能自固其类的根本原因;为了自固族类和打破私天下,倡导分权而治的公天下,是王夫之政治思想的核心。作者向我们描绘和呈现了一副船山政治思想体系的图景,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为我们勾勒的船山政改方案;但个别以西方制度之名包裹下的改革措施是否代表了船山本人的原意,颇值得商榷。
对船山政治观有专门研究和论述的是陈远宁。他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是船山政治思想研究领域里的专著。该书从“公天下”的思想、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治、德教与刑罚、养民与治吏、举贤才与养士、论“民变”和论“华夷之辨”八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船山政治思想的内容。其中的一些见解值得注意,比如,王船山的“公天下”思想本质上是对传统儒家“公天下”思想的继承,但又多少吸取某些“异端”思想的因素;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他的基本倾向是继承儒家强调圣君贤相的“人治”观点的,而他的新特点则主要在于,更加明确地运用了“任人”与“任法”的概念,并对之作了具体阐发,同时把法治提到更高的地位;等等。作者的结论是,王船山的政治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它是沿着正统儒家思想的轨迹,以重民思想为核心,兼采诸家之长,对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作者虽然比较全面地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读通鉴论》中体现出的船山政治思想,但缺乏对这些不同侧面之间相互关系的解读,没有真正地走进船山政治思想的世界。
与上述几位学者对船山政治思想的积极评价不同,劳思光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下》中认为,船山政治思想最显著的特色有三:民族主义之倾向、传统主义之倾向和对“权力均衡”及“社会平等”之反对。具体说来,“船山之强调民族独立,并非以‘民族平等’之观念为基础,而实以民族之‘优劣’分别为假定”○53;船山“从未致疑于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之有缺陷,亦未深究君主制度内部结构有无问题,但就特殊行动立论。”○54同时,他对“相权”无确实了解,因而其在《读通鉴论》中的论述颇多舛误。船山心目中只肯定君权,其政治思想只停留在“圣君贤相”之理想上。
论文方面。谷方在《论王夫之的民本思想》(《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中论述了船山民本思想的表现和主要特点,并得出结论说,王夫之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非是地主阶级,而是贫困的农民群众。允春喜则在分析了王船山民本思想的政治逻辑○55后认为,王船山把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传统发展到了极致,但仍渊源于传统的民本思想,这使他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缺少对专制制度犁庭扫穴般的勇气。他在认识上最终没有迈入“近代”的门槛。在刘先枚看来,《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政治哲学的代表作,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但作者对仁义哲学特点的分析并不明确○56。李宝臣《论王夫之的治统道统观》(《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则认为,王夫之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治统”、“道统”的历史通则。基本内容可归纳为:圣君、人治(臣操)、农本、等级、尊贤、华夏几个方面。
4.民族思想的角度
萧公权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下)中探讨了王夫之的制度论和民族思想两大内容,尤其推崇其民族思想。认为“船山思想上最大之贡献,为其毫不妥协之民族观”○57,船山所揭橥者乃“二千年中最彻底之民族思想”,云云。与以往的观点相反,作者认为船山抛弃了传统思想中以文化为标准之民族观而注重种族之界限。其中缘由有二:一是本诸群类自保之义,种族之自存自固乃自然界之普遍规律;二是船山认定中国之文化高尚优美,远非外族之所能及。
陈远宁在《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中认为,“华夷之辨”是王船山民族观的核心,其根本旨归是在于,保持华夏族的强大及其在“九州”之内的绝对统治,认为这是超越于“王道之三纲”的最高治国原则和封建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作者同时不讳言,“王船山的民族观确实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人们把王船山的民族观评价过高,是值得再研究的”○58。
所见专题论文亦不多。针对有论者断言王船山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种族主义偏见在其晚年已不再占主导地位,谭承耕撰文《论船山晚年的民族观》(《船山学报》1985年第1期)予以回应。谭文通过征引和分析材料,得出了如下不同意见:船山早年、晚年的民族观是一贯的,晚年是早年的继续。在晚年虽有些新内容,但并无本质的变化。他对清朝政府的敌视态度,到晚年也无改变。胡发贵则为王船山的夷夏观进行了翻案,他坚持认为,那种主张夷狄是禽兽的论断乃是对船山著作断章取义的误读和曲解。王夫之夷夏论中确有一些鄙薄、贱视夷狄的成分,但主要是基于文明观照之上的文化优越感,而并非是对夷狄的全盘否定。他是根本不可能主张夷狄禽兽论的○59。彭传华的文章主要分析了王船山民族思想的历史成因及影响(《船山民族思想历史成因及影响探源》,《北方论坛》2009年第11期),作者对历史成因的分析比较有价值。他认为船山民族思想的产生主要有四大原因,其中的两点原因乃作者本人所掘发:自身理论的内在需求和“心理防御机制”作用的结果。
综上,相比于《读通鉴论》的针对性研究,该部分相关性的研究不仅起步早(发端于上个世纪30年代),而且取得的成就也最多。其次,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部分学者不苟于成见,勇于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为《读通鉴论》研究贡献了不同侧面的观照,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是书。第三,多视角、多面向的考察和探索《读通鉴论》是这部分研究的特色之一。这无疑大大丰富了该书的研究领域,为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该书提供了条件。第四,研究过程中运用和体现出的新方法、新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不失为一条以他者的视角观照自身的好途径。同时,该部分的研究也透露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首先,由于是围绕着《读通鉴论》一书而作的研究,就意味着该书并非研究者采用的唯一资料。事实是,《宋论》、《尚书引义》甚至《黄书》等船山的其他史论著作也为研究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和借鉴。缺少针对性的研究有时候让我们难以明确论者由以得出观点和主张的材料出自船山哪本史论著作,这于《读通鉴论》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是大打折扣的。其次,在某一段时期或者在个别学者那里,该书的相关处理明显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的不正常影响。不少著作和论文完全是在用某一套史观的理论和思想去范围和架构船山思想,从而非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独立和严谨的学术研究。船山思想在一些论者那里最终沦为了某种史观和理论在资料上的“批发中心”,这无疑是对船山思想的大不敬。再次,不少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在踵步前人,陈陈相因,缺乏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论者多满足于对该书字面意义的解读,不愿进行深入的诠释和理解。更有甚者,断章取义者也不在少数。或者,一些研究者自动束缚于前贤设定的研究范式中,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原有范式的修修补补或者重新包装,换汤不换药。这点明显地反映在以历史哲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上。大陆和台湾地区几代学人对此的主要研究无非分别坚守了两个不同的范式或理路,前者由嵇文甫所创发,后者则是唐君毅所启牖。
总之,自该书以寻常的姿态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后,便成为学界80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从业者不可谓不多,取得的成就不可谓不多,但为了进一步更好地推动《读通鉴论》研究走向深入,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和思考:第一,研究的态度上,应继续秉持实事求是和客观的精神。研究者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质疑的精神值得提倡。不必拘泥于前贤甚至所谓“学术权威”的做法,要批判地继承和创新他们的成果。第二,研究的内容上,一方面,在前人开掘出来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深入的研究,避免字面意义上或肤浅地解读,拒绝断章取义,孤立地阐发某句或某段的意思;另一方面,在原有研究领域外,努力寻找和开发新的研究点和方向,力争以更多的角度去处理该书。第三,在研究的方法上,不妨大胆借鉴和吸收其他一切可能对研究《读通鉴论》一书有益的方法或范式。但也应当注意避免随意性,比较方法的研究中尤其不应当做随意的比附和发挥。第四,一些具体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比如,为何王船山会在生命的最后五年着手撰述该书?该书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等等。
注释:
①煌煌16册的《船山全书》(岳麓书社整理,2011年)应是迄今为止对船山学说和著作作全面广泛而又深入的整理、出版之大成。
②笔者所见惟三种,均集中于船山的哲学著作,分别是:周兵:《天人之际的理学新诠释: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刘荣贤:《王船山〈张子正蒙注〉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庄凯雯:《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④如汪茂和点校、王之春撰:《王夫之年谱》,中华书局, 1989年版;王孝鱼:《船山学谱》,广文书局,1975年版;张西堂:《王船山学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等各种年谱记载。
⑤参考刘荣:《王船山〈读通鉴论〉考论》,待刊。
⑥⑦宋小庄:《读〈读通鉴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94页。
⑧欧厚钊:《释王夫之的“清贞”》,《船山学刊》1995年第1期。
⑨徐麟:《试析暮年王夫之的刘琨情结》,《船山学刊》2000年第3期。
⑩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84页。
○11○35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2页、122页。
○12岳麓书社整理:《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09页。
○13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页。
○14○17萧萐父:《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江汉论坛》1962年第11期。
○15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03页。
○16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5页。
○18萧萐父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20○52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15页、230页、380页。
○21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第673-689页。
○22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23○24○25○26○27黄明同、吕锡琛:《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8页、17页、38页、110页。
○28[法]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五卷第十四章按语。
○29孙钦香:《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阴山学刊》2013年第1期。
○30叶建华:《王夫之的史学本体理论》,《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31施丁:《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严衡山:《王夫之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32张世英:《略谈古今之变——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想到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33段塔丽:《王船山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船山学刊》1998年第2期。
○34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9页。
○36○37○38○39○40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7卷,《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627页、627页、629页、657页、515页。
○41罗光:《罗光全书》第18册,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76页。
○4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0页。
○43○44○45曾昭旭:《王船山哲学》,里仁书局,2008年版,第292页、271页、275页。
○46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 1987年版,第76页。
○47○53○5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4页、549页、555页。
○48熊十力:《读经示要》,广文书局,1960年版,第129页。
○49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1-142页。
○50○51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页、20页。
○55允春喜等:《王船山民本思想的政治逻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6刘先枚:《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5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5年,第640页。
○58陈远宁:《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254页。
○59胡发贵:《王夫之夷夏观新论》,《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Review on Research of Wang Chuan-shan's Du Tong Jian Lun in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LIU Rong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In the past,the scholar circle has few scholars to study specifically,systematically and precisely about one book of Wang Chuan-shan,a great scholar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Du Tong Jian Lun is one of the books which had been valued highly.Though this book had experienced a tortuous and complex process of publishing and popularization before aroused the academic attention and study,it had become the object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for the scholar circle since more than 80 years when it came into the scholar circle in 1930's.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is fruitful.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It can not only making up for a deficiency of the research in the scholar circle,but also hope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 future's research on this basis.
review;Du Tong Jian Lun;nearly one hundred years;Wang Chuan-shan
K204.3
A
1673-0313(2015)04-0013-10
2015-05-10
刘荣(1985-),女,山东临沂人,博士生,从事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