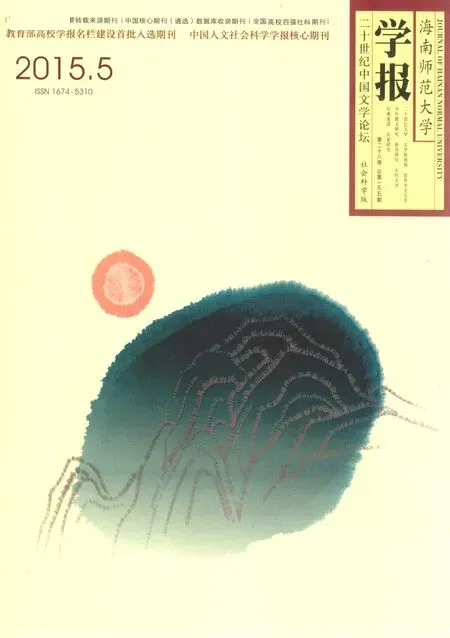回避历史与走向传统——寻根作家题材转变的文学史意义
徐 勇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一、题材转变的意义及其局限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中,题材的意义非同小可,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出现了“题材决定论”的倾向,题材的重要与否直接关系到小说创作的价值高低,这一状况到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仍有一定的延续。80年代初,大凡引起广泛争议的,很多都是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这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以及知青写作中都有呈现。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的寻根写作中,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转变。郑万隆和郑义是很明显的例子。在写作“异乡异闻系列”之前,郑万隆创作了《当代青年三部曲》(1980年、1981年、1983年)《同龄人》(1981年)、《夜火》等表现知青或青年题材的小说,但从1984年下半年起,作者陆续推出了《反光》《老马》《老棒子酒馆》等一系列以“异乡异闻”为总题的小说,①1986年9月以小说集《生命的图腾》的形式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这种转变之快在在让人惊异,很难想象这些作品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同样,1979年,郑义曾以批判“文革”的短篇小说《枫》而闻名,但到了1983年和1984年,他的小说《远村》和《老井》相继出现之后,他的笔触开始转向偏远的农村,开始写些不太关乎现实变革的小说。此外,还有贾平凹,在发表《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1984年)之类的改革小说之前,他就写了《商周初录》(1983年)这样的寻根之作。特别是李杭育,一本《最后一个渔佬儿》更是把我们带到了超越时空的葛川江上,而在此之前,他也创作了反映“文革”题材的小说,如《沉浮》等,在这前后还写过带有时代印记的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
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中,被例举为寻根写作的作品,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说很小。而即使是被称为寻根写作的作家,像郑万隆、郑义以及韩少功等等,他们的被称为寻根写作的小说作品也不是很多,这在王安忆那里尤为明显,除了《小鲍庄》和《大刘庄》等外,王安忆的很多小说并不能归到寻根写作中去,而且王安忆也并非有意要寻什么“根”。而即使是韩少功和郑义等寻根作家,他们在提倡寻根的主张后,所创作的作品仍有很多并不能被称为寻根小说。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数量并不是很多,虽轰动一时但转瞬即逝的小说创作潮流能不断被人言说,并能在文学史占有醒目的位置呢?这是否与其所带来的题材上的转变有一定关联?
作为寻根文学重要的批评家兼作家的李庆西,在时隔多年以后反思寻根文学时,他这样总结道:“文化”其实是“一个替代物”,“这是一个朦胧无间、指向不明的庞然大物。于是,评论家们在谈论‘寻根文学’作品时,出现了‘楚文化’、‘秦文化’……等说法……所有这些都跟‘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其实,‘文化’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确立一个价值中立的话语方式。这是一个叙事策略,也是价值选择。”[1]这种说法诚然如此,但李庆西其实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寻根文学为什么要“跟‘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拉开”距离呢?而实际上,“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80年代的共识和超级能指,其在80年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对于这样一个具有超级能指的话语,寻根文学仅仅是要拉开距离吗?若此,寻根文学又如何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显然,问题并不像李庆西所说的那么简单。可以说,表面上,寻根写作是要同“‘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保持距离,但其实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同它达成一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化”显然是最为主要的“叙事策略”。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次“看似反拨的顺应”①参见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 页。。其实,题材的转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韩少功和阿城他们仍旧执着于知青题材的写作。事实上,他们的有些知青题材小说,如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系列和韩少功的《诱惑》等,往往也被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被例举。这一情况表明,题材的转变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别处。
二、从具体现实到模糊时空
讨论寻根作家题材的转变,不仅要看到寻根写作的题材特征,还要注意到寻根作家的创作轨迹。可以说,大部分寻根作家,像韩少功、王安忆、阿城、李杭育、郑万隆、郑义等都是知青作家出身,并且都写过知青题材的小说。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有些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往往不被看作知青小说,而被视为寻根写作的代表作,最为典型的就是阿城的“三王”,其他如韩少功的《诱惑》《空城》等也是如此。因此,对于这些作家而言,都有一个从写作知青小说到寻根小说的过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知青题材的小说被命名为寻根写作时,从这种急于同知青小说撇清的姿态中,不难看出文坛对超越知青写作的内在焦虑。
在杨晓帆的一篇分析《棋王》发表后如何最终被确认为寻根小说的文章中,作者分析道:“随着寻根意识的渗透,王一生作为城市底层出身的知青身份渐渐模糊,他的社会属性或阶级属性变得无关紧要。当秉承现实主义文学成规的批评家力图从知青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来解释王一生的性格行为,从历史学或政治学角度发现其现实意义时,寻根批评中的王一生更接近于一个没有个性的符号。”[2]诚然,这里有一个阅读的不同角度和面向的问题,但似乎并不仅仅如此。因为这其实还是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棋王》(1984年)先是被指认为知青小说,而到了1985年前后又被追认或重构为寻根文学的经典作品?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棋王》是否是知青小说或寻根小说,关键在于这种命名说明了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有些作品被命名为知青小说,而有些以知青为背景的却被视为寻根小说?这种命名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在今天,研究者大都倾向于认为寻根文学是对知青文学的反拨和超越,而不太注意其间存在的内在关联,似乎寻根作家一个个都是横空出世,甫一出现就震惊世界,实际上并不如此。阿尔都塞曾经指出,“概念”的变化,其实反映的是“问题总领域”的变化,换言之,是新的问题的出现,生产了新的对象,并决定了新的问题的提出方式和解决方式。在他看来,这一新的对象,在此前的问题领域或问题系中,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这一问题域早已预先决定了原有对象的存在,在这一问题系中,被看到的只有这一对象。②参见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6 页。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不在于通过“寻根文学”这一范畴,去指认何为寻根小说,何为知青小说,而是要去探询,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根”的发现,以及“根”的呈现方式。这一文学之“根”,如按柄谷行人的说法,其实就是“一套认识装置”,其发现的关键在于“内面的颠倒”和内面之人的产生。①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一、二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在这里,关键是要去探讨“根”是如何被发现的。李庆西曾多次强调:“在对‘寻根’的研究中,不要把‘根’与‘文化’看得太重要,重要的是‘寻’,而不是‘根’。”②见李庆西1993年写给宋寅圣的信。另见《“寻根文学”再思考》(2009年),《当代文学60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庆西突出所谓的“寻”的过程,其实正道出了“寻根文学”这一新的“认识装置”的重要意义。正是有了新的认识装置,文学之“根”才会被“看”或“寻”出来。仍以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为例。在这篇文章中,被作为“文学有根”的例子被推举的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以及乌热尔图的描绘鄂温克族生活的小说(实际上即《七叉犄角的公鹿》等小说)。此外,王安忆和陈建功小说的新变,也作为文学超越性的代表被例举。毫无疑问,这种例举实际上就是一种命名,其通过例举和指认,借以凸显这些小说与此前小说创作的截然不同,似乎寻根文学就是某一横空出世的新物,让人惊羡不已。但其实就像杨晓帆那篇文章所显示的,小说《棋王》发表后引起的批评和接受上的差异,不在于被接受者——即小说,而在于接受者。也就是说,其实是接受者的“认识装置”决定了他们眼中的《棋王》到底为何物——即,是作为知青小说来读,还是作为寻根小说来读。同一篇小说,却引起截然不同的读法,足见知青写作和寻根写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截然两分。而实际上,《棋王》也被选入了贺绍俊、杨瑞平编选的《知青小说选》(1986年3月出版,编选工作应该在《棋王》发表后不久结束)中。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在那篇被称为“寻根文学”旗帜的《文学的“根”》中竟没有把《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实绩例举,这是否是有意的疏忽?显然,韩少功写作这篇文章时,《棋王》已经发表,因为作者在文章的末尾也提到了这篇小说,“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显然,这里并不是把它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来举例的,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韩少功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棋王》这部小说,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韩少功没有把它作为寻根文学的实绩来例举呢?韩少功是一个理论意识很强(被称为“小说界的‘理论家’”③参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 页。)并有鲜明自我意识的作家,这从他自80年代以来写的大量的理论文章可以看出,也从他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一行止得以窥见。看来,这种“遗漏”不能归因于作者的疏忽或大意,而只能从别处去找原因。
而若从与这篇文章几乎同时写作的小说《爸爸爸》《蓝盖子》以及《归去来》(都是写于1985年1月)来看,或许能看出某种端倪。《爸爸爸》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自不必说,作者自己也并不否认这点,④参见马国川编著《我与八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9—211 页。关键要看《蓝盖子》和《归去来》,这两部作品其实可以对照着读。“蓝盖子”既是小说名,也是一个意象,更是一个象征,即象征那噩梦式的“文革”岁月,于是就有了小说中的陈梦桃不断地寻找“蓝盖子”这一奇怪的举动。所不同的是,对于陈梦桃来说,那是“个永远也找不到的盖子”,故而他也就注定了永远走不出“文革”及其阴影;但对于叙述者“我”而言,却不同,虽然“我”有时也分不清“渐入夜色的参差屋顶”“穿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屋顶)不知从什么地方驶来”,但仍要“仔细地看着它们,向它们偷偷告别”。这种“告别”的意识在《归去来》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在这部小说中,知青历史是以梦境或幻觉的形式出现的,而即使是当那个在现实中叫着“黄冶先”的人意识到自己就是曾经的知青“马眼镜”时,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离,因为,就像“黄冶先”这一名称所表明的,他其实早已在意识中忘掉了知青岁月那一段历史,并且不愿再记起来,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这两篇小说都表现出“告别”历史的冲动,虽然不一定能告别得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爸爸爸》的“横空出世”了。在这篇小说中,看不到任何现实的影子,时空模糊不辨。如若联系作者写于同时的《文学的“根”》一文,可以发现,作者提倡“寻根”的主张其实是从告别现实和近史(即“文革”)的角度立论的。换言之,寻根是以现实和近史作为“他者”来建构自身的主体的。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作者没有把《棋王》作为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品来举例了,因为显然,在《棋王》中,知青生活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而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以及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族文化小说中,现实和近史是不多见的,即使出现(如在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请求》等小说中),也是作为自然自足状态的对立面或被否定的对象。而从王安忆和陈建功当时的小说创作来看,他们也并没有一直纠结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他们的创作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少功提出“寻根”显然是针对那些现实主义的写作的,而实际上,像“葛川江系列”、“商州系列”以及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文化小说,也是不能被归之于现实主义的,即使是《蓝盖子》和《归去来》也很难被归到现实主义,而毋宁说带有象征主义色彩,更不要说《爸爸爸》这篇小说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清楚“寻根文学”这一“认识装置”所为何物了。其显然是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理论预设,其意图即在于超越现实或告别历史(即近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或批评者往往把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具有浪漫主义的风俗市井文化小说纳入寻根文学的范畴,虽然寻根提倡者们并不一定愿意。①参见李庆西1993年写给宋寅圣的信,《当代文学60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 页。而像阿城的《棋王》,小说中明显就有现实细节的影子,甚至还直接写到了知青的生活,及对吃的偏好,韩少功的文章对它避而不提就很自然;而实际上,现实生活在韩少功的寻根写作中也是被作了象征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处理的。韩少功的寻根写作明显表现出远离现实的倾向,这在他所称赞的如郑万隆、李杭育、贾平凹等作家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其显然与阿城的世俗写作并不相同,而这也正表明了寻根文学的不同路向。
在这里,郑万隆、李杭育、郑义等作家纷纷远离现实,从事模糊时空的小说创作,同寻根的主张之间,虽可以互相指认,但其实是两回事。对于那些创作而言,可能代表某种共同的倾向和趋势,但在当时的批评家眼中是不被作为寻根小说指认的,而只是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发表之后,在这一理论视域中,那些作品才被作为寻根的代表提出,因此,可以说,文学寻根是一次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有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若从郑万隆、郑义和李杭育等人此前的小说创作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的题材转向,显然又潜在地暗含着某种共同的自觉的意向。从这点来看,韩少功率先提出“文学的根”的主张,其实是把他们自觉的创作意图作了理论上的表达。韩少功虽然有意识地表明了文学寻根这种共同主张,但其实又在另一方面遮蔽了这种共同倾向,因为他并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根本就是忽略和遮蔽了他们创作题材上的集体转变。
三、题材转向与不规范文化的提出
事实上,韩少功之所以对《棋王》视而不见,还在于其并不属于他提出的“不规范文化”之列。在韩少功那里,只有“不规范文化”才有值得去“寻”的价值,而“规范文化”其实也就是主流文化,主要存在于中心地带。虽然这两者都属于“传统文化”,韩少功更倾向于“不规范文化”。在他看来,似乎只有那些边缘地带的“不规范文化”才真正具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属于不规范文化。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统。它们有时可被纳入规范……反过来……有些规范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流入乡野,默默潜藏……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托着我们规范文化的地壳。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上层文化绝处逢生,总是依靠对民间不规范文化进行吸收,来获得营养和能量,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文学的根》)显然,在韩少功这里,“不规范文化”主要存在于乡村等边缘地带,而且这一边缘地带,从韩少功的寻根写作来看的话,更多的时候是那种模糊时空,即使同时代社会纠缠在一起,也往往自成一格而相对自足,这与阿城那种直接表现知青生活或以知青形象作为视角的小说明显不同,后者(即阿城的《棋王》)不被韩少功作为寻根写作的典范,也就可想而知了。
应该说,“不规范文化”的提法,在寻根文学的提倡者那里比较普遍。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这一所谓“我们的‘根’”,用作者的话说也即在“规范之外”。他同韩少功一样,并不是想从传统规范文化中寻“根”,而是把眼光投向了边缘地带,只不过在李杭育那里,这一边缘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非汉地。“与汉民族这个规范比较,我国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象,从经济形态到风俗、心理,整个文化的背景跟大自然高度和谐,那么纯净而又斑斓,直接地、浑然地反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种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比起我们的远离生存和信仰、肉体和灵魂的汉民族文化,那一味奢侈、矫饰、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文化的文化,真不知美丽多少!”[3]从李杭育的这段描述可以看出,“规范之外”的文化,比起规范文化来,还在于虽“质朴”,但“生气勃勃”,这与韩少功对“不规范文化”的评判基本吻合。郑万隆也有相似的看法。“那个地方(指黑龙江边上一个汉族和鄂伦春人杂居的山村——引注)对我来说是温暖的,充满欲望和人情,也充满了生机和憧憬。”[4]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对于寻根的倡导者来说,提出“寻根”,其实是基于对现实的主流文化的某种判断,即主流文化作为规范文化,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僵化而没有活力了。这一主流文化某种程度上即现实主义文化传统,用李杭育的话说,就是载道的文学:“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适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美学的。”[3]这话说得很明白,这一“载道的文学”就是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在80年代的复兴——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思潮。虽然这些思潮都指向“一个比较合适宜的‘道’”,但终究是“道”,距离他们所理解的文学相差甚远了。
可见,寻根作家提出寻根,其潜在的认识论根基还在于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因此,寻根文学的“认识论装置”还表现为一套关于“文学”的新的认识。这在李杭育那里尤其明显,即文学是主情的,而不是主智的。“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重实际而黜玄想的传统,与艺术的境界相去甚远”。[3]这是一种斥理性功用(即李杭育说的“实用”)而诉诸想象和浪漫,追求一种无用之用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虽通过溯源到古代而得以“理”出一条脉络,“寻”到一条“根”,但其实这种对“起源”的追溯和重构,正是因为有了“文学风景”这一新的认识装置才得以可能的。而这一认识装置的产生,虽然可见出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如康德关于美的无功利性观念的影响,但终究还是通过“内面的颠倒”和内面之人的产生才成为可能。
四、重新发现“风景”:在穷乡僻壤中发现“美”
这可以以知青小说中的自然描写为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小说讲的是中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建设祖国的号召支农的故事,小说视角的转变很有象征性。这是一些在城市里的中学生,他们没有到过农村,他们对农村的想象,主要来自于想象和叙述,与真实的农村很有一段距离,因此,当最初坐上西去的火车,看到沿途的农村景象时,心中充满的只是豪情:
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壮、瑶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可荒凉有什么要紧?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西望茅草地》)
显然,这只是一个想象中之自然,与真实的自然并不一致,毋宁说这只是一个主观心灵中的自然景观,很有“风景”的味道,但一俟他们来到这个在想象中“描绘”过的自然后,发现一切并不是这么回事,于是“风景”不再是“风景”,而还原为自然的本真: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钯钉和锄口每天磨溶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西望茅草地》)
从所引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风景”显然是与“内面之人”有关的,换言之,即“风景”是人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通过想象而形成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审美状态。所谓风景,也即那种主观合目的性的产物,而对于那些身处“风景”中的人而言,审美所应有的距离消失了,“风景”扑面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先那种想象性的关系而变为直面的关系,“内面之人”遂在这种直面的自然中,成为“外面之人”,自然变得“一点也不诗意”也就顺理成章了。显然,在这种自然中,人是作为“外面之人”或者说具体时空中的人而存在的,这与“风景”的产生中那种想象中的“内面之人”明显不同。相对于“内面之人”的主观抽象状态,“外面之人”则表现得客观而具体,这是一个个实体性之人,是不可磨灭的实存。“内面之人”则是那种可以抽象为非个体的超级主体,他不是一个个实体性的人,而是可以具有某种符号性特征的象征物。
显然,在知青小说中,自然是很难表现得很美的,因为小说中知青很难同自然之间保持一种恒久的审美距离。即使偶尔表现得很美,那也是小说主人公表现出的超然态度所致。但在寻根写作中,自然则普遍表现出美感来,这是一种常态。“自然”在寻根小说中,并不仅仅是背景式的存在,而往往成为了小说的构成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寻根写作中,往往有大段的景物描写,而这在知青写作中是很难想象的。若还以韩少功为例,可以发现,如果说,知青写作表现出把“风景”变为“自然”的倾向的话,那么寻根写作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把“茅草地”从“自然”重新变为“风景”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此前的“风景”,如《西望茅草地》中所显示的是,他人给予并叙述,最后通过自己的想象完成的,而这时重新发现的“风景”则是知青作家或叙述者本身通过有意识的审慎和超越而建构起来的。因为就像小说《诱惑》中所显示的,瀑布一直都在,其在村民眼中并不一定很美,它的美是在知青“我们”的眺望中生成的,这显然是一种身处其中的对现实情境的超越。因为,同样是身处其中,在《西望茅草地》中的“我们”眼里的茅草地的美无疑早已褪色,而在《诱惑》中的“我们”眼里的瀑布却表现出美,这显然就在于距离的产生和对现实的超越态度:
总是在雨后,这一钩银光就出现于苍翠远景。雨越大,它就越显眼地晶莹灿烂,然后一天天黯淡下去。
那时候,我们在马子溪洗尽一层汗盐,哆哆嗦嗦爬上岸,甩去耳朵里暖和的水珠,常常远望着这道大瀑布,猜测大概不曾有人到那上面去过。
当夜色落下来,它自然熄灭了。而白日里远近相叠的峰岭,此时拼连融合成一个平面的黑暗,一个仰卧女子的巨大剪影。这女子一动不动,想必是累了,想必是睡了,想必是在梦想往事。她的头发太长太多,波浪形地向北舒摆开去,每夜都让星光来晒着,让山风来抚着——等待朝霞来再一次把她肢解。
那时候,我们的自由部落就建立在这里。大家常去山下的寨子里挑粮,听农民说些话。他们说马子溪是从这羞女峰的什么地方流出的,女子们喝了,会长得标致,而且将来多子多福。他们是瑶民,或者苗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们黑洞洞的门槛里,地面坑坑洼洼,有嗡嗡的蚊蝇和朽木的酸味。
显然,在这里,瀑布之所以美,没有有意识的心理的努力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我们”身上有“汗盐”,劳动的辛苦,“哆哆嗦嗦”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美感产生的。只有“当夜色落下来”,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的时候,远山和瀑布才能变成“风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外在的视觉受到了限制,距离得以产生,想象也开始发挥作用,内部的感觉变得异乎寻常的敏捷,“自然”于是变得充满美感了。
同样,对于像《空城》这样的小说也是如此。这篇小说中的空城,即锁城,这个锁城并不美,而且似乎有点恐怖,在锁城中发生的故事,也不尽动人,甚至充满血腥。就是这样一个锁城,在叙述者“我”的叙述中,这个锁城却是那样地充满遐想和神秘: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由“自然”变成“风景”的过程。这一“风景”的产生,无疑与叙述者“我”的位置有关。这是叙述者“我”以一个回城后的知青的身份回忆中的锁城,这一回忆的远距离对于锁城之美的产生很重要。另外,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叙述者“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的位置。锁城并非作为知青的“我们”劳动的地方,而是在这之外作为我们劳动的草场的对照出现的。如果说“茅草地”对应的是迫近的现实和自然的话,锁城则是作为这一现实之外的、想象中的神秘的“他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一位置决定了锁城作为“风景”的可能。另外,“我们”在锁城言语不通,因而对锁城就又多了一重审视的距离。最为重要的是,“我”虽然是知青,虽然也有现实中的冲击,但这一冲击却是以浓缩的方式被跳过:“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我们就骨架粗硬,喉结突出,进入了中年。”(《空城》)但,是真的“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吗?显然不是,而之所以这样叙述,无非表明叙述者“我”的那种超越现实和历史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有意的自我意识,锁城最终成为一个想象中十分美好的“风景”得以产生。
从对韩少功寻根写作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文学风景的发现,其实是由那些摆脱现实羁绊的“内在之人”发现的,他们可以是知青主人公,也可以是作者/叙述者。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等就是这样的典型。可以以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为例。其实,早在写作“异乡异闻”系列之前的1980年,郑万隆就写过在题材上十分接近“异乡异闻”的小说,那就是《长相忆》。这是一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和回忆的口吻叙述幼年时的经历的故事。“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找。找一个人,一个老头儿,我的鄂伦春族的爸爸,是他把我的心带走了,教我怎么能不找呢?!”这是小说的开头。如果撇开小说写作的日期,这简直就是一篇寻根小说。而实际上,这篇小说很富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个“鄂伦春族的爸爸”并不是叙述者“我”的亲生父亲,而只是义父,因此,这种寻“找”就带有寻找“精神之父”的意义了。而如果从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叙述者“我”再到“异乡异闻”系列中的叙述者的转变,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叙述者从主人公“我”到无人称的叙述者的转变,正好表征了寻根文学的出现:寻根写作正是这样一个从主人公“我”转变为无人称叙述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的正是无人称叙述者的主体地位,这一主体以无人称的姿态出现,其实也正是知青作家的有意识的自觉的集体亮相和出场。
如果说,寻根写作是把知青写作中的“自然”重新变成“风景”的话,这其实是知青写作中返回倾向的延续。知青写作中的返回,早在《本次列车终点》《村路带我回家》《南方的岸》等作品中就有呈现,但这一返回无疑是现实中失败后的返回,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充其量不过是某种精神上的返回,就像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开了》所表明的,对叙述者——也即主人公——来说,他还要回到城市,因为那里有他(她)们的位置,有他(她)们的梦想,而在穷乡僻壤,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对于这些小说而言,虽然也写到乡土中的“自然”,但他们的眼光并没有在这上面停留,故而也就很难表现其永恒的美来,这样的“风景”其实只是浮光掠影。但在寻根写作中,自然风光——风景——则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之所以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就在于这样的“风景”寄托了作者/叙述者深厚的感情,但这样一种情感的寄托并不是直接的倾泻,而是客观化的呈现。如果说,在那些具有返回倾向的知青写作中,“风景”是由那些现实中失败的知青主人公返回乡土时发现的话,那么在寻根写作中,“风景”则更多的是由作者/叙述者超越现实后所发现的。这一作者/叙述者显然不同于那些现实中的失败的知青主人公,他们比这些现实中的失败主人公更进一步,他们没有通过返乡来建立自己的主体,而通过精神上的烛照,就能在自然中发现美的风景,并以此寄托他们的情思和愿望。因此,在这里,对于寻根写作而言,题材的转变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待自然或现实/历史,以及它们背后的自我。如果取自自我之外的启蒙理性,“自然”在他们眼里就是落后而不美的,但这时他们也只能成为外在启蒙理性的符号,这表现在那些知青写作中。而如果从内心出发而达到对自然的超越,叙述者或主人公就能成为他们自身的代表,这就是寻根写作。
这样,就能理解阿城的小说为什么很难用知青写作涵盖了。因为,在阿城的小说中,自然之美是同现实的纷扰相对立的,而这自然之美则来自于内心的超然态度。在寻根写作中,阿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这种独特性即表现在他的寻根写作并不表现出超越时空的倾向,相反,他追求的是那种日常生活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日常生活对抗宏大生活,这种对抗即表现在沉溺于日常生活中而对宏大生活的不见,用阿城自己的话说就是“世俗之门”,这扇门是被“寻根文学”“撞开”的,[5]在这扇门里看见的自然就只能是俗世生活而非宏大生活了。从这一脉络下去,就有了阿城自己梳理的像王朔、新写实,刘震云、叶兆言等作家,后者其实距寻根文学已经很远了。另一方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呈现,即他所说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他要挖掘的正是那在人类生活中深藏的“文化”制约因素。这种超越性恰好就与老庄哲学的某些精髓相似,这也是阿城特别喜欢老庄的缘故。
虽然阿城后来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本书里梳理了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间的关联,但理解阿城的寻根小说,却不能局限于此,因为若此,他就和那些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写作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对阿城而言,沉溺日常只是其第一步骤,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以此才能对抗宏大生活,之后才是超越,即沉溺日常中的超越,这个超越靠的是文化。这一脉写作虽然在寻根写作中不占很大的比重,但其实十分关键。因为这一脉络直接表现的就是知青的下乡岁月,但它们不是作为“伤痕”来写,而是作为背景或前景的存在,是需要对之进行超越的。批判或启蒙式的知青写作,虽也表现出超越,但那是以现实生活秩序的合理性作为承诺的。而在寻根写作中,这一承诺是以“文化”的名义给出,因此,其针对的就不仅仅是主人公,还包括叙述者在内。换言之,在批判或启蒙式的知青写作中,主人公对现实的超越来自于主人公之外的启蒙理性或批判精神,而在阿城的寻根写作中,主人公对现实的超越却来自于内心的努力,他无视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而能静守内心的超然。这一超然来自于不同于宏大的革命叙述的日常叙述,即他所谓的“世俗之门”,但问题随之而生,即这一世俗日常,虽能表现出超越宏大叙述的意图,但其最后却把文学引向日常的泥淖中,终于难以回头,这是后话。不过阿城代表了寻根的另一脉和走向,却是事实。
[1]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J].上海文化,2009(5).
[2]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J].南方文坛,2010(6).
[3]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J].作家,1985(9).
[4]郑万隆.我的根[M]//生命的图腾·代后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310.
[5]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379.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