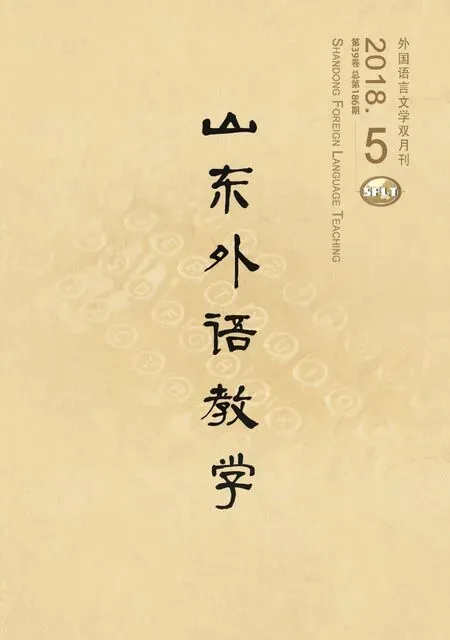库恩科学哲学视阈下口译研究技术范式与技术转向之名实考辨
赵奂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1.0 引言
口译研究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随着研究视角日新月异、研究路向日渐多样而蓬勃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范式,并出现过几个明显的研究转向。然而,近年“范式”和“转向”二词随处可见,更似有误用之趋势。例如,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的翻译研究大量引入了技术手段,便认为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业已出现(O’Hagan,2013;张霄军、贺莺,2014;张成智、王华树,2016;覃江华、王少爽,2017),并宣告翻译研究技术范式的诞生(刁洪, 2017)——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范式(黄立波、王克非,2011)就是其中一典型。口译研究的学科归属为翻译学(Pöchhacker,1993;仲伟合、王斌华,2010),口译研究的技术转向(赵毅慧,2017)一说实属可以理解,但该领域内究竟形成了何种范式,现代技术参与的口译研究是否可命名为技术转向、是否促生了新的研究范式,尚无定论。而厘清此类名实之辩的关键,是明确“范式”及 “转向”这两个科学哲学术语的内涵属性和外延特征。
2.0 科学哲学对“范式”和“转向”的界定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中将希腊语“paradeigma”译为“exemplum”(例示);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剑桥大学讲演时曾频繁使用“范式”一词,该词虽也出现在其1953年的伟大著作《哲学研究》一书中(伊安·哈金,2012:xix-xxi),但仍属冷僻词;直到1962年,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的问世,“范式”一词才逐渐受到热捧,其伴生词“范式转换”(paradigm change/shift)也应时而诞。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2006)将“转向”等同于研究范式的转换与革新,因此库恩所言“范式转换”实为今日惯常使用的术语“转向”。
2.1“范式”和“转向”的内涵属性
引起哲学界震动的《结构》一书是库恩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书中提出了研究的“范式”这一具有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哲学术语,同时还贡献了“范式转换”、“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科学革命”和“不可通约性”等伴生词。
然而, 库恩对“范式”灵活的释义导致人们的理解出现了分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今学术界对该术语的滥用和误用。据统计,《结构》全书先后对范式做了20余种解释(Masterman,1970:61;Kuhn,2012)①。为正本清源, 库恩于1974 年特意撰文《对范式的再思考》(SecondThoughtsonParadigms),再次对“范式”进行了规约性界定。笔者经过比对总结出4种典型的“范式”内涵属性:1)一种科学成就, 规定了科学共同体应关注什么问题和采用何种方法(Kuhn,1996:X);2)现存的科学实践传统(1996:6);3)理论框架(1996:85);4)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1996:175)。可见,库恩界定的“范式”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系统:研究对象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兴趣,共有的世界观、理论框架是认识论,实践传统和研究方法是方法论。
文本回归让笔者特别注意到,术语的命名必须强调其哲学假设的本质。“范式”是有哲学思考的、理论的假设,是比共有规则更优先的存在,具有“优先性”(Kuhn,1996:43-51)。维特根斯坦提问怎样才能毫无争议地使用“椅子”、“树叶”或“游戏”等词语,库恩的回答是人们必须在意识中直观地知道“椅子”、“树叶”或“游戏”等每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即维特根斯坦所言之家族相似性(同上:44-45)。因此,范式是形而上的(Kuhn,2012:1,4),优先性哲学假设应该是其属概念。
而与“范式”内涵息息相关的“范式转换”,即“转向”,源于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和科学革命。“转向”总是伴随新发现和新理论的诞生。因为新范式摈弃科学共同体曾经的信仰和研究过程而重构研究的理论框架,所以转向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是科学的重新定位(Kuhn,1996)。
2.2“范式”和“转向”的外延特征
外延特征是命名合理性的外在判定因素。结合《结构》和《对范式的再思考》,笔者梳整出“范式”的4个特征:1)每一范式都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Kuhn,2012:2-3),令他们组成区别于以往的新的科学共同体;2)共同体成员基于同样的研究兴趣开展常规科学实验,常常促生新的规则(同上:7-9),因此范式具有开放性:如同不断出现的问题留待共同体集结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范式作为一个综合系统也留待实践者完善和构建;3)范式之间不可通约(Kuhn,1996:4):新范式创造新的术语(同上:55),或在沿用前范式术语(vocabulary/terms)时赋予部分术语新的意义(同上:149,183,198) ,共同体成员用自成一体的术语交流,令范式成为自洽的系统;4)新范式下共同体内的科学实验并不以追求新奇为目的(同上: 35),这一点既解释了为何学界对口译实证研究成果的评价常似不证自明,又说明了为何新技术支持的实证研究虽不新奇但仍有必要展开。
“范式”的外延特征决定了“转向”的判断标准。判断是否出现转向,首先应进行检视,因为一个理论的变形通常预示着危机,而突破危机可能要求新范式的诞生。其次,科学革命初期新范式会在遭受攻击后趋于变化:转向将同一组数据置于新系统之中,往往会遭遇极大的阻力,典型有如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向文化研究范式时曾面临的巨大质疑。最后,因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转向体现为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竞争和转换(Kuhn,1996)。由此可见,转向发生的过程经历信仰危机→寻求突破→科学革命→范式转换四个阶段,令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全新的面貌。下文基于库恩撰写《结构》一书时展现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对口译研究中范式的形成和转换进行有效梳理。
3.0 口译研究技术范式与技术转向之名实考辨
“范式”的引入为翻译研究者开启了全新的观察方式。受库恩的启发,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2006)、霍姆斯(Holmes,2012)、皮姆(Pym,2014)、廖七一(2015)、文旭(2018)等翻译理论研究者尝试使用“范式”这一术语对翻译研究进行描述性分类。尽管他们的研究出发点相异,但对“范式”的使用均与库恩科学哲学对该术语内涵及外延的界定相符。口译“是翻译的一种类型,是将源语的一次性表达向其他语言所作的一次性翻译”(Pöchhacker,2004:11)②,因此口译研究可以借鉴翻译研究的经验和库恩科学哲学对术语的界定。
口译研究自身携带“多模态”基因。仲伟合和王斌华(2010:9)认为,口译研究是一门认识口译活动、描写口译过程、评价口译产品、考察口译活动涉及的各种问题的学科,研究视角与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语篇分析、交际学、系统功能语法等学科交叉,研究对象包括口译的理解过程、目标语发布、口译教学、职业实践等。研究视角及对象的多样性,对口译研究采用的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口译研究技术范式和技术转向之说的出现实属情理之中。但是,这两种命名合理与否,尚需通过梳理口译研究范式的演进和转向过程,和技术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来进行考证辨析。
3.1 研究范式、转向与研究技术之关系考
口译研究的发展大致历经了四大主流范式。每个新范式都提出了异于已有范式的理论假设,搭建起崭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框架,令新共同体的成员得以在该框架内使用一套自洽的术语对话,并开展常规研究。笔者通过考察技术与口译研究四大范式的关系发现,迄今为止,技术作为常规口译研究的手段之一,一直在口译研究的某一范式内部发挥作用,并未促发范式革命,因此口译研究技术范式无从谈起。
3.1.1 语言对应范式与技术
语言对应范式滥觞于译员的口译实践与自发思考,技术极大地推动其发展。
上世纪50年代以降,口译译员受实践的启发,对口译行为本身产生了共同的认识:口译是一种用语言当场口头再现另一种口头语言的活动(钟述孔,1999:1)。这样的认识论其理论假设为语际可转换性,使研究者长期将目光聚拢于语言层面的对应,根据字、词、句间的等值程度进行口译活动的质量评价。该阶段内的口译研究局限于语言对应型讨论,其主要术语多源自对比语言学。这种讨论的 “科学性和学术性并不强”(廖七一,2012:181),“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李德超、唐芳,2012:21),随着时代的发展,蒙娜·贝克 (Baker,1993) 将语料库方法和技术引入口笔译研究,激发了语言对应讨论者的热诚,推动了一批收存了大量真实语料且标注严格的知名口笔译语料库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口译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语料库技术的加入令语言对应型讨论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属性,蜕变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齐备的语言对应范式。
语言对应范式对口译实践中的技术应用研究影响尤甚,此类研究分为计算机辅助翻译及机器翻译两个领域。前者如奥斯特米勒(Austermühl,2014)论及电子百科全书、术语数据库、网络词典、翻译机器等多种辅助翻译的电子工具,又如将智能笔用于交传笔记并检视该方法的有效性(杨柳燕,2017)。后者则是更为浩然的领域,如谷歌的神经元翻译(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GNMT)技术引发了人工智能界和翻译界的轰动(Wu, et al.,2016),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口译服务更是日新月异。然而,此类研究就技术而论技术,其理论基础仍是传统的语词对等,尚未肇启新的口译研究范式。
语言对应范式追随者甚众,但一直也遭受着各种质疑:以语际转换为核心的讨论何以未能有效提高口译质量?究竟何为口译活动的实质?质疑之声标志着信仰危机的显现,科学革命正值来临前夜。
3.1.2 意义生成范式与技术
意义生成范式源自对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其酝酿到成熟的整个过程中,技术的参与程度非常低。
自上世纪70年代始,受分析哲学的启发,口译学界开始关注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的哲学关系,研究视角由语言对应转向意义生成。语言对应范式基于对比语言学,其中的关键术语“第三者标准”(Tertium comparationis)意指存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某种功能或信息的参照物,即译者根据从原文中解读出这个标准生产不可回逆的译文。除了受分析哲学奠基人弗雷格的语义三角理论的启发,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Seleskovitch & Lederer,1984)正是在第三者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释义理论及其三角模型(Pym,2014:17)。
释义理论开启了口译研究从语言到意义的转向。根据库恩的界定,意义生成范式关注的对象是意义的产生机制, 其理论假设是意义可脱离语言外壳。研究者基于对意义生成模式抱有的共同兴趣,建立了新的科学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主要将释义理论与口译增效研究结合,以求提高译员培训的实质效果。然而这一典型的科学革命中几乎没有技术的直接参与。根据CNKI的统计,对意义生成范式与技术相关性的研究寥寥,其中李鑫、胡开宝的研究论及口译释义理论与语料库技术的结合(2015),已是极为难得。
意义生成范式遭受的挑战有如,释义派的三角模型描述了口译的物理过程,但并未揭示译员如何有效实施该过程;又如,该范式过于抽象,译者从源语中获得信息进行加工、生成意义再产出译文的理论假想是弱隐喻(Pym,2014:17)。技术手段无法捕捉的意义究竟为何物?译者脱离语言外壳后,从何处获取普遍意义(universal sense)?脱离语言外壳、失去符号表征的意义是否仍能存在?各种质疑声向旧研究范式发起挑战,与此同时,正处于酝酿之中的新范式在认知心理学中寻得其理论支撑。
3.1.3 认知加工范式与技术
认知加工范式是目前口译研究与其他学科交互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甫一形成便集合了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及语言心理学 (Jakobsen, 2017: 173)等各学科的技术手段,尝试对口译活动中的“黑盒子”——认知加工过程加以窥探。
基于心理学家乔尼·斯维勒(Sweller,1988)提出的认知负荷理论,口译被认定为一种认知负荷较高的活动。区别于意义生成范式,认知加工范式关注的是口译活动中促使意义生成的心理加工过程。有趣的是,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2002)早在1975年“语言与记忆——交传笔记研究”一文中就已提及注意力分配的概念,也就是认知加工范式中的心力、脑力,这更能说明认知加工范式是意义生成范式内部的突破。认知加工范式下最有影响力的口译研究理论假设莫过于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型(Gile,2009),此外还有同传过程模型(Gerver,1976),同传信息处理流程模式(Moser-Mercer,1978),认知测试焦虑模型理论(Cassady & Johnson,2002),事件域认知模型(王寅,2016)等。
探索认知加工的过程中,语音学、精神学、心理学、神经学乃至医学等领域的检测技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口译研究的方法论。例如,研究者采用ERP技术研究口译过程中的认知神经机制,用眼动实验、热感实验、核磁共振实验等跟踪测探译员的心理负荷,用音频软件图示化非流利产出的影响因素从而逆向检视认知过程等,成果斐然,令人瞩目。
根据库恩对“范式”的界定,认知加工研究既有新的理论假设,又启用了跨学科的技术手段,逻辑自洽且拥趸者甚众,完美地构建了新的范式,实现了口译研究的范式转换。但是,认知范式共同体也同样面临着危机,比如认知负荷模型无法解释译员如何消解冗余负荷;技术检视手段虽能精确定位认知负荷,却无从说明影响和干扰译员抉择的因素等。后续研究的突破口就此打开。
3.1.4 社会文化研究范式与技术
社会文化研究范式下,研究者聚焦影响译员抉择的社会和文化等外在因素,技术手段难以发挥其长。
近20年来,跨文化交际、社会学互动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口译研究的评价机制,干涉译者身份和抉择的责任、调解、权力关系等纷纷进入研究视野。维也纳大学副教授波赫哈克(Franz Pöchhacker,2008)注意到并论证了口译研究对社会因素的关注。随后仲伟合、王斌华(2010:10-12)提出的口译研究的五种视角也包含了社会互动行为视角、文化视角及其对应的研究范式,明显展示出向社会学转向的趋势。2014年安吉莱莉(Claudia V. Angelelli)著书专门讨论了口笔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这一观察得到了任文(2016:70)的关注和认同,她指出,从社会学角度重新思考口译与权利的关系是一场突变。2017年Target第一期首篇开宗明义谈“中国口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社会网络分析”(Xu,2017:7-38);TheTranslator上有学者开展调查,考察语言调解者扮演中间人、调解人、职业译员等多重身份的情况 (Hlavac,2017);同期还出现了针对译员伦理和社会责任的讨论(Drugan,2017)。2018年4月的TranslationStudies更是集中刊登了对社区翻译/口译的书评(Ciribuco,2018;Tesseur,2018)。在社会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法庭、社区、跨国界、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口译历史或实时案例,社会实践论中场域、惯习、资本、权力等常用术语也随之进入口译研究者的话语体系。
社会文化研究范式涉及的变量纷繁复杂,因而技术检视手段难以介入其中。在CNKI搜索社会学相关的口译研究文献,至今尚未见与技术相关联的成果。而令人惊喜的是,客岁TheTranslator第三期中已有学者探讨译员与机器翻译的“共舞” (Ruokonen & Koskinen,2017),将社会学调查手段与技术相结合,考察译员对人机互动体验的评价。相信社会文化学的宏大视野会源源不断地为口译研究注入勃勃生机,孕育更多有益的成果。
综上,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视角纵观口译研究范式的演进路线,可见技术在某些范式内部扮演着定性定量的工具性角色,参与范式理论假设的证真或证伪,但至今尚未触发任何范式转向;真正促成边际革命的终究还是信仰危机,以及研究者对危机的突破。从这一角度而言,所谓的口译研究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转向尚不足以合乎库恩科学哲学界定。
3.2 技术范式与技术转向之命名辨
蒙娜·贝克(Baker,1993)曾指出翻译(口译)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规约性到描述性的转向,这一转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语料库翻译研究。而口译研究天生的跨学科属性,令研究人员纷纷开始对语料库、眼动仪、ERP(脑电波)、热感、瞳孔检测仪、核磁共振技术等现代检视手段加以运用。除此以外,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的迭代升级,日臻成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口译的传统研究手段进行着重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口译研究孕育了新的技术范式甚至技术转向?
诚然,常规科学实验见证了现代科技发展为方法论革新带来的益处,但由于技术本身并不涉及先在性哲学假设,“技术范式”这一命名并不符合库恩科学哲学对范式的界定。笔者回溯并爬梳了2010年至今CNKI上涉及技术的口译研究文献后发现,除就实践中的技术应用开展的研究外,这些文章均将技术作为常规科学研究手段,以实证研究法论证理论假设,而研究无外乎以下四种:首先,绝大多数研究聚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工作记忆与口译质量的正比关系;其次,窥探口译活动的信息加工“黑盒子”,检测认知负荷,以期找到译员的认知规律,制订提质增效方案;再次,考察现代技术与译员的互动是否有助于达成语际对应或生成意义;最后,借助技术手段对场域口译进行话语分析,讨论影响译者抉择的因素。也就是说,采用技术手段开展常规科学实验的口译研究均以分属于前述四种范式的理论假设为依据,即它们在本质上属于某一已有范式。简言之,先在性的哲学假设作为“范式”这一术语的属概念,是判断某种研究归属于何种范式的根本;口译研究的“技术范式”这一命名,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因确无必要,所以勿增实体。
遵从库恩对“转向”这一术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科学哲学视阈中观察技术与每一次转向的关系,口译研究的“技术转向”命名是否具有合理性一目了然:
首先,根据《结构》一书,技术的采纳是为了向某一科学研究提供事实支持,目的在于“澄明范式已提供的现象与理论”(Kuhn,1996:24),是范式的维系手段。比如研究者采用认知心理学实验中的ERP、眼动甚至核磁共振等技术手段对理论假设进行证真或证伪,应划归认知加工范式下,而非产生了口译研究的ERP、眼动等转向。
其次,技术支持的口译实证研究属于常规科学研究,其目的并非产生新奇(Kuhn,1996:35,169)。以最新的科学手段对口译活动进行实证考察的研究者深得学界尊敬,他们的成就并非促进了研究范式的边际革命,而是使用新工具,以更精确可靠的方式重新验证了已有范式的理论假设。与此同时,正因为有技术支持的实验证明了某一理论假设为真,所以技术支持下的口译实证结论常常给人以意料之中的感受,甚至引起“不证自明”的误解,然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参与证真伪的必要性。
最后,转向发生的全过程呈现“信仰危机→寻求突破→科学革命→范式转换”式的规律性样态,采用技术手段开展口译研究并不符合这一规律。因此“技术转向”命名违背库恩对转向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实属误用。相比之下,蒙娜·贝克(1993:242)将语料库翻译研究定义为“语料库驱动的方法论”(corpus-driven methodology),此说可能比口译研究技术转向更为妥帖。
4.0 结语
口译研究中已有范式和转向与研究技术之关系考以及技术范式与技术转向之命名辨均充分证明了口译研究“技术范式”和“技术转向”命名的不合理性。
库恩科学哲学视阈中参与口译研究的技术,其作用是在已有范式下开展更精确的观察和定性定量的实证研究,是对已有范式的方法论的支持和对研究工具的补充。技术本身不携带理论假设,不具备形而上的属性,因此,绝不能因其出现给学界带来的震撼而认为口译研究形成了技术范式。
技术是参与口译研究的重要手段,是追求定性定量的常规科学实验方法,技术参与研究其本身并非转向。手段绝非范式,到目前为止亦未催生新的口译研究范式。科学实验的目的不是生成“新奇”,而是证明哲学假设的真伪。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并不排除有技术参与的实证研究带来突破性发现或原创性理论假设的可能性。
综上,研究者在为某种研究现象命名时,须谨遵“范式”和“转向”的科学哲学属性。
注释:
① Margaret Masterman 统计出21种,而库恩自己统计了22种。
② 文中对外文文献的直接引用均为笔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