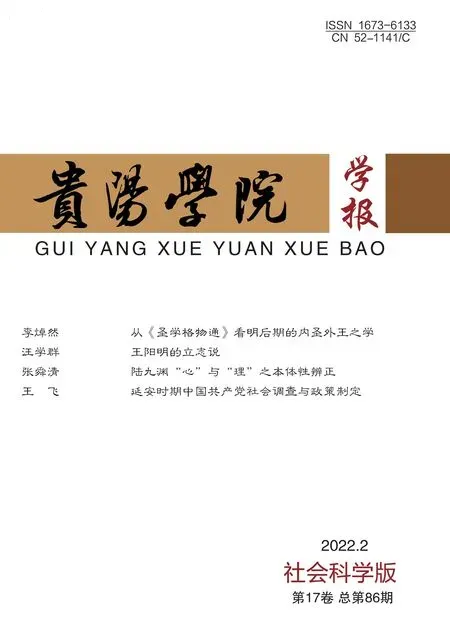陆九渊心学思想系统中的“精神”概念探析
卢 涵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陆九渊所代表的心学思想以“心即理”为标志,与理学思想相区别,但是设定“心即理”来反对“性即理”不仅需要将天理与人心简单地合为一体,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建构说明“心即理”在人的现实实践中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如在推行与理学有着明显差异的心学工夫论时需要在实际操作入手处找到与“心即理”思想相符的概念——“精神”。与现今对“精神”代表着意识、思维、神志的理解类似,宋明学者也认为无论是人的内在心理活动还是外在的行为都离不开“精神”的运用,所以“精神”在宋明已然是普遍使用的概念。尽管在思想上有差别,但是朱子和陆九渊都常用“精神”来描述社会问题,并用“精神”来教导学者。由此可见,明确“精神”的正确运用方式以及“精神”的性质是心学理论现实性和真实性的保障,通过对陆九渊思想中“精神”概念的讨论,能够进一步理解心学强调“心即理”,与理学中“性即理”相区别的目的及其合理性。
朱陆意见最大的分歧在于对“心”和“理”关系的理解上,换言之,在以“理”作为本体,与“理”同体的概念具有本体性的前提下,陆九渊认为“心”具有本体性,“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1]149,而朱子认为只能说“性”有本体性,并不能说“心”有本体性。两者的差异可以总结为对“心”的本体性认知不同,并且这一差异延续到工夫的具体手段上,产生了两者内向涵养和外向格物的不同取向。那么由于两者皆认为“精神”与“心性”一样,是个人的基本属性,且“精神”在工夫中的重要性超越了工夫内向与外向的分别,“为学有用精神处,有惜精神处,有合著工夫处,有枉了工夫处。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将来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将来看得这文字”[2]2874。理清“精神”与“理”的关系对于朱子和陆九渊来说如明确“心”本体性一样重要,“心即理”或“性即理”虽然是理论的根基和工夫的依据,但若没有以此而来的现实工夫的证明,便只能是意见而非真实,而由于“精神”直接与身心活动相关,一旦确认了“精神”与“理”的关系,就能够把“工夫”从设定转为现实。所以明确“精神”的本体性对于心学理论的完整性和合理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的本体性既可作为“心即理”的确认,也是心学理论与工夫一贯性的保证。
二、心学的“精神”概念: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性
在陆九渊看来,人心便是宇宙,其中天生道理皆备,无须在外求理,所谓至善的抵达,即是自作主宰,自作主宰则一切个体的行动等同于德行标准,内外皆不受外物之恶的干扰。“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舜不能惑。”[1]4但同时,陆九渊也认为,虽然人的内心中天生道理皆备,但是这不等同于自作主宰的状态,在人明得自己内心所备之理之前,只是“能”而非“真”为主的状态,所以后天工夫不可或缺。对于工夫的描述,陆九渊有言:“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1]456对比前述陆九渊从本体的角度说明天理皆备来看,两句的形式相近,此处说明工夫以“收拾精神”为主,能呈现自作主宰的效果,而前述以“明得此理”为自作主宰的前提,故可知“收拾精神”等同于“明得此理”,其中“理”即“道”,自然是目的对象,而“收拾”与“明”为手段,故与“理”相对应的“精神”也同样应被视为目的对象,而非达成“理”的工具。因而在陆九渊看来,“精神”与“理”在本体性上没有差别:“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如此,于此迟疑,不便着鞭,宜其在己未得平泰,于事有不照烛,子细观察,有何滞碍?‘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我未见力不足者’,圣人岂欺后世?……诚之愈自弃耶。”[1]51“自弃”“自埋没”“未见力不足”都说明了大丈夫“精神”与天理一样,原本是至善完满的,但内在于人时须通过工夫修养外化为德行,所以“用力”“着鞭”对于“精神”展现其主体性同样关键,除却“心即理”的设定,陈述“精神”本体性的关键在于决定工夫的取向和下手处。
因而,在陆九渊对工夫的具体描述中,“精神”也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并且“精神”本体性通过工夫的方式和效果进一步得到明确:“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见得端的后,常涵养,是甚次第。”[1]454文中陆九渊将德性工夫区分为“见得端的”与“常涵养”两部分,前者是立志确定目标,后者是在目标的指引下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尽管由此来看,“精神”的特点有所分化,似乎与具体的事务相近,但这两部分内容中所反映出的“精神”内涵都与朱子思想中的“精神”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可以通过两者的对比进一步明确“精神”的本体性。从前者来看,陆九渊特别强调“端的”在工夫中的首要地位,因为“端的”就是明确“理”在内还是在外的区分点,只有明确了天理的内在性,涵养静处的工夫才是合适的,更重要的是,这同时也是“精神”的本体性根据。因为不管“精神”地位如何,其作为人内在的部分是朱子与陆九渊都认可的普遍意见,所以天理的内外直接影响其与“精神”的关系,若不以“见端的”为工夫前提,以为“理”在外,须通过“事”证明,则“精神”在内的本性在格物时便只能沦为内外沟通的媒介,从而丧失“理”的本体性;反之,“精神”与“理”皆在内,可涵养自明,不须外事证明,精神的聚集正是天理的明白。所以“见端的”作为心学工夫的关键,与陆九渊将“精神”作为本体是一致的。
既已明确“精神”作为本体在心学工夫中的前提性,那么从后者来看,“常涵养”则是陆九渊从手段的角度出发对“精神”内涵的说明,是从反面对“精神”的本体性的进一步证明。如上述,朱子描述工夫时,多以读书、做事为例说明“精神”的重要性,“万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2]138,“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读书安得精专”[2]2855,均意在以“精神”集聚的消耗为读书精专、万事做得的条件。但是反观陆九渊对工夫的描述,则是以收拾、涵养为本,“惟精惟一,须要如此涵养”[1]455,精、一原本是对本体的形容,而此处用于描述涵养手段的特点,可见“精神”在工夫中是作为目的存在的,所以“精神”在人见端的后只以“涵养”为要,更不须提读书做事,读书做事是在以“精神”为主为本的前提下的自然生发之用,而非对集中之“精神”的消耗。所以尽管朱子与陆九渊对于“精神”皆提倡收敛、集聚,但由于两人对“精神”的定位不同,其用意是完全不同的。“既知自立,此心无事时,须要涵养,不可便去理会事。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圣人谓‘贼夫人之子’。学而优则仕,盖未可也。初学者能完聚得几多精神,才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样完养,故有许多精神难散”[1]454,“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闲说话,渐渐好后被教授教解《论语》,却反坏了”[1]455。如上,朱子以为“精神”要聚而不散是以聚精神利于读书做事的消耗而言,但陆九渊以为涵养以聚精神则是为了人的自立,自作主宰,在“精神”尚未收拾聚集之前,由于外在事物会分散消耗“精神”,故反而要避免陷于琐碎的事务。
但这并不是说陆九渊认为涵养工夫是完全寂静的沉思,相反,陆九渊同样重视事上的功效,以及事物对“精神”的培养,如同天理内在。但“精神”同时也是化生万物的根据,虽以聚集为善,但也应该流动与外物相通,只是其中有次第的先后而已。“人不肯心闲无事,居天下之广居,须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说,方有精神”[1]455,“本分事熟后,日用中事全不离。此后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犹自救不暇,难难。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难难。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1]468。“精神”在人身上,与人心息息相关,其本质是活动的,自然有逐外的天性,说话、读书、做事等一切人的行为都是“精神”的活动处,“精神”的本体性价值正是通过人的动态和事务的效果得以呈现的,正如人心自然天理全备,但须后天通过德行实践将其外化才可谓自作主宰,实现了人道合一。故在描述工夫时,陆九渊皆以“事”为载体,如“本分事”正是以“精神”为本体的涵养之事,而“日用中事”则是一切日常的具体事务,此两者皆为“事”,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且在“用工”时全不离,工夫就在“日用中事”上。但是这一效用实现的前提是“精神”在内,即“见端的”。“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切己致思,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若先看难晓处,终不能达。”[1]407“精神”虽为本体,但是与“事”一贯,只要工夫以涵养精神为先为主,则工夫中所涉及的事理皆可顺势而解,反之,若将工夫的重点落在事理上,则终不可通达。“凡事莫如此滞滞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长,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1]459。换言之,尽管工夫不可与事务之属的“为费宰”或“闲说话/教解《论语》”等割裂,但也绝不可置于涵养“精神”工夫之先,因为从工夫而言,“本分事”是所以“日用中事”价值的来源,“精神”的本体性是心学工夫的前提。
综上可知,不论是在对本体的直接陈述中还是在对工夫条目的说明中,陆九渊都将“精神”视为等同于道、理的概念,“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1]408。在他看来,“精神”是“理”在人身上的具体化,“理”内在于人心或难以感知,但对人而言,“精神”的状态却不仅是自知,而且也是自明的,如文中“精健”与“损伤”之间有明显的可视差异。“精健”即精神聚合,明得此理的状态,而“损伤”则是“精神”分散逐于外物的状态,所以用“精神”指主宰可以使陆九渊心理合一、吾心即宇宙的思想表达得更为明确。同时,以“精神”为主宰亦可使体用一贯,工夫不断:“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瑟所以养吾之德性。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1]473其中陆九渊将“精神”作为本体,与“德性”对应,以“精神”之长为“德性”的修习,从而使“精神”落实处皆化为德性工夫,又人处世之间“精神”遍布全体,故道、艺合一,理、事合一,只须明“精神”之理则道德工夫无处不在。由此可见,在陆九渊看来,准确理解“精神”的本体性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入手处,精神为一,而事为多,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精神”的本体性不可动摇,是工夫的前提,也是自作主宰的关键,不可因“精神”在处事上的功能而将“精神”视为工具,与“事”混为一谈。所以尽管在具体的工夫中,“精神”与事一贯,但工夫仍以“见端的”为前提,否则一切工夫皆是本末倒置,天理不明,不可谓之德性修养的工夫。“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被事物牵将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坏了”[1]456,唯有在“精神”的本体性确立之后,人才能在工夫中受“精神”(道)的主导,不被一事一物限制。故陆九渊的工夫并非无事可做,涵养精神便是做一切事,其所谓工夫无事只是不以“精神”为事,“精神”出入于事,两者合理的关系应是以涵养“精神”实现明理为本,外化为人以完满的状态(自作主宰)展现在一切事务的合理处置。
三、“虚精神”与“实精神”:作为社会规范意义的精神概念
由以上分析可知,明确“精神”的本体性对于完善心学理论架构来说是必需的,但对于陆九渊来说,心学作为正道,并不只是构建出理论而已,而是有现实作为证明的。所以“精神”的本体性作为天理内在的具体化,可以直接用于许多社会现象的反映,同时也是解决个人以及社会问题的关键,陆九渊通过许多具体的现象分析,进一步增强了“精神”作为本体的真实性。
在社会现象上最为典型的就是风俗的变化,“古者风俗醇厚,人算有虚底精神,自然消了。后世风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为害,难与语道”[1]404。古今风俗不同,古者醇厚,今人浮华,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而陆九渊将这一系列问题总结为“虚精神”的蔓延所造成的风俗败坏。在陆九渊看来,风俗改变的原因之所以可以归结为“精神”的虚实,是因为如果只是将“道”的遮蔽作为原因的话,一则过于抽象,二则过于表面,对于风俗的改善没有帮助。由上可知,一方面“精神”的内容是具体实在的,且人人天生皆备,风俗源于群体,最终仍要落实在个体身上,以“精神”为视角,能够有解决问题的入手处。另一方面,“精神”作为本体,与“道”一致,“道”有明与不明,“精神”自然也有虚实的差别,倘若其本体性不明,便会虚化,所以风俗败坏的根源可以总结为个人对“精神”的一种错误意见的流行,而将“精神”由虚转实是个人修习步入正途、纯化风俗的关键所在。
“虚精神”是人对“精神”的一种错误意见而非事实,因而这种异端在古今都具有产生的可能性,但这一意见在古今有不同结局,正是因为风俗决定了主流意见。但风俗终究归结于人,所以“虚精神”之所以能在当今流行起来,还是因为当今学者的心理和行为与古人不同,所以陆九渊通过对当今学者状态的分析,描述了“虚精神”的具体表现(导致的问题),由此进一步明确了“实精神”(精神的本体性)的重要性。
古今在为学上最大的差异一方面在于个人的内在心理,明显有“为人”和“为己”之别,另一方面在于个人做事,事功效率明显有高下之别。在陆九渊看来,“为人”的心理与“难成事”的问题根本上都是因为“精神”不实,导致人陷于事中,被物欲牵制,只需要令人明白“精神”的本体性,改变工夫修养的次第,便可以回复古时之醇厚的风俗。
从前者来看,今人做学问之所以有“为人”的心理,并不是今人与古人天生不同,起先人做学问皆是为了明理,而不是引起他人的羡慕,今人亦是如此,但由于“虚精神”的误导,在人用工时会出现两类问题,最终导致“为人”的风俗化。一类是在用工之前,人没有明白天理的内在性和精神的本体性,不见“精神”之实,以为理不在己而全在事上,故消耗精神,遍求世事,将知识的积累作为道理的明白。“今人读书,平易处不理会,有可以起人羡慕者,则着力研究。古先圣人,何尝有起人羡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见有奇特处,便生羡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风。如唐虞之时,人人如此,又何羡慕?”[1]441所以在读书遇到奇特困难之处时,由于此处相较于他人皆知的平易处,更能反映学问工夫、道德境界的深厚,学者便有特别的追求和关注。一方面忽略了道理平易的本质,导致读书虽多但是依旧不能明理;一方面又逐渐在人心中形成了比较、竞争的心理,读书不以自知为善,反而以他人不知为善。这种心理的蔓延及与天理的疏远最终造成了“为人”的风俗以及“虚精神”的流行。一类则是在用工之前,人没有通过内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性格(内在精神的实在状态),明确“精神”与工夫的关系,以为读书做事自古以来就是工夫之法而盲目用工,导致工夫之法不适于自己,既无法明理,又使得读书做事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的模仿游戏而已,形成“为人”之学的风俗。以古人为例,人的才智各不同,工夫之法亦不尽相同,但是总归有“实精神”就能保证“为己”工夫。“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辞。然其会归总在于此。颜子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难。仲弓精神不及颜子,然用力却易。颜子当初仰高钻坚,瞻前忽后,博文约礼,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尔。逮至问仁之时,夫子语之,犹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复礼为仁’,又发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既又复告之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尝谓此三节,乃三鞭也。至于仲弓之为人,则或人尝谓‘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静,不佞、无口才也。想其为人,冲静寡思,日用之间,自然合道。至其问仁,夫子但答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此便是也。然颜子精神高,既磨砻得就,实则非仲弓所能及也。”[1]397
颜子与仲弓天资不同,前者天生精神力高,精神本体自明,任何工夫之法皆不伤精神之实,故遍求力索亦可;但后者才是常人的一般情况——精神不及。所谓“不及”是指与颜子相比的差距,也就是“实精神”并非天生自明,从自觉的角度来说是尚处于“虚”的状态,倘若按颜子那样下遍求的工夫,则做事愈多,深度愈浅,理愈不明,最终与“理”所赋予的实在性渐行渐远,促进精神的进一步虚化。但是若仲弓不模仿颜子用工,而先从“实精神”用力,便能得知自己冲静寡思的特点,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三鞭之法,自然合道。由此可见,陆九渊以“虚精神”为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要否定外求而明理的行为和天下之事理存在的事实,只是要人明白,尽管工夫的内容不过是读书做事,但重点不在书和事,而在于人去读去做,而“实精神”正是个人用工的标准,并且“实精神”的工夫不同于遍求力索对天赋有很高的要求,只是平常人就可以实现的工夫。并且不管是颜子,还是仲弓,这一工夫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也是明理的唯一工夫。“我与学者说话,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势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1]404至于后续对“实精神”在事上的运用,则自然依据各人天赋有所不同,但已然不影响天理之明、风俗醇厚。
“古人之学,不求声名,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学,正坐反此耳”[1]441,而今人为己,无论是天理内外的混淆,还是工夫次序的颠倒,皆是由“虚精神”对工夫的影响导致的,使得当世学者把读书之事也沦为物欲之类,使原本的道德工夫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人无论是否先前接受了“虚精神”的意见,只要人未能有“实精神”的觉悟,那么“精神”就难为读书做事之主,而人处于世间,不可回避日用中事,“精神”定然会作为工具在外物上不断消耗,最终在个人心里形成或强化“虚精神”的意见,导致“虚精神”作为风俗流行。
从后者来看,“古人精神不闲用,不做则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须要一切荡涤,莫留一些方得”[1]468,对比今人,古人做事时非常彻底,且具有针对性,所以容易成事。而由上可知,凡读书做事应皆以“实精神”为依凭,倘若精神为“虚”,则“精神”随事万变,容易发散转移,自然不能达到成事的集中度,故今人凭借“虚精神”所实现的事用,皆是效率低下的闲用而已。由此可知,陆九渊不仅并不排斥读书做事,如其并不否定颜子“磨砻得就”的卓立,认为这是非常人所能及的成就,并且还特别强调古今学者在事功上的差别,将事功作为工夫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今人做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可以直接用“虚精神”来解释,更是因为事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改善社会的不良风俗。这才是陆九渊提出“虚精神”的目的所在,“精神”虽然可以解释学者的心理和行为,并且其虚化可以作为问题的根源,但是更重要的依旧是“精神”在解决问题上的作用。在“虚精神”作为个人所产生的意见而不能彻底消灭的现实下,唯有醇厚的风俗能够有效阻止“虚精神”意见的流行,所以通过“实精神”让工夫在具体事务上得到落实,从而直接对风俗进行改善才是陆九渊最终的目的,故陆九渊在工夫上对学者闲说话的问题,尤其注重防范。
当世学者常以“闲说话”①“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近后生,未知藏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置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司马温公文集》卷四五《论风俗札子》)为工夫,“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闲说话,渐渐好后被教授教解《论语》;却反坏了”[1]455,“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曹立之天资甚高,因读书用心之过成疾,其后疾与学相为消长。初来见某时亦是有许多闲言语,某与之荡涤,则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随减。迨一闻人言语,又复昏蔽。所以昏蔽者,缘与某相聚日浅。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则复相过,某又与之荡涤,其心下又复明白”[1]437。在陆九渊看来,今人好闲说话而不成事,正是因为“虚精神”的流行。“闲说话”是“虚精神”在内的必然反映,故不论是董元息还是曹立之,不论个人的天资如何,即便一时改了“闲说话”的坏习惯,但由于“虚精神”占据风俗的主导,个人内在精神不实,一旦与外在接触就容易再次回到“闲说话”的状态。但是倘若能觉察到“实精神”的真相,就会发现“闲说话”的工夫与“精神”为本的涵养工夫全然相反。一者“闲”与“实/正”相背,没有根本和中心,容易使人迷失、陷溺;一者“说话”与“事”相远,所言之事愈多,落实处愈少。故一旦“闲说话”流行,天下之事理便愈发不明,但若能认识到“精神”在本体上的实在性,则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又添得一场闲说话。一实了,万虚皆碎”[1]448。正如“闲说话”与“虚精神”互为表里,做实事与“实精神”也互为表里,“实精神”保证了精神的集中度和事理的一贯性,故人自然日用中事全不离,沉静寡言,用心专一专精,若人人皆如此,形成直观的社会现象,那么即便学者有虚精神的倾向,也不容易误入歧途,所以陆九渊特别重视“防闲”的教育。
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敢废防闲。”先生云:“如何样防闲?”伯敏云:“为其所当为。”先生云:“虽圣人不过如是。但吾友近来精神都死,却无向来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异说坏了。夫人学问,当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1]443
“防闲”作为工夫落实处,重点在于“为”,与“闲说话”相反,但是并非所有的“为”都有“防闲”的效果,只有“为其所当为”才行,而“当为”与否的判断标准就在于“精神”的活性。因为“防闲”的目的在于风俗的改善,唯有个体产生“实精神”的自觉才能维持做实事的工夫,从而形成醇厚的风俗,所以“实精神”的特点,即“精神”的本来状态——由本体性而来的持久和高度的活性,是确定“防闲”正误的关键,如伯敏那般精神都死的状态,自然是处于虚精神的状态,其所谓“防闲”也只是不能成事的闲用而已,
先生云:“……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实大声宏,若根本壮,怕不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问自学问,若此不已,岂止两段?将百碎。”问:“近日日用常行觉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先生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若能无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患不成?”[1]444
一则,“防闲”以“实精神”为目的,应是事理一贯的,因而“防闲”与“闲说话”的零落相反,专一专精,在诸事之中,不局限于一事或事物的表象,而在于事物内在的道理,从而使人不仅能与自己的内心相通,而且能够与万物相通,没有分别和断裂。二则,个人“防闲”以消灭“虚精神”为目的,剔除虚假的部分,还原个人和世界原本的面貌,所以不以时空的变化为干扰,而以长久处于适意的状态为标准。
先生云:“……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世之弊。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1]444
“闲说话”是“防闲”最主要的目标,如文字的分别和口说都可以归结为“闲说话”,故“闲”可以包括一切不必要增加的概念,这些人为增添的概念不具有实在性,如果过度关注这些概念,让这些内容消耗了自己的“精神”,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人的“精神”就会与这些无实性的概念一样逐渐虚化,最终丧失自觉“实精神”的能力。“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1]441所以“防闲”工夫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将人的注意力从无实性的概念转移到实在的事物上,并且在做事的过程中通过个人自明的“精神”状态来判断和维持,使人的工夫重心保持在内在“精神”本体上,而不陷溺于事中,从而将“精神”的本体性实践出来,纯化社会的风俗。
不同于“精神”在心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重点在于对“精神”本体性方面进行充分的说明,以上所分析的内容,不论是“精神”作为社会风俗的描述,还是“精神”作为人心理和行为的动机动力,皆可视为陆九渊对于“精神”的实际应用。而在应用中还需要明确“精神”的现实性,如此才能说明以“精神”的虚实来概括个人和群体的状态是找到解决方法的直接途径。在解决“为人”心理问题时,陆九渊提出内省;在解决“闲说话”行为问题时,陆九渊提出防闲。在这些解决方案中,“实精神”都只是前提而已,其中内省所认识到的能力、性格,防闲做事对事物的改变和对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都依赖于人的另一个属性——“血气”。“血气”与“精神”不同,但在陆九渊的思想中两者关系之密切,在“实精神”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精神”代替“血气”来表达其作用的,而这正是“精神”的现实性,以及其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根据所在。
所以尽管在陆九渊的思想中,“精神”的内涵以本体性为重点,但由于“实精神”和“血气”的一体性,“精神”的本体性并不与“精神”的现实性相矛盾。以上引文中对颜子和仲弓的比较,以及对学者精神高低的描述,“人精神千种万般,夫道一而已矣”[1]451。“精神”作为本体(实精神)在个人上因为“血气”的差异可以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正如天理能划分成各种不同的事理,但并不影响“理”的本质。不过,这都是基于“实精神”的前提,“血气”的多样性不能影响在个体“精神虚实”判断上的一致性,倘若人处于“虚精神”的状态下,由于“血气”与“精神”性质的差异,此时“血气”与具有本体性的“精神”之间就存在矛盾和断裂,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不现实的。
在陆九渊看来,尽管“血气”与“精神”都是个人的基本属性,并且“血气”是“精神”的现实性来源,但这是从现象角度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而从本体角度来看,“精神”有实在性,“血气”只有现实性。两者不同,前者与天理一致,是纯粹至善的,后者由天理化生,与人欲交杂,所以“血气”只是“精神”现实性的载体。“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有一段血气,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1]451“精神”与“血气”本质上就有主次的差别,“精神”作为本体是自主的,故可作为“血气”的主导;而“血气”没有实在性,故本无主,若“精神”为虚,即人未能意识到“精神”的本体性以及其与“血气”的正确主次关系,则“血气”展现为欲望,若“精神”为实,即还原“精神”的本来面貌,则“血气”受“实精神”的主导,表现为工夫。“一学者听言后,更七夜不寝。或问曰:‘如此莫是助长否?’答曰:‘非也。彼盖乍有所闻,一旦悼平昔之非,正与血气争褰作主。’又顾谓学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为君子以向晦入宴息也。’”[1]429可见,“血气”作主为非,“精神”作主为正,两者并非并列的关系,“实精神”下“精神”主导“血气”的一体关系才是内外和谐的关键,单言“血气”即是“虚精神”,单言“实精神”即有“血气”的现实性。“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1]464通过对“血气”以及其与“精神”关系的说明可知,“精神”虚实的自觉不仅是自明,而且会展现在可以被直接观察的“血气”活动上,如“为己”“闲说话”都是欲望活动,说明其中“血气”处于无主的状态,自然可知内在是与真实相反的“虚精神”,故说“精神千种万般”不仅是指“血气”的多样性,也是指“精神”对“血气”的不同控制程度产生的结果,不仅不与“精神”作为本体的真实性矛盾,而且进一步加强了陆九渊思想中“精神”作为本体的意识以及“精神”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关键性。
综上可知,在陆九渊的思想中,“精神”不仅是人类个体的重要特征和组成部分,而且是人与道、事与理一贯的中介和评判标准。所以“精神”的本体性不受个体肉身的限制,其表现状态也不只是工具性的,“精神”的虚实状态适用于每个人类个体对于“心即理”自觉程度的描述,并可由“血气”的反映直接观察,故可以用于群体心理和行为的象征以及从古至今的社会风俗的象征。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一则,陆九渊认为“虚精神”是当今社会风俗的状态,它主要由群体心中欲望压制天理的过度增长和闲说话替代成事的习惯构成,因为天理和事物为实在性的根据和代表,而人欲和闲说话是虚的表现,所以“虚精神”的风俗指的就是当今社会群体未能有“实精神”主导“血气”而产生内心空虚,以及行为上的碎片化和散漫化的状态。二则,陆九渊认为解决当今“虚精神”风俗方法就在于个体产生“精神”对“血气”主导的认识,从而形成“实精神”,因为如果风俗是由可观的“血气”表现为内容的话,那么用于描述风俗的“虚精神”和个人的“精神”自觉状态就是一贯的。“虚实”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只要把握“精神”的本体性,血气无主的行为自然消失,就能使风俗恢复古时的醇厚状态。所以陆九渊在谈论事上的具体操作时(血气的表达),特别注意引起人对“精神”的关注。一方面提出工夫目的不在于事,而在于人,故工夫之前应先进行自我反思,关注内在心性的特点,明确自己能力的限度。由于“精神”不仅决定了人的特质,同时也控制着事物的处理,所以在先的内省可保证学者从人人皆备的“精神”入手,意识到“精神”在行为中的主导,完成实践“实精神”这唯一必需的工夫,不会使“血气”无主而盲目模仿他人的工夫之法或与他人比较工夫的多少。另一方面则提出工夫之事在专一专精,不在于多少,亦即“防闲”和“闲说话”的对比。因为这两种状态正与个体“精神”内在的虚实相应,人内在意识到“精神”为主,其“精神”才得以涵养获得较高的集中度,才能在处事上实现一和精的针对性和彻底性。反之,人不知“精神”为主,其“精神”不涵养在内而发散在外,深度不足,处事时效果只浮于表面,且血气无所主,凡所说的话、做的事都没有实在性(理的支撑),皆为不明理的闲用。
四、总结
综合陆九渊思想中对“精神”的描述和应用,可知“精神”的本体性是心学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与心即理一样,是与理学区别的关键所在。同时,“精神”也是心学工夫论的核心内容,决定了心学和理学在读书做事上的不同态度。所以在对“精神”的描述上,陆九渊直接将“精神”视为天理在内心的具体化,认为修养工夫的目的就是还原本来天生自足完满的“精神”,并在自觉“精神”的本体性(见端的)的前提下,保证了工夫内容内向、涵养的特点。反之,倘若只说心即理,而不以“精神”为本体,那么由于“精神”是人活动的根据,不论其虚实,都是工夫的下手处,此时强调内向涵养,“精神”只能作为手段来涵养内心,不仅会导致内在的“精神”与内心分为两段,若如此,即便通过“精神”明白了心即理的道理,由于两者分别,内在的天理也无法操控“精神”顺理而行,人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道德修养工夫便会丧失其价值。而且内在“精神”执着于内向运用会导致人远离外界事物,此时“精神”的目标只是内心,日用中事“精神”皆不管,最终人陷入完全的寂静,与世隔绝,自然不合儒家的思想。“学问固无穷已,然端绪得失当早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1]2由此可见,相比于心即理的学说,确认“精神”的本体性才是心学工夫现实化的关键所在,一旦“精神”为本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的问题,而且能弥补理学工夫中的缺陷。心学工夫由于以涵养“精神”为先,故日用中事的处置以“精神”为主,且“精神”有内在的天理为根据而生生不息,即便事物繁多,“精神”也不会穷尽,人不至于受事物的限制。
并且对陆九渊而言,“精神”的本体性并不是为了心学的合理性才提出的,而是“精神”的本体性证明了心学的合理性,在社会风俗讨论中可以看到,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以“精神”为内因,由“血气”而直接反映。对比古今风俗,今人“为己”和“闲说话”的行为有典型血气欲望的特点,而古人“为人”和“防闲”的行为则与天理特质相符。其中“血气”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物质属性,以群体来看,从古至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更不可能从有到无,所以并不能用于解释为何古今存在明显差异的统一风俗,故变化的原因只能用“精神”替换了“血气”的位置来说明。而倘若“精神”没有本体性,便只能与“血气”并行,不可主导“血气”而替换其位置,故可知“精神”具有本体性,并且从风俗差异来看,其本体性有明与不明两种可能性,当其不明而“虚”时,“血气”无主的内在状态便通过欲求行为表现出来。由此可知,社会风俗可以归结为“精神”的虚实变化,并且“精神”以“血气”为载体,落实在个体上,“精神”的明与不明由个体主导,只要人有“精神”本体性的自觉,就会有“精神”主导“血气”的行为,从而抑制社会中无所主(虚)的现象,最终通过“实精神”的流行改善社会的风俗。
不论是从现象归纳还是从理论假设的角度分析,“精神”的本体性都是陆九渊心学理论真实性和合理性的保障。在理论假设中,“精神”本体性能够让人明确事、理性质上的差异,获得正确工夫之法;而在现象归纳中,“精神”本体性能够让人将理的实在性融入事的现实性。在陆九渊看来,当今学者并非没有用力工夫,或者在读书内容或目标上与古人有不同,只是不理解“精神”的本体性,便最终只能沉溺物欲,无法成事,故“精神”的本体性是导致/解决个体修养以及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