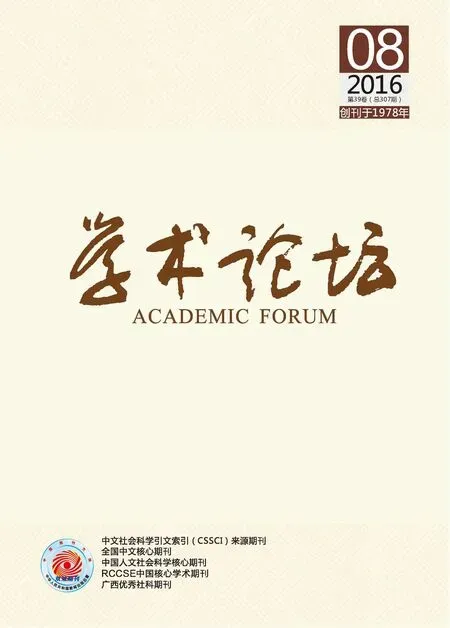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
李大平,左伟
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
李大平,左伟
中国社会有注重家庭的传统,一般而言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更多的时候成为医疗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儒家的齐家情怀与疾病的儒家家庭共担是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的伦理起点与归宿;“仁心”与“不忍人之心”为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提供了伦理基石。相信家庭相比个人更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提倡家庭共同参入医疗决策,同时照顾到患者的自律权,在必要时要根据患者的最佳利益对家庭决策予以限制。
医疗决策;儒家家庭主义;仁心;不忍人之心
当前西方临床上由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Tom Bcauchamp和James childress所建立的以原则主义之共同道德性为主流的医疗伦理决策模式,其应用的主要概念是尊重自主(Respect for Autonomy)、不伤害(Nonmaleficence)、有利(Beneficence)和公正(Justice)等四个原则①原则主义(Principlism)是由Tom L.Beauchamp与James F.Childress共同提出的一个生命伦理学系统,强调以若干基本的道德原则为主干的理论。他们自称“以原则为基础的普通道德理论”。。这些原则建立在西方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之上,以病人自律为优先。它所预设的人际关系乃是“公民式”的契约关系,医疗决策局限于医师与病人[1]。病人的自主权利提高了,但在某些状况下,将医疗决策权交给因病而使判断力下降的病人并不一定见得合理;病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取舍和价值会产生棘手的问题;病人与家属意见不一致时也会导致两难的道德难题。在中国,由于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涉及生命权利的诸多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个体的疾病会由家庭共担起来。因此,强调家庭自律,医疗决策适当顾及并采纳家庭的意见,可以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并相信我们每位患者能在家的德性下得到很好的保护,并有助于医疗方案的实施,这种模式,我们将其称为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模式。
一、儒家的齐家情怀与疾病的家庭共担是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的起点与归宿
(一)儒家的齐家情怀
家的概念对于儒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正家而后天下定矣”[2](P228),家是事功的根本;宋明理学将儒家之学分为外王之学和内圣之学两种,《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是外王之学,其出发点就是齐家,家齐了才能国治,国治了才能天下平;而格致诚正是内圣之学,内圣之学也就是修身之学,修身之目的便是齐家。
对儒家而言,每一个人不论他身处何时何地,其存在必须以家为基础,没有家,人就无法存在。生活于儒家文化圈中的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家庭,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因此,要齐家的第一个条件就必须保证家人之健康。这一点,在现代医疗决策的过程中常常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病患是家庭成员之一,一个家庭出现了病患而得不到照顾,那么意味着“家不齐”,家不齐即不能治国、平天下,也意味着其修身之功夫不到家,其内在道德是有缺憾的。
在儒家看来,家庭伦情乃一切人伦关系之出发点。父母子女之间的至真至诚之情,乃人伦之中最为根本的一环。在亲情伦理之中,恒见心中只有对方,而忘了自己,像慈母为儿女而忘身,孝子为其亲而忘其身,凡人伦情感厚者,皆彼此牺牲自我,心中念念总以对方为重[3](P169)。所谓因情而有义,因为在彼此互相牺牲奉献的过程中,才更凸显与成就伦理情感之神圣崇高,而人生意义之寻得,也常是在更高的心灵情感层次中,获得更大的意义与更高的价值。
北宋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4]儒家之家庭观念并非仅仅停留在单门独户的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关系,而是一种大天下的家庭主义,这样家庭主义并非口号式的荒诞不经,而是具有强大的悲悯之力,它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监督其人民的道德践行,督促并奖励其人民尽其善行,而这一点,对现代医疗决策而言,有敦化善行之功效。
儒家要营塑的是个重情义的社会,在情义的社会下,人与人之间,恒常是内心紧系着彼此,且事事因情而时时为对方着想。以儒家观点而言,个人生命的意义在于完成仁义与人伦的道德责任,其终极目的则在强调道德使命与伦理责任的完成,成为对整体家庭、家族生命与生存的正面推进力量,而非追求个人一己的幸福与快乐[5](P69)。
(二)疾病的儒家家庭共担
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家庭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基本单位,家庭是一个人自我认同和人格同一性的主要依据,从一个人长远利益来看,一个人需要与其亲密的人分享做决定。如Tom L.Beauchamp认为:“天生的关怀”是人类道德推动力量的源泉[6]。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天生最纯净的关怀,可知个人和其家庭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此后个人必须同其它人一起生活,特别是与家庭成员中关系密切的亲属,在生病时他需要依赖他们并照顾他们的利益,当他们需要时,换作他们也会做相同的事情。
传统的中国家庭家长辈因年老体弱多病,为人子女护父母心切,总是会介入医疗决策。我们深受儒家文化所影响,至今人们的行为、习性、价值观与信念,仍旧保有儒家之观念,这也影响行事处事之态度。直到今天,家庭依然是我们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遇到重大决策会共同参与决定。
因此,依照儒家的伦理,一个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也是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健康是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儒家社群下,家庭仍是个人医疗与健康照顾的第一线,每个人在生病或受伤的时候,同时也是最脆弱无助时,往往需要家属或朋友的照顾和陪伴。对我们的社会而言,大部分的人均觉得照顾生病中亲人是家庭成员的责任。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固然须视病人与家属为一整体,因而在医疗决策过程中,让家属参与是必要的。
儒家家庭功能是因家庭成员出现了健康的问题,威胁了家庭的恒定性,家属便会应用熟悉的调适方法来适应新的变化,以达成家庭系统的平衡状态。家庭功能维持完整有系统的关系,各种任务都让家庭成员不断成长,当面临压力或是各种事件时,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到每一个成员,大家都是互相依赖生存的,不是单一个有机体。我们所说的意思自治往往是在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上实现的。因此,家庭将被看待成为自律实体和合法的权力来源。
在儒家的社会里,家庭自主权的理念和实践已经透过儒家理解家庭和个人本性的形成。根据儒家,每个人出生于一个家庭是上天的安排,和其它来自家庭的成员与个人的生活有分不开的特别关系,家庭的关系如此重要,他们认为儒家主要强调基本人际关系[7]。因此一名家庭成员受伤、生病或者残疾一定被认为是一整个家庭的问题,而且因此医疗决定应该由整体家庭来做[8]。
儒家家庭主义,在临床背景就是对家庭进行知情同意,例如,如果一位医生直接把一种末期疾病诊断通知病患而不是一名家庭代表,它将被认为极其粗糙和不适当。由于知情同意的实践,家庭代表性人物应该担负倾听与医生讨论的责任并传达给病患,咨询其他家庭成员和最后签署正式的同意形式。以儒家的伦理关系自律中强调维护病人咨询同意权的根本价值是一家庭整体之事,而不只是个人的事,这对于病人而言,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平常生活中最亲密和最分割不开的共同生活体的支持,这是最能达成病人真正意愿的一个途径,不致为医疗专业人员所控制[9]。在此概念下,儒家关系伦理是以家庭为自主自律的单位,以自律形式的知情同意亦包括家庭之同意。
二、仁心与不忍人之心是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的伦理基石
(一)仁心与不忍人之心
儒家家庭主义的医疗决策模式之道德根源在于孔子的“仁心”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
人因为具有仁心,因而具有对自己行动之道德价值之判断,故知道什么事当为,而什么事却不能为。因具感通之能力,所以对他人的苦难可以感同身受,因此,仁心与感通之能力,成了人面临医疗伦理困境时,在心中权量轻重的一把尺,得以作出最符合伦理之决断。
所谓“仁心”,最早出自《孟子·离娄上》:“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於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10](P256)仁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内心操守,这种内心操守通过合适的方式得以展开,才能使得所有人都收益,那么,这种人人都有的仁心究竟为何?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中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0](P171)孟子把孔子之“仁心”之要义,以“不忍人之心”来诠释。孟子认为不忍人之心是每个人皆具有的,是道德的根源。当我们见到别人遭受痛苦,我们因不忍不安会有所行动,以解除其苦痛,这是自然而然的无条件的行为,不是因为救了就有美名,不救会得到恶名声。不忍人之心可说是人所本具的本心本性,是纯然内在于人的心,亦是人人所内在本有的。
不忍人之心是孟子仁爱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之所以如此基本且重要,是因为孟子赋予了它非常神圣的意义。他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庹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0](P290)依孟子所言,人与禽之间的区别极其微小,这种微小的存在便是内心的“仁”,对于一个真正的人,亦即君子,其目标就在于存有、扩展它,而庶民则耽于物欲要去除它。
而人与人之间的感通是源自于人类最深处的情感,亦起源于不忍人之心,看见他人受苦,我们并非只是从外在的方式去理解它,知道它,而是如同自己受苦,而这样的感觉,即是人心之感通,这是最终极的道德根源。以西方的语言表示,这种感通即人类的道德上的“同情共感”①对于“同情共感”(Sympathy),休谟(David Hume)指出,在许多与我们自己或亲友无关的事情中,如听到凄厉的叫声,即从而在心灵上浮现出它的原因,从手术室的种种安排而想到它的结果,即开刀的痛苦,我们都是只从有关的原因或结果而产生出最强烈的情感反应来。这种反应之出现是我们若似把自己代入到当事人或物之内,因而在他人身上所产生的痛苦或快乐有如直接在我们身上发生一样。这是人类所具有的同情共感所产生的作用。,故会激起内在的道德良知,并实现为道德行为。苦难是一般人皆逃避的,因为它造成人身体与心理的莫大折磨,因此,我们见他人遭受苦难,心里亦会涌起一阵不安,心里会有一股难过与不忍的情绪感受,彷佛自己感同身受般,人类因具有这种特性,即是一道德之主体,故面对这种情境不会置之不理,内在存有之仁心与不忍人之心会自动发显出来,以实践的行动化解当事人的苦难。甚至在能力所及时,会伸出援手帮助对方。
除了强调以仁心、不忍人之心为道德根源之外,道德实践上儒家特别强调德行的表现,如孔子多论述仁、义、忠、孝、信等,并以“仁”统摄各种美德;孟子则以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不忍人之心的具体展现,这四端即是实现不忍人之心的道德原则。
(二)视病犹亲
仁爱原则(Principle of Beneficence)应是一种带有道德义务含义的概念,对当事人可说是具有义务的要求行为,具有道德的强制性,即是“我们应当促进他人必须而且重要的利益”[3](P44)。仁爱正是仁的最直接自然表现,而做出于他人有益的善行,是不忍人之心要求的道德行为。这牵涉到其他人的重要利益且对于当事人是必须的,是因为这属于当事人的权利。儒家以孔、孟学说为主要方向的伦理,以仁心或不忍人之心为道德根源的关键[3](P44)。
仁心、不忍人之心具体到我们对家人的医疗决策上,就是要“视病犹亲”。如没有相称客观“仁”的这个特色是漠视病人拥有的渴望、偏爱或期待。例如,一位病患拒绝治疗,因为他判断他的生活不再值得生存,当相关的其他人依照客观“仁”的概念却不这么认为时,无论病患是否有行为能力,病患的愿望将不被倾听。儒家家庭自律包含一个“仁”的客观概念,家庭自律原则是一个以家庭决定为方向的原则。
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家庭参入医疗决策者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忍人之心,不是因为个人之好恶、名声、利益而去为病患作出医疗决策,而是出于感同身受的不忍人之心,以自己的心去感受病患的痛苦,以自己的爱去为病患抚平伤痛。这样的不忍人之心才是家庭医疗决策的出发点。
三、为仁由己、仁者成己是医疗决策的儒家家庭主义遵循的伦理原则
(一)“为仁由己”与家庭自律
那么,根据家庭自律原则,谁在临床决定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答案是家庭。这和西方自我决定的模式形成对比,儒家的社会反映出家庭决定的模式。在儒家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清楚的,在西方一位有能力的病患于一般医学决定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儒家作临床决定之前,病患和家庭成员必须先达成协议[11]。例如,当病患请求或者拒绝治疗和家庭有关成员持相反意见时,即使病患是明显有行为能力,医生一般将不会仅仅如同西方一样只采纳病患的愿望;相反的,在他能承担医学行为前,医生应该告诉病患和家庭成员协商并且提供协议,这种儒家的家庭自律强调家庭一致。
在中国独特的儒家伦理下,病人自律的决定常是以家庭为一生命共同体,因而李瑞全对此提出“病人中心之伦理自律”的观念:此为“伦理关系的自律”(ethical relational autonomy),视家庭与病人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以及互相道德之权利与义务。因而在医疗决策上,需以整个家庭为自主自律的单位,而所作出之决定,自然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首要考虑。李瑞全指出:在这概念下,基本上是以家庭为自主自律的单位,以家庭为进行决定的整体,病人并不单独享有自律的权利,而家庭的共同决定也常是外人对一个个体的决定是否接受的基础[12]。因此,在临床实务里,须把家庭视为整个自律之单位,不能仅听取病人之意愿而将家属排除在外,需把病人与家属总括起来一起作咨询。事实上,病人不但希望得到协助和指引,也常需与家人共同商讨。也就是进行家庭整体的伦理咨询模式,简而言之这是尊重家庭的自律[13]。病人的生活无法从其“家庭”之间抽离出来,病人和家庭的利益是相连的,治疗的选择对病人的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冲击,身为家庭的一分子,能够做出对所有成员最好的决定。
在医疗决策过程中,每个人的行动都以病患的康复为目的,每个人的行动都朝着康复这一“仁善”的目标前进,都在行“仁”,“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0](P264)。在这一过程中,不但病患本身要有主观的仁善的信念,家庭成员也都要有“由仁义行”的自觉。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14](P171)践行仁善的只能是本己,仁善之决定如果由乎他人,那就成了“行仁义”了。在现代医疗决策中,家庭成员如果没有出乎自己“仁心”的践行,只是因为考虑到利益、名声以及家庭权威等因素,那就不仅不是“视病犹亲”,而是“视亲犹邻”。因此,在儒家家庭伦理中,“为仁由己”是本位的,它不仅要求病患本身要自觉,其家庭成员亦当自律。
家庭自律,在临床背景下指的是对家庭进行知情同意,由于知情同意,家庭代表性人物应该担负倾听与医生讨论的责任并传达给病患,咨询其他家庭成员和最后签署正式的同意形式。传统的社会中,家庭是个人医疗与健康照顾的第一线,每个人在生病或受伤的时候,往往需要家属或朋友的照顾和陪伴。儒家家庭功能是因家庭成员出现了健康的问题,威胁了家庭的恒定性,家属便会应用熟悉的调适方法来适应新的变化,以达成新的平衡状态。
之所以强调儒家家庭主义在临床医疗决策中的作用,是由于儒家对家庭的观念异常重视,而充分利用这一文化现象对临床医疗决策有着极大的帮助。在儒家思想中,家庭不仅是承载着基本的基因遗传的实体,也承载着家庭之文化、先辈之心血,是一个群体生命得以延续的存在。因此,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健康都关乎这个家族的延续。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死都关乎其家人的生活。因此,在现代医疗决策过程中,引入儒家家庭主义将会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2](P23)父子、兄弟、夫妇,每个人在儒家之家庭中都有应尽的本分,每个人都必须自觉地去践行其义务和责任。这一责任不只是说做其应作之事,不干预其他人,而是说,每个人都对其家庭成员有着相对的义务和责任。这种家庭伦理在字面上给人以混沌的感觉,而在践行中却真正显示出儒家的智慧。在现代医疗决策中,让家庭成员以儒家之伦常智慧来尽其本分,才能做到家道正,而后天下正。
什么时候家庭决定将被否决?答案是家庭的决定明显违背病人的最佳利益时。如果不知病人之前的意愿,而病人目前已无行为能力,但家属的医疗决定与病人之最佳利益不一致,此时,医护人员是病人道德的代言人,必须依病人的最佳利益而行。家庭决定医疗的权限,并非没有限制,患者的自主性及利益仍应被考虑及尊重。医疗决定必须符合患者利益,及基于患者信仰、价值观、生活型态、个性等作为家庭判断的基准。支持儒家家庭主义的伦理是仁心与不忍之心,其支持一个善的客观概念,如没有相称客观善的这个特色是漠视病人拥有的渴望、偏爱或期待。
如果医护人员对家庭所作出决定有疑义,发现家庭要求的医疗与病人最佳利益不兼容时,医患双方须进一步进行相当程度的沟通与协调,以不忍人之心做调解,将由伦理咨询专员或伦理委员会的代表成员作为召集人,协调、沟通使医护、家属和病人三方做出合理的决定。医护人员须确保在重要的医疗选择中,病人与家属充分了解相关的疗程,可能风险、选择和利益,使病人和家属得以作出真实的咨询同意的自愿决定。
(二)“仁者成己”与病人自主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P324)。
透过道德自我要求以达到“至诚”,即所谓“圣人”的境界,以此协助让人、物皆能有所长,也能发挥其所长,这就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尊重自律原则、不伤害原则、仁爱原则、公益原则等是同一理路。要能使一切万物都能各遂其性、各适其情的充分发挥,没有尊重其自主自律是无法让其充分发展,做出任何伤害事件更是有损其发挥的空间,又不具仁爱之心的促进其利益,如何能尽其性呢?再者,能使人与物各尽其性地展现,充分显示出是以公义地对待天地万物,并未限制或不许其开展所长。即使天道化育万物有不足之处,亦可藉由人道去做相对应之变,弥补天道的遗憾,即是参赞天道原则中仁爱的实际发挥[15](P224)。
“成己,仁也。”[14](P121)病患的决定必须基于家庭这一生命共同体。在儒家文化起作用的社会里,个人自主权的理念是很重要的,因此,成己意味着个人本体的形成和家庭基础的构成。但“成己”并非能够单独构成个人本体和家庭,它需要“成物”,“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14](P56)。对儒家而言,每个人和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在医疗决策过程中,病患自主权家庭成员的自律权应当协调一致,既要“成己”,也要“成物”,合“成己”与“成物”之道,方能成就仁善之目的。
儒家伦理学认为自律正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最根源的道德实践。“我欲仁,斯仁至矣!”[14](P66)道德行为的真正具有道德价值是行动者依自我的不忍人之心自行作出的道德要求与行动,是出自于人性,来自于良心,为一种无条件的付出,是一种自律的行为。当来自于道德良知的自律行为被阻挠时,不论其有意或是无意,都可视作不道德行为。因其违反自律原则,使自己或他人不能实践应有和应尽之道德义务。此为儒家不忍人之心与原则主义的自律原则相融。李瑞全教授以为自律原则更进一步将不忍人之心化为具体指标:个人方面,道德人格所要求的道德实践得以实现;社会方面保障每一个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发挥和表现、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保障每一个体不会遭受非人的对待。自律原则是最常用也最先受到考虑的道德原则。人的自主自决以至自律为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一旦违背,即是剥夺侵犯人的基本人权,若是涉及生死的伦理问题中,便是可影响他人生死。从此可见自律原则之重要性[6]。病人如果是在具行为能力情况下,所选择的医疗决定,需予以尊重,保障病人应有的权益。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家庭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基本单位,家庭这一神圣的实体为个人提供了永恒。在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事务面前,即使他具有行为能力,他也不能单独面对。从一个人长远利益来看,一个人需要与其亲密的人分享作决定。在传统儒家思想看来家庭通常是关怀备至、通情达理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同体,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一个人较多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来自家庭,家庭有着良好的关怀与保护功能,家庭共同决策还有助于培养家人的幸福感与德性。家庭是一个人自我认同和人格同一性的主要依据,家庭共同决策有着至善性与权威性。也许家庭的决策有时候可能与医生的专业判断严重不一致,我们得为此预留规则空间,但我们相信大多数病人依然生活在正常发挥功能的家庭之中和受到家庭德性的爱护。因此,基于儒家家庭的医疗决策模式,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1]石致华.诺丁关怀伦理学的道德理论研究[D].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2011.
[2]杨天才,张善文.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M].台北:鹅湖出版社,1999.
[4]夏雯洁.西铭哲学思想浅析[J].博览群书,2015,(3).
[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香港:三联书店,1989.
[6]Tom L.Beauchamp,James F.Childress.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6.Auflage[J].Ethik in Der Medizin,2010,(2).
[7]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J].孔子研究,2014,(1).
[8]刘海鸥.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J].伦理学研究,2003,(8).
[9]李瑞全.应用伦理与现代社会[J].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3,(8).
[10]方勇.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陈浩文.末期病人的决策伦理[J].中外医学哲学,2011,(4).
[12]李瑞全.伦理咨询理论与模式[J].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3,(4).
[13]林美香.西方个人主义与儒家政治思想之研析[D].国立中山大学,2008.
[14]陈晓芳,徐儒家.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李瑞全.儒家道德规范根源论[M].台北:鹅湖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刘烜显]
李大平,广东医科大学生命文化研究院教授;左伟,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东莞523808
B222
A
1004-4434(2016)08-0018-06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预立临终医疗指示制度研究”(15YJAZH030)和2015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预立医疗指示制度研究”(GD15CSH04)的共同研究成果